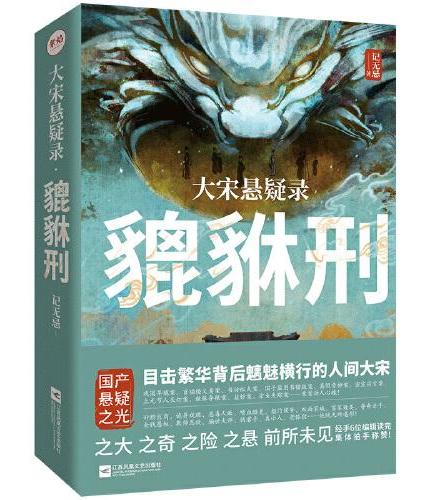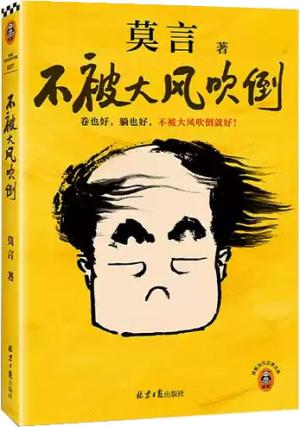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股权控制战略:如何实现公司控制和有效激励(第2版)
》
售價:HK$
98.8

《
汉译名著·哲学经典十种
》
售價:HK$
761.2

《
成吉思汗传:看历代帝王将相谋略 修炼安身成事之根本
》
售價:HK$
61.6

《
爱丁堡古罗马史-罗马城的起源和共和国的崛起
》
售價:HK$
76.8

《
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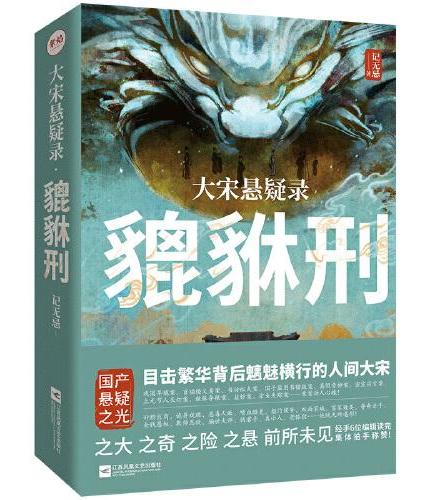
《
大宋悬疑录:貔貅刑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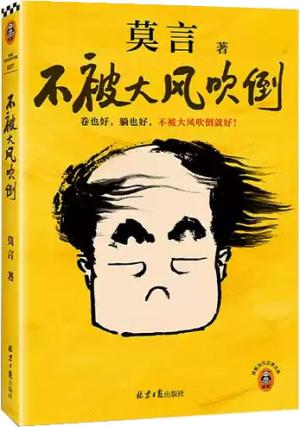
《
不被大风吹倒
》
售價:HK$
65.9

《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四十讲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伟大土耳其作家唐帕纳尔的代表作《时间调校研究所》是当代土耳其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作品,一部令人捧腹的、关于现代化的悲喜剧,极富艺术色彩,狂想曲搬的笔触和辛辣的反讽完美融合,宛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狄更斯、伏尔泰灵魂附体。如果你喜欢《变形记》《好兵帅克》《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小说*不会让你失望。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曾评价本书是一部寓言般的杰作,唐帕纳尔在作品中尝试让土耳其西方化,描绘了人类道路分岔的同时进展缓慢的现代化。
本书荣获《独立报》年度*引进版图书称号。
|
| 內容簡介: |
《时间调校研究所》讲述了天真而迷人的反英雄主人公海利伊尔达尔的遭遇。海利与一群古怪的,甚至离经叛道的角色电视神秘主义者,涉猎炼金术的药剂师,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贵族,以及终生艺术家哈里特阿亚希一同创建了时间调校研究所。
研究所具有堂吉诃德式的宗旨:确保土耳其全境所有的时钟设定为西方时间。作者以此为切入点,对如灾难般涌入西方价值与传统土耳其价值的融合进行了出色地反讽。
《时间调校研究所》带有悲剧色彩,却又令人捧腹;惊人描写随处可见,但却十分真诚。小说以狂想曲般的笔调,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发生激烈碰撞的土耳其荒诞众生相。
|
| 關於作者: |
阿赫梅特哈姆迪唐帕纳尔
土耳其著名小说家、诗人、随笔作家,被称为当代土耳其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系,之后教授文学、艺术和艺术史、神话学。四十岁当选土耳其国民议会议员。其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曾引起广泛争议。作品吸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瓦莱里和柏格森的写作特色,构建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世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以及大胆前卫的作品风格为其在世界文学史中搏得重要地位,受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罕帕慕克的推崇。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背景之外》《镜中女人》《安宁》《时间调校研究所》,中短篇小说集《夏之雨》,随笔集《五座城市》等。
|
| 內容試閱:
|
后来,我在那个研究机构里认识了拉米茨医生。我被带到那里去的时候,他刚好站在法医研究院负责人身边。对我的事情,他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兴趣,他专注地聆听了我的案情,然后提出要亲自接手这个案例,对我进行检查。我们下楼直接去了他的办公室。当时法医研究部门就安排在多玛巴赫切皇宫侧翼的一幢建筑物里。拉米茨医生的办公室在底楼,房间相当简陋,只有一个窗户通向外面,正对着花园里的一段围墙。房间里,洗手池安装在一面墙上,水龙头滴滴答答漏着水。一进屋,拉米茨医生先去洗手。我站在那里,脑海中翻来覆去思考着自己的命运。
就在来多玛巴赫切皇宫的路上,我看到了大海。蔚蓝的海水在秋天的太阳下闪烁着金光,仿佛在警示什么,我和我的命运之间隔着这片海,我被迫花了很长时间才让自己习惯它。
当时,我万分迷惘。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我的家,一切都仿佛在我眼前远远退去,退向遥不可及的远方。
我再次回想起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令自己的内心感到极度恐惧的东西,那就是有人硬是要把我,还有我的妻子卷入这件事当中。奇怪的是,直到现在,法官还一直让她置身事外。这让人不由得产生了希望。是不是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把那些对我的指控当真。可是他又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里来呢?不,他肯定是在等着。他们一定会把艾米妮也牵扯进这张可怕的罗网之中。尽管我已经被关押了十天,可我的眼前还一直浮现着当时的情景,我的妻子在家门口和我道别,双手搂着我的脖子。她的眼睛下面眼袋浮肿,两颊凹陷下去,声音哽咽。她拥抱着我,双手发烧一般火烫。我透过窗户,眼中看见几株秋天的花,落满尘土,仿佛在围墙下苦苦熬着荒芜黯淡的生命,我心里思绪万千。一只胡蜂径自朝这边飞过来,虚弱地停在离我不远处的外窗台上。这幢楼里不知哪儿传来悲恸的哭喊声。拉米茨医生的双手已经洗干净了,他还从公文包里掏出古龙水喷在手上,倍添清爽。
有人敲门,一名办公室职员走了进来。门一打开,哭喊声更加清晰。
萨利姆医生让我通知您,他们现在要开始解剖尸体了。您也过来吗?
我禁不住心惊胆战。拉米茨医生摆动着古龙水打湿的双手,答道:
不去了,我这里正忙着。让他们把胃煮沸消毒。等一下我过来看。
他转身对我说:
又有人中毒了。至少我们推测是这样。
接着,他又拿过他的公文包,这款公文包黄色皮质,带锁,有很多实用的夹层。我后来才听说,我这个朋友身上从来什么都不带,所有东西全在那个包里,每次打开过之后,他会再小心翼翼地把它锁上。他掏出一盒烟,递给我一支,自己也拿了一支。我在身上摸索着找火柴,没找到。他又给我点上了烟,吩咐一直还等在那里的办公室职员送咖啡来。
拉米茨医生年纪很轻,三十出头,肤色深而泛黄,身材算得上高大,而且相当健壮,大眼睛颜色极深,目光中透出隐隐沉思的神情。尽管如此,他给人留下的第一眼印象,既不是这双眼睛,也不是他那相当匀称的脸部线条。第一次见到拉米茨医生的人,首先会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觉得这张脸上不知哪里有点不对头。后来我慢慢习惯了他的模样,才发觉这种印象的由来,其实是因为他前额突出,凌驾于瘦骨嶙峋的面部之上,而下颌不知怎么终止得过早了,仿佛每一根线条都要脱离控制,额头与下巴让人感觉不怎么协调。这个收缩的下巴似乎并不是他脸庞真正的终点。他的声音也有类似的特点。他说每一句话,开始总是很大声,重音强调的节奏有点怪,结果到最后却变成了喃喃低语,好像音量马上就要消失,不留一丝痕迹。无论是他的模样还是声音,都让我莫名其妙地联想起奇形怪状的螺旋。拉米茨医生在维也纳上的大学,不久前刚从那里回来。后来有不少人向我确认,他是个好医生,有希望前程似锦。他的专长是心理分析,而且还曾在一家研究机构工作过,运用的就是心理分析方法。
不过,其实在那天第一次接触时我就已经明白了,拉米茨医生并没有把心理分析看作患者需要时可以简单采用的治疗手段,在他的眼里,这更是拯救世界的仅有的途径,除此之外,唯有宗教才能给予这个世界救赎。这门崭新的学科对他来说完全意味着一切。简而言之,恶行、罪孽、疾病、贪婪、贫穷、困窘、灾祸、伤残以及仇恨,这些不从人愿,将生活陷入不可忍受境地的因素,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在他的眼里,唯一存在的,只有心理分析。任何人与事都是它导致的结果。心理分析,是解开生活之谜的唯一钥匙。
他从维也纳归来之后,并没有人给他提供足够的机会和财力,用那个神奇的工具来彻底改变整个国家,这不免让他怨恨周围所有的人。就在我跟他打交道的那段时间里,他身上这股怨气如同浪潮一般,时不时发散出来。
尤其当拉米茨医生对各种社会问题表示出特别的兴趣时,这种情况格外明显。无论是谁,只要认真地听他好几个小时之久,滔滔不绝地谈论他的不满,他的分析和他眼中未来的前景,心里都会不由得暗自思量,能够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每个人只做自己拿手的事,那定是一大幸事。谁都渴望这样的世界。
当时,我也马上意识到,拉米茨医生的不满应该源于他的性格。他不停地高谈阔论:话题总是一下子就绕到年青一代、社会事件、公民教育、生产,尤其是社会运动上去。他根本就没法不跑题,事实上,要想让他快乐,恐怕只有让他去完成一件迫不得已必须解决的工作,或者是随便抱怨点儿什么。所以说,尽管他有一份优越无比的职业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他还是觉得自己非常值得同情,自己就是个充满幻灭感的倒霉蛋,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或许他对我青眼有加,想将我揽入自己的羽翼下,其实都因为他把我看成同他自己一样,与周围格格不入、心怀不满的人。自他从维也纳回来之后,跟每个人都闹翻了,过着近乎孑然一身的日子。
我们时常探讨的首要问题是公共状况。一直以来,在我这个人眼中,只要自己没有陷入绝境,这世界就是纯粹的天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根本无法理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我逐渐适应了他的思维方式。对他来说,这里那里,时时处处,不对头的事情无所不在。整个社会观念和民众的普遍心理状态都陈旧过时。像他和我(!)这样的年轻人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机会。只要看看我们俩的现状,就一清二楚了。难道一定要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而他自己呢,尽管已经回国两年,还是没有任何一点机会,能让他将心理分析方法真正投入应用。自他到这个机构工作以来,这还是头一回把一个患者交给他。万幸的是,我可以算得上一个相当重要的病例,这对他而言不无安慰。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情况可完全两样。那里的人懂得尊重专业知识,心理分析的地位好比每天的面包,不可或缺。
我们的咖啡送来时,他在写字台边坐下,让我在他的对面就座。他又一次打开自己的公文包,取出烟盒,抽出两支烟,再把烟盒装进包里,并且再次把包锁上。
我在这儿相当不受欢迎,他接着说,他们用的工作方法早就落伍了。这里也没有我真正的位置。在这儿,我必须完成任务。嗯,再不济也把您托付给我了。院长早就答应过我。他说过,只要什么时候来点儿有意思的事情,就交给我做。
谁说我们俩不是天造地设的绝配!
他激动地发表完以上看法之后,话锋一转,主题又回到维也纳和其他德语地区上。那些地区秩序井然,方便舒适,令我们大为羡慕。
咖啡喝完了,他站起身,收走了杯子,说道:
现在该您谈谈了!
就这样,他把话头交给了我。我先简单描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不过,紧接着,他希望听我谈谈我的全部生活经历。我讲述的时候,他不停做着笔记。尤其在听我谈及童年经历的时候,他在这个话题上停留的时间特别长。我说到的几乎每个细节,他都会大声重复几遍。
特别是有关那座福报钟的事情,让他兴致勃勃。他问了我一大堆问题。而且言语之间一直用我母亲的叫法来称呼它。
这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钟呢?
一座很大的落地钟。质量一流。老英国货。还是阿卜杜梅其特苏丹年间买下的。不过已经坏了。我妻子把它放到阁楼上去了。您要是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去亲眼瞧瞧。这钟敲起来的声音相当好听。
我眼巴巴地望着他,心里盼望他会买下这座钟。要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羁押期间,我从一个看守那里听说,隔壁囚室的犹太阔佬在里斯本把一艘退役的大船卖给了一名来自本德布什尔的伊朗人,甚至事先就把中介费拿到了手。这样的事情我也能干。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我便宜点儿给您!您要是愿意,咱们现在就走,去看看那座钟吧!
这可是再合适不过了。我的心怦怦直跳,心里暗自思量:啊,要是他真的那么好奇,那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回家,我又能见到艾米妮了。她一定会用院子里的水泵打水给我喝,我还可以洗把脸,然后跟泽拉一起,唱一支童谣
您刚才说,钟坏了?
嗯,这个,用我们的话说,是年久失修了吧。
他思索了一会儿。
可不是嘛,它也理当如此了。
为什么理当如此呢?这话让我不明白。照努里埃芬迪的说法,一只钟表就必须正常运转,永远不能让它停着不走。我耸了耸肩。我们还有可能很快言归正传,回到卖钟的事儿上去吗?不可能了,因为现在拉米茨医生已经把话题转到我父亲的身上。然后又谈起了我的母亲,接下去又是努里埃芬迪。只要是我认识的人,他个个都感兴趣。最后,我们说到了塔克利比阿梅特埃芬迪那座未能完工的清真寺。
您家里以前经常谈起这座清真寺的事吗?
没有,其实并不怎么提。要是我父亲刚好信心十足,认为自己能得到一笔小钱,有时候他就会自己提起这座清真寺,否则谁也不准在他面前讲半个字。这座钟老是勾着他想起这些事情,甚至有点让他恼火。
哪座钟啊?
还不就是那座大落地钟嘛。
那座福报钟啊?您就直接说它的名字好了!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有个名字,咱们提起它的时候也应该用这个名字嘛!他不无责备地说我。
我有点震惊,我居然好像忘了这回事儿,他挺得意自己创造的这句妙语,接下来我们又把话题转回福报钟上,讨论了好一会儿。他不断地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我不停地说,想到什么说什么,完全没意识到这简直是自讨苦吃。
有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那只钟突然敲响了。我父亲气愤起来,暴跳如雷:行了行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钱。眼下就是不行。我连这个家都快养不活了。现在不比从前。你干吗还非要这样来烦我?
他这些话,是跟福报钟说的?
是啊,有几分像。具体我也说不准。
很有可能是这样。这可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十分罕见,但是具有典型意义。真是太谢谢您了
他感谢我,自然是因为我表现很好,配合得不错。
情况真是这样的吗?
他专注地盯着我的脸,神情迫切。
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您可以把整件事的经过再叙述一遍吗?
我遵命照办。
这个案例太奇特了,真的很罕见。这里头产生了一件圣物,围绕着它,有许多不同的情结各就其位。这样的情况早先出现过。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门古老的大炮,在爪哇岛或是另外一个什么岛上,一直被尊为圣物,没有孩子的妇女们为了祈求怀孕,把碎布头绑在大炮上面。我想试试换个话题。
我们这儿,以前也有类似的事。那艘有三个货舱的旧战舰玛穆迪耶就是这样的。夜里,它悄没声息地起航,前去参加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炮轰防御工事,第二天清早又回来了。我父亲还能回忆起那艘船。船里头应该像塞里米耶军营那么大。
这船也在您家里吗?他问道。
他是心不在焉?还是真把我当成了疯子?或者,更要命的是
不,不我叫出了声,我说的是在我们这座城市,在伊斯坦布尔。
为了证明自己没疯,我想把话说得更准确些。
一艘巨大的战舰怎么可能装得进一所房子里呢?真要那样,恐怕得圣索菲亚大教堂才装得下。
圣索菲亚大教堂?
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就是举个例子。我飞快地说着,为了避免再次节外生枝,我把整个故事又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他一脸严肃地听着,一边作着记录,然后再次对我表示感谢。接着,他向我说出了他的看法:
这件事情也挺有意思,不过这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一码事。
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把小刀,拿它磨指甲。他修完指甲,我以为他会把小刀给我用用。我突然陷入了某种出人意料的情境,要是手上有点事情做做,还真的不错。可是,他并没有把小刀递给我,而是把它塞回包里。接着又从包里取出那瓶古龙水,我们俩都用了不少。随后又轮到香烟盒出场。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医生先生,我开口说道,您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您觉得
我被自己的冒失吓了一跳。可是他只微微一笑,说:哎,您也知道,这么谈更舒服些。
原来如此,他对舒服的理解就跟我继母对幸福的看法差不多。唉,人啊!
您这个人相当对我的脾胃,海利贝伊。我们要是在维也纳就认识该多好!
话锋自然转到维也纳上。这个拉米茨医生最喜欢的城市,把我的事情挤得无影无踪。然而,就在我已经不敢抱任何希望的时候,谈话又回到了我的身上。
您母亲肯定非常在意福报钟,是吗?
可能是吧。
您试试回忆一下?
他再次盯着我,样子极为迫切。
有可能吧。那座钟相当古怪。它总是做出反常的举动。它走得很随意,几乎可以称作自说自话。也可能只不过因为它本来就已经坏了。反正我们觉得,它做的一切都很奇怪。
我说这些的时候,他简直两眼放光。他仔细倾听,不停地点着头。随后,他把自己的记录念给我听。
古怪、反常的举动、随意、自说自话、它所做的一切是这样,没错吧?太有意思了。还有呢?
实际上就这些。
我已经烦了。给我做检查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他一点儿都没再提。
是啊,您母亲,您说的
慢慢地,那只钟让她越来越不踏实。她只不过是个没什么知识的妇女,那种根深蒂固的旧式女人。
旧式还是新式,根本就不重要。原始人和我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清醒自觉状态下的生活和潜意识状态下,完全是一样的。又能怎么样呢,心理分析
这个词从他唇间迸了出来,像一只煮得梆硬的鸡蛋落在我面前,这将是我后半生频繁听到的词汇之一。
他站起身。
就这样吧,咱们明天继续。现在您先好好休息!您的铺盖已经送到了吗?
我妻子会让人送来。我答道。
那就好。您就睡在这个房间吧。那个大寝室太不安静了。我去找院长说说。
他面露担心的神色,又补充了一句:
我在这里不招人喜欢。他们也不听我的。不过既然您已经是我的病人
为什么说我是病人呢,医生先生?您现在不是已经把一切都了解清楚了嘛。难道我有病吗?
他根本不听我说什么,径自朝外走去。那一刻,他的背影看上去有些意味深长。
我试着安慰他:
别太在意了,医生先生,今天晚上我一定加油。那头狮子肯定还没走远,有可能今晚还会再来。
绝不可能的,太笨了。您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
他望进我的眼睛,眼里有切切实实的悲伤。
亲爱的朋友,咱们还是别再欺骗自己了。您压根儿就不想康复。那头狮子怎么还能回来呢?走了,就是走了!
他说得没错。这头狮子恐怕像我父亲一样,已经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遭遇,它再也没有在我的梦里露过面。
不过,此次狮子事件也稍稍提起了我的兴致。第二天,医生问我:您说的,一头狮子就意味着公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向他解释了古老的解梦书。
我们的祖先也早就已经在很认真地解梦了。不过跟您的说法完全两样,没有一星半点相符的地方。
那就是说,咱们这里,也有一把通往梦境的钥匙?他问道。
不是的,不是钥匙,是一本书!书里写着每个梦代表什么。
医生对一切货真价实的本土东西都有点偏爱,不过,要让他想起这些传统的老玩意儿,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原因似乎不是他在外国待的那短短几年,而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生活之间,隔着一片真空地带。啊,对啊,就是的他记起了那类解梦书,马上连连点头。
您知道,我们的祖先就是一笔永不枯竭的宝藏。
为什么一提到祖宗先人,我们就必须马上点头称是?这是一种习惯,一项传统,或者可能是一种病?
当天,我们一直在谈解梦书,直至深夜。他想以此为题,为维也纳的一次国际性会议撰写一份书面报告。因为我对这方面了解相当深入,他请求我助他一臂之力。在他眼中,我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不再是他的病人,由于一个正在审理的案件接受他的观察,他也不再是医生的身份,我们变成了朋友。他不时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件事。
他离开的时候,我还是问他,我今天夜里应该做什么梦。他不解地盯着我,只说了一句:
报告您写那份报告啊!学术会议过不了多久就要召开了!
当然,这份报告最终也没写成。但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已经在我的新朋友眼前开启。古老的疗法、手相学、算命术、祷告术、炼金术、犹太教神秘教义,要是用舞台的行话来说,这就是赛义德鲁特弗拉的全部保留节目,这些可怜的只鳞片爪的学问,有印刷制品,也有手抄本,一堆堆地摆在旧书摊上,一下子令这个家伙如获至宝。然而最奇怪的是,他总想从我这里了解这些东西。
我求您了,这些事情书里全都写着呢。您还是直接去一趟贝雅齐特的旧书贩子那儿,花上八到十个里拉,想要多少有多少,只要您拿得动!
可我还是想先从您口中听到一些事情。我当然也会去找书来看,不过,知识最好还是口口相传。我不是在短短几天当中,就已经把整个心理分析学说向您全部解释过了吗?
我很幸运,这段时间里,法官又认真地细细研读了他手里的卷宗材料,并从中得出结论,我的证词与阿布杜塞拉姆女儿女婿的证词是一致的,也许,至少他对整个案件中涉及我的这一部分,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当时,拉米茨医生满脑子都是他的新研究领域,把我的事情完全忘到了脑后,他可能早已断定,我已经奇迹般地痊愈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天,法官宣布了我无罪的判决,这就是说,我与整件案子再无任何关联了。
好事和坏事总是如影随形,结伴而至。这份判决下来的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足以令拉米茨医生欣喜若狂。这个梦如此尽善尽美,哪怕只是回想起它,都会让我对自己产生深深的怀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