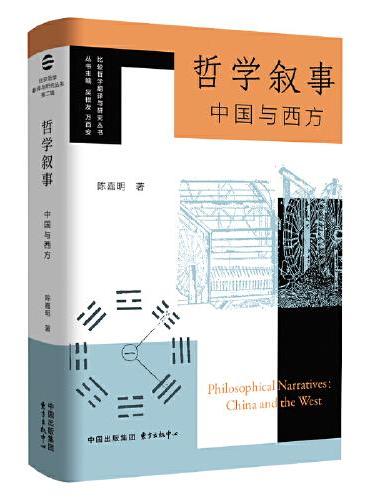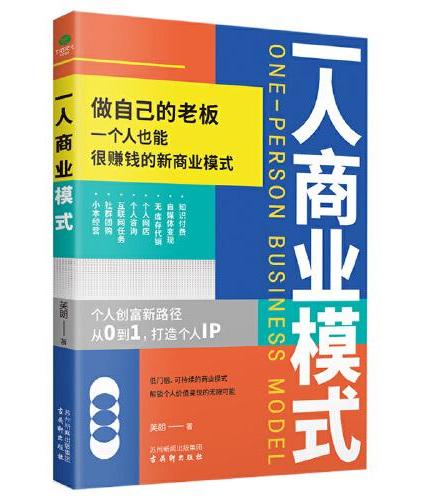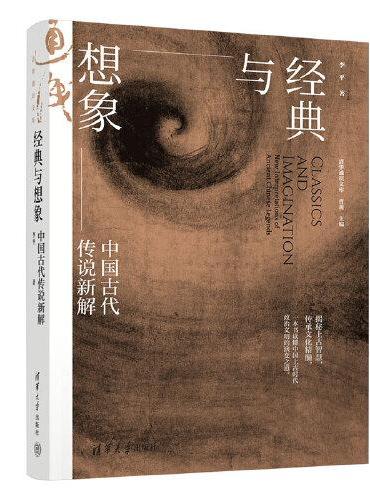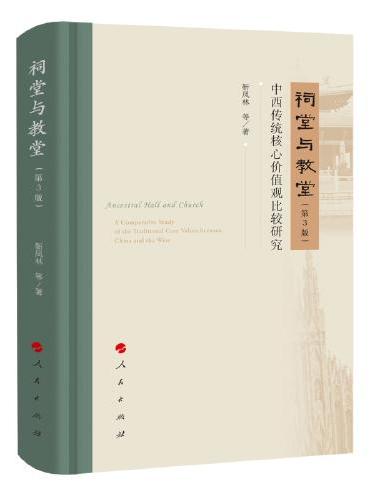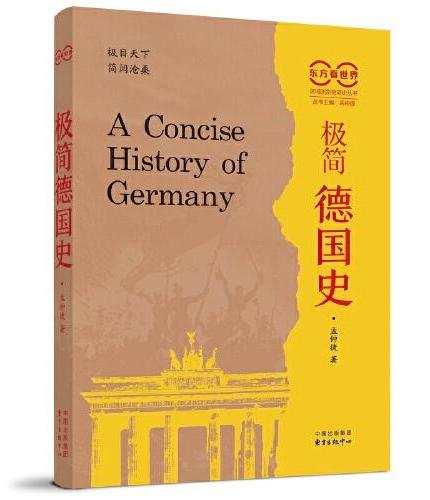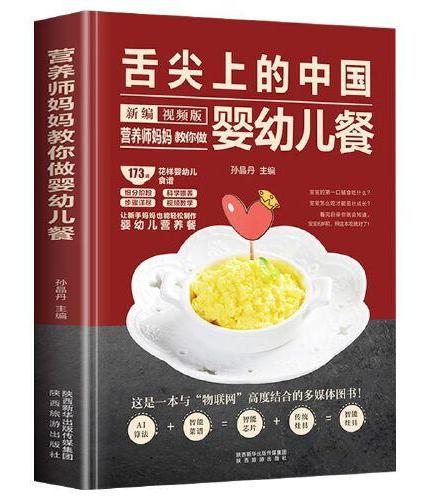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更易上手!钢琴弹唱经典老歌(五线谱版)
》 售價:HK$
54.8
《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
》 售價:HK$
107.8
《
一人商业模式 创富新路径个人经济自由创业变现方法书
》 售價:HK$
54.8
《
经典与想象:中国古代传说新解
》 售價:HK$
85.8
《
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第3版)
》 售價:HK$
118.8
《
极简德国东方看世界·极简德国史
》 售價:HK$
74.8
《
舌尖上的中国新编视频版营养师妈妈教你做婴幼儿餐
》 售價:HK$
63.8
《
Scratch创意编程进阶:多学科融合编程100例
》 售價:HK$
107.8
編輯推薦:
我们知道,尼采是大哲学家,他的的思想广博而精深。其“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和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等这些法国当代哲学家,就被称为新尼采主义者。这本《尼采遗稿》,是尼采生前未刊稿的精选本。那个把思想当做铁锤,在击碎传统价值体系中建立新价值的尼采的形象,在本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尼采站在他所反驳的偶像的反面,成为了预言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
內容簡介:
本译著由尼采论德国教育机构的未来与古希腊悲剧等20篇专题报告组成,多数是国内翻译界和哲学界尚未有人涉猎的内容。这是对哲学研究领域的一种补白,其学术意义深远。
關於作者: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德语: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其兼具艺术家的浪漫气质,是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他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论道德的谱系》等。
目錄
目录:
內容試閱
第一个报告:希腊音乐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