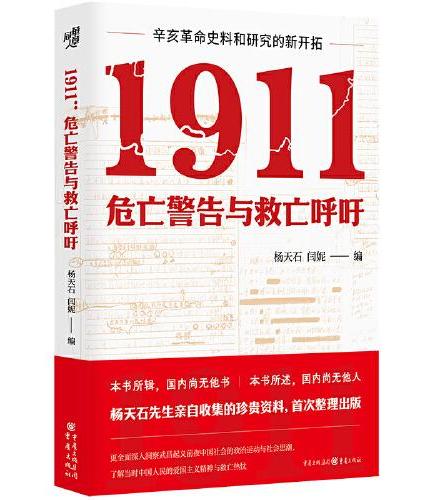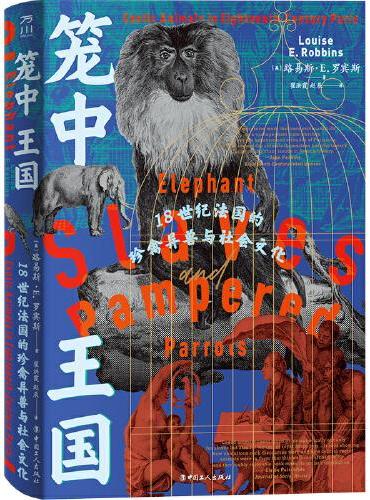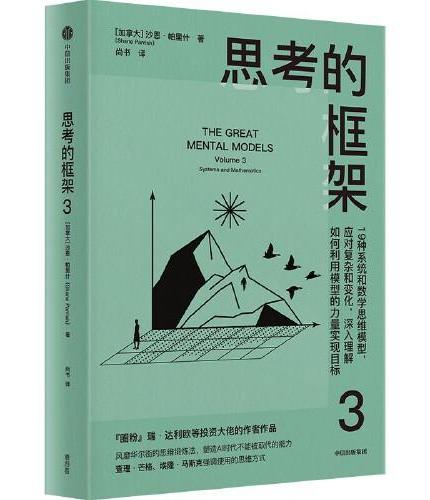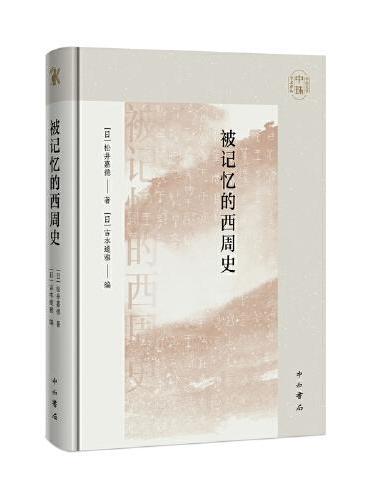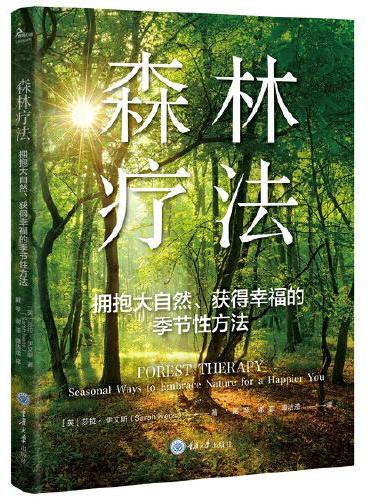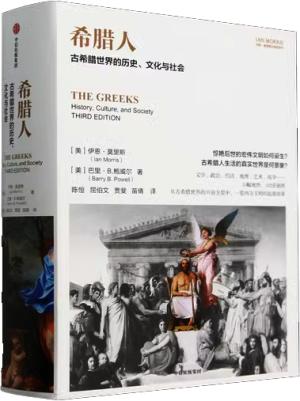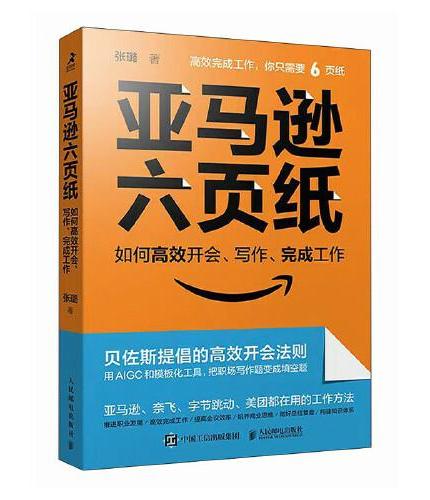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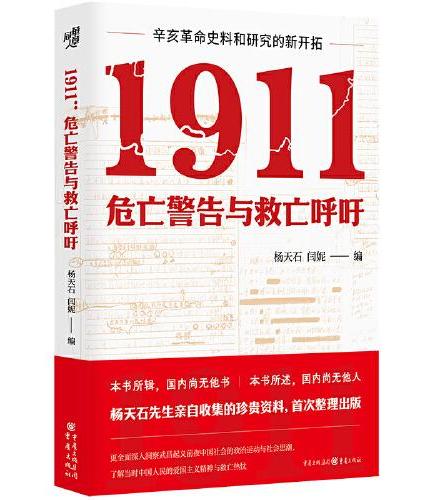
《
1911:危亡警告与救亡呼吁
》
售價:HK$
76.8

《
旷野人生:吉姆·罗杰斯的全球投资探险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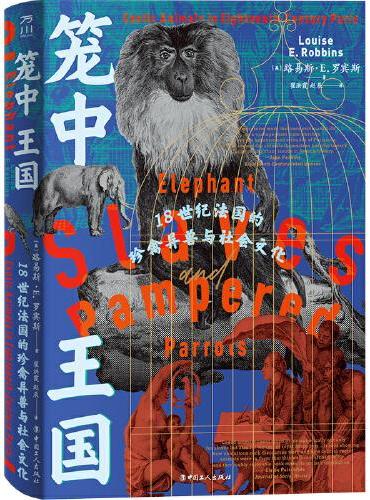
《
笼中王国 : 18世纪法国的珍禽异兽与社会文化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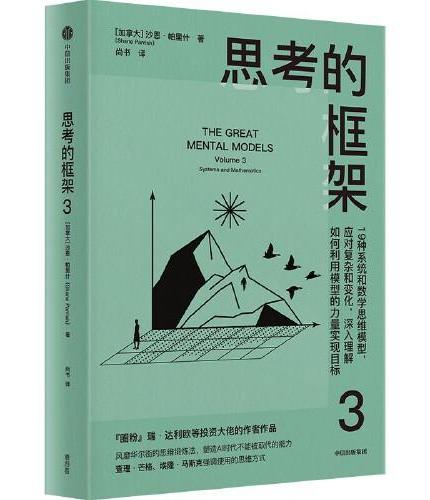
《
思考的框架3:风靡华尔街的思维训练法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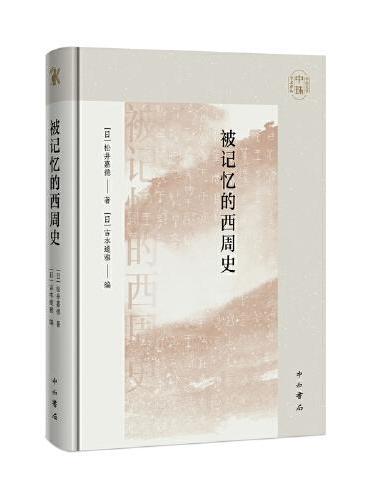
《
被记忆的西周史(中山大学中珠学术译丛)
》
售價:HK$
1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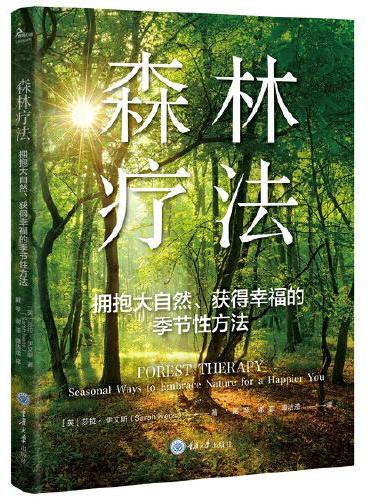
《
森林疗法:拥抱大自然、获得幸福的季节性方法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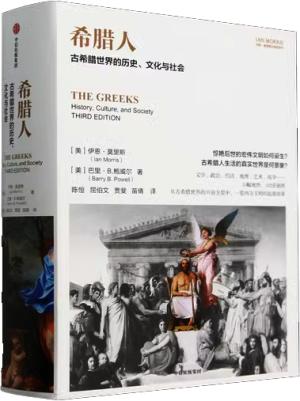
《
希腊人(伊恩·莫里斯文明史系列)
》
售價:HK$
18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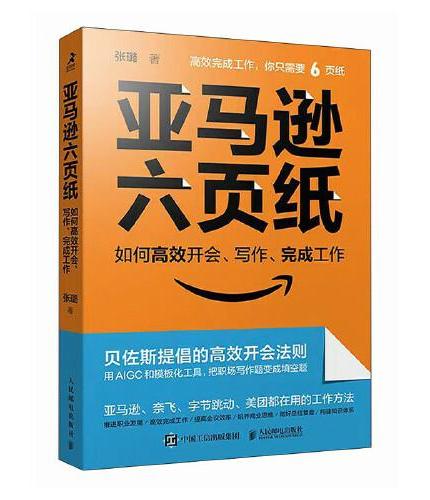
《
亚马逊六页纸 如何高效开会、写作、完成工作
》
售價:HK$
76.8
|
| 編輯推薦: |
世世代代的俄国人深深着迷和眷恋“圣愚”,然而在埃娃·汤普逊的研究之前,“圣愚”在俄国历史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西方承认。作为美国当代重要的俄罗斯和东欧文化研究学者,埃娃·汤普逊在这本《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中,通过对政治、宗教、社会、文学等领域中“圣愚”现象的认真梳理,旁征博引,得出了开拓性的结论,即:“圣愚”来自把基督教合法性强加给萨满教行为,成为俄罗斯民族心理中双重信仰的*完整、*重要的表现。这一成果,是对俄罗斯民族心理的研究创新,有力地探索了俄国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本书是三联书店1998年简体中文版的修订译本,改正了前一版的众多讹误。
|
| 內容簡介: |
|
红场上,圣瓦西里教堂的拱顶举世闻名,而教堂守护圣人瓦西里的历史行踪却神秘莫测。世世代代的俄国人对他所象征的“圣愚”态度和价值观深为眷恋。作为俄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民族文化现象,“圣愚”在俄罗斯民众记忆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到政治、宗教、社会、文学等领域。本书回顾了“圣愚”现象的来龙去脉,梳理了俄国历史和文学上具有代表性的“圣愚”人物,分析指出“圣愚”源于萨满教的独特性,而东正教的加入又助长了这种现象的民间威信。俄国人对其自身的文化解释深受“圣愚”现象影响,俄罗斯民族心理中充满悖论的双重信仰正是其典型体现,必须加以正视。
|
| 關於作者: |
|
埃娃·汤普逊,1963年毕业于华沙大学,并获得索波特音乐学院硕士学位,1967年获得范德堡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俄罗斯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主要著作有《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1987)、《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1979)、《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2000)等。她还是SarmatianReview杂志的创办人。当前的研究兴趣包括欧洲白人对白人的殖民在想象文学中的反映、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以及俄国和波兰作家的专题研究等。
|
| 目錄:
|
前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描述与定义:圣愚规则
第二章:圣愚:俄国的精神病症和精神常态
第三章圣愚与教会:关系暧昧
第四章俄国圣愚和萨满教
第二部分
第五章:俄国文学对圣愚的描写
第六章:圣愚与俄国文化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青年一代冷落老年领袖的事当然并不限于俄国。但是,这种冷落来临之迅猛,与之俱来的轻蔑表现之强烈,在俄国是史不绝书的,但是在欧洲则截然不同。从俄国民间故事中对假德米特里的猛烈嘲笑,经过对惨遭失败的普加乔夫的恶毒笑骂,到猛烈攻击倒下的苏联英雄,在俄国政治社会历史中,崇敬与嘲讽的交替一直频频出现。我认为,圣愚造成的解释习惯助长了俄国居民对俄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对圣愚的崇敬和恐惧与粗鲁的嘲讽并行不悖,二者之间的更迭又屡见不鲜。事实上,这类态度一再出现在对俄国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的待遇之中。
在赫尔岑迅速垮台之后,民粹派运动领袖P.L.拉甫罗夫成为颇孚众望的自由派人物而代替了他。他也像赫尔岑一样,在国外编辑出版刊物,刊物在1870年代的俄国所享有的盛誉堪与前十年赫尔岑的《钟声》媲美。“深入群众”,或者敦促知识分子到小城镇和农村去,让他们和农民打成一片,这个思想首先是在拉甫罗夫的刊物上倡导的。在《前进报》大走红运期间,拉甫罗夫是俄国最受敬佩的人士之一。激进派彼得·特卡切夫和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是他的门徒。特卡切夫还一度和拉甫罗夫合办刊物。两位门徒比拉甫罗夫更为激进,最后终于抛弃了他和他的纲领。他们公开抨击往日老师的气焰,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几乎是前无古人的。这两位人士都极尽讽刺与嘲骂之能事,一心败坏往日挚友的名誉,而不满足于指出他的错误,让他在安宁中下台。应该强调指出,他们不是和他争夺政治地位,而且,他们粗暴反对老师,也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个人的好处。可以说,他们的粗鲁是大公无私的。正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自传》中嘲笑和败坏附近修道院中贪图舒适的修女的那个圣愚一样,特卡切夫和斯捷普尼亚克嘲笑拉甫罗夫是“为了原则”。特卡切夫是这样嘲笑拉甫罗夫的未来社会观的:
到那时候,农民手里的牛马和鸡鸭多得数也数不清嘛。每个人,天天早晨、中午和晚上都有吃不完的肉、喝不完的甜酒……人人都可以爱干多少活儿就干多少活儿,爱吃多少东西就吃多少,要是想睡觉,随时都可以往火炉旁边一靠,想睡就睡。真是大享清福了哟!
斯捷普尼亚克也同样使用了敌视和嘲笑的语调:
有了白璧无瑕、明确清醒的纲领,俄国人一定会飞黄腾达嘛,你等着这一天就行啦!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能出什么主意呢?……你劝我们“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啦什么的……哼,哼,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原来就是——聊大天……
这种攻击终于摧毁了拉甫罗夫的声誉。对他来说,这种嘲笑比对赫尔岑攻击的效果更为持久。赫尔岑虽然被门徒抛弃,死后却大受赞扬。而拉甫罗夫则被忘得一干二净。在苏维埃俄国,儿童们很少知道他的名字,而赫尔岑的名字却经常出现在教科书中。拉甫罗夫被遗忘一事当然和苏联人放心大胆随意修改历史的再三努力不无关系,但是,部分原因也是俄国社会中赞扬变为指责轻而易举之故。
应该补充说明,拉甫罗夫也曾使用同样的戏剧般的诋毁手段对付过特卡切夫。他正确地从直观得知,在俄国,嘲笑和讽刺是对付往日备受称赞,后来又由于某种原因而失势的人的最为有效的武器。他没有和特卡切夫辩论,而是竭力嘲笑他的设想:通过严密地组织少数人在俄国强行夺取政权并实行社会主义。他没有成功。特卡切夫的失败来临得晚得多,而且不是拉甫罗夫造成的。可是,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情况中,他们都采取了嘲讽而不是严肃辩论的语调。拉甫罗夫写道:
有些人可能认为,最好使用旧社会的一套习惯方法:制定一套社会主义法律章程,外加一节恰如其分的“论惩罚”;从最可靠人士(当然,主要是社会革命同盟盟员)中选出“公安”委员会,以伸张正义和施行审判;组建社区和地区秘密警察部队以缉查违法事件,组建财产保安队以维持“秩序”;对“明显的危险分子”实行社会主义警事监督;建立相当数量的监狱,可能的话,还有绞刑架,适当配备社会主义监狱专家和行刑专家;最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再以工人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过更新的旧制度机器运转起来。
对于俄国知识分子来说,体面地退出政治是不可能的。死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退休。每一个领袖人物都不得不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的作家卡尔马齐诺夫的命运。“从崇高到滑稽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这句话最适合于俄国知识分子不过了。离开公众舞台的人必定受到某种诋毁,必须在群众冷嘲热讽声中退场。
和赫尔岑与拉甫罗夫的命运一样,特卡切夫的命运为他自己嘲笑以往政治明星的积习提供了一个讽刺性的脚注。在俄国,他很快遭到了忘却,应该给予他的思想的那份荣誉,被特殊地给予了列宁。在晚年,特卡切夫甚至没有受到他往日同事和门徒们的尊敬。1877年,他患病,在巴黎的一所医院里住了三年。在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是完全孤独的。他被埋葬在巴黎,因为他的那块墓地在五年期满之后没有人购买,他的遗骸被移葬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这位世俗的圣愚死后没有受到崇敬。这种有意的忘却遭遇,在俄国,恐怕是常常强加给往日叱咤风云、极受欢迎人物的那种嘲笑和蔑视的最终形式。
社会广泛接受革命知识分子激进做法的这种现象,一直令外国评论家们困惑不解。为什么俄国人对他们的知识分子及其独断做法一直不持更为批评的态度呢?涅恰耶夫和巴枯宁的思想依据不是“目的说明手段”这一条吗?车尔尼雪夫斯基藐视西方自由主义和他对彼得大帝的赞扬难道不是他对大一统主义有所偏好的表现吗?赫尔岑关于俄国农民公社及其社会主义精神的论著不是表明他对民族主义谬论俯首帖耳吗?拉甫罗夫“深入群众”的号召难道不是他对俄国农村现实状况无知的例证吗?但是,知识分子迷恋于种种悖论的这些表现和其他表现,却不妨碍一大批俄国人钦佩和像替身那样认同于他们那些斗争性强的知识分子。
这类疏忽的原因,看来,部分地在于解释性的期待从圣愚身上转移到了知识分子身上。即使知识分子提出的见解是不现实的、不道德的,或者含混不清的,只要提出这些见解时伴同那种严肃激进的劲头,也能把他们的见解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是颇有吸引力了。在俄国,精神生活的依据是“强硬和悖论即一切”这一观念。知识分子成员互相诋毁的做法因袭了圣愚苛责他们所不赞同的人的那种全力以赴的强硬劲头。曾经一度作为圣愚禁脔的强硬精神,变成了俄国社会里一切追求领袖地位之士的标记。革命激进派之所以被接受,就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人虽然表面上看不顾实际情况,但是具有真诚性格和真正的智慧。激进的论文作者们虽然判断失当,却得到了谅解,正如圣愚们虽然明显地精神失常,也得到了宽恕一样。俄国社会受过教育的阶层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极明显地类似于没受过教育的人对圣愚的解释。
俄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观念,都在对俄国传统的不加批判的忠诚和全然放弃现存社会结构之间摇摆,在空想的完美和“目的说明手段”原则之间摇摆。知识分子们拒绝过去,但是同时又欢迎过去。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又提出实现完美社会的不人道手段。相互竞争的领袖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和嘲弄圣愚或对圣愚下跪的群众的态度可谓异曲同工。赫尔岑、拉甫罗夫和特卡切夫的命运表明,对优秀领袖的崇拜和这些领袖的骤然失宠,是俄国历史反复出现的特征。备受尊崇的拉斯普京遭到可怕的谋杀,看来,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极端表现。
赫然出现在旧俄圣愚身上和革命知识分子著作中的这种毫不妥协的极端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统治者们对付内部不同政见和外界批评的态度,考虑这个问题的确意味深长。看来,旧俄国的各种态度在1917年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而是又被拿来在新的条件下运用。设计和监督新制度下社会机制的那些人,无疑是知道圣愚们对社会结构的激烈反对态度的,而且,他们还知道俄国优秀作家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所提供的持这种拒否态度的文学形象。这些人理所当然认为他们国家的社会结构能够,而且应该完全摧毁:过去备受崇敬的精神领袖们已经暗示,这些结构价值甚微。
时至今日,在俄国,粗暴侵犯法律对公民的保护作用的做法依然得到高度的容忍。公民对于有如无处不在的偷听电话和对公民身份日益频繁地反复检查的行径,并不提出抗议。虽然苏联政府的可信度在苏联公民当中已遭损害,但是,在俄国社会中,对于独立于政府公理结构重要性的感知今天依然微弱。国家无孔不入地监督俄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这一事实的明显容忍态度的依据可能不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且在于对圣愚现象辩证法记忆犹新,这种辩证法意味着,如果意图“良好”,手段即使残暴也可接受;这种辩证法称赞放弃一切“有结构的”社会义务的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
因此,俄国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看来正是圣愚特征的世俗化显现。19世纪俄国改革运动的最大悲剧,可能就在于运动成员酷似他们所极为蔑视的那种“旧俄国的残余”;这是一个一半异教一半基督教、天生狂热、扩张成性、好走极端,并且顽固不化的旧俄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