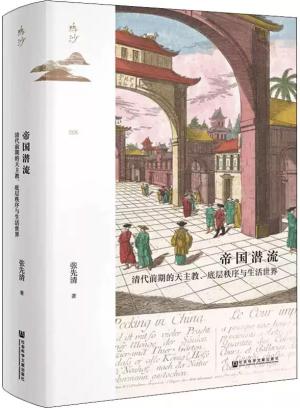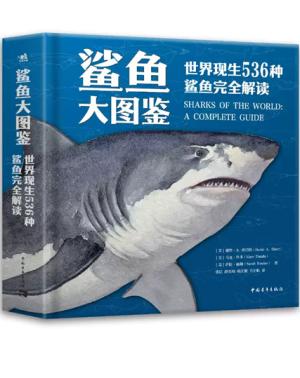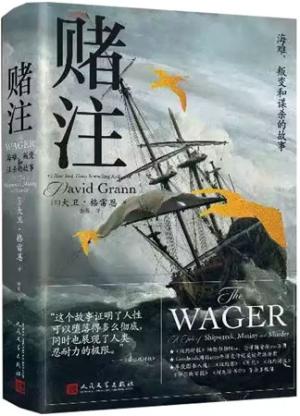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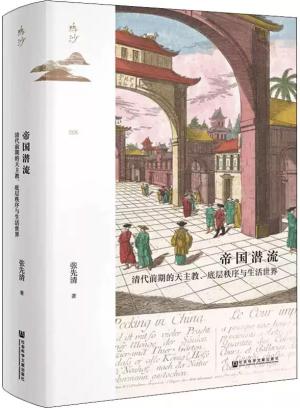
《
帝国潜流:清代前期的天主教、底层秩序与生活世界
》
售價:HK$
1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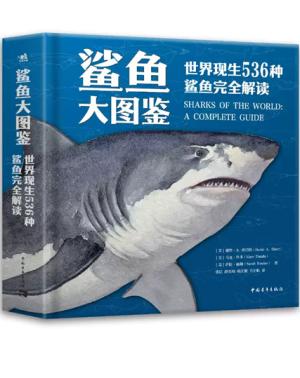
《
鲨鱼大图鉴:世界现生536种鲨鱼完全解读
》
售價:HK$
469.6

《
佛教与晚唐诗(修订本)晚唐诗人的群星闪耀时刻
》
售價:HK$
55.0

《
大模型智能推荐系统:技术解析与开发实践
》
售價:HK$
141.9

《
别字之辨
》
售價:HK$
140.8

《
八段锦 百岁国医大师邓铁涛健康长寿之道
》
售價:HK$
43.8

《
黄帝内经精讲
》
售價:HK$
1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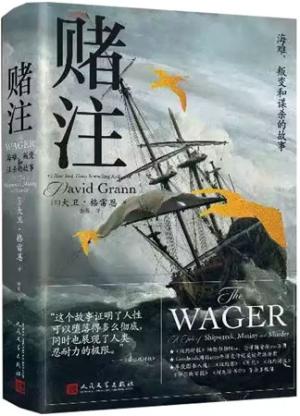
《
赌注:海难 叛变和谋杀的故事
》
售價:HK$
75.9
|
| 編輯推薦: |
历史的经验 智慧的沉淀
一部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深刻启示录
厘清中国传统政治发展脉络 透析中国古代政治智慧
大政治家周公旦、公孙鞅、刘彻、李世民、孙中山……在这里相遇
看懂五千年中国政治哲学的第一本书
|
| 內容簡介: |
|
大纲者,提纲挈领是也。中国政治史大纲,聚焦了周公、孔子、商鞅、韩非、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孙中山等顶级政治精英人物对中国政治在理论或制度方面的开山创举及历代最重要之政治智慧。该书不蔓不枝,旨在通论,着力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找出各朝代引导历史前行的火车头,形成一个脉络清晰的中国政脉。本书所论所述,皆是中国历代极重要之政事,极重大之人物,他们汇成了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可以让人们迅速鸟瞰中国政治史的天地之大,以及那个天地之限,并领略到一种注定要长久影响我们生命群体的政治文化模式。
|
| 關於作者: |
|
马平安, 1964年生,河南卢氏人,历史学博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史,出版著作15部,发表论文30余篇。
|
| 目錄:
|
自 序
第一章 周政之精髓
第一节 大政治家周公旦
第二节 周政之精髓
第三节 孔子对周政的扬弃
第二章 秦政之是非
第一节 大政治家公孙鞅
第二节 韩非的长短版
第三节 秦政之精髓
第四节 国人心中的“秦始皇情结”
第三章 汉家之制度
第一节 大政治家刘彻
第二节 汉承秦制
第三节 亡秦之鉴
第四节 “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第四章 唐宋明清之新元素
第一节 大政治家李世民
第二节 三省制的发展
第三节 内阁制的演进
第四节 科举制与文官制
第五章 近代转型期下之求索
第一节 大政治家孙中山
第二节 步履艰难的晚清预备立宪
第三节 五权分治的民国模式实践
第六章 晚清政治之检讨
第一节 全球变局潮中的官方回应
第二节 晚清改革启示录
第三节 腐败是个癌细胞
第四节 社会精英与政治参与
|
| 內容試閱:
|
腐败是个癌细胞
官员腐败成风是导致晚清改革失败与清政权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腐败现象,迅速削弱了政府对民众的向心力,堪称历代王朝覆亡前兆的典型。晚清的腐败问题既是传统专制政权痼疾的复发,又是因为政府现代化改革不完善带来的新问题,追根溯源是中国官本位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历史现象。
晚清政治十分腐败,首先是以捐纳为形式变现出来的卖官鬻爵的现象为最典型。
卖官一事,据史料记载,在我国历史上少说也有二千年之久了。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时,就有纳粟一千石,拜爵一级的记录。
汉袭秦制,继续纳粟拜爵。
汉以后各代,关于卖官之事,同样史不绝书。
清入关主宰天下以后,虽然历朝都有禁止卖官鬻爵的上谕,然而持续到清朝灭亡,卖官一事事实上并未真正停止,实与清王朝存亡相终始。
从某种程度上讲,金钱与官职交易,可以视为是一种特殊的交易,买卖双方都具备了双重身份:在这场交易中,买方也具有卖方的身份,卖方也具有买方的身份。买者用钱买了官,有了将本求利的基础,就可能在此后的任职期内贪污腐败,一本万利;卖方卖去了政府要求官员之能成为官员的道德与法制的标准;卖去了官员应该遵守的规矩,卖去了官员应该承担的义务,卖去了官员从政良心和对国家的忠诚。既然,千里做官只为吃穿享乐,买方成交后,上任后尽管捞本赚足就是了,别的事情找政府,找皇帝去,本老爷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而政府作为卖方,虽然暂时得到了金钱,换得了财政危机的暂时缓和,却也因此收获了贪污成风的吏治,这是卖方与买方双方的利益和性质所决定的。
政府在出卖官职的同时,把政府的尊严、官场的廉洁与官员应该遵守的责任与义务全都折价变卖了。这种情况,朝廷也都心知肚明,可就是不愿意停止下来。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皇帝在召见张集馨时,曾经说过:
“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
张集馨问捐班既然不好,何以还准开捐?
道光皇帝拍手叹息曰:“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吗?”[1]
晚清时期,国势日弱,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为了开辟财源,以卖官鬻爵为内容的捐例之风大开。卖官买官的结果,不仅造成国家的名器不尊,仕途拥塞,还造成了清王朝官员素质的严重下降、吏治的日趋腐败、民心的逐渐丧失,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加速了清政权衰亡的历史进程。
清代捐纳,创于康熙,备于雍、乾,嘉、道因袭之,咸、同以后则泛滥成灾。
19世纪的最初几年,白莲教大起义送走了康乾盛世,清王朝从此衰落下来。
到了道光时期,伴随着国库空虚以及接踵而来的鸦片输入、白银外流,清政府的财政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便开始把纳捐卖官作为主要的敛财渠道。从道光开始,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各朝,清政府把捐纳卖官之事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
道光末年,两粤用兵,军饷浩繁,各省争请捐输,遍设捐局。道光皇帝在位30年,年年都有卖官的记录。仅捐监一项,就收入白银3388万多两,每年平均收入100多万两。到咸丰时期,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外有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而导致的巨额赔款,内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巨大冲击,清政府的财政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咸丰皇帝绝望之余,更把捐纳作为重要敛财门径提上重要的日程。同光时期,虽然国家财政有所好转,但卖官鬻爵情况较前更加严重。当时,捐纳是国家卖官的主要形式,主要有:捐实官、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捐贡监、捐分发指省、捐加级等等。虽然光绪五年(1879年)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两次下诏,明令停止捐纳卖官行为,然因积重难返,诏谕行同具文,直至清朝灭亡,以捐纳为表现方式的卖官买官的行为实际上始终未能真正终止过。
晚清时期,等候候补职位的捐员多如牛毛。对于候补官之多,时人讥为“过江名士多于鲫”、“官吏多如蚁”。江南有句名言:“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官场现形记》说:“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补官员总有好几万人。”
以江宁(今南京)为例,宣统末年,江宁的各种候补官数目是:道员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百余员,佐贰杂职二千余员,共计四千余员。而江宁的官缺,合道、府、厅、州、县计之,总计才不满五十缺。二者比例为180。一班钻营之徒利用朝廷政治腐败的空隙,将卖官买官、聚敛搜刮发展到了巅峰。
史传,浙江山阴县人蒋渊如看到官场有利可图,若买到知县的官职,每年少则可捞得银子几千两,多则可达10万两。但他一时又拿不出那么多的本钱,于是便想出个与其他4人集资捐买的办法。蒋渊如出资最多得任县令,其余4人则分别担任刑名师爷、钱粮师爷或办事、守门的家丁,而所得赃款按集资多少分成。于是,5人通力合作,上下其手,贪赃枉法,年收入银子竟高达20多万两。3年后,蒋等虽以贪污罢官,但5人皆如愿以偿,满载而归。
以捐纳制度为特征的卖官鬻爵现象加剧了清王朝政治的进一步腐败,对晚清政治产生了十分严重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捐纳制度导致了晚清官吏素质和能力的严重下降,削弱了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能力。
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一书中说:
“政界之变相,始于光绪辛卯、壬辰间,此后遂如丸走坂,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辇金鬻官者,必资望稍近,始敢为之。至是乃弛纲解弢,乳臭之子,汛埽之夫,但有兼金,俨然方面。群小之侧目于先帝,亦至是而愈甚。”
清朝前、中期,选拔官吏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考试,虽然也有捐纳卖官一途,但在官吏的选拔过程中尚不占主要地位。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吏,虽然大多都是埋头八股,不懂经济之道的仕子,但他们毕竟经过多年的传统文化熏陶,尚能知道礼义廉耻,讲究忠君报国,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晚清时期,卖官和买官泛滥,通过捐纳、贿赂上来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一些平庸无能道德修养极低之辈,他们大都贪污、敛财、投机、钻营,很少去考虑如何去承担自己本职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这样的官,很难谈其为官的素质和治理能力。对于这种情况,道光皇帝曾经有所察觉。
道光十六年(1836年),道光皇帝在召见翰林张集馨时说:
“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2]
但是,面对世风日下的晚清社会,平庸守成的道光皇帝又何能扭转乾坤,改变习气?
2、纳捐制度助长了晚清官场的贪污腐败之风。
在晚清官场,无钱什么事都办不成。
纳钱给国家只能捐到做官的资格,捐官者能否得到实缺,还要看所捐之人向所管官员的行贿程度。握有实权的官吏借此大贪特贪,聚敛无度。
同光时期,恭亲王的岳丈、协办大学士桂良刚刚就任直隶总督,便向下属官员大肆索贿巨金。一名姓卞的候补者向桂良行贿巨金,才得到了个署理冀州的官职,节日还要送银1000两,才能保住近一年的官位。桂良到永定河去视察工程,他的孙子跟他走上一趟,即收了当地官员之礼三万余两,苦苦度日的一名穷候补人员竟然为了得到实职也借钱送礼达五万余两白银。湖广总督官文被弹劾免职回京时,因银子太多,装运困难,就地开了9个当铺。没有实权的翰林们本应是无什么油水可捞,但清苦难耐,竟也琢磨出一种吃印结费的生财之道。因为清朝制度规定,凡外省在京考试、捐官者,必须有同乡京官出具盖有六部印的保证书为之担保,名谓印结。被保证人只有出钱贿赂才能得到印结,而印结费有时竟比买个知县的价钱还要高,这简直又是一种变相的卖官。捐纳泛滥所导致的恶果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清末,主持中央行政工作的庆亲王奕劻更是置朝廷与国家利益于不顾,财迷心窍,大肆接受贿赂,谁送给他的钱多,他就给谁的官大。以捐纳为出身、以军功而起家的地方实力派首领袁世凯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用巨金将他收买,从而将其私党遍布朝野,形成了“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局面,逐渐挖空了大清王朝的权力的墙角。捐纳导致的秕政恶果由此可见一斑。
3、捐纳制度卖掉了人心,卖掉了大清江山。
咸丰末年,冯桂芬就曾指出:
“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坏,吏治坏而事变益亟,事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招乱之道也。”
卖官买官不仅降低了官吏的从政素质,造成了官场的混乱与腐败,更重要的是,由此导致的是人们对政府信任力的丧失。
陋规是晚清官场中无处不在的另一种腐败形式。
清末陋规花样甚多,据学者任恒俊在《晚清官场规则研究》一书中统计,这种腐败的方式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数种:
别敬——也称别仪。外省官员进京引见、请训,离开京城时,送给京官的贿赂性礼物,一般是银子,按官阶高低数量不等。贿赂加上一个好听的字眼,叫仪、敬,带上了礼物的性质,送受双方都心安理得。
冰敬——外官夏天送给京官的礼物。夏季炎热,意使凉爽,表示敬意。
炭敬——外官冬天送给京官的礼物。冬日严寒,取意暖和,表示敬意。
年敬——外官过年时致送京官的礼物。
节敬——官员遇节日送给上司的礼物。
喜敬——官员在上司喜庆日子,包括生日、嫁娶、生子等,致送的礼物。
门敬——官员送给受礼官员门房或仆人的礼物,也叫跟敬、门包。没有这种礼物,其他的礼物就送不上去。
妆敬——送给官员女性眷属的礼物,亦称妆仪。
文敬——送给官员家读书公子的礼物,亦称文仪。
印结——清朝制度规定,凡外省人在京考试、捐官,皆须同乡京官出具保证书,保证考试、捐官的同乡身家清白,并无虚伪等情。保证文书叫结,盖印的叫印结。上边必须盖六部印。要想得到印结,被保证人必须出一大笔银子,同乡而并不熟识,这显然是一种买卖行为。在京每省设一印结局,公推年高资深者主持,凡入局为同乡出名具印结者每月都可以分一次印结费。
耗羡——征收田赋,或征粮食,或折成银子征收时,都要把粮食运输中的损失、银子销熔时的损失计算加入正额收缴,加征的粮食、银子,称作耗羡。耗羡又称羡余、火耗,是附加税。耗羡一般进入官员私囊。雍正时规定耗羡归功,另给官员养廉银,但各级官员任意加征养廉银,使贪污合法化。
棚费——考试时,地方官向民间摊派银两,送给主考。
漕规、到任规——州、县官在征收钱粮或新官到任时,送给上司的一笔银子。
花样——清末官多缺少,候补人员太多,补缺先后,除原有班次外,增加了“本班尽先”、“新班遇缺”、“新班遇缺先”等班次名目,作为补缺先后次序的标准,叫作花样。捐官交上六成银子可以得到优先派缺。要想尽快补缺就得交上银子,争得机会。这就叫捐花样。
部费——中央部门索取的贿赂。吏部索补缺费、保奖费。户、工、兵三部索取报销费。备省军事、工程经费贪污中饱,以少报多,要得到户、工、兵部批准,送给三个部门的贿赂。
现在以别敬为例来说明陋规在晚清官场中所起的作用。
下面是曾国藩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日记摘录:
十四日 袁子久来久谈,旋核别敬单,二更四点睡。.
十五日 夜写信,与朱修伯商事,核别敬单。二更三点睡。
十六日 夜与许仙屏核别敬单。二更后,张竹汀等来一谈,三点睡。
十九日 早饭后清理文件,核别敬单三纸。旋见客多次.料理城内送礼各事。中饭后见客,直至二更,未曾停止。是日会客二十余次,深以为苦。二更后写澄沅弟信一封,添应敏斋信一叶。小睡片刻,三点睡,三更后成寐。
二十日 早饭后至间壁谢公祠一坐,核别敬各单,旋归会客三次,巳初起行出京。[3]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腊月入京请训,在京城盘桓一月有余,于正月二十日出都赴保定上任。从十四日起,就开始筹划别仪,此后,除十八日外,每天在深夜临睡前都要费心审核别敬单,甚至出都的当天上午,又最后仔细核定一次。官拜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京应酬往来,几无虚日,虽然位极人臣,而对“别敬”一事,还要如此认真、很害怕因此会出现一点差错,足见此事不可等闲视之。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补授陕西督粮道。
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写道:
“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因托龙兰簃编修在广东洋行借银九千两,九厘行息;又借包怡庄观察千两;又借汪衡甫同年五百两,二行行息;江翊云同年五百两;又借西人项五千两。……余京中连买礼物数百金,共用别敬一万七千两两。而就道盘川无几矣。”[4]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入京请训,又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5]
诸君看了这段记载,“别敬”的意思即不难明白。它作为礼物馈赠亲戚朋友、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无可厚非。但是,从军机处到中央各部院寺监,按官阶高低,不论认识与否,交情有无,几乎人人有份,这就不像是礼物了。说“别敬”是贿赂,但是,亲朋世好、同乡、同年、老师等等照例致送,这类人又何须行贿?岂不是对亲情友谊的亵渎?应该说,“别敬”银两,具备礼物与贿赂两重性格,它是一种以礼仪形式送出的变相贿赂。这种贿赂集礼仪与贿赂为一体,既降低了礼仪的意义,又抬高了贿赂者的身价,贿赂者送之坦然,受贿者纳之有理。别敬这个典雅别致的名字,真不知道遮盖了多少丑恶,这简直堪做是中国几千年消极文化之典型代表了。
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初八,年满花甲的张集馨守制期满,奉旨署福建布政使。这次,张集馨一反常态,陛辞离京时,不再留别敬给众官员。
他为什么敢带头破坏这种官场中盛行的潜规则?难道他不想再要他的乌纱帽了?
张集馨这样吐露心扉:
“余自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间即可望升巡抚,乃一为萨迎阿陷害,一为桂良陷害,流离琐尾者几及十年。中间虽任甘藩一年半,而缺分清贫,又不肯妄有作为,故于八年回京时,依然两袖清风。家中薄有所积,又为大林经理不善,挥洒一空。今复得此区,颇难部署。瘠京中同人,以及同事,原该留别,窃思时势艰难,无从借贷。且我年已六秩,官兴阑珊,不值热中要求权贵,即或百端罗拙。抵任后无力偿还,累己累人,诸多窒碍。且思命中如果能升巡抚、何至两遇坎坷,其福命之衰薄,已可想见!今已立定主意,三五年内决志回京,何苦终身不悔,甘心降气,为人属吏耶!”[6]
原来,张集馨一是看到他年老在仕途上已经升迁无望,二是因为他的囊中也实在羞涩,深怕日后还不起借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怕承担骂名,做一次随自己心愿者,决定急流勇退了。
外官留别敬,早已成为官场不成文的规矩,外官、京官也都因此形成了心理刻板现象,在认识上也形成思维定势。张氏混迹官场30年后,却敢于突破心理刻板现象和认识上的思维定势,终于违背了官场存在之潜规则,这种现象实在有其探索的价值。
张集馨道光九年(1825年)中进士,道光十六年(1836年)京察一等记名御史,特旨外放山西朔平知府,颇著政声。5年后又以特旨调升福建汀潭龙道。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送别敬一万七千两,调陕西督粮道的肥缺,两年后,送别敬一万三四干金,实授四川按察使。此后任甘肃布政使,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请训时,召见多次,皇帝许愿我今日叫汝做藩司,是要汝做好督、抚,汝不可自暴自弃。次年调任河南布政使,留别敬一万二三千金。眼看要跨上巡抚的台阶,进入封疆大吏的行列,孰料在甘肃布政使任上被牵连于琦善捕杀良番一案,革职遣戍军台。一年多释回赏四品顶戴,补授河南按察使,未赴任平调直隶,并帮办军务,不料被直隶总督桂良诬陷,留胜保军营效力。直到咸丰六年(1856年)才又赏四品顶戴,署甘肃布政使,在布、按这个台阶上浮沉蹉跎了十年。这次又是署布政使,督抚的职任,对于他像荡秋千一样,在面前晃来晃去,眼看就要得手却最终与他无缘。每次的留别,年节应酬、红白喜事的礼物,十分丰厚,但是,没起作用。张氏在他的自订年谱中慨叹道:
“应酬不可谓不厚矣。及番案牵连,朝右士大夫持公论者甚少,转以附会琦文勤为余罪案……余资格官声,当开府者久矣。而抑于藩司者十载,曾未闻有力陈政绩上达宸知者,则应酬又何足恃乎……岂非人各有天命,而君相并不能造命耶?余今已老矣,灰烬余生,断无奢望,学问经济、颓废日深,更不必攀附要津,以幸提挈。自信此生休问天,转悔从前之阅历未深耳!今则大彻大悟,如桶脱底。” [7]
看来,张集馨并不是因为大彻大悟,而是因为一来他囊中确是无钱可送,二来则因为自己年事已高,灰心赌气的结果。
在官场,官欲由“热”而“凉”,大多是因为送礼没有达到期望的目标,希望变成了失望,从而在无可奈何之下,“大彻大悟”,“官兴阑珊”,而变得无所顾忌,破罐子破摔。这种情况何止张集馨一人。别敬大送特送的时候,心理上未尝不是从众,加上自己的热衷做官,京官吃外官别敬,习以为常,在致送的竞争队伍中,缺少一个张集馨,又有什么奇怪? 可悲的是,在这种腐败官场无形枷锁的制约下,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张集馨那样的潇洒?又有多少人敢于像张集馨那样不顾一切地决绝而去?
第三,清代官场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怪现象,有一种人,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人员,甚至还在国家的正式编制之外。但是,千万可别小觑了这些小人物的能量。他们在晚清官场中的能量不可小觑,在各个部门运作中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公然挟制当道。这些小人物即幕宾、长随、官亲等,总称胥吏。
晚清官场当事人张集馨在他的自订年谱中记载了他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件事情:“(陕甘)总督乐斌,由旗员出身,公事全部了了……奏折文案,以委之幕友彭沛霖,而彭幕因此招摇撞骗,官吏趋之如鹜。臬司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及同知章桂文,结为兄弟,登堂拜母”,胡作非为。[8]像这样胥吏依仗上司,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者,在晚清官场处处可见,比比皆是。
胥吏是一种依附在大清国政权这棵大树上的一个个寄生虫。
《清代野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光绪初年,河南镇平县出了一件盗案,盗者是王澍汶。过了一段时间,胥吏们报告知县说王澍汶抓住了。知县方某,是少年进士,一上任就是地方实职,对于官场这潭水的深浅,本来就一无所知,遇事只能处处仰仗幕僚班子。在审理这件案件时,他见刑名师爷东涂西抹,与王澍汶的口供多有不符,就觉得奇怪,问他怎么回事。该师爷毫不顾忌地说道:“我等都是老资格了,大人你才初出茅庐,不懂得其中玄妙。”方知县一想也是,就不敢再追问了。谁知等到王澍汶绑赴市曹要开刀问斩时,大声呼冤,恰巧被巡抚大人听到,命令将案子重审.结果发现要斩首的王澍汶并非真身,而是假冒者。原来为了破案,衙役抓住王澍汶的娈童,要他假冒王澍汶,教他供词,骗他说王澍汶已经为他谋划好出狱的门路了.只要照做就不会有事。那人就冒充了王澍汶,等到发现自己真要被推出去斩首了,才知道被骗,高声呼冤不已。此案最终被刑部提讯,结果是刑名师爷下狱,知县方某革职,白白断送了大好前程。
关于胥吏对清代官场政治的影响,乾隆时人邵晋涵总结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可见,胥吏虽然不属于国家正式编制,但这类人在清代官场中的地位却是十分的重要。
胥吏,《辞海》定义是“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元代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说:“夫吏,古之胥也,史也,上应天文,日土公之星,下书史牒,曰刀笔之吏。”程大昌《演繁露续集》说:“案牍、法令、书判,行移悉仗胥吏。”《大清会典》卷一二说:“设在官之人以治其房科之事,曰吏。”
实际上,在清代,胥吏就是官衙中掌理案牍、钱财、法令以及为官员出谋划策的小吏。从京师到外省,这个阶层遍布清代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行政机关。以京吏为例,仅户部书吏就有一千余人。胥吏在清代官场上十分活跃,对于清代政治的运作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晚清官员郭嵩焘曾这样纵论古今天下,以吐胸中郁闷之气: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则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9]
胥吏对于晚清政治影响十分恶劣,长期盘踞衙门的胥吏们勾结起来,连行政长官也奈何不得。他们甚至能把长官的乌纱帽弄丢。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作伪、敲榨索贿、挟制长官等,不一而举。因此,胥吏素有“蠹吏”、“衙蠹”、“书蠹”之称。清沈起凤在《谐铎·祭蠹文》中讥刺
“胥吏舞文,谓之衙蠹”,“借文字为护符,托词章以猎食,皆可谓之书蠹”。“彼,刀笔小吏,案牍穷年。窃尔生平之一字,辄舞文而弄权”。
胥吏挟例弄权是清代一大弊政。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总要调动,胥吏则长久盘踞衙门,加上熟悉地方情况,因而往往不怕违逆现任官员的意旨而敢于公然挟权谋私,勒索贪污。
清人陆陇其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
即使连以严苛著称的雍正皇帝,竟也对胥吏作弊也无可奈何。
他说:
“各部之弊.多由于书吏之作奸。外省有事到部,必遣人与书吏讲求。能饱其欲,则援例准行;不遂其欲,则借端驳诘。司官庸懦者,往往为其所愚;而不肖者,则不免从中染指。至于堂官,事务繁多,一时难以觉察。县既见驳稿,亦遂不复生疑,以致事之成否,悉操书吏之手,而若辈肆无忌惮矣!”[10]
在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经常要办理大量有关任免官吏、刑名钱谷、兴办工程等内容的公务,办公过程中要处理大批案牍文书。对于这些案牍文书.堂官(尚书)、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衙门负责人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帖括制义、四书五经,并不习法令世务。尤其是清代处理刑名等事,不但要依据《大清律》,还须谙熟繁多、灵活的“例”,对这些律例,官员们就极为生疏。他们倾尽青春之力所学的知识竟然与社会实际完全脱节,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就不能不同从胥吏的摆布。湖北巡抚胡林翼叹息:“《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他们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操作空间很大,常可执例以挟制长官。官员们因为知道自己在这方面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吏进稿便只能唯唯画诺。如中央各部办理案牍的情况是: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查阅成案比照律后,进呈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此案就算定了。
嘉庆皇帝曾在一次谕旨中提到堂司官因不熟悉例而受制于书吏的情况:“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惟命是从,一任书吏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争之情节与其所为之弊窦。” “堂司如此庸碌,书吏如此狡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可知胥吏作恶之事连皇帝自己也都心知肚明,但也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盛怒之下过过嘴瘾而已。
《凌霄一士随笔》中说:“清代书吏之权最大,利最厚。经承之居要地者,每致巨富,次焉者亦多获素封。北京号为首善之区,人文宜盛,而土著科第起家者极罕。大宛两县蘶科之士,类系侨寓入籍者。盖书吏一途,为之易而得钱多,远胜仕宦,故土著入塾读书之人,多趋于斯,不肯治举业以博难得之科第。其舍名取利,固不可谓非得计也。”[11]
在晚清官场,有书吏曾经这样形象比喻: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
晚清官场又有谚语说:“堂官牛,司官驴,书吏仆夫为之驱”“随你官清如水,难免吏滑如油”,“清官难逃滑吏手”。
方苞在《狱中杂记》中记载:
“都下老胥,家藏伪章,文书行下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能辨也。”
嘉庆年间,工部书吏王书常用私刻的假印,以修水利为由,一年之内冒支国库银达数千万两。某罪犯应斩立决,但某书吏向其索贿千金后,暗换文书,竟以另一犯人代替此应该处决者受了极刑。[12]
胥吏实权在握,常常肆无忌惮,放手作奸犯科,大肆索贿纳贿。他们的口号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以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索贿为例。六部书吏权力甚大,人谓之曰“无异宰相之柄”。
各部公务不同,书吏索贿便各有特点。吏部掌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在铨选名单上“开列其先后”;如果“贿不至,非驳斥,即延阁”,所以求官者都肯花大价钱巴结吏部书吏。户部掌管着各省款项的销核,由于军费报销往往出入很大,可在一百几十万两银之间,所以户部书吏索贿的数目一般都很大,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因而有“阔书办者必首户部”、“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侯”的说法。
在晚清,户部索贿居各部院衙门之首,书办胥吏最富者首推户部。军费报销得经户部,晚清内外战争频繁,报销数字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千万。凡是报销一案,实际上先是户部书吏与地方督抚谈判好贿赂数字,双方同意,则报销顺利。否则,往返辩驳长达数年不能报销。户部官员甚至作为堂官的尚书、侍郎也染指分肥。此事在官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封爵拜相、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员与中兴功臣,也不得不放下架子通过贿赂渠道结好户部书吏而达到捍卫自己地方利益的目的。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报销剿捻军费,曾国藩、李鸿章共报三千多万两,事前让布政使李宗羲托许缘仲关说户部书吏,谈妥贿赂数字八万两。但是,朝廷为了关照功臣,所批的上谕是“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就是说,全部报销,不用户部再作审核。曾国藩为此给儿子曾纪泽写信说:“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13]批准报销,免于部议,竟然比得到高官厚爵还感激涕零,可见廉如曾国藩者心中也并不踏实。但是原定给户部书吏的八万两贿赂,仍照送不误,这就是是曾国藩老于仕宦之处。八万两白银不是一笔小数目。对此曾国藩颇有割自己的肉的感觉。但能够风物长宜放眼量,以八万两不必要的贿赂,结好书吏,放长眼光,作为日后修桥铺路、打通门径的用度,这就是曾国藩此老的过人之处了。
在胥吏面前,晚清第一封疆大吏曾国藩都得如此小心谨慎,唯恐得罪了这帮惹不起的小人,其他官员在晚清的发展门径及与政府打交道中的艰难就更可窥见一斑了。
第四,在晚清社会,没有近代的法制和规章,儒家的道德破灭了,新的道德理念还没有树立起来。要想有所作为,都有要靠所谓的人情和关系。当时,官场的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银子”铺路已成为官场进取者必具的法宝之一。
以官场达人袁世凯为例,他本人就是一个善于利用“金钱效应”扩展自已政治势力圈子的高手。在他的眼中,金钱是百用百验的灵丹妙药,它可以化疏远为亲近,化异己者为同党,甚至化敌人为朋友。袁统帅军队,靠的是私恩而非近代民族精神为凝聚力。同样,他搞政治,也就是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和奔走趋奉上下功夫。他无意于在世风日下吏治腐败的社会中扮演自命清高一介不取但却仕途冰塞的倒霉角色,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用银子铺道,因而得以飞黄腾达,能够在历次政海波潮之中事著先鞭,摇而不坠。
袁世凯在早年求官生涯中早已熟练地掌握了这种生存技能。他深知,权力往往同金钱利益连在一起,有权力即有金钱,利用金钱又可以换取更大的权力。因此,在发挥“金钱效应”上,袁世凯则无所不用其极。
早在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就以大把金钱孝敬大学士荣禄,受到荣禄的提拔和庇护。荣禄死后,袁世凯又对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重金馈赠。以金钱为媒介,袁世凯与奕劻日益亲近,奕劻从此成为袁世凯北洋集团的重要后台。
由于被袁世凯用金钱所收买,奕劻对袁世凯是有求必应,言听计从,几近傀儡。袁世凯向奕劻推荐的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时,奕劻甚至主动让袁世凯推荐人才。“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世凯,表面上说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至于袁世凯对于宫廷的供奉,那就更是无微不至。早在两宫逃亡途中,袁世凯就雪中送炭,率先敬献贡品,输送银两,为各省督抚之冠。1900年8月29日送上白银30万两。三天后,即8月31日,又进献中秋贡品一大批,除博粉、恩面、凤尾菜、各项羊皮外,还另献绸缎160匹,袍褂料40套,水果四十桶。
在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除照例进献金钱财帛外,还通过贿赂宫内太监头目李莲英等了解慈禧太后嗜好所需。诸如慈禧太后不喜欢中国古董,喜欢西洋玩意等等。在金钱的作用下,天津直隶总督署的电话可直达京师大内总管太监处,凡宫中一言一行,顷刻传于津沽,朝廷之喜怒威福,悉为袁世凯所预先揣测清楚,他因此能够轻易地迎合流弊,取悦慈禧太后。
为了贿赂朝中权贵,袁世凯甚至还和北洋某些大员和商人集资在北京开办了“临记洋行”,专门供袁世凯集团联络走动北京权贵。
通过金钱途径,袁世凯陆续将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荫昌、太监总管李莲英、崔玉贵、张兰德、马宾廷等清廷内的重要角色都纳入自己的集团范围内,致使形成了“太后方向用,亲贵与交欢”的极不正常的局面。
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继续发挥他的金钱效应,内外兼下,最终夺得了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记载:
“隆裕太后允下退位之诏,其内幕实出于某亲贵之劝逼。隆裕事后颇悔,然已无及矣,故哭泣数月即薨。而某亲贵者,乃受袁氏之运动金五十万,及许以永久管理皇室之特权,始不惜毅然为之者也。”
摄政王载沣的第弟载涛在《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一文中也提到:“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劻)、那(桐)、张(兰德)三人之手。”
综合本节内容,可以得出结论:官员们的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恶行最终腐蚀了大清王朝的政权基础,对此事关注不够与处理不善,这是导致清政权移鼎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清】张集馨撰:《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120页。
[2] 【清】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
[3]【清】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
[4] 【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页。
[5] 【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 —90页。
[6] 【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7] 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8] 【清】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1——202页。
[9] 《凌霄一士随笔》(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89页。
[10] 转引自李茗公:《官场怪圈定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11] 《凌霄一士随笔》(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88页。
[12] 李乔著:《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7—39页。
[13]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34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