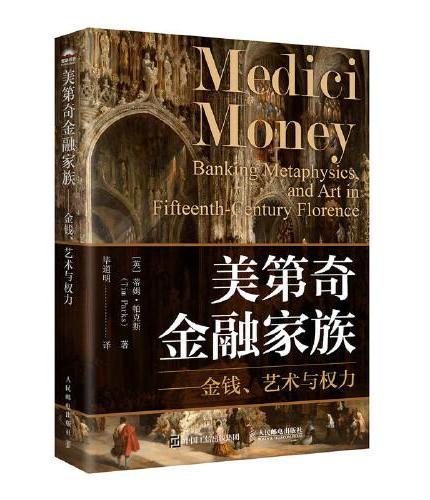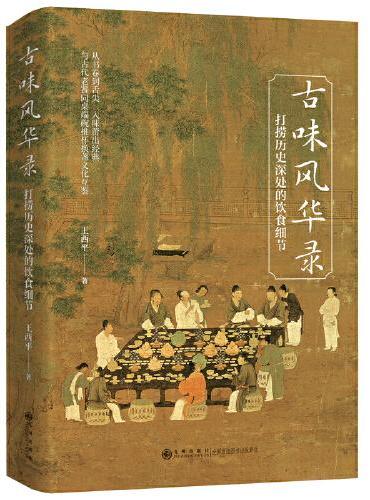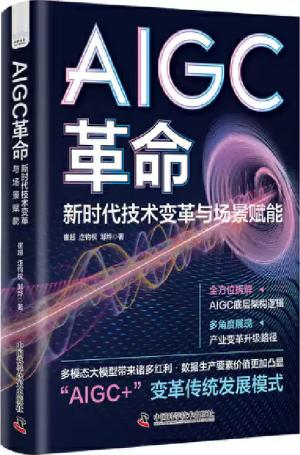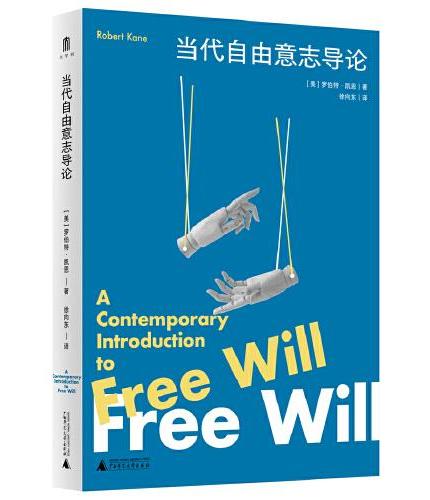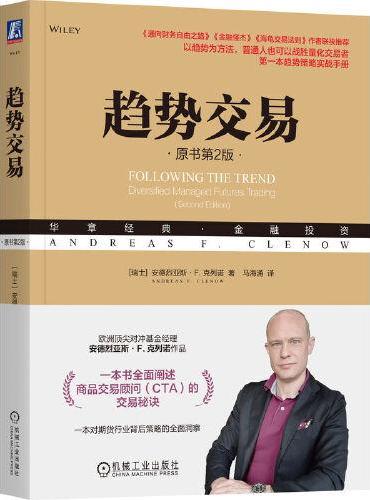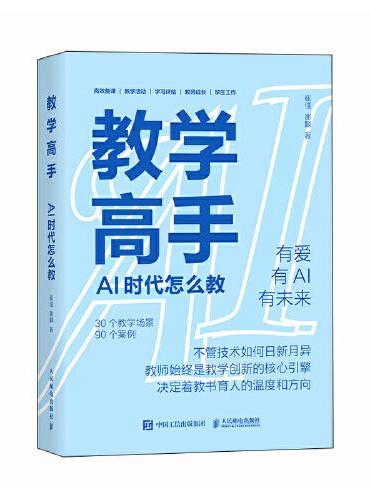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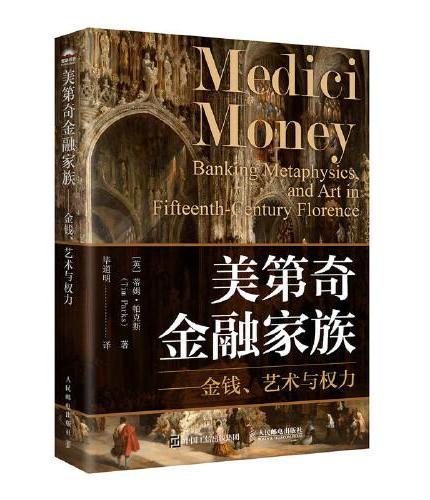
《
美第奇金融家族——金钱、艺术与权力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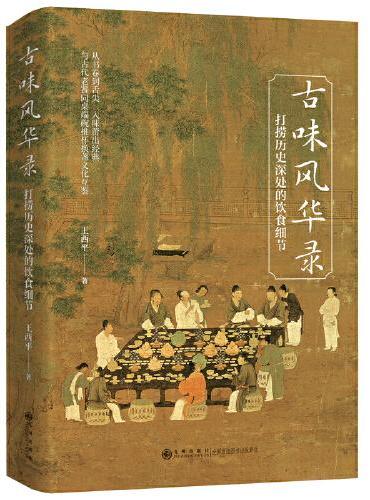
《
古味风华录:打捞历史深处的饮食细节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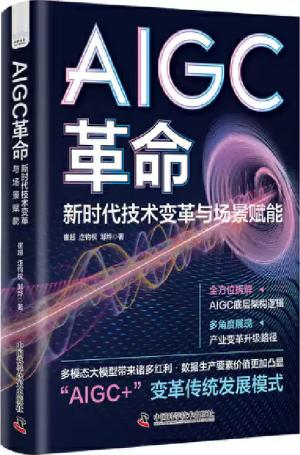
《
AIGC革命 :新时代技术变革与场景赋能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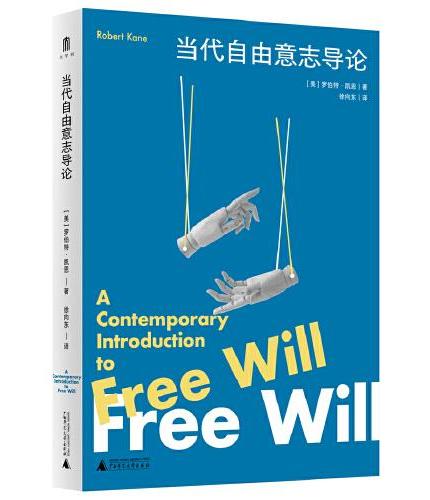
《
大学问·当代自由意志导论(写给大众的通俗导读,一书读懂自由意志争论。知名学者徐向东精心翻译。)
》
售價:HK$
74.8

《
(格式塔治疗丛书)进出垃圾桶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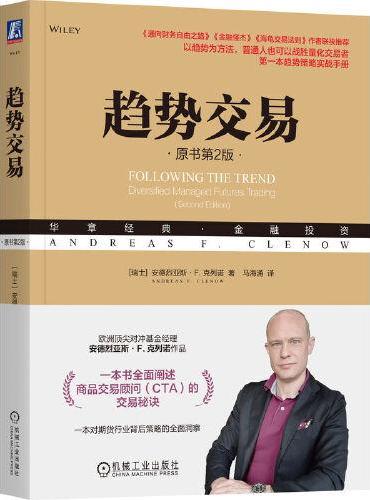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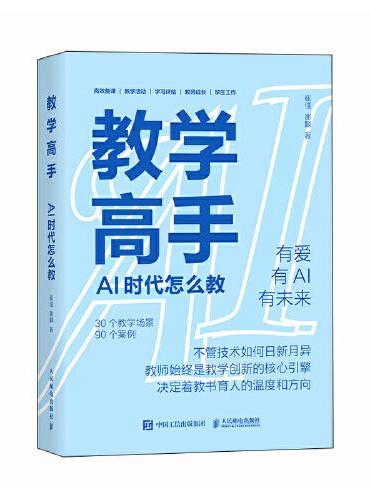
《
教学高手:AI 时代怎么教
》
售價:HK$
65.8

《
中国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报告2025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
这本书刚刚完稿时,曾因多重阻力未能出版。作者只能印制百余本在老友间传阅。今天,我们非常欣慰地是,这样一本关于“文革”记忆的真实故事终于可以呈现给广大读者。
|
| 內容簡介: |
|
这本书向我们透露了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秘历史。带我们回到半个世纪前,重演一段曾发生的“荒谬”历史,体会在大环境下人性的改变、扭曲;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不溢美,不隐恶的立体式回忆录,向人们讲述个人坎坷的生涯,剖析自己曲折的心路。是成功的,供人家借鉴;是缺点,任别人批判。使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了解一点他们这些耄耋老人走过的路、蹚过的河、爬过的坡、跌过的跟头。倘真能如此,也就够了。
|
| 關於作者: |
|
叶笃义,生于1912年,944年加入中国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起协助民盟主席张澜工作。他曾参与了民盟创立与发展的许多重要活动,与司徒雷登、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等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过从甚密。他的经历是以救国、兴国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缩影。1957年反右中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以“特嫌”罪名被关押四年之久;1978年政治上得到彻底平反,以后曾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
|
| 目錄:
|
前言
自序
一我的出身
二开办天津知识书店
三我同张东荪的关系
四我参加了民盟
——筹组民盟华北总支部
五我参加民盟中央工作
六我担任民盟政协代表团秘书
七国民大会召开之后至民盟被迫解散之前
八民盟被迫解散的前前后后
九民盟被迫解散之后至全国解放之前
十全国解放之后
十一关于罗隆基小集团
十二我在1957年当上了右派
十三1957年~1966年
十四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十五我的四个朋友和老师
十六我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附录
耄耋之年再请命
后记跋
|
| 內容試閱:
|
关于罗隆基小集团
罗隆基小集团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在解放之前我同罗的关系就已经密不可分了。
1946年我由北平到重庆参加民盟总部工作。当时他是民盟的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我是一名中央委员。中外记者到民盟访问,总是我帮助他招待。因此,我在总部工作一开始就同他的接触比较多。1946年6月23日南京“下关惨案”我被特务殴伤,在下关车站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罗隆基一个人坐着车子把我从下关车站抬回来,以后又送我到中央医院治疗。我当时很自然对罗隆基发生一种感激心情,为我同他以后的私人关系打下了基础。
1946年代表民盟对外联系的是张君劢和罗隆基,因此我同他们二人的联系一样多。张君劢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的国民大会,我同张君劢的关系断了。以后民盟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会上对盟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取消以前张君劢任主任的国际关系委员会,对外联系由宣传委员会负责。罗隆基被推选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我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从此我同罗隆基的联系更多了。
从一届二中全会到解放以后的四中全会这段时间,我同罗隆基的关系已在前面详细谈过。他在会上受到批判,我接着就想撂挑子不干了。四中全会之后罗隆基感到自己在民盟受到排挤,于是拉拢一小批过去盟内比较接近的人形成一个小集团,我自然身在其内。
我到北平的第二天晚上,罗隆基就约我同到刘王立明家谈话。为什么到刘王立明家而不在北京饭店当时我和罗都住在北京饭店?罗解释说北京饭店的房间来往人多,说话不方便。张东荪当时也在刘王立明家。当天晚上罗对我说,我只弄到一个候补代表,还是张东荪和他力争出来的,张表老没有替我说一句话。他还说沈钧儒和章伯钧各有一个小圈子,而又互相合作,我们盟内一些无党派的人应当彼此多联系,否则一定处处吃亏。我听了这一席话非常动容。于是以后经常不断地到刘王立明家碰头。经常参加的人是罗隆基、张东荪、刘王立明、周鲸文、曾昭抡和我,偶尔参加的人是潘光旦和范朴斋。碰头的地点是固定的,参加的人是固定的。虽然谁也没有说我们要在盟内成立一个小组织,而以罗隆基为中心的一个小圈子实际上已经形成了。
小圈子第一个集中谈的是政协及政府人事安排问题。张东荪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心满意足了,把政协委员让给曾昭抡。罗隆基看到章伯钧和史良当了部长,而他没有当上,满腹牢骚。周鲸文想当政务院委员,我想当副部长。除了张东荪而外,其余的人都为自己的安排不满意,而认为自己在盟内受了排挤。
政府安排固定之后,小圈子第二个谈论中心是有关民盟四中全会的问题。最初是想使会开不成。大会后来终于开成了。罗隆基受到集中批判。我当时有兔死狐悲之感。我是大会的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召集人,会开到一半,我就托病回家不出席了。四中全会上成立了盟中央政治局,章伯钧任政治局秘书长,罗隆基又是不服气。我没有当上常委,心里也不舒服。
四中全会以后,小圈子开会讨论最多的是有关盟中央和各地盟组织的人事安排问题。罗隆基这样注视人事安排是有他的打算的。他经常说:“沈衡老和章伯钧在盟内各有自己一个小圈子,我们也应当组织起来。统战部怎样对待我们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意思就是说有多少人。”为了要“本钱”,除去盟内的小圈子而外,罗隆基还组织了一个包括盟外人士的聚餐会。约请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名之曰“以文会友”,做学术报告和讨论。真正的目的是借此机会把一批人拉进盟来做自己的“本钱”。如果他们不进盟,也可以扩大自己在社会上,尤其在教育界的影响。罗隆基经常讥笑章伯钧、史良和高级知识分子没有联系,认为知识分子也看不起他们。聚餐会是不定期的,人也不是固定的。我在罗家参加过两次这样的聚餐。除了当时小圈子的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而外,会上碰到过吴景超后来也加入了民盟、梅汝璈、邓以蛰等人。一次是潘光旦作了关于苏南义田制度的历史研究报告,一次是梅汝璈讲了美日媾和的法律问题。在这个聚餐会的基础上,当时还准备办一个学术性刊物。1950年香港盟员王振宇过去在香港曾资助民盟办《光明报》,后来在1948年经罗隆基在上海介绍入盟到北京观光,罗隆基告诉王振宇要办这样一个刊物,请王资助。王振宇拿出了当时两千万人民币。后来刊物终未办成。
小圈子除了上述基本人士而外,在外地的有上海的彭文应、陈仁炳、赵文壁,苏州的陆钦墀,浙江的姜震中,四川的潘大逵。这些人都是属于盟内无小党派的。罗隆基注重人事安排,而张东荪却不感兴趣。他对政府和国家中的名位都无所谓,而想的是可能变天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罗隆基经常公开骂美国,而张东荪从来不敢这样做。张东荪对罗隆基说:“燕京大学骂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很快就会知道。”罗隆基说:“我们已经搭上了共产党这条船,不论它是贼船或者是诺亚方舟《圣经》中上帝教诺亚为避洪水而造的方舟,我们只有跟到底,不能想变天。一旦真的变了天,左舜生、蒋匀田这班人回来也会杀我们头的。”
我参加罗隆基、张东荪小集团,内心不是没有矛盾。1949年政务院一成立,我被任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在所有委员当中,我是唯一的正式上班有工作的。1949年底,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派我领导一个组出去视察,不久又委任我为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1950年中央机关干部忠诚老实学习运动的时候,我是政法委员会五人核心领导之一,对机关干部几次大的报告都是我作的。当时曾昭抡曾说我得到党的信任。罗隆基、张东荪说我在党内有人缘。我当时曾向政法委员会秘书长陶希晋要求参加党的“同情组”。陶希晋答复已经取消了那样的组织,但是说只要努力,将来可以进一步要求参加党。
我在解放前曾经为罗隆基的口才所折服。第一次在1946年4月重庆追悼王若飞的会上,他的精彩发言曾博得群众的热烈喝彩。第二次在当年9月上海天蟾舞台上海市政府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会上约请了当时在上海各方面人士参加,事前安排好了特务群众分散坐在会场各个角落。当时会上讲话的共有四人:一是郭沫若、二是邓颖超、三是潘公展、四是罗隆基。主持会的是上海市长吴国桢。第一、第二个人讲完了,下面接着潘公展发言。他的讲话离了题,满篇净是反共的谰言。预先安排好了的特务群众为之欢呼喝彩。最后是罗隆基发言。他本来预备好了一篇讲话稿子,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暂时放下稿子,首先针对潘公展的讲话,针锋相对地一一加以反驳。特务毕竟是少数,广大群众的欢呼喝彩声压下了少数特别的叫嚣。罗隆基反驳完了潘公展的讲话之后,从容地拿出稿子来宣读。最后他说道:“两个人倒下去了,千百万人站起来了!”之后,全场予以经久不息的长时间热烈鼓掌。这确是一场转败为胜的精彩表演。会后,邓颖超、李维汉和罗隆基热烈握手,祝贺他演说成功。
解放后,罗隆基那套口才过时了,没有用武之地了。章伯钧说:“罗隆基是一个好的在野党议员,但是是一个蹩脚的在朝党部长。”李维汉说解放后罗隆基“江郎才尽”了。
解放后我一方面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党的信任,一方面觉得罗隆基、张东荪同章伯钧、史良比起来有些像扶不起来的阿斗。虽然我对罗张小集团的活动越来越不积极,但是我也舍不得抛弃它。我觉得他们终究是我的老师老朋友,在盟内他们总归还是帮我说话的。我经常劝罗隆基多同统战部接触,借此同章伯钧、史良竞争。我经常劝张东荪多写些表示态度的文章,怕他的消极态度惹起党的不满。罗、张既然觉得我在党的面前人缘还算好,因此他们同统战部谈话的时候,总喜欢拉我一同去。我记得罗隆基在他家里几次请李维汉、徐冰,我总是在座。我几次向李、徐说:“解放以后,民盟已没有左中右之分了,有的只是宗派上的纠纷。”我当时这些话深得罗隆基、张东荪的称赞。
小集团的活动从1949年一直继续到1951年底。1951年内小集团内两个人出了问题。一个是刘王立明。她把苏联军队在东北的违反纪律的行为公开揭露出来。她的这个“反苏”言论在盟内遭到严厉的批判,开过几次斗争会。当时她的儿子刘光华曾去找罗隆基说他母亲有自杀的可能,叫罗加以帮助。罗说,他无法在会上为刘王立明说话。他说:“你母亲已经掉下井了,我站在井上可能对你母亲还有些帮助。我不能随她一同下井。”刘王立明“下井”之后,同小集团的关系很自然地断绝了。
另一个是张东荪。1950年8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我偶尔一次见到梁漱溟,梁对我说:“东荪先生准备面见毛主席,在外交上有所进言。”我马上跑到张东荪那里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现在还不准备去见他,等到打一个时期打不下去的时候,我才去说。”他的这个所谓“进言”,就是建议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我当时极力阻止他,我说那是绝对不能谈的。1951年7月党的三十周年大庆,大家都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的文章。解放后张东荪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当年春天,报上登出在他儿子张宗颖天津的家里搜出美国遗留下来的电台,我当着罗隆基的面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内幕。他坚决否认同这件事情有任何关系。我当时引用了一句美国人在法庭作证时常用的话追问他,我说:“你敢赌咒你说的句句是实话,并且除了实话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吗?”他当时回答说:“我敢。”我叫他在报上或者在盟的会上公开表示一下态度。他拒绝了。他这样说:“反正共产党是知道我的。他的这句话是有根据的。他在和平解放北平这一件事上,曾奔走努力过。据说毛主席曾经在民主人士聚会上公开表扬过他至于盟里的人怀疑不怀疑由他们去好了。”事后罗隆基对我说,我当时逼张东荪太过分了。
等到张东荪勾结美国特务叛国事件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害怕了。罗隆基对我说:“张东荪太不够朋友了,瞒着人做那样的事。幸亏李维汉保我过了关指‘三反’关,不然我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这样一来小集团作为一个固定的东西就无形中瓦解了。当然那些小集团的人仍然还继续同罗隆基接近,但以后就是个人之间的来往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成形的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