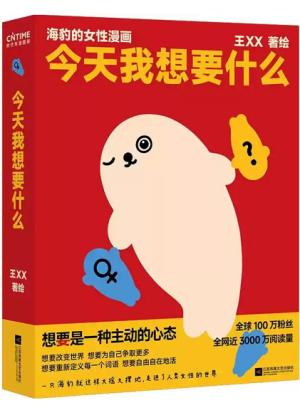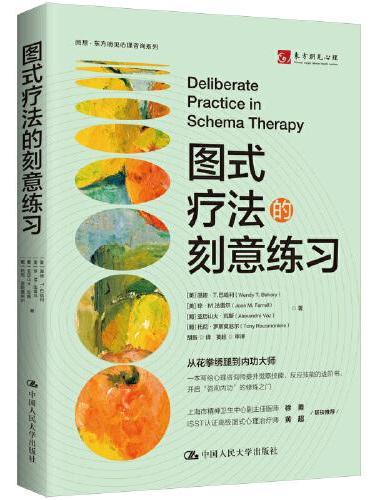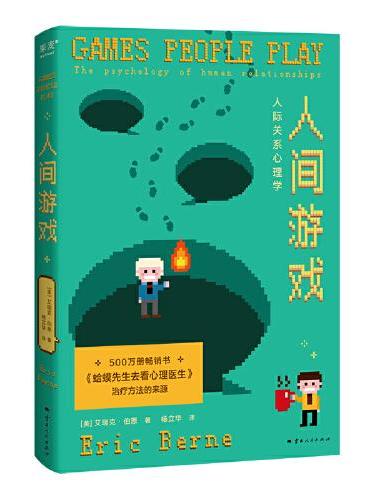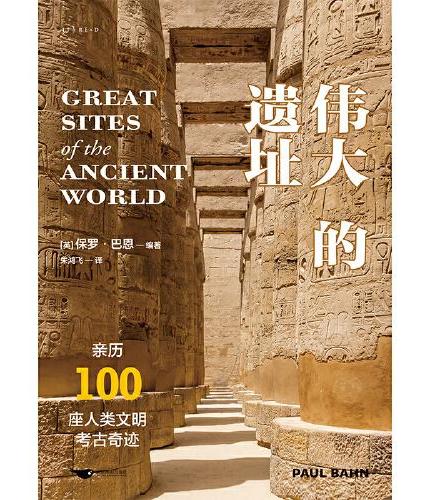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107.8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HK$
3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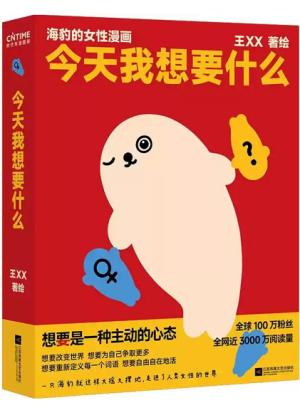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HK$
74.8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HK$
74.8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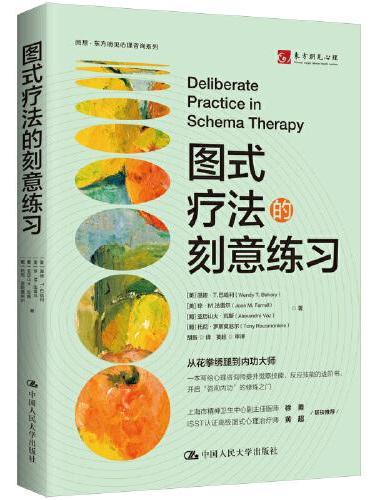
《
图式疗法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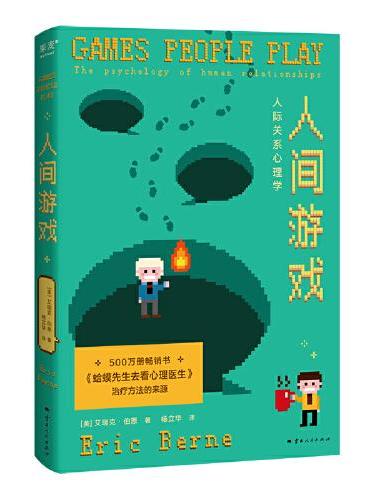
《
人间游戏:人际关系心理学(500万册畅销书《蛤蟆先生》理论原典,帮你读懂人际关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
售價:HK$
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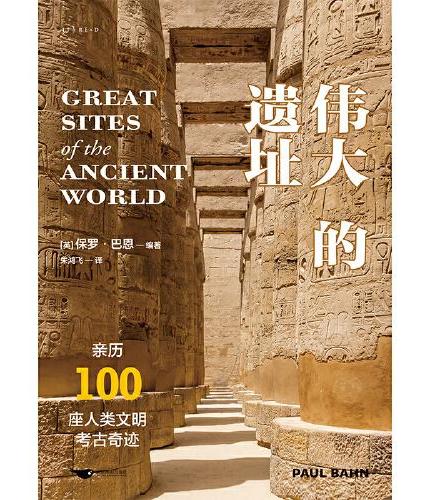
《
伟大的遗址(亲历100座人类文明考古奇迹)
》
售價:HK$
206.8
|
| 編輯推薦: |
1、 中国唯一正版授权,杜拉斯最后一位情人,小她39岁的扬安德烈亚的最珍贵回忆录。全球最特立独行的女作家杜拉斯生前最后一位情人,与她共同创造最惊世骇俗恋情的扬安德烈亚亲笔撰写的回忆录。随着2014年扬的去世,这本著作独一无二的珍贵性更加凸显。
2、 王小波、庆山(安妮宝贝)、林白、陈染、虹影、洁尘、伊能能等国内作者、明星最推崇的作家杜拉斯之情史秘辛。在《那场爱情:我和杜拉斯》里,扬把自己与杜拉斯这场惊世骇俗的爱情中的一切都说了出来:绝望的情欲、无法实现的欢乐、疯狂的嫉妒、酗酒、散步、漫无目的的游荡、发奋的写作、放声大笑……深度揭秘杜拉斯人生的最后16年。
3、 最不可思议的爱情,最优美独特的文笔,引领我们深入爱情的核心,再度了解爱,相信爱。扬不仅是杜拉斯的情人,也是杜拉斯的崇拜者、学生,最后他甚至部分地成为了杜拉斯。他的思想和文笔都深受杜拉斯影响,本书也具备强烈的杜拉斯风格。爱她,就成为了她。
4、 典雅精装,值得珍藏。硬壳双封面精装,100G纯质纸内文,装帧精美典雅,值得收藏。
|
| 內容簡介: |
“我是在等待黑头发的年轻水手时给你写的信,我想他想得浑身发抖,所以爱你。”早在认识他之前,杜拉斯已把扬安德烈亚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单方面给杜拉斯写了七年的信之后,1980年夏,扬安德烈亚带着一瓶酒,终于敲开了杜拉斯的房门。他放下简单的行李,说:“现在,我来了,我就留在这儿。我别无所求,要么认识你,要么死去。”
此后16年,他们一直在一起,直到死亡将彼此分开。
在这本书里,扬把这场惊世骇俗的爱情中的一切都说了出来:绝望的情欲、无法实现的欢乐、疯狂的嫉妒、酗酒、散步、漫无目的的游荡、发奋的写作、放声大笑……他余生一直生活在这场爱情的魅影里,直至2014年,死神将他带到杜拉斯所在的国度。
|
| 關於作者: |
|
扬安德烈亚(Yann Andréa,1952-2014)原名扬勒梅,杜拉斯的最后一个情人。他在卡宴上大学时遇到杜拉斯,从此迷上了她的作品,疯狂地给这位大作家写信。七年后,扬终于走进了杜拉斯的生活。他给杜拉斯当助手和助理,协助她完成了许多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后来自己也写书,出版了《M.D》《那场爱情:我和杜拉斯》《就这样》《上帝每天清晨开始》。杜拉斯去世后,他长时间陷入抑郁状态,深居简出,拒绝采访。2014年,他于巴黎寓所神秘死亡。
|
| 目錄:
|
003 读她的书是孤独的。
006 她不能忍受别人看我,看见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
031 她创造,并且相信自己创造的东西。
038 她索取了一切,我奉献了一切。完完全全。
049 最后一个夜晚,谁知道是在什么时候?
057 1996年3月7日星期四那天,都停止了。
071 我坚持不下去了,精疲力竭。
086 我们喝了一杯。我们不分手了。
090 写书没必要,但我毕生都在写书,只写书。于是,于是一无所获。
101 我留下来是为了让您活着,也是为了爱您,爱您的文字,爱您的故事。
106 您说:“扬,永别了。我走了。拥抱您。”
112 “您爱我吗?告诉我。”今天,是我这样问您。
128 去那儿,什么都不管,遗忘,忘掉我。
139 那首旧歌,永远唱个没完,永远不会停止。
150 在荒凉的加尔各答有她威尼斯的名字。
156 什么都不干,继续一种普通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165 这些文字,我终于可以给您写了。
169 后记
171 附录一关于杜拉斯
192 附录二关于扬安德烈亚
205 附录三关于本书
219 附录四访谈录
243 附录五杜拉斯生平与著作年表
|
| 內容試閱:
|
我想谈谈1980年夏到1996年3月3日这16年当中的事。谈谈我跟她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
我说的是“她”。
我总是难以说出她的名字,我无法说出她的名字,除非写出来。我从来不曾以“你”称呼她。有时,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希望我以“你”称她,希望我能直呼她的名字。但我叫不出来,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痛苦。我知道,我看出来了。然而,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想,我可能不小心以“你”叫过她两三回。我看见她露出了笑容,孩子般的笑容,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欣。要是我一直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
我叫不出她的名字,我想是因为我首次读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这个名字就马上把我迷住了。这个笔名,这个化名,这个作者的名字。总之,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
事情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康城 ,我在那个城市学哲学,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我读的是《塔吉尼亚的小马》。当时,我和克里斯蒂娜B和贝内迪克特L同住一个套间。我是在套间里发现那本书的,书是贝内迪克特的,被扔在地上,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中。我是偶然看到的。这是一种一见钟情。我开始喝苦康巴利酒。我只喜欢喝这种酒。在康城的小酒吧里,要找到可并不容易。
所以,初次相遇就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第一次读,第一次喜欢。后来,我抛开了一切,抛开了所有别的书: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司汤达、马居斯和别的哲学家或作家的书。我开始读她所有的书,所有的书名,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文字。
作者的名字越来越使我心醉神迷。我亲手把她的名字抄在一张白色的纸上。有时,我试着模仿她的签名。
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真模样?我记不清了。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的。
我扔下了所有别的书,只读她的作品。这个作者,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并不认识她。谁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然而,我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她了。这已成定局。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
我喝着康巴利酒。
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我现在还是这样)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巧合。在她和我之间,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扬之间,有一种巧合。
读她的书是孤独的。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我怕谈她的书。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要是别人不喜欢,或不怎么喜欢,或喜欢得不够,那怎么办?所以,我宁愿缄口不语,把话留在心里,接着读她的书。独自读,躲起来读,羞耻地读。
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我已经想保护她了。她已经跟我在一起,但她本人还不知道。我是一个读者,第一读者,因为我喜欢她写的所有文字、全部文字,毫无保留。“杜拉斯”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我全身心地爱着它。它刚好落在我头上。我再也没有离开她,我无法离开她,永远也不能,她也同样。
当时我还不知道,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
1975年,康城的“吕克斯”电影院在放《印度之歌》。电影放完后,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当时,导演习惯与公众交谈。因此,必须组织一些讨论。我想买一大束鲜花,但又不敢买。我害羞。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我没有买花。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我想要一个签名。灯光重新亮了起来,她出现了,她穿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那件栗色皮背心,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那条裙子,她一穿就是二十年。那件背心,她后来给我穿了,是借给我穿的。那件背心质量很好,是软皮的。
“扬,我不能离开它,我不能把它给你。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我很乐意借你几天,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
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
我坐在第一排,就在她对面。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弄糊涂了。她笑了,帮助我,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并且作了回答。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看到她站在那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我都替她害怕。怕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不喜欢《印度之歌》。就像这有可能似的,就像这事会发生一样,就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她喜欢这部电影,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部电影,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爱上了德尔菲娜塞里格 ,爱上了安娜-玛丽斯特莱特 的红裙子,爱上了卡洛斯达莱西奥 的探戈。她绝对喜欢《印度之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印度边缘那座破败的宫殿。加尔各答就在这里,在法国。我看见她了,我看见她了。她怕别人破坏这些形象、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我害怕,但我想给她献花,但愿大家都保持沉默,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看《印度之歌》。就她和我。
问答结束了,还有十来个大学生围在她身边。我掏出《摧毁吧,她说》请她签名。她签了。我对她说:“我想给您写信。”她给了我她在巴黎的地址。她说:“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然后又说:“我渴了。我想喝杯啤酒。”我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去。她喝了一杯啤酒,然后说:“我要回特鲁维尔去了。”几个年轻人陪着她。她上了一辆小汽车,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她把我扔在康城火车站对面的那家叫作“出发”的小酒吧里。我和其他人在一起,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喝咖啡。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上面有她的签名和地址: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路五号。
故事开始了。第二天,我就写了一封信。以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我一直在写。信很短,每天写好几封。有时,我几天不写,然后又开始写。我新写了一封信,但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东西,我立即把信寄走,我不想留着它。我给她寄了几箱信。我不期望回信,没有回信可等。我什么都不等,但我在等待。我继续按那个地址写信。那条马路,我并不认识。那个套间,我并不熟悉。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信她是不是都看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我给这些书的作者写了几句话。那个女人,《印度之歌》放完后,我在电影院里见过她。
让娜莫罗 歌唱那场传奇式的爱情。我买了唱片。我别的不听,只听这张唱片,只听莫罗的声音和卡洛斯达莱西奥的探戈。我被迷住了,我也跟着唱。我不等她的回信,然而,我还是希望她能回,希望她会回,希望她会给我写信。没有回答。没有。哪怕写一句亲切的话,礼貌礼貌也好,比如说“感谢您”“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信”之类。没有。没有任何回音。写几句亲切的话,礼貌的话,这不是她的风格。决不。我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读了她的书。我让自己天真地这样想:总有一天,她会给我写一个字的。
我继续读她的书,别的书我一概不碰。我放弃了任何别的活动,我不再上课,我什么都不干,我天天晚上喝威士忌。我换了套间,现在跟贝内迪克特L和帕特里克W住在康城的欧仁布丹街,就在公墓对面。帕特里克和我都喜欢贝内迪克特,她却不想再见到我们。她和弗朗克L一起准备文科教师的资格考试。我们有时在套间里遇到弗朗克L。我们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们。贝内迪克特不再和我们深夜去“穆卡”喝强身的杜松子酒,听朱里奥伊格莱西亚的《你也没有改变》和阿达莫的《下雪了,你今晚不来》了。她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很用功。她一举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找了丈夫,有了孩子和一幢漂亮的房子。在那段时间里,她不想再看到我们,不想看到我,也不想看到克里斯蒂娜和帕特里克。那个在我们之前阅读杜拉斯的作品、买了那本《塔吉尼亚的小马》的女人,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不想再见到我们了。她会继续读杜拉斯的书吗?她还会那么爱我吗?为什么不?这并非不可能!
我则继续写信。圣伯努瓦路五号。总是没有任何回音,一个字都没有。后来,1980年,她寄给我一本《坐在走廊里的男人》。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我不怎么喜欢,就是说,我看不懂。我寻思这个关于性的故事有什么意思。我很震惊,很落后。可怜的天真汉。我不想弄懂。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不想撒谎,我不会。她马上就会感觉到的。我没有回信,我停止写信了。我收到了第二本书,书中附了几个字:我想你没有收到第一本。您又换了地址。我什么都没说,不再写信。
再后来,我又收到了《黑夜号轮船》《奥莱丽娅斯泰纳》和《否决之手》。
蓝色的封面,法国水星出版社出版的。我疯了,我喜欢得发疯。我去巴黎巴比伦路的宝塔电影院看《黑夜号轮船》。我想她一定会在放映厅里。我去剧院看克洛德雷吉和比奥吉埃、米歇尔隆斯达尔、玛丽-费朗斯所演的那出戏。我回去看了好几遍这部电影。诺伊利的情人们。我第一次去了圣伯努瓦路,我在五号前面经过。我怕遇到她。遇到她怎么办呢?说什么好呢?
什么都没见到。我又乘火车回到了康城。
终于,我得到了消息,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病了,现在好多了,都是酒闹的,我好多了,我刚刚写完了《奥莱丽娅斯泰纳》的电影剧本,我想其中有一段是为您而写的。”她没有说哪一段,也没有说是“巴黎的奥莱丽娅”还是“温哥华的奥莱丽娅”。
她给我这样写道:“我为您写了《奥莱丽娅斯泰纳》这部东西。我并不认识您。我读了您所有的信。我都留着呢!我好多了。我停止了喝酒。我要做这么一件事:拍电影。我将不那么孤独。”
我又重新给她写信,每天好几封。我疯了,我喝好多威士忌。贝内迪克特差不多再也不来套间了。帕特里克很痛苦,回来也少了。他在的话,我们便喝一些酒。我写了一些诗,一些短文,用向贝内迪克特借来的旧打字机打的。我热烈地爱上了这台灰色的机器。有几个晚上,我通宵打字写文章。我想出了一个很棒的题目:美丽的痛苦。喝酒。我喝点“芝德拉”帮助睡眠,睡到下午才起来,听《印度之歌》。我独自待在欧仁布丹街的那个套间里。
有一天,贝内迪克特告诉我说,我必须走,离开这个套间。她说她兄弟要来康城,学医,要住在这里,住在我现在住的房间里。
我走了。我找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我随身带了一个铁箱,里面装着几本书。
后来,是的,我到了那里。1980年7月的一天,我打电话到特鲁维尔。我知道她在那儿。我每周都读她在《解放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她谈论波兰、格但斯克,谈论灰眼睛的孩子、孩子突兀的脑袋和年轻的夏令营辅导员。我敢肯定她在写我。这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
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我是扬。”她开口了,说了很长时间。我担心没有足够的钱付电话费,我在康城的大邮局里打电话。我不能对她说“别讲了”,她忘了时间,说:“来特鲁维尔吧。这里离康城不远。我们一起喝一杯。”
1980年7月29日,我坐长途汽车去了特鲁维尔。汽车站就在多维尔火车站对面。我走在木板路上,经过黑岩公寓。我什么都不看,登上大楼梯的台阶,从街道那段在公寓前经过。我不知道她的套间在哪里。我不敢看,不敢抬头。我胳膊底下夹着一把雨伞,尽管天根本就没有下雨,我不知道拿雨伞怎么办。我走进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两小时以后见面。我正在工作,很难脱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