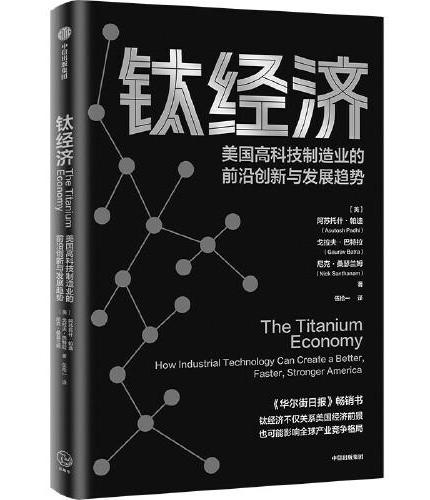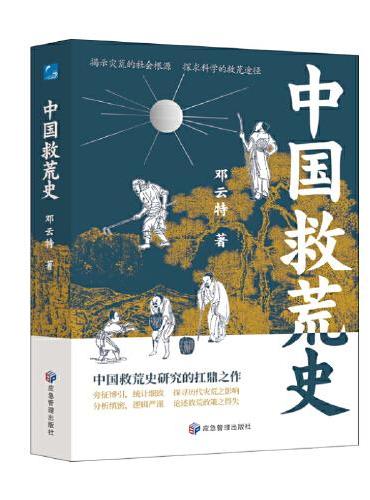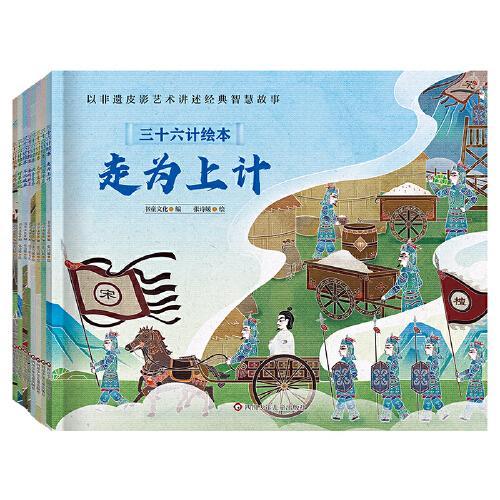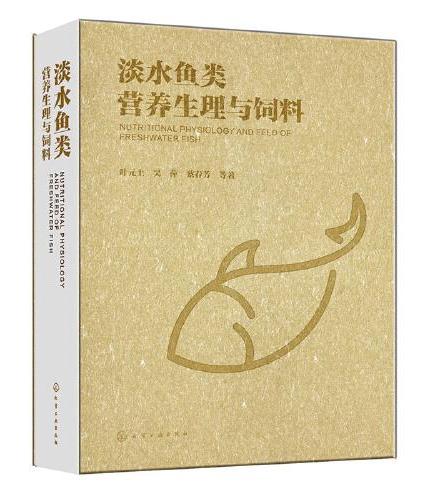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现代化的迷途
》
售價:HK$
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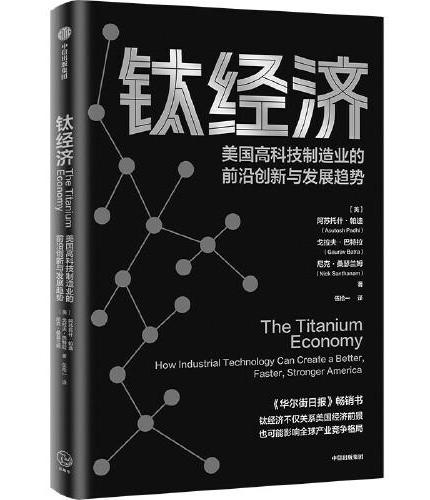
《
钛经济
》
售價:HK$
77.3

《
甲骨文丛书·无垠之海:世界大洋人类史(全2册)
》
售價:HK$
3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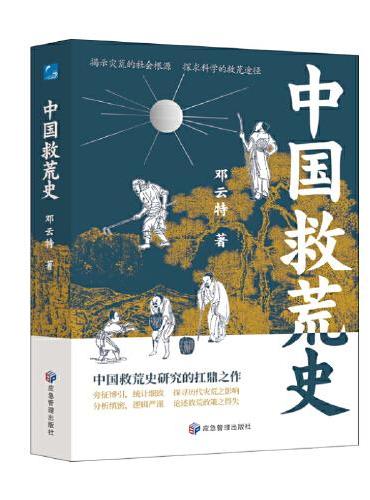
《
中国救荒史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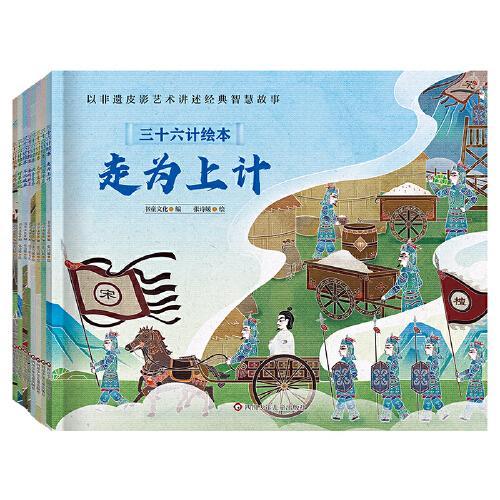
《
三十六计绘本(共8册)走为上计+欲擒故纵+以逸待劳+无中生有+金蝉脱壳+浑水摸鱼+打草惊蛇+顺手牵羊 简装
》
售價:HK$
177.4

《
茶之书(日本美学大师冈仓天心传世经典 诗意盎然地展现东方的智慧和美学 收录《卖茶翁茶器图》《茶具十二先生图》《煎茶图式》《历代名瓷图谱》等86幅精美茶室器物图)
》
售價:HK$
65.0

《
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
》
售價:HK$
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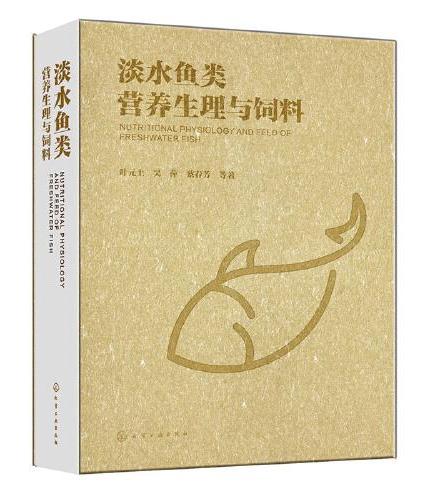
《
淡水鱼类营养生理与饲料
》
售價:HK$
333.8
|
| 編輯推薦: |
与安徒生并称丹麦“文学国宝”
两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备受海明威、塞林格、麦卡勒斯推崇的女作家
经典代表作最美全译本
|
| 內容簡介: |
|
1914年,二十九岁的凯伦·布里克森旅居肯尼亚,在恩贡山下的农场经营咖啡种植园。直到1931年,凯伦离开非洲。她返回丹麦,写下这十七年间在非洲这片奇妙的大陆上动人的经历。在她笔下,非洲大陆笼盖着一种广袤而又柔和的气氛,而鲜活其中的,是和这土地颜色最相贴合的人和故事。疾病、死亡、失败、割舍,是她在非洲的生命旅程中不断上演的课题,但这本书不是一幕悲剧或一首恋旧的挽歌,而是一种自由与勇敢的生命力的宣扬,一种纯粹、明净、深远的爱的渗透。
|
| 關於作者: |
|
凯伦·布里克森(1885—1962),丹麦著名女作家。1914年,旅居肯尼亚,经营咖啡农场。1931年农场大火后返回丹麦。后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以笔名“伊萨克·迪内森”出版成名作《哥特故事七则》,后陆续出版《走出非洲》《冬天的故事》《草地绿荫》《埃赫雷加德》等。曾获安徒生奖和彭托皮丹奖,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走出非洲》是她最著名的代表作。
|
| 目錄:
|
译者序 走出非洲 001
卷一 卡芒提和露露
第一章 恩贡农场 007
第二章 一个本地小孩 024
第三章 移民者家里的野蛮人 041
第四章 一只瞪羚 060
卷二 农场上的走火意外
第一章 走火意外 079
第二章 在保留地骑马 090
第三章 瓦玛依 100
第四章 旺阳盖里 114
第五章 基库尤头人 128
卷三 农场访客
第一章 大舞祭 143
第二章 亚洲来客 153
第三章 索马里女人 157
第四章 老克努森 167
第五章 逃亡者逗留农场 175
第六章 有朋来访 183
第七章 贵族拓荒者 189
第八章 翼 200
卷四 移民者手记
萤火虫 221
生命之路 222
野兽互助 225
艾萨的故事 226
鬣蜥 229
法拉和威尼斯商人 230
伯恩茅斯的名流 232
出于尊严 233
公牛 234
两个种族 236
战时远征 237
斯瓦西里计数系统 243
“我不会让您走,除非您祝福我” 245
月蚀 247
土著与韵文 247
关于千禧年 248
基托什的故事 248
几种非洲鸟类 253
潘尼亚 256
艾萨之死 257
土著与历史 261
地震 263
乔治 264
凯吉可 265
长颈鹿去汉堡 265
动物展览 268
旅伴 272
自然学家和猴子 273
卡罗曼尼亚 274
普兰·辛格 276
奇遇 279
鹦鹉 281
卷五 作别农场
第一章 艰难时世 285
第二章 奇南朱伊之死 297
第三章 山间的墓地 305
第四章 法拉和我清家 321
第五章 告别 336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恩贡农场
我在非洲有一座农场,在恩贡山脚下。农场坐落在六千英尺高度以上,赤道在北方一百英里外横贯而过。白天,你觉得自己升得很高,逼近太阳,清晨和晚上则澄澈宁静,深夜清冷。
地理位置和土地的高度一同构成了一卷图景,全世界没有第二处可与之相比。这里没有一丝丰腴,没有一点繁茂,它是凝结在六千英尺高空的非洲本身,是这片大陆强劲凝练的结晶。色调干燥、灼焦,有如陶器。树木生出的枝叶轻巧纤弱,结构与欧洲的植被不同;它们不呈弓形或圆塔形生长,而是平铺开来,这种形态使得高挺孤独的树木神似棕榈树,又像扯满风帆的船只整装待发,英勇而浪漫。同时,它还赋予了树木边缘一种奇特的外观,好像整棵树都在轻微颤动。无垠大地上散布着扭曲光秃的老荆棘,草地散发出百里香和甜杨梅的辛香气味,有些地方都香得冲鼻子。你在平原上发现的所有花朵,还有原始森林里攀爬在藤蔓上的那些,都像生长在丘陵里的花儿那般小巧精灵,只有在长雨季的开始,大朵大朵香气馥郁的百合才会突然冒出平原。视野无限广阔,你眼见的万物都在趋向伟大与自由,以及无与伦比的尊贵。
这些景貌的最主要特质,以及你身处其中生活的最主要特质,就是空气。回顾在非洲高地的游居岁月,你会对在云端度过的这段时光深有感触。天空的颜色最深不过淡蓝或紫堇色,大量有力、轻盈又不停变幻的云朵层叠漫游,但天空同时又蕴藏着一种蓝色的活力,将近处的山丘和树木都涂抹上鲜明的深蓝。正午,地面上的空气苏醒过来,像火焰在熊熊燃烧,像流水一样在闪烁、摇摆、发光,让每样东西反射又重影,创造出莫甘娜仙女伟大的海市蜃楼。在高处的空气中你呼吸自在,吸入心脾一份重要的确信感和轻松感。你在高地的清晨醒来,心想:我在这里,在我理应所在的地方。
恩贡山自北向南伸展它的绵长山脊,四座雄峰为冠,就像与天空对峙的暗蓝海浪,不可撼动。山体海拔八千英尺,东面高出邻地两千英尺;西面的落差更加深邃,更加陡峻—山脉直落东非大裂谷。
高地的风从东北偏北有规律地吹来。这股风就是非洲沿海及阿拉伯人口中的季风,也叫东风—是所罗门王最得意的快马。在这里,这股风的感觉就像是地球冲进宇宙空间时经受的空气阻力。恩贡山正面迎风,山坡是架起滑翔机最理想的位置,机身会被气流抬升,飞越山巅。与风同行的那些云团要么撞上山腰,萦绕徘徊,要么被留在峰顶,聚而为雨。至于那些选择了更高航线的云团则避开山礁,消散在西方大裂谷燃烧的沙漠上空。我许多次从家里出发,一路跟着这支强大的队伍前行,却惊讶地发现自豪的飘浮大队一越过山峰就消逝在蓝空里了,一去不返。
从农场看去,山峦的形貌一日多变,有时看起来真切逼近,有时又非常遥远。晚上天色渐暗,你凝视它们,开始就像是天空中有笔淡色的银线沿着深色山脉的轮廓一路描绘;接着夜幕降临,四座山峰就像被抚平来又抹开去,好像山脉在自行延伸舒展。
站在恩贡山上,你会有独一无二的视野,朝南看是巨兽乐土的广阔平原,一路伸展到乞力马扎罗山;往东和往北看,山麓下是公园一般的乡野,背后是森林,基库尤保留区连绵起伏的土地延伸至一百英里以外的肯尼亚山—小块的玉米田、香蕉林和草场组成了马赛克般的画面,土著村庄的蓝色炊烟四处升起,房屋像鼹鼠的尖顶小丘般聚集成簇;但面朝西方,下面深卧的却是非洲低地干旱如月球般的景象。小丛灌木不规则地装点着褐色沙漠,蜿蜒的河床和曲折的深绿小径交织相错。那些绿径是巨大的伞状金合欢树丛,它们有荆棘一样的尖刺。仙人掌也生长于此,这里是长颈鹿和犀牛的家园。
如果你深入探索这片山丘,会发现它惊人的广阔,有如画卷,神秘、不可思议。狭长谷地、灌木丛林、绿色山坡和嶙峋峭壁变化多端,高处一座山峰下甚至有一片竹林。山间有泉水和水井,我曾在附近露营过。
在我那个时代,水牛、大羚羊和河马还住在恩贡山上—很老的土著们记得大象也曾住在那里。恩贡山竟没被全部纳入野生动物保护区,我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只有一小块属于保护区,以南峰上的灯塔为界。当殖民地繁荣起来,首都内罗毕变成大都市的时候,恩贡山本可以成为一座无与伦比的野生动物公园的。但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年里,内罗毕的年轻生意人在星期天骑着他们的摩托车冲进山里,不管看见什么都放枪,我相信那些大动物们早已离开山林,穿过南方更远的灌木丛和石头地了。
在山脊和四座山峰上走路倒很容易,因为草丛都像修剪过的草坪一样短,到处有灰色的石块在草间引路。在峰峦间的山脊里爬上爬下则要跟着一条动物踩出的狭窄小道,像平缓的“之”字般蜿蜒而行。在山间露营的一个早晨,我沿着这种小道行走,发现了一群大羚羊刚踩出的痕迹和新鲜粪便。看来这种平和的大型动物在日出时曾排成长队走在山脊上,你很难想象,它们来到这里,别无他求,只是为了登高俯瞰山脊两侧的旷野。
我们在农场种植咖啡。这里的地势种咖啡确实有点太高了,而且要维持下去需要辛勤的劳作。我们经营农场从来没赚到钱。但咖啡种植园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死死抓住你,让你不得脱身,而且永远都有事情要做:你总会比工作进度要落后那么一点。
在一片莽莽无序的旷野之中,这么一块工整划定、还种上了作物的土地看起来非常美妙。后来我在非洲飞行,在空中对农场形象渐渐熟悉后,更是会对自己的咖啡种植园满心惊叹,它那么鲜明地葱茏在一片灰绿色之中,我意识到人类的潜意识多么向往几何图形。内罗毕周边的所有乡野,尤其是城北的这一片,规划都大同小异。这里住着这么一群人,他们未曾停歇的所想所说都是关于种植、剪枝和采摘咖啡的事,他们夜晚躺在床上都在冥思苦想如何改进咖啡工厂。
种植咖啡是细工慢活。当你还年轻、满怀希望时,在绵延的雨季,你捧着一箱箱从温室里取出来的亮闪闪的咖啡幼苗,在田地里和雇农一起将它们插进湿土里的整齐洞列,然后从树林里折下树枝厚厚地为它们遮蔽日光,因为这些小家伙们需要阴凉。但一切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光是等这些树苗结果就要四到五年,其间你的土地会遭受旱灾、病灾,而且蛮横的本土杂草—鬼针草—会密密麻麻爬满整片田地,它们有粗糙的长种皮,牢牢地钩在你的衣服和长袜上。有些树苗没种好,主根都折了,它们一开花就会死。一英亩地可以种上六百棵出头的树苗,我种了六百英亩,公牛拉着犁架在田里树间往返,来来回回要走上几千英里,耐心地等待着未来的收成。
咖啡园有它极美的时节。雨水伊始,咖啡树开花,一片光芒辉映的景象,就像是一片白垩色的云朵,在迷雾和细雨中笼罩着六百英亩的土地。咖啡花有种微妙的淡苦香气,像是黑刺李的花香。当田野被成熟的咖啡果渲染成一片艳红时,所有的女人和小孩—他们被叫作托托—都被喊来,和男人们一道从树上采摘果实,然后四轮的牛车和两轮的马车会把咖啡果拉去河边的工厂。我们的机器总会出问题,但这座工厂是我们亲手规划建起来的,所以对它十分珍视。有一回整座工厂都烧掉了,要从头再来。巨大的咖啡烘干机转啊转,咖啡豆在它的铁胃里隆隆作响,那声音就像海浪冲刷着鹅卵石。有时咖啡豆会在午夜烘好,要赶紧从烘干机里取出来。那真是非常生动的时刻,昏暗的大厂房里挂着许多防风灯,到处都吊着蛛网和咖啡壳,而那些热切灼烫的黑色脸庞全凑在灯光下围着烘干机。你觉得这座工厂,它孑立在非洲浩瀚的夜幕之中,就像镶嵌在埃塞俄比亚人耳洞里的一颗明珠。之后咖啡豆会被手工去壳、分级划类,然后装进马具商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麻布袋里。
最后,在清晨时分,天还是黑的,我躺在床上,听到四轮牛车满载着咖啡麻布袋,每十二袋为一吨,每辆车由十六头公牛拉着,攀上漫长的工厂山路,踏上前往内罗毕火车站的征途。耳边是喊叫声和咔嗒咔嗒声,那是车夫在跟着牛车一路跑。我欣慰地想到,这是他们路上唯一的一段上坡,因为农场比内罗毕市镇高出一千英尺。晚上我步行去迎接回来的队伍,疲累的公牛耷拉着脑袋拖着空车,同样疲累的一个小托托领着它们,困倦的司机挥着鞭子跟在飞扬的尘土里。现在我们尽己所能了。咖啡一两天内就会漂洋过海,我们只能祈求在伦敦的大拍卖会上能有好运气。
我有六千英亩土地,因此除了种咖啡之外还有许多地闲着。农场的一部分是原始森林,还有大约一千英亩是佃农的,他们管这片地叫作香巴地。佃农们是土著,带着一家人在白人的农场上占几英亩土地。作为回报,他们一年要为白人工作固定的天数。我觉得,我的佃农们对这层关系有另一种理解,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就出生在农场上,他们的父辈也是,所以他们很可能把我看作是他们土地上的某种高级佃农。佃农的土地比农场其他地方要更加有生气,一年四季随着季节的变迁而变化。你走在踩得很实的狭窄步道上,两边是高大的绿色兵团发出的瑟瑟响声,玉米长得比你还高,然后该收割了。豆子在地里成熟,女人们把它们采摘回来,豆茎和豆荚堆成一堆烧掉,所以有的时节里,农场各处都升起稀薄的蓝烟。基库尤人也种番薯,藤蔓一样的叶片爬满了地面,像是一块密织的席垫,还有好多种黄色和绿色的斑点大南瓜。
无论何时你走进基库尤人的香巴,立即吸引你视线的一定是一个小老妇人,撅着臀部耙着她的地,就像一只把头埋进沙里的鸵鸟。每个基库尤家族都有好几个圆锥形的小草棚和储藏棚,草棚间的空地是热闹的所在,土地实在得像水泥地,玉米在这里碾磨,山羊在这里挤奶,孩童和鸡仔在疯跑。蓝色的日落前夕,我一度常去佃农屋旁的番薯地里射鸡鹑,家鸽就站在长秆穗状的大树上咕咕地唱出一首嘹亮的歌。曾经有一片森林覆盖整片农场,现在只剩些大树还伫立在香巴的各个角落。
我的农场上还有两千多英亩的草场。强风袭来,长草翻滚有如海浪,基库尤的小牧童们就在这里放牧大人的牛群。寒冷的季节里,他们从草棚里带来红炭,装在柳条篮子里,有时这会酿成草地大火,对农场上的牲畜来说是场灾难。在旱年里,斑马和大羚羊会造访农场的草场。
内罗毕是我们这儿的城市,离农场十二英里远,坐落在群山之下的一小块平地上。这里有政府大厦和中央办公室,是国家的行政中心。
要说一个城市对你的生活没有影响,那是不可能的。甚至不管你对它是爱是恨,它都能通过某种精神上的万有引力法则把你的心吸过去。入夜后,我从农场的一些地方能看到城镇上空晶灿的薄雾,它让我心绪起伏,回忆起欧洲的大都市。
我刚到非洲时,举国上下还没有汽车,我们骑马去内罗毕,或是赶着六头骡子的货车进城,然后把牲口关进高地运输公司的马厩里。在我的整个旅居时光里,内罗毕都是一锅大杂烩,有精美的新式石头建筑,也有整片整片波纹铁皮房的店铺、办公室和平房,这些建筑和成排的尤加利树一起,排列在光秃秃的尘土飞扬的街道两旁。高等法院办公室、本地事务部还有兽医部的楼房都很不堪,我真心对那些政府官员抱有极高的敬意,他们被扔在酷热漆黑的小房子里,还能把所有该做的事都做好。
但内罗毕毕竟是个城市;在这里你能买到东西,听到新闻,能去酒店吃午饭、吃晚餐,去俱乐部跳跳舞。而且它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地方,像流水一样在运动,像年轻人一样在成长,它一年一年在变化,甚至在你外出狩猎时都在变。新的政府大厦建好了,是一栋庄严而出色的建筑,有精美的大舞厅和漂亮的公园。大酒店盖起来了,让人难忘的农产品展览和不错的花卉展览都办起来了。我们这些殖民地的潮流人士也不时给镇上带来情景剧一般的活力。内罗毕对你说:“尽情地享用我吧,享用时间。我们再不会这样年轻了—这样的烂漫和贪婪,一起来吧!”总而言之,我和内罗毕彼此很理解,一次我驾车穿越城市,心中灵光一现:没有内罗毕街巷的世界,不能称之为世界。
土著和有色人种移民的住地与欧式城镇相比要大得多。
斯瓦西里镇坐落在去穆塔伊加俱乐部的路上,虽说它名声不好,却是一处热闹、脏乱而艳丽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去,那里都上演着一堆事情。这个镇大部分是用砸平的老煤油罐子搭建而成的,生锈的程度不一,看上去像珊瑚岩,先进文明的精神从这些石化结构里渐渐流失。
索马里镇离内罗毕很远,我猜个中原因是索马里人对他们女人的隔离制度。在我那个年代有一些美丽的索马里年轻女子,她们的大名家喻户晓。她们住进大巴扎,给内罗毕的警察带来不少麻烦,因为她们能施展魔法,魅惑众生。但本分的索马里女人决不在镇上抛头露面。索马里镇的位置四面顶风,没有阴凉又飞尘滚滚,这一定让索马里人忆起了他们故土的沙漠。同在这里安家很久的欧洲移民者们,有的甚至已经移民好几代人了,他们没法接受游牧民族对自己居家环境的这种完全的漠然。索马里人的房子就这么无序地散建在光地上,但若你走进其中一间,就会发现里面那么整洁和清新,空气中飘着阿拉伯香薰,有精美的地毯和挂帘,有铜器和银器,宝剑有象牙刀柄和上好的刀刃。索马里女人自身有种高贵而优雅的仪态,她们热情、好客又快乐,大笑起来如银铃一般。透过我的索马里仆人法拉·阿登这层关系,我在索马里村庄里非常自在。在非洲期间,法拉一直在我左右,我去过很多次他们的庆典。大型的索马里婚礼是华丽的传统欢宴,我作为贵客被领进洞房里,墙壁和婚床上都挂着闪着微光的老织物和刺绣,黑眼睛的年轻新娘很拘谨,披戴着丝绸、黄金和琥珀,装扮得像根元帅的指挥棒。
索马里人是牛贩子,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交易。为了运输货物,他们在村子里养了一些灰色的小毛驴。我在那里还见过骆驼:骄傲又强韧的沙漠产物,像仙人掌和索马里人一样能超越尘世间的任何苦难。
索马里人总是不厌其烦地挑起激烈的部落内讧。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认知、理论方式和其他民族不同。法拉属于哈布尔·尤尼斯部落,所以在吵架的时候我个人是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有一次,索马里镇上有场动真格的械斗,在杜尔巴·汗提斯和哈布尔·查奥洛两个部落之间展开,来复枪火并,还有人纵火,政府介入时不知已经死了十个还是十二个人。当时法拉有一个同部落的年轻朋友,名叫赛义德,他过去常来农场看望法拉,也是个优雅的男孩。家仆们告诉我,赛义德当时去了一户哈布尔·查奥洛家庭走动拜访,一个愤怒的杜尔巴·汗提斯部落分子经过那里时乱放了两枪,子弹穿透屋墙打断了赛义德的腿。我听了之后十分难过。为了他朋友的不幸,我去安慰法拉—“什么?赛义德?”法拉激动地大喊,“赛义德活该。他干吗要去一个哈布尔·查奥洛人家里喝茶?”
内罗毕的印度人控制了巴扎庞大的本地商业区,了不起的印度商人们在城外都有自己的小别墅,比如杰万先生、苏莱曼·维吉和阿里丁那·维斯蓝。他们都偏爱用这个国家的软石粗制而成的石梯、栏杆和花瓶—就像小孩用粉色装饰砖块搭出来的建筑。他们在自家花园里开茶餐会,提供和别墅本身风格一样的印度油酥点心,他们都是聪明、见识广博的斯文人。但在非洲的印度人是一群特别贪婪的商人,和他们在一起,你永远不知道对面是一个独立的自然人还是某个公司的头头。我去过苏莱曼·维吉家,有一天我看到他家仓库的大院子上空降了半旗,我问法拉:“苏莱曼·维吉死了吗?”“半死不活了。”法拉说。“他还半死不活,他们怎么就在降半旗?”我问。“苏莱曼死了,”法拉说,“维吉还活着。”
我在接管农场前曾十分热衷于射击,也去游猎过好多次。成为农妇后,我就收起了我的来复枪。
马赛人,这个拥有牛的游牧民族,与农场比邻而居,住在河的对岸,他们时不时就会有几个人到我的住处来,抱怨某头狮子拖走他们的牛,让我去帮忙把它打死。我总是有求必应。有时在星期六,我会步行去乌隆吉平原,给农场雇工们打一两头斑马开开荤,我的身后总会跟着一长串乐天的基库尤小孩。我在农场上打鸟,鸡鹑和珍珠鸡吃起来很不错。但有好几年,我没有真正打过猎。
我们仍常常在农场里讨论过往的游猎。露营地牢牢地钉在脑海里,就好像你生命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一样。你会像记得一个朋友的容貌般,清楚记得你曾在莽原上留下的一弯车辙。
我曾在游猎时目睹过一个水牛群,共有一百二十九头,它们一头跟着一头,从铜色天空下的晨霭中走出来。那感觉就好像这种长着威猛的平弯角、色深如铁的庞然大物不是在步步靠近,而是在我眼前当场被上帝之手创造,然后一完工就被派下凡间一样。我还曾目睹一个走过茂密原始森林的象群,日光透过繁盛的藤蔓斑斑驳驳地洒进来,它们缓缓踱步,似乎与世界尽头有一个约会。这幅带状画面像是一块古老珍贵的波斯地毯的饰边,是它的现实放大版,用绿、黄和黑棕色织染而成。我一次次地目睹长颈鹿队伍以它们怪异得无法模仿的植物般的优雅姿态穿过平原,好像它们不是一群动物,而是某种罕见的长茎斑点巨花在缓缓前进。我跟踪过两只犀牛的晨踱,当它们在黎明的空气里喷气吸嗅时—太冷了,所以鼻孔会疼—看起来像是长谷里的两尊怪石在相依着享受生命。我见过日出之前的一弯残月下,王者之狮在猎杀后穿过灰色的平原回家,他从脸颊到耳根都是血色;或是在午睡之后,满足地卧在他的家族中,卧在非洲后花园里的金合欢宽阔的泉状树荫下的短草上。
当农场生活变得无趣时,想想这些会让我喜悦。那些大动物们还在,还在属于它们的领土上;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再次找到它们。它们的近距离存在为农场氛围带来一抹亮色和轻快。尽管法拉和我游猎时带的本地老仆人们都对农场事务日渐感兴趣,但他们仍盼望着再次出发游猎。
在野外,我学会了审慎行动。与你打交道的生灵们害羞而警惕,它们有一种在你不经意间避开你的天赋。没有任何家养动物可以像野兽一样沉静。文明人已经丧失了沉静的资质,在被荒野接纳前,必须要向它学习修静的功课。轻缓行动的艺术,没有一丝唐突,是猎手首先要钻研的,对带着相机的猎手更是如此。猎手们不能执意孤行,必须与风同步,与景貌的色彩和气味相融,必须让自己与合奏统一节拍。有时荒野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一律动,他们也必须跟上。
当你跟上了非洲的韵律,你就会发现,她所有的乐章都如出一辙。我向这个国度的野兽习得的,也适用于我与土著居民打交道。
如果说男人们生性热爱女人和女性的柔美气质,女人们生性倾慕男人和男性的阳刚气概,那么,对南方国家和南方民族的情有独钟就是北欧人的特质。诺曼人想必曾多次与异国陷入爱河,先是法国,然后是英国。十八世纪史书和小说里的绅士们一直在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等地游历,他们的天性里没有一点南方气质,却被另一极的事物完全吸引和掌控。古时,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画家、哲学家和诗人们第一次来到佛罗伦萨和罗马的时候,会双膝跪地顶礼膜拜。
正是这群脾气暴躁的人,对异域世界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包容心。就像一个真男人永远不可能被一个女人激怒;对女人而言,一个男人,只要他仍是个男人,就永远无法被彻底轻视,或被全盘否定。同理,急躁的红头发北方佬也能无休止地包容热带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无法忍受国内的或与自己人交往时的烂糟事,但他们可以谦逊而顺从地接受非洲高地的干旱、不时的中暑、牛群的瘟疫,还有他们家土著仆人的无能。正是因为对方与自己之间存在差异,北方人在可能与之融洽交往的前提下,渐渐失去了对自身个性的坚持。南欧人或混血民族就缺乏这种特质,他们对此苛责,或嗤之以鼻。正如男人的哥们会鄙视唉声叹气的恋爱中的人,同样,那些对自家男人缺乏耐心的理智女性也会对温驯的葛莉赛达怒其不争。
至于我,从刚到非洲的那几周开始,就对土著产生了一种热爱。这是覆盖所有年龄、不分性别的强烈情感。对深肤色民族的探索让我的世界华丽地拓开了一大片。我这种情形啊,就好比一个天生与动物有心灵感应的人,出生在一处没有动物的地方,然后在晚年才接触到动物;或是一个对森林草木有着本能喜爱的人,在二十岁时才第一次踏入森林;或者某个有音乐天赋的人,在成年后才第一次听到音乐。遇到土著之后,我的日常生活节奏才开始与交响乐章同步。
我的父亲是丹法军队里的军官,他年轻时在都佩勒做中尉,写过一封家信:“在都佩勒,我是一支纵队的军官。工作艰辛,但很光荣。对战争的热爱也是一种激情,你像迷恋年轻女人一样爱着你的士兵—爱到发疯,而且爱着一个时不会排斥另外一个,女孩们都了解这一点。不过对女人的爱一次只能投向一个人,对你手下士兵的爱却可以包括整个军团,如果可能,你甚至希望爱得更大。”土著和我之间,是一样的。
想了解土著并不容易。他们耳朵很灵,瞬息即逝。如果你吓到了他们,他们会一秒内退回自己的世界,像野兽受到你唐突的惊吓而逃跑一样—就那么不见了。除非你已经很了解一个土著,否则不可能从他嘴里得到直截了当的答案。对于直接疑问句,比如他有多少头牛,他总迂回地回答:“像我昨天告诉你那么多。”这种回答方式对欧洲人来说很伤感情,不过,很可能这种问话方式对土著来说也很伤感情。如果我们对他们施压或穷追不舍,想从他们口中套出一些行为习惯的解释,他们就会尽可能地退让,然后用一种荒诞可笑的错觉把我们引到歧路上去。即使是小孩,在这种状况下也有老牌手的素质,他们才不关心你是高估还是低估了他们手上的牌,他们只求让你搞不清真相。如果我们真正闯入了土著的宇宙,他们的举止就会像蚂蚁被你的棍子捅进蚁穴一样。他们孜孜不倦地抹去伤害,迅疾而沉默,好像在抹去一次不当的举止。
我们不知道,也无从想象,他们所畏惧的来自于我们双手的威胁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会觉得,他们害怕我们,就好比你害怕一阵突如其来的可怕噪音多于害怕吃苦或死亡。但我也说不准,因为土著们善于拟态。在香巴的清晨,有时你会遇上一只鸡鹑从你的马前方飞过去,她的翅膀好像断了,好像很害怕被狗逮到。但她的翅膀根本没断,而且她也不怕狗,情急时她会对着狗飞沙走石,她这么做只是因为她把一窝雏鸡藏在了附近,她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和鸡鹑一样,土著假装害怕我们是因为某种更深层的恐惧,这恐惧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猜不到。也可能,他们对我们的行为表现归根到底只是某种奇怪的玩笑,这些害羞的人其实根本不怕我们。对于生命,土著不像白人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意识。有时在游猎,或是在农场上,在极端紧张的片刻,我与土著同伴目光相触,那瞬间会感觉到彼此之间相距甚远,我对所冒风险的忧虑让他们不解,我忽然意识到可能他们的生活与自身生命本就水乳交融,这一点我们永不能及,就像深海里的鱼一辈子也不能理解我们对溺水的惧怕。他们拥有这种潜游般的本领,我想,是因为他们仍保着一种智慧,那是被我们的祖辈丢失的智慧。在各个大陆之中,只有非洲可以教会你:神魔是合一的,最高力量永远共生,它们不是两个独立永存的权威,而是同一个。土著从不混淆人,也不分立实质。
通过游猎和农场生活,我和土著从相熟到逐渐相交,我们成为好友。我接受了这一事实,尽管我永远无法真正懂得他们,他们却彻底摸透了我,且能感知到我要做的每个决定,甚至比我自己确定的都早。我曾在吉尔吉尔有一处小农场,我坐火车来往于吉尔吉尔和恩贡,在那里住帐篷。我可能非常突然地在吉尔吉尔下个决定,一下雨我就回自己家。但当我回到基库尤火车站时—这是铁路沿线上我们那一站,从那里到农场有十英里—竟有我的仆人在那里牵着骡子等我骑回家。我问他们是怎么知道我要回来的,他们就会环顾左右,而且看起来很不自在,似乎是害怕或是嫌烦,就像有个聋子坚持要我们解释一支交响乐时,我们会表现出来的神情一样。
当土著已经对我们的唐突和迸发的噪音感到安全时,他们就会坦率地对我们说起好多事情,比欧洲人彼此之间坦诚得多。他们从来靠不住,却异常真诚。“好名字”,也就是声誉,在土著世界里意义重大。不知从何时起,他们似乎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你的联合评定书,之后就不会再有异议。
有时农场上的生活十分寂寞,在凝滞的夜晚里,时钟一分钟一分钟滴落,生命仿佛也随它们离你而去,只是因为没有能说得上话的白人。但我一直能感觉到土著们沉默而隐晦的存在,与我并肩同行,虽然我们处在不同的层面。我们彼此交相呼应。
土著是非洲的血肉化身。裂谷之上雄伟的隆戈诺特死火山、沿河的广阔合欢树、大象或长颈鹿,都不如土著—这些无垠布景里的小人更能真实地代表非洲。所有一切都是同一心念的不同表达,同一主题的变奏曲。这不是异质元素的东拼西凑,而是相同质素的各种契合,好比橡树叶、橡实和橡树产品本是同根生一样。穿着长靴的我们永远都匆匆忙忙,常常与全景不协调。土著却与它一致,高瘦、黝黑的黑眼睛民族跋涉的时候,通常是一个紧随一个,因此即使是最重要的本土交通要道,也只是狭窄的步道;或是他们在土地上劳作、放牛,或举办舞会,甚或告诉你一个故事时,都是非洲本身在漫步,在跳舞,在逗你欢欣。在高地上,你忆起诗句:
我发现
土著们尊贵
而移民者无趣
殖民地在变化,而且自我定居后已经变了很多。我只是尽可能精确地记录我在农场的体会,以及关于这个国家、关于平原上和森林中的栖居者的故事,这或许有一点历史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