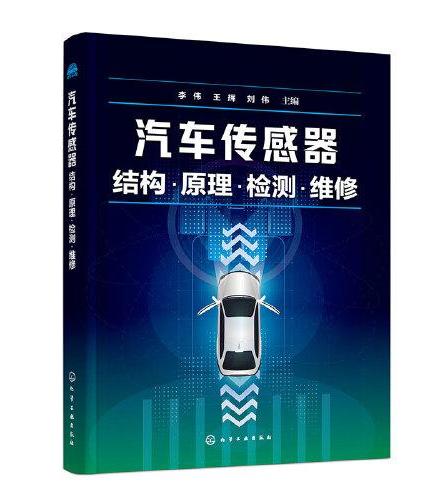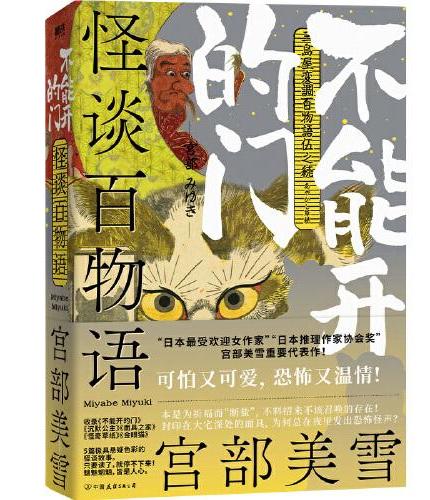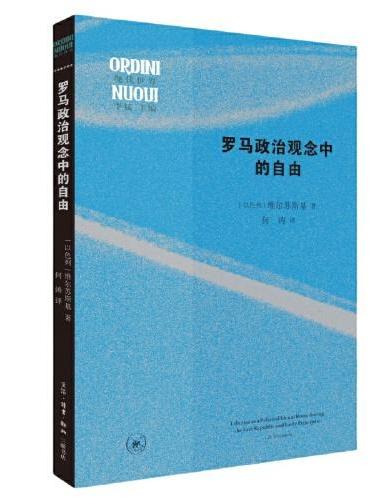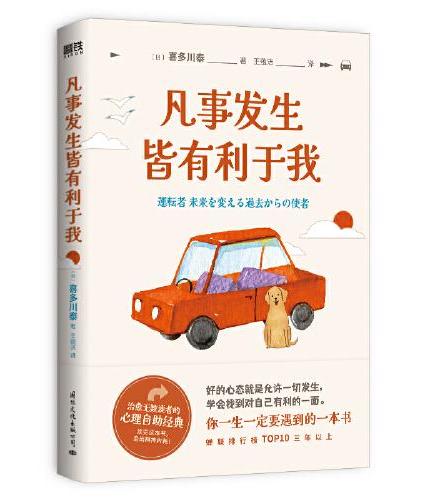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儿童自我关怀练习册:做自己最好的朋友
》
售價:HK$
71.3

《
高敏感女性的力量(意大利心理学家FSP博士重磅力作。高敏感是优势,更是力量)
》
售價:HK$
62.7

《
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中华学术译丛)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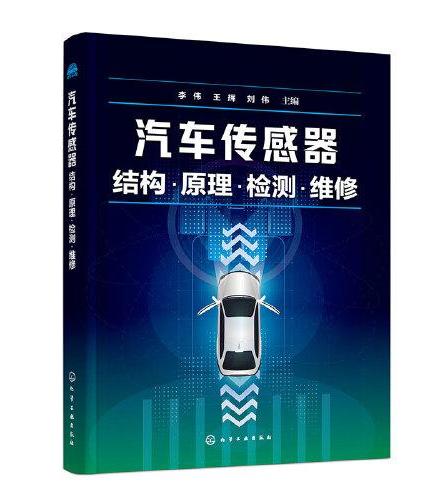
《
汽车传感器结构·原理·检测·维修
》
售價:HK$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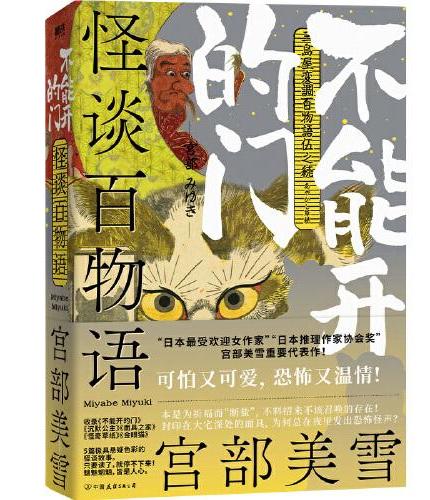
《
怪谈百物语:不能开的门(“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宫部美雪重要代表作!日本妖怪物语集大成之作,系列累销突破200万册!)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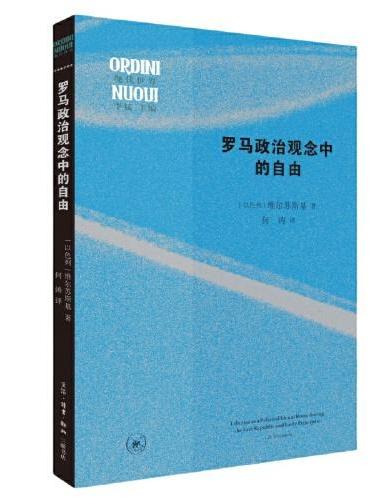
《
罗马政治观念中的自由
》
售價:HK$
51.8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宠位厮杀
》
售價:HK$
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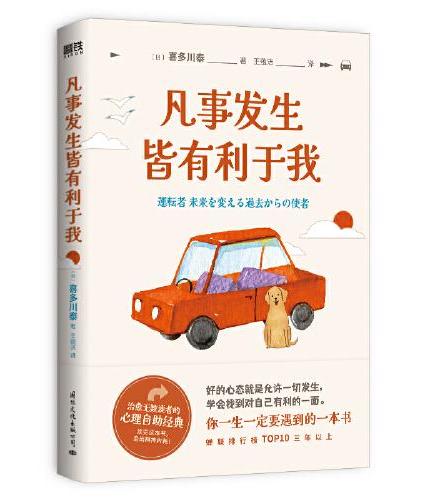
《
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是一本读了之后会让人运气变好的书”治愈无数读者的心理自助经典)
》
售價:HK$
45.8
|
| 編輯推薦: |
1. 奥斯卡最佳影片同名原著,全球狂销1000万册
根据此书改变的同名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在内的79个国际大奖,原著小说40多种语言发行,全球狂销1000多万册。
2. 电影只拍了这本书的5%
在电影中,这只是一个离奇的异域故事:一个贫民窟的穷小子答对了电视节目的所有问题,赢得了金钱和美人,但在书中,它还展示了印度社会、文化、宗教的各个方面,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意义。
3. 印度版《活着》,本土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一个社会最底层孩子的奇幻经历,神奇的故事中蕴含着斑斓的印度文化和不屈不挠的生命力,这既是一场问答比赛,也是一场人性的考验。
4. 全译注释本,完美呈现印度文化的多样性
本书由精通印度语言和文化的著名译者于海生操刀,将印度多种语言的韵味、多样文化的深层含义一一揭示,是本书最完美的收藏版本。
5. 独家图书奖、联合国作家奖、南非布克奖、英联邦作家奖 获奖作品
本书获得国际各大文学奖项的褒奖和肯定,是一本获得文学界和读者肯定的经典小说。
|
| 內容簡介: |
我叫拉姆穆罕默德托马斯,是一个孟买的孤儿。
我被捕了,因为我在一个电视竞猜节目中赢了10亿卢比的巨奖,而他们都认为作弊了。理由很简单:一个贫民窟孩子的知识怎么可能可能如此渊博?就在我被残忍折磨的时候,一个美丽的女律师出现解救了我。我向她讲述了我的神奇经历,从孤儿院到妓院,从列车劫匪到丐帮头目,我所经历的每一种苦难,都成为了最宝贵的财富。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充满了纷繁芜杂的喜剧、惊心动魄的悲剧,以及现代印度催人泪下的迷乱气氛……这部作品不光节奏极快,情节跌宕起伏,内容也异常丰富。
同名电影保留了小说的框架,却无法展现小说中深远的印度风情和复杂的情节、人物关系。只有看过了原著,你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故事的内涵。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维卡斯史瓦卢普是一名印度外交官,曾在土耳其、美国、埃塞俄比亚和英国任职,目前任职于印度驻日本外交机构。处女作《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售出近1000万册,并被搬上银幕和舞台;同名电影获得包括2009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在内的79个国际大奖。
最新作品为《超级富豪的七次考验》。它既是一个独立的精彩故事,也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本书的续集。
译者简介:
于海生,男,辽宁大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曾任报社记者,自由撰稿人,译有《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少有人走的路》、《另一条道路》、《资本的秘密》等。翻译并出版近30本外文图书,其中不乏超级畅销书,至今仍热卖。
|
| 目錄:
|
001序幕
015奖金1000:英雄之死
027奖金2000:一位神父的隐秘重负
041奖金5000:弟弟的承诺
055奖金10000:残障儿童的秘密
077奖金50000:怎样说澳大利亚语
095奖金10万:看住你的纽扣
109奖金20万:西方快车谋杀案
121奖金50万:一个士兵的传奇故事
139奖金100万:杀戮执照
153奖金1000万:悲情女王
171奖金1亿:焚心之爱
211奖金10亿:第十三个问题
221尾 声
224鸣 谢
225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背后的故事
|
| 內容試閱:
|
新德里的帕哈拉甘吉火车站人声嘈杂,万头攒动。灰色的站台沐浴在晨光中,火车头冒出烟雾,汽笛像焦躁的公牛一样嘶吼。
如果要在这个拥挤的迷宫中寻找我的身影,你的目光会投向哪里呢?你可能会从那几十个流落街头的孩子当中寻找我的踪影,他们此时正摆出各种姿势,在平整的水泥地面上休息或睡觉。你甚至有可能把我想象成一个十几岁的小贩,四处兜售塑料瓶装自来水——它们的水源取自火车站卫生间,却要冒充纯正的喜马拉雅山矿物质水。你还可能以为,我是穿着脏衬衫和破裤子的清洁工大军的一员,拖着一把大扫帚在月台上曳步而行,将人行道上的尘垢扫到铁轨上。你也可能在那些急速穿行于人群之间,穿红色制服、肩扛沉重货物的搬运工当中寻觅我的踪迹。
都不是,你再想想吧。因为我不是小贩,不是搬运工,也不是清洁工。实际上,今天我是真正的乘客,我将乘坐卧铺车厢前往孟买。一点儿不错,我买的是卧铺,而且是提前预定的。我穿着一件笔挺的带衬套的纯棉白衬衫和李维斯牛仔裤——是的,是李维斯牛仔裤,我是从“西藏市场”买来的。我正在目标明确地走向五号月台,准备踏上开往孟买的“帕什姆号”西行快车。一个搬运工和我并肩而行,肩上吃力地扛着一个浅棕色手提箱。这个搬运工是我花钱雇的,他扛的是我的箱子。里面有几件衣服,一些旧玩具,一堆《澳洲地理》杂志和一部准备送给萨利姆的电子游戏机,这个手提箱里一分钱也没装。我听到过太多火车劫匪的故事,他们会在夜里下药让你昏迷过去,然后带着你的物品逃之夭夭。所以,我绝不会把我最贵重的货物——我从泰勒夫妇那里领到的工资——放到手提箱里。因此,那个装满崭新的1000卢比面额的钞票——一共50张——的信封,我是随身携带的,我把它藏在一个没人看得到的地方。在我的内衣里面。我把剩下的2000卢比作为这趟旅行之用。我将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这身衣服、火车车票和送给萨利姆的游戏机,而现在我要付钱给那个搬运工,还要购买一些食物和饮料。我飞快地瞟了一眼口袋里那几张零散的钞票。我想,这些钱刚好够我打一辆嘟嘟车,从班德拉终点站直接开到萨利姆在加特考帕尔住的分租公寓。
当萨利姆看到我不是乘坐本地火车而是坐嘟嘟车赶回去,他会不会感到惊讶?当他看见那部游戏机时,我希望他不至于幸福得晕过去。
五号月台比德里超级市场还要拥挤。那些兜售商品的小贩,就和政府办公室外面的抗议示威者一样卖力。在预定铺位名单上搜寻自己名字的乘客,就和查阅考试成绩通知单的学生一样专注。我发现铁路部门完全搞错了我的名字,把它写成了“T.M.拉姆”。尽管如此,我还是高兴地发现,我被分到了S7车厢的3号下铺。
这节车厢几乎在这列长长的火车的尽头,当我们赶到那里并走进去时,搬运工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我在恰好靠近门边的那个指定铺位安顿下来,把手提箱整齐地塞进铺位下面。我付给搬运工20卢比。他想多要一点儿,理由是从火车站入口到这节车厢的距离太长了,于是我又多给了他2卢比的小费。打发掉那个搬运工以后,我才开始打量身边的情况。
我所在的包厢一共6个铺位。一个在我上面,两个在我前面,两个在我侧面。坐在我对面下铺的是一个四口之家: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和我差不多大,另一个是女孩,比我稍大点儿。父亲是一个中年商人,穿着一件名牌黑马甲上衣,带着一顶黑帽子。他长着浓密的眉毛,笔直的胡须,脸上挂着严肃的表情。他的妻子与他年龄相仿,看上去同样严肃。她穿着绿色莎丽和黄色衬衣,用狐疑不定的眼神看着我。那个男孩身材瘦长,看起来很友善,但是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的,是坐在窗边的那个女孩。她体形纤细,容貌清秀,穿着蓝色的莎丽搭配的克米兹,一条南亚长披肩垂到胸口处。她长着会说话的略施粉黛的眼睛、完美无瑕的皮肤和十分性感的嘴唇。她是我很长时间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是那种会让你忍不住多看几眼的女孩。我觉得,我就要迷失在那一双摄人魂魄的眼睛里了。
不过,我还没来得及更多地回味她的美貌,侧面铺位的那个突然大声哭泣的婴儿分散了我的注意力。那是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坐在母亲的膝盖上。他的母亲是一个表情阴郁的年轻女子,穿着一件发皱的红色莎丽。她好像是独自带着孩子旅行,她试图用橡胶奶嘴让孩子安静下来,但那孩子仍在哭叫。
她最后只得撩起衬衣,把一个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孩子心满意足地吮吸着,她轻轻摇晃孩子哄他入睡。从我的座位上,我能够瞥见她那丰满的棕色乳房的下沿,这让我一时间感到口干舌燥,我注意到那个商人正在盯着我,我才把目光转向车窗。
一个卖茶水的小贩进入车厢,只有我要了一杯茶,他把微温的茶水倒进一个陶制容器里,喝起来略带一点儿土腥味。他后面跟着一个报童,那个商人买了一份《印度时报》,他的儿子买了一本《阿奇漫画》,我用所剩不多的零钱买了最新一期的印度《星光》电影杂志。
火车最后一次鸣笛,开始移动,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半钟头。我看了看手表,尽管我能够清楚地看到月台数字时钟显示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半。我以不同角度晃动手腕,希望其他人,尤其是那个女孩,能够注意到我戴的是一款显示日期和星期的日本卡西欧全新数字电子表,它是我在帕里卡市场买来的,花掉了我200卢比的巨资。
那个父亲在一心一意地读报纸,他的儿子在看那本漫画,母亲在为全家人准备晚餐。那个年轻的母亲已经入睡,孩子仍在有滋有味地啃咬着奶头。我假装在看那本电影杂志。我翻到了中间插页,上面展示的是正在走红的性感明星、穿着比基尼的普拉姆辛格的形象,但是我对她外形的傲人资本毫无兴趣。我一直在偷看那个女孩,只见她心不在焉地望着从窗口迅速掠过的城市景象,她甚至都没正眼瞧我一眼。
晚上8点钟,一个穿黑马甲的查票员走进车厢。他检查我们每一个人的车票。我动作潇洒地把我的车票迅速掏出来,但他根本就没仔细看。他只是在票上打个眼儿就把它还给了我。他刚离开,那个母亲就打开一个装着食物的长方形纸盒。里面有各种货色。我看到了压瘪的普里糕、金黄的土豆、红色的泡菜和甜点。家常玫瑰奶球和豆蔻腰果条令人垂涎的香味溢满了车厢。我也开始觉得饿了,可是餐厅工作人员还没来登记晚餐订单。也许我原本应该想着从车站买点儿吃的带上车。
这家人尽情享用晚餐。父亲狼吞虎咽地接连吃掉了好几个普里糕。母亲就着多汁的辣椒咸菜,飞快地扫荡金黄的土豆。男孩的目标集中于那些软乎乎的玫瑰奶球,还一边“咕噜咕噜”地喝着浸泡奶球的糖浆。只有那个女孩在细嚼慢咽,我一声不响地舔着嘴唇。说来也奇怪,那个男孩竟然主动递给我几个普里糕,不过我礼貌地拒绝了。我听过很多劫匪化装成旅客的故事,他们把掺入迷药的食物给同路人分享,然后再偷走他们的钱。谁敢说喜欢看《阿奇漫画》的男孩就一定不是劫匪呢?不过,要是那个女孩给我东西吃的话,我倒是有可能——不,我肯定会——欣然笑纳。
吃完晚餐后,那个男孩和那个女孩开始玩一种叫“大富翁”的棋类游戏。父亲和母亲并排坐着聊天。他们讨论最新的电视肥皂剧、购买房产和去果阿邦度假之类的事情。
我轻轻地拍拍我的腹部。在那里,在我的内衣束腰带的里头,藏着崭新的5万卢比钞票,我感觉到这些钱所具有的力量,正在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的胃、我的肠子、我的肝、我的肺、心脏和大脑当中。于是,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不可思议地消失了。
看着我眼前这个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我不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我不再是只能窥探他们那舒适的生活方式的局外人,而是能够与他们平起平坐、用他们这个阶层的语言彼此交流的局内人。和他们一样,我现在也能看中产阶层的肥皂剧,在周末玩任天堂游戏以及去儿童大世界。
火车旅行意味着各种可能性。确切地说,它可能导致某种状态的改变。当你到达目的地时,你和出发时相比可能已经判若两人。你在途中可能结交新朋友,或者发现你的宿敌;你可能因为吃了不新鲜的萨莫萨油酥卷而出现腹泻,或者因为喝了受污染的水染上霍乱。而且——恕我直言——你甚至有望找到真爱。乘坐2926A次火车并坐在S7车厢的三号铺位上,内衣里藏着5万卢比,我感觉到一种诱人的前景正在刺激我的感官,正在激荡我的心灵,那就是:我有可能(只是有可能)爱上一个穿蓝色谢尔瓦格米兹的同车丽人。而且这里所提到的爱,不是指我们普通人对于电影明星和名人那种单相思的不对等的爱。我是指真正现实的、可望而又可即的爱,不是那种只会变成伏枕大哭的爱,而是那种最终走进婚姻殿堂的爱,那种很快就将喜得贵子的爱,那种全家都要去果阿度假的爱。
我只有5万卢比,但每一个卢比都寄托着五彩斑斓的梦想,它们在我的大脑宽银幕上无限伸展,最终变成了5000万美元。我屏住呼吸,希望这一绮丽的景象尽可能多延续一段时间,因为相比于熟睡时的梦幻,白日梦更为短暂、也更易消逝。
过了一会儿,那对姐弟厌倦了他们的“大富翁”。那男孩走过来,坐到我旁边。我们开始交谈。我了解到他叫阿克沙伊,他姐姐叫米娜克什。他们住在德里,这次是要去孟买参加一个叔叔的婚礼。阿克沙伊滔滔不绝地炫耀他的PS2游戏机和电脑游戏。他趾高气扬地想要告诉我什么是MTV和上网冲浪,也提到了一些色情网站。我告诉他,我讲英语,喜欢看《澳洲地理》,玩拼字游戏,有七个女友,其中三个是外国妞。我告诉他,我有一部PS3游戏机和一台奔腾5电脑,而且我不分昼夜地上网冲浪。我告诉他,我要去孟买见我最好的朋友萨利姆,而且要从班德拉终点站直接打车去加特考帕尔。
我本应知道,现在这个世道,要糊弄一个16岁的少年可比糊弄一个60岁的老人难多了。阿克沙伊看穿了我的谎言。“哈!你根本不懂电脑,PS3还没出呢,你丫就是一个吹牛王!”他嘲笑我。
这话谁能受得了,我不得不奋起还击。“哦,那你觉得我都是在扯谎,是不是?那么好,阿克沙伊先生,那我就在此时此地告诉你:我兜里就有5万卢比。你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吗?”
阿克沙伊根本不信我的话。他挑战似的叫我把钱拿给他看看,我无法抑制地想要镇住他,让他见识一下我的实力。我转过身,把手伸进裤腰里,掏出了那个略带潮湿气和尿臊气的信封。我鬼鬼祟祟地拽出那沓硬铮铮的5万卢比钞票,得意扬扬地在他面前划拉了一下,然后又把钱塞回去,把信封在原处藏好。
你真应该看看阿克沙伊的那双眼睛,那对眼珠子简直都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了。这是一个值得永远回味的胜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用具体有形的东西、而不是靠白日梦来证明自己。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别人的眼睛里,看到有某种不一样的东西在向我投射过来。尊重。它让我学到了宝贵的一课。梦想只能控制你自己的大脑。但是有了钱,你就能够控制别人的大脑。这也再一次让我感觉到,我的内衣里的5万卢比犹如5000万卢比。
现在是晚上10点了,所有人都准备睡觉了。阿克沙伊的母亲从一个绿色旅行包里拿出床单,准备他们一家四口就寝时用。那个搂着婴儿的年轻母亲在旁边铺位上早已入睡,根本没有理会枕头和床单的事情。我没有准备床单之类的东西,而且也不太困,所以就坐在窗口旁边,感受着冷风吹拂我的脸颊,看着火车穿过沉沉的黑夜。我对面的下铺睡着阿克沙伊的母亲,上铺就是米娜克什。那个父亲爬到我上面的铺位,阿克沙伊睡在我侧面的上铺,他上边便是那对母子。
那个父亲马上就睡过去了——我能听到他的鼾声。那个母亲掉过身去,把被单拉到身上盖好。我伸长脖子想要瞅一眼米娜克什,但我只能看见她的右手,还有手腕上戴的金镯子。突然间,她从床上坐起来,开始对着我的方向俯身脱鞋。她的长披肩滑落下来,透过蓝色克米兹的V字形领口,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她的双乳上缘。这让我的后脊梁不由自主地迅速掠过一阵快感。我觉得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我在看她,因为她快速地把长披肩拉上去盖住胸脯,还有些不满地白了我一眼。
过了一会儿,我也沉沉睡去,做起了中产阶层的美梦:购买100万种不同的东西,包括一辆红色法拉利和一个穿着蓝色谢尔瓦格米兹的漂亮新娘。这一切都是用我的5万卢比搞定的。
有什么东西顶在我的肚子上,我被惊醒了。我睁开眼,看见跟前站着一个留着浓密的黑胡须、肤色黝黑的男人,他用一根细木棍戳着我的身体。让我感到紧张的不是那根棍子,而是他右手的那支枪,它并没有专门对准哪个人。“这是抢劫。”他平静地宣布,听上去仿佛是有人在说“今天是星期三”一样。他穿着白衬衫和黑裤子,头发很长。他样子很年轻,就像一个文艺青年或者一个大学生。但话又说回来,我以前从未在电影院以外的地方见过劫匪。也许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大学生也未可知。他再次开口说话了。“我要你们都从铺位上下来,慢慢地给我下来。只要没人逞能想当英雄,我保证不会有人受到伤害。别想着逃跑,因为我的兄弟把那头儿也堵住了。你们只要乖乖地合作,用不了10分钟就完事了。”
阿克沙伊、米娜克什和他们的父亲同样都在枪口的威逼下从铺位上爬下来。他们一个个睡得迷迷糊糊,完全乱了方寸。当你在深更半夜被突然叫醒时,大脑的瞬间反应总是很迟钝的。
我们都坐在下铺床位上。阿克沙伊和他父亲坐在我旁边,米娜克什、她的母亲和那个带小孩的女人坐在我对面。那个孩子又任性地哭了起来。母亲试图安抚他,但那孩子哭声变得更大了。“给他喂奶。”劫匪粗声粗气地命令她。那个母亲惊慌失措。她掀起了衬衣,两只乳房(而不是一只)都露了出来。劫匪对她咧嘴一笑,做出要抓她的乳房的动作。她尖叫着匆忙把乳房遮住。劫匪大笑起来,这一次我丝毫没有感觉亢奋。
一把子弹上膛的枪杵在你的脑门上,要比一只裸露的乳房更刺激。
现在那个劫匪已经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他便开始下一步行动了。他左手高举着一只棕色麻袋,右手持枪。“OK,现在我要你们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放到这个袋子里。男的要把钱包、手表和口袋里的现金交给我,女的要把手提包、手镯和金项链交给我。谁要是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立刻一枪崩了他。”
米娜克什的母亲和那个年轻的母亲听到后同时尖叫起来。我们听到车厢另一边传来了哭声。大概是劫匪同伙对其控制的乘客发出了同样的指令。
那个劫匪把敞着口的麻袋拎到我们跟前,逐个儿地让我们把东西放进去。他从那对母子开始洗劫。那个女人带着惶恐的表情拿出棕色皮革手提包并迅速打开,掏出橡皮奶嘴和奶瓶,然后把手提包扔进麻袋里。她的孩子一时间被迫中断了吃奶,又开始号啕大哭。米娜克什看上去目瞪口呆。她摘下了金手镯,不过就在她准备把镯子放进麻袋时,那个劫匪丢下袋子,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比这个镯子可漂亮多了,亲爱的。”他说,米娜克什拼命地想要挣脱这个家伙铁钳一样的手掌。劫匪松开手腕去抓她的克米兹。他抓住了米娜克什的衬衫衣领,而她赶紧向后退去,在这个过程中,衬衫几乎被撕成了两半,她的胸罩露了出来。我们看着这一幕都吓呆了,米娜克什的父亲再也无法忍受了。
“你这个浑蛋!”他喊叫着冲向那个劫匪,但后者的反应像豹子一样快。他放开米娜克什的衬衫,用手枪枪托砸向她的父亲。商人的额头立刻裂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开始往外渗出,米娜克什的母亲再次尖叫起来。
“闭嘴!”那个劫匪咆哮着说,“不然我把你们都给崩了,一个也不落。”
这句话产生了威力,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了。恐惧让我窒息,我的手开始发冷。我听着每个人艰难的呼吸。米娜克什低声哽咽着。她的母亲把手镯和手提包扔进袋子,她的父亲用颤抖的手指交出了他的手表和钱包,阿克沙伊问,他是否应该把《阿奇漫画》放进去。这激怒了劫匪。“你以为这是开玩笑吗?”他的嘴里发出一阵嘶嘶声,随即扬手给了那男孩一个嘴巴子。阿克沙伊痛得叫了一声,用手捂住了脸颊。由于某种原因,我觉得刚才这一幕相当有趣,就好像是一部恐怖电影插入了一个喜剧片段一样。那个劫匪不乐意了。“你笑什么?你身上有什么?都交出来!”他厉声说。我从口袋里掏出剩余的钞票和硬币,把它们扔进麻袋,只留下我那1卢比的幸运币。我开始解下我的手表,但那个劫匪看了一眼说:“这是冒牌货。我不要。”
他似乎对这一车厢的战果非常满意,并且准备离开,就在这时,阿克沙伊大声说:“等一下,你忘了一样儿东西。”
我看着这个场面如同慢动作一样展开。那个劫匪原地转过身来。阿克沙伊指着我说:“这小子身上有5万卢比!”他轻轻地说,但是我觉得,整节车厢的人都听见了这句话。
那个劫匪威胁性地看着阿克沙伊:“这又是一个笑话吗?”
“不——不是。”阿克沙伊说,“我发誓。”
那个劫匪低头看看我的铺位下面:“是在这个棕色箱子里吗?”
“不是,他藏在内衣里了,在一个纸袋里。”阿克沙伊回答说,他不自然地傻笑了一下。
“啊哈!”那个劫匪喷出一口粗气。
我浑身颤抖——我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愤怒。劫匪走近我。“你是要乖乖地主动把钱交给我,还是想让我当着所有人把你剥光?”他问。
“不!这是我的钱!”我叫起来,又本能地护住下腹,好像一个足球运动员在拦截任意球一样,“这是我辛辛苦苦挣的,我不会把它交给你的,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劫匪发出一声狂笑。“你难道不知道劫匪是干什么的吗?我们就是要拿不属于我们的钱的,被我们抢劫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名字,这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麻溜儿地把那个纸袋交给我,不然我就把你裤子扒下来,我自个儿去拿,你想要哪样儿,嗯?”他把手枪在我眼前挥动着。
就像被击败的战士一样,我在手枪的威力面前投降了。我慢慢地把手指插进裤腰带里,掏出了那个信封,它上面沾着汗水,沾着屈辱的尿臊气。那个劫匪从 我手里一把夺过去,把它打开。当他看见那沓崭新的5万卢比钞票时,他兴奋地吹了声口哨。“你他妈从哪搞来这么多钱?”他问我,“肯定是偷的。无所谓,我不在乎。”他把它丢进麻袋里:“听着,在我和我兄弟在这个车厢会合之前,你们全都待着别动。”
我呆若木鸡,眼睁睁地看着我的5000万的梦想被人抢走,被丢进一个棕色麻袋里,和那些中产阶层的手镯和钱包混在一起。
这个劫匪走向这节车厢的下一个包厢,但我们没人敢去拉火车上的紧急停车索。我们在各自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就像葬礼上的哀悼者一样。10分钟后,他背着那个扎紧袋口的麻袋回来了,右手依旧握着那把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