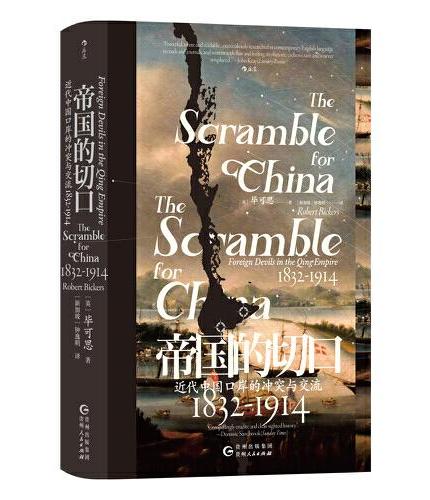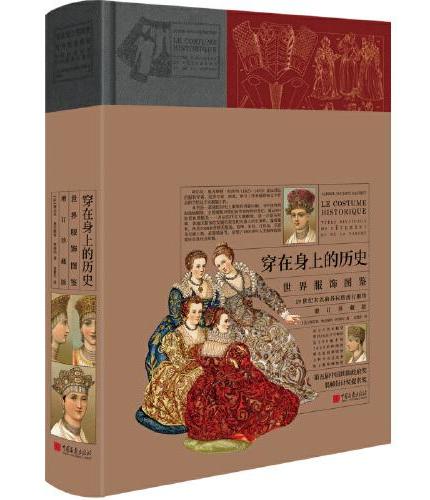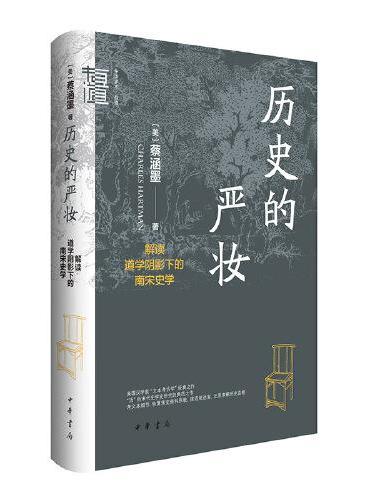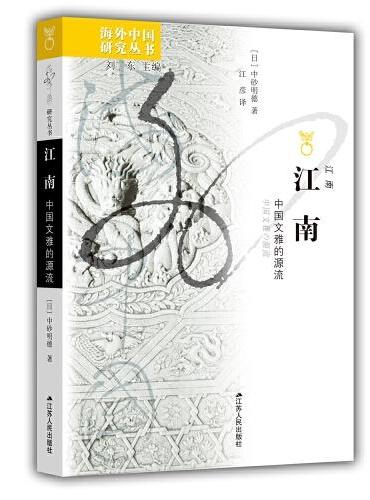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能成事的团队
》 售價:HK$
111.9
《
现代无人机鉴赏(珍藏版)
》 售價:HK$
78.2
《
汗青堂丛书·晚清风云(4册套装):帝国的切口 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 太平天国运动史 冲击与回应
》 售價:HK$
427.8
《
穿在身上的历史:世界服饰图鉴(增订珍藏版)
》 售價:HK$
557.8
《
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109.8
《
海外中国研究·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
》 售價:HK$
76.2
《
迟缓的巨人:“大而不能倒”的反思与人性化转向
》 售價:HK$
77.3
《
我们去往何方:身体、身份和个人价值
》 售價:HK$
67.0
編輯推薦:
★ 意大利国宝级文学大师,二战后欧洲最具影响力巨著,意大利中学生指定读物。
內容簡介:
“我”在都灵一个喧闹的家庭长大。父亲,一个犹太裔大学教授,脾气暴躁,经常大吼大叫;母亲,一个文艺气质的家庭主妇,总喜欢在饭桌上重复地讲那几个故事,纵容父亲的坏脾气;两个哥哥,一个是家庭的骄傲,一个总是不学好;一个姐姐,在青春期爱上普鲁斯特,忧愁地在花园里散步;一个结实强悍的女佣,总是“他”“她”不分,说话颠三倒四;来来往往的家庭的朋友,孩子们的朋友,裁缝,医生……一个熙熙攘攘的20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家庭。
關於作者:
娜塔丽亚· 金兹伯格
內容試閱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