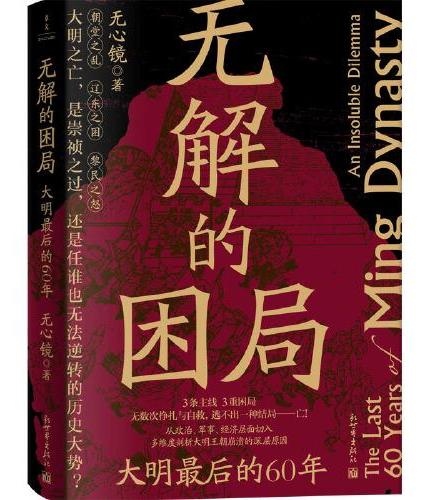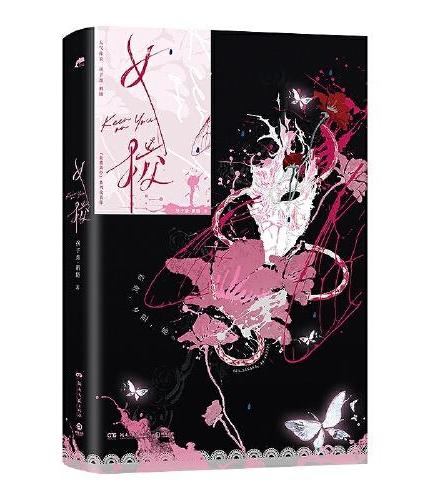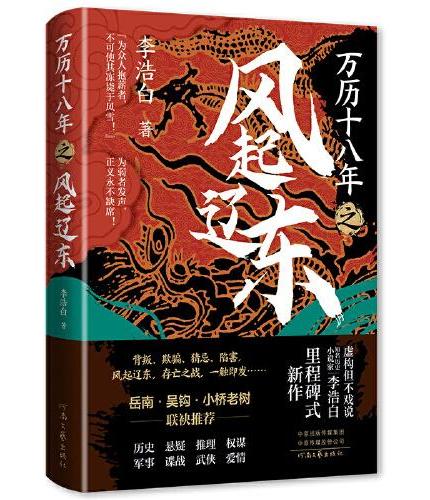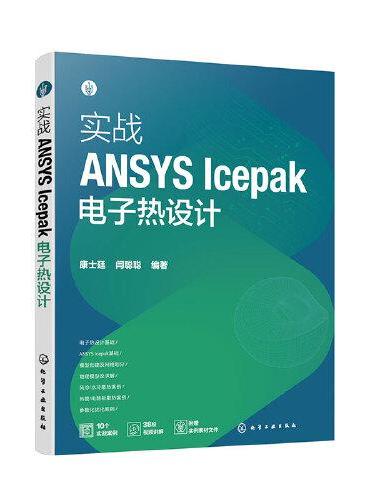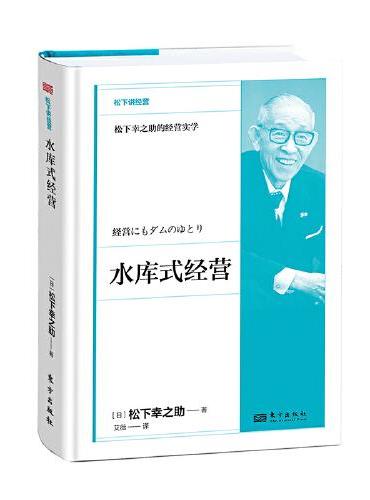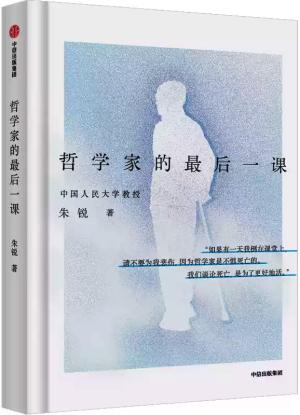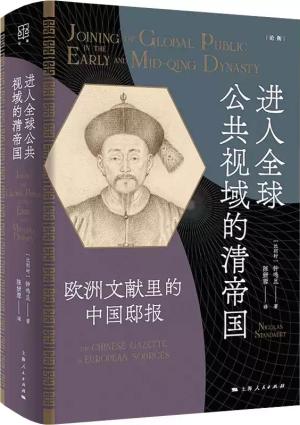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HK$
60.5
《
无解的困局:大明最后的60年
》 售價:HK$
66.0
《
女校(人气作家孩子帮·鹅随“北番高中”系列代表作!)
》 售價:HK$
60.5
《
万历十八年之风起辽东
》 售價:HK$
85.8
《
实战ANSYS Icepak电子热设计
》 售價:HK$
97.9
《
水库式经营
》 售價:HK$
61.6
《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 售價:HK$
57.8
《
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
》 售價:HK$
139.2
編輯推薦:
再访天竺 自明中土
內容簡介:
文化、权力、民族国家,是贯穿杜赞奇学术研究的关键词,他始终在探索这样的问题: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如何从历史的极权话语里找回被压抑者的声音,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来自上面的“攻击”。
關於作者:
杜赞奇,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并任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主任,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
目錄
复划符号:关帝的神话
內容試閱
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