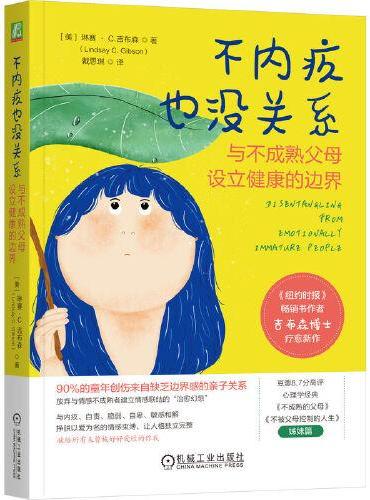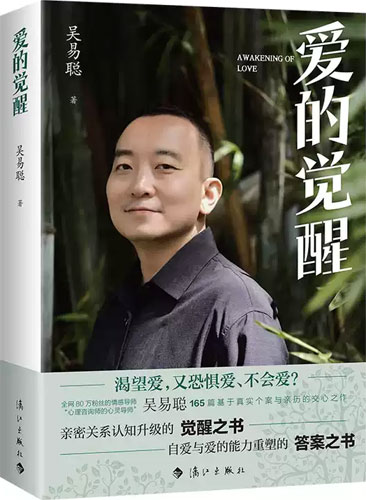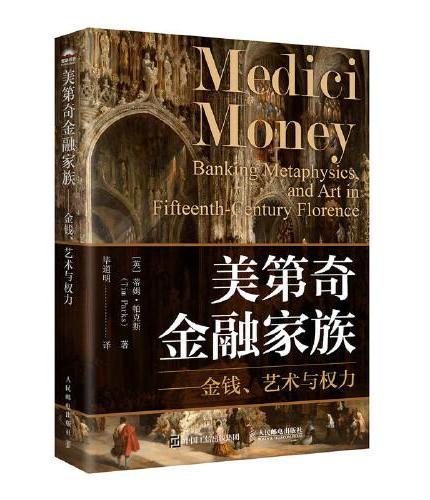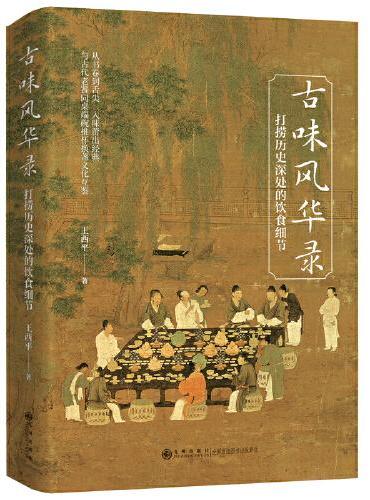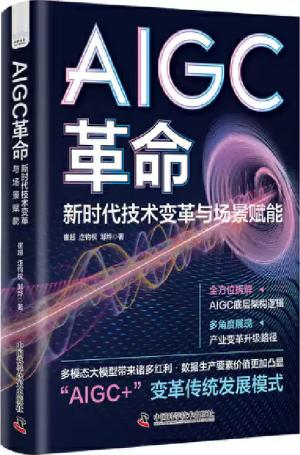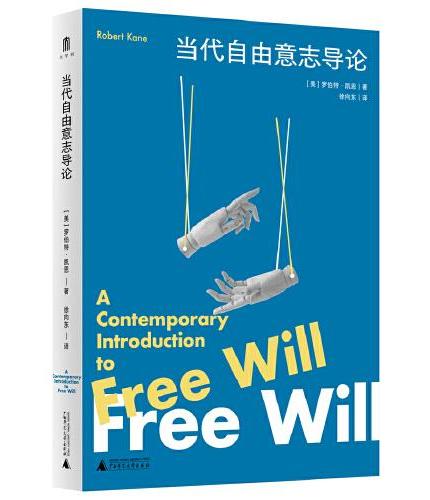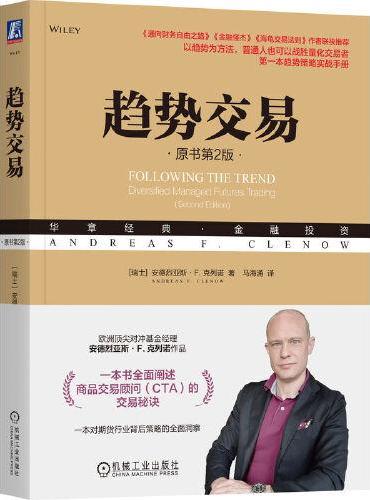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不内疚也没关系:与不成熟父母设立健康的边界
》 售價:HK$
75.9
《
爱的觉醒
》 售價:HK$
85.8
《
美第奇金融家族——金钱、艺术与权力
》 售價:HK$
65.8
《
古味风华录:打捞历史深处的饮食细节
》 售價:HK$
74.8
《
AIGC革命 :新时代技术变革与场景赋能
》 售價:HK$
75.9
《
大学问·当代自由意志导论(写给大众的通俗导读,一书读懂自由意志争论。知名学者徐向东精心翻译。)
》 售價:HK$
74.8
《
(格式塔治疗丛书)进出垃圾桶
》 售價:HK$
96.8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 售價:HK$
97.9
編輯推薦:
再访天竺 自明中土
內容簡介:
在印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印度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庶民阶层如何发挥了其自然而潜在的“政治性”作用?从《庶民研究》这一主题杂志的立意和相关研究出发,查卡拉巴提围绕上述主题,分别在本文集收录的五篇文章中展开详细论述。
關於作者:
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目錄
作为机遇的滞后:庶民历史再研究
內容試閱
后殖民与历史的诡计:谁可以为“印度”的过去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