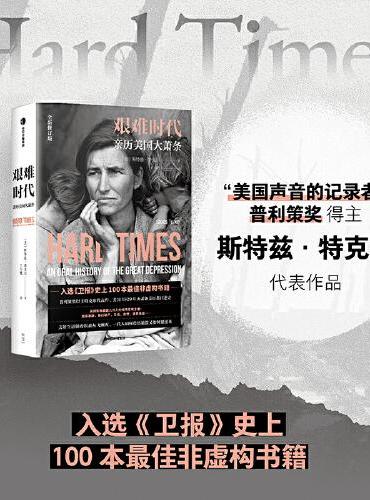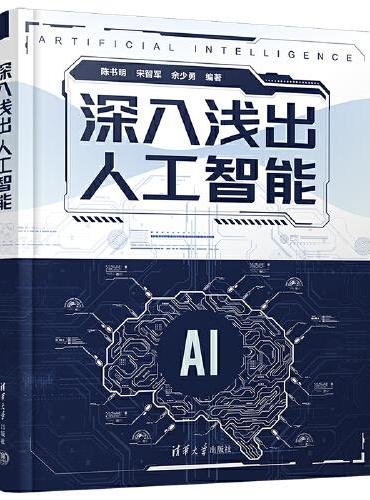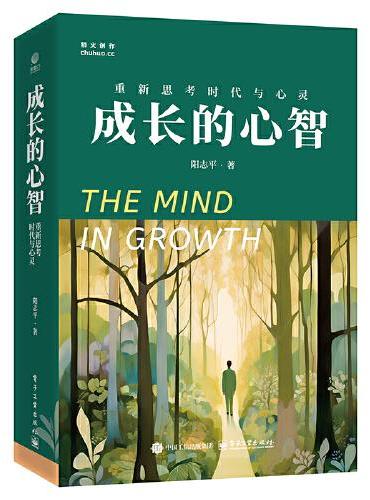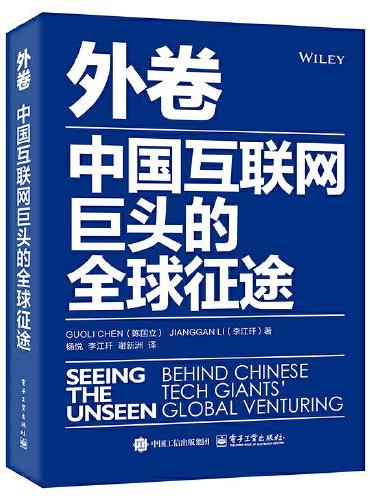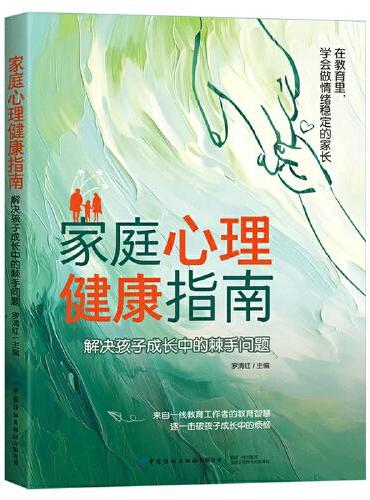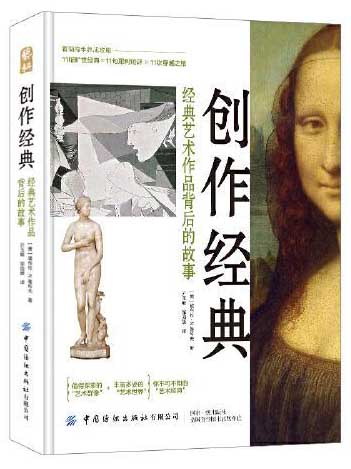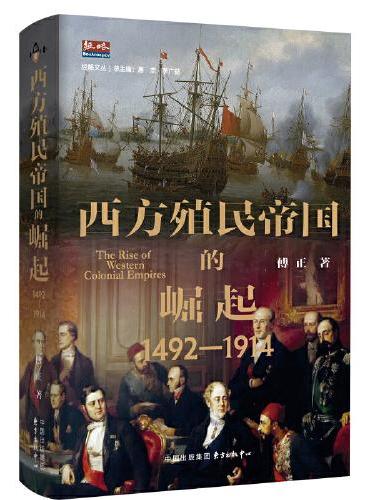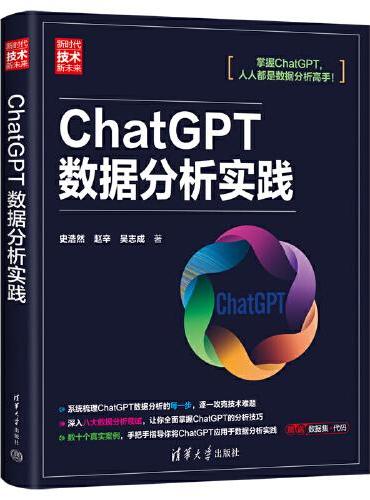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艰难时代
》 售價:HK$
96.8
《
深入浅出人工智能
》 售價:HK$
75.9
《
成长的心智——重新思考时代与心灵
》 售價:HK$
96.8
《
外卷: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全球征途
》 售價:HK$
140.8
《
家庭心理健康指南:解决孩子成长中的棘手问题
》 售價:HK$
65.8
《
创作经典
》 售價:HK$
140.8
《
西方殖民帝国的崛起(1492?1914)
》 售價:HK$
96.8
《
ChatGPT数据分析实践
》 售價:HK$
108.9
編輯推薦:
★黑塞常被人说起的是他的小说,也因小说闻名于世。但他同时也是位出色的诗人与散文家,这些散文多记录的是他对历史、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內容簡介:
黑塞的散文集,收录《漫游记》《秋日人生》,及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的自传体札记《温泉疗养客》。
關於作者: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
目錄
译者序 朝圣者之歌
內容試閱
温泉疗养客(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