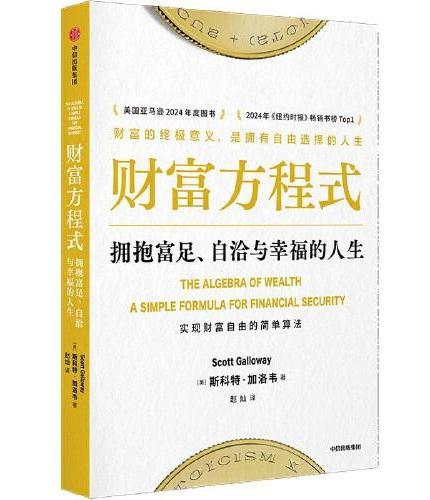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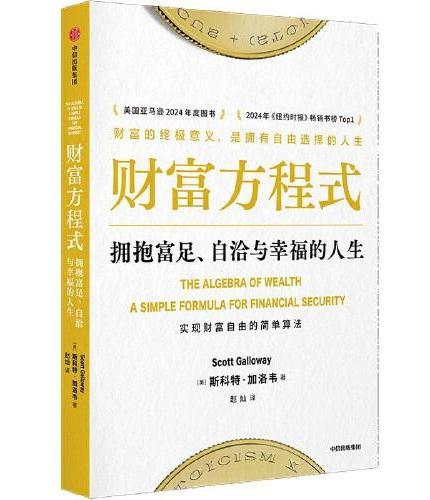
《
财富方程式
》
售價:HK$
77.3

《
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在线百科”
》
售價:HK$
99.7

《
我读巴芒:永恒的价值
》
售價:HK$
132.2

《
你漏财了:9种逆向思维算清人生这本账
》
售價:HK$
55.8

《
我们终将老去:认识生命的第二阶段(比利时的“理查德·道金斯”,一位行为生物学家的老年有用论
》
售價:HK$
91.8

《
谁是窃书之人 日本文坛新锐作家深绿野分著 无限流×悬疑×幻想小说
》
售價:HK$
55.8

《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第3版
》
售價:HK$
110.9

《
8秒按压告别疼痛
》
售價:HK$
87.4
|
| 編輯推薦: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
| 內容簡介: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
| 關於作者: |
|
雷蒙·阿隆(1905-1983),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导论》、《连锁战争》、《工业社会十八讲》、《知识分子的鸦片》、《政治研究》、《阶级斗争》等。
|
| 目錄:
|
序言
第一编 政治的神话
第一章 左派的神话
第二章 革命的神话
第三章 无产阶级的神话
论政治乐观主义
第二编 历史的偶像崇拜
第四章 圣职人员与信徒
第五章 历史的意义
第六章 必然性的幻觉
论历史的控制
第三编 知识他子的异化
第七章 知识分子及其祖国
第八章 知识分子及其意识形态
第九章 寻找一种宗教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命运
结论 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
|
| 內容試閱:
|
第一编政治的神话
第一章左派的神话
左派与右派两者之间的抉择还有意义吗?谁要提出这一问题,就立即会有可疑分子之嫌。阿兰曾如是写道:“当有人问我,左派政党与右派政党,左翼人士与右翼分子之间的鸿沟是否还具有意义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向我提出这一问题的人肯定不是一位左派分子。”我们不必因这一禁令而裹足不前,因为它暴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对以理性为基础的信念的爱慕,毋宁说是对偏见的依恋。
根据利特雷词典的说法,“左派”是“法国议会中的反对党,该党的议员坐在议长的左侧”。然而,该词所表示的意思与“反对”并非相同。各个政党会轮流上台执政,但左派政党即使执政,它依然还是左派。
在强调“左派”与“右派”这两个术语的意义时,人们并未满足于指出,在政治力量的“分布”中,围绕着一个不断受到动摇的中心,往往会形成两个彼此对立的集团。人们会提出:或者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态度是根本对立的;或者存在着两套概念,这两套概念之间的对话通过词汇翻新和制度的变化始终进行着;最后,或者存在着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充斥于数百年来的编年史当中。除了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想像之中,除了被德雷福斯事件的经验和选举社会学的颇值得怀疑的解释所滥用,这两类人、两种哲学、两种党派还存在于其他地方吗?
在自命为左派的不同群体之间,从未有过深刻的统一性。一代又一代的左派,其口号和纲领也在变化。而且,昔日为宪政而战斗的左派与当今在人民民主政体中表现出来的左派难道仍有某些共同之处吗?
怀旧的神话
法国被认为是左右对立的故乡。当“左派”、“右派”之类的术语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仍很少出现在英国的政治语言中时,它们在法国早已取得了合法身份。在法国,左派享有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温和的或保守的党派也绞尽脑汁从对手的词汇表中借取某些修饰语。人们彼此比试着谁最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
根据时下流行的看法,有两种情况使得左右之间的对立在法国显得格外严重。旧制度的统治者所遵奉的世界观是通过天主教的教育获得的,而为革命的爆发做准备的新思想则指责权威的原则,似乎后者既是教会的原则,又是王国的原则。进步党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同时与王权和教权展开斗争。进步党之所以倾向于反教权主义,乃是因为教会的等级制度有利于,或看起来有利于抵制进步的党派。在英国,宗教自由显然是发生于17世纪的大革命的原因和结果,故此,其先进的党派更多地保留的是独立派、非英国国教派、激进派等基督教派别的痕迹,而不是无神论的理性主义的痕迹。
法国在实现从旧制度到现代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中,具有一种绝无仅有的突然性和野蛮粗暴的色彩。在拉芒什海峡的另一边,宪政制度是逐渐地建立起来的,代议制亦产生于其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的习俗的议会。在18、19世纪,民主制的正统性在君主制并未完全被消除的情况下取代了它。与此同时,公民之间的平等亦逐渐地消除了等级差别。尽管英国人没有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剧烈行为挣脱锁链,但是法国大革命以急风暴雨的方式在整个欧洲大肆推广的一些观念,如主权在民、权力的行使要符合规则、议会得通过选举产生并拥有最高的权力、取消个人身份的差别等等,它们有时在英国却实现得比法国还早。在英国,“民主化”成了对立的党派的共同事业。
法国大革命,不管你认为它壮烈还是恐怖,是灾难的渊薮还是革命的史诗,它毕竟把法国的历史一分为二。法国大革命似乎建立起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法国。这两个法国,一个不甘消失,另一个则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两者均认为自己体现了一种几乎是永恒的人类社会的类型。它们一个让人想起家庭、权威和宗教,另一个则让人想到平等、理性和自由。在前一个法国中,人们尊重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秩序;而在后一个法国,人们却公开声明,他们相信人类有能力根据科学知识来重建社会。右派是尊重传统、维护特权的一派,而左派则是崇尚进步、尊重智力的一派。
这种经典的解释并没有错,但是,确切地说,它只道出了一半真相。在所有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这两种类型的人(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法国人皆属于这两类人中的一类):奥梅对本堂神甫,阿兰与饶勒斯对泰纳与莫拉斯,克列孟梭对福煦。在某些情况下,当冲突尤其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的时候(如围绕着教育法、德雷福斯事件或政教分离所发生的冲突那样),往往会形成两个阵营,而其中的每一个阵营都以公认的信条作为基础。然而,同样应当强调指出,两个阵营的理论本质上是怀旧的,它的作用是掩盖导致各所谓的阵营内部四分五裂的种种不可调和的争论。不管是各种右派,还是各种左派,他们均无法共同执政。正是这一点,构成了1789年以来法国政治史的特征。“左派”的神话只是对1789和1848年的一连串失败的虚拟性的补偿。
直至第三共和国获得巩固之前,除了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之间的几个月,19世纪的法国,左派一直扮演着反对党的角色(由此也造成了左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混淆)。左派反对复辟,因为它自认为是大革命的继承者。左派从大革命中获得了各种历史上的称号、过去的光荣的幻想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但是,尽管如此,“左派”仍如同它所仗恃的异乎寻常的事件一样,含混不清。这种怀旧式的左派只具有神话中的统一性。从1789年到1815年,左派从未有过统一性。1848年,当奥尔良王朝的垮台使共和国得以填补宪政的真空时,左派同样并不具有这种统一性。我们知道,右派也同样不是铁板一块。1815年时,君主派分裂成极端派与温和派,前者梦想复辟旧制度,而后者则接受既存事实。路易—菲利普的登基使正统派处于“在国内流亡”的境地,而路易—拿破仑的上台亦不足以使奥尔良派与正统派和好,尽管他们同样地仇视这个篡位者。
法国19世纪的内部纷争重现了使革命事件具有戏剧性特征的那些冲突。君主立宪制的失败导致了一种半议会制的君主制的出现,半议会制的君主制的失败导致了共和国的出现,而共和国则又第二度退化为实行全民表决的帝国。同样,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之间无情的争斗最后均让位于一位被加冕的将军。这些派别不仅代表着为拥有政权而你争我夺的群体,而且他们在法国政府的形式、所使用的手段以及改革的规模等问题的看法上均各执己见。希望在法国建立一种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君主主义者,仅仅是在仇视旧制度的这一点上与那些梦想在法国实现平均财产的人相一致。
在此,我们无意去探究大革命为什么会具有灾难性的过程。G。费雷罗在其晚年热衷于阐述两种革命,即建设性的革命与破坏性的革命的区别。前一种革命力图扩大代议制,并确立某些自由;而后一种革命是由正统原则的崩溃引起的,同时又缺少新的能取而代之的正统性。费雷罗的这种区分颇令人满意。建设性的革命几乎可以与我们予以好评的各种事件的结果融为一体:代议制、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与思想自由。反之,破坏性的革命则得为恐怖、战争和专制统治承担责任。人们不难设想,君主制在衰退中自身逐渐引起了在我们看来是大革命的成果的一些基本的东西。然而,鼓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严格地说,它们与君主制并非不可调和——却动摇了王权赖以存在的思想体系。它们引发了正统性的危机,而大恐慌与恐怖则又源自这种危机。不管怎样,事实是,旧制度几乎没有进行自卫就一下子崩溃了,此后法国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以寻找另一种能为大多数国人接受的政体。
从19世纪初开始,大革命的社会后果似乎是明显的、不可逆转的。人们对摧毁特权制度,对民法,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问题已不可能改变主意。但是,是选择共和国还是君主制,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民主的愿望并非仅仅与议会制度联合在一起;波拿巴主义者就是以民主观念的名义取消了政治自由的。任何一位严肃的法国作家都不会承认在那个时期的法国存在着一个具有共同愿望的统一的左派,也不会承认左派能把所有与旧法国的捍卫者斗争的大革命的继承人包括在内。进步党只是反对派的一个神话,这一神话无法与选举的实际情况吻合。
当共和国保证能够生存的时候,克雷蒙梭居然不顾历史事实,声称“共和国是一个集团”。这种主张表明左派内部过去的争论已经结束。民主制已与议会制消释前嫌,“一切权威源自人民”的原则得以确立,普选制度将有利于维护自由,而不是有利于专制君主的上台。自由派与平等派、温和派与极端派已不再有消灭对方或互相争斗的动机,因为各党各派分别提出的一些目标最后都已同时得到实现。第三共和国既是一个立宪的政体,同时又是一个民众性的政体。它通过普选制度在法律上接受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且给自己虚构出一个光荣的祖先——大革命的集团。
然而,当第三共和国的巩固结束了资产阶级左派内部的争论时,一种自巴贝夫密谋以来,也可能是自民主思想萌生以来缓慢出现的分裂突然爆发。反对资产阶级的左派继承了反对旧制度的左派。这一新的左派宣称,生产工具是公共财产,经济生活应当由国家来组织。如果说旧的左派反对的是王权的专断、特权制度或行会组织的话,那么,新旧左派的指导思想和追求的目标难道是相同的吗?
马克思主义曾经有过一种提法,这一提法既保证了新旧左派之间的连续性,又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决裂。作为紧接着第三等级而来的第四等级,无产阶级接替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曾经打碎了封建制度的锁链,把人从地方共同体、个人效忠和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个人在摆脱了传统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并得毫无防备地面对盲目的市场机制和资本家的巨大权力。无产阶级将实现解放,并重建一种人类秩序以取代自由经济的混乱状态。
是强调社会主义作为“解放者”的一面,还是作为“组织者”的一面,这得根据国家、流派和局势来定。人们时而强调它与资产阶级的决裂,时而又强调它与大革命的连续性。在德国,1914年以前,社会民主党通常装出对民主制的纯政治的价值观念不感兴趣,并公然蔑视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坚定的捍卫普选制和议会制的态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