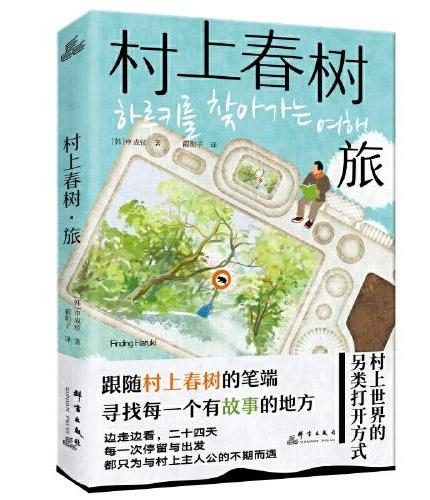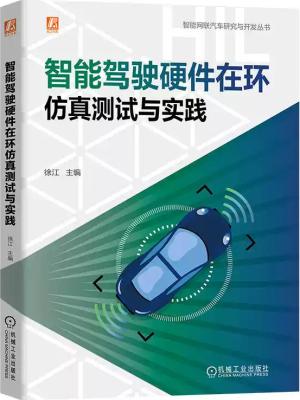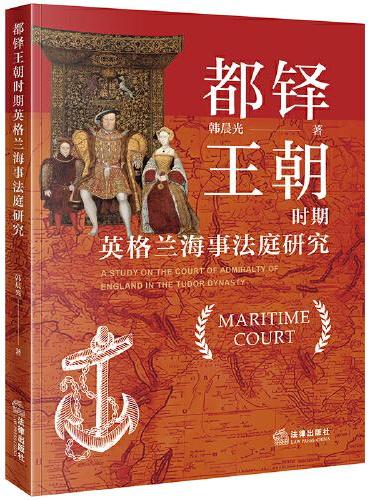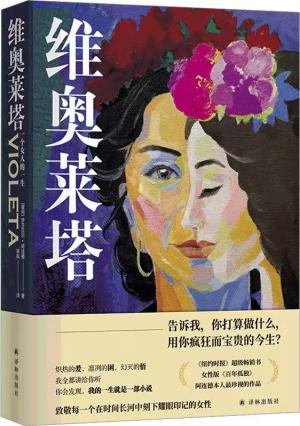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从工具到实例
》
售價:HK$
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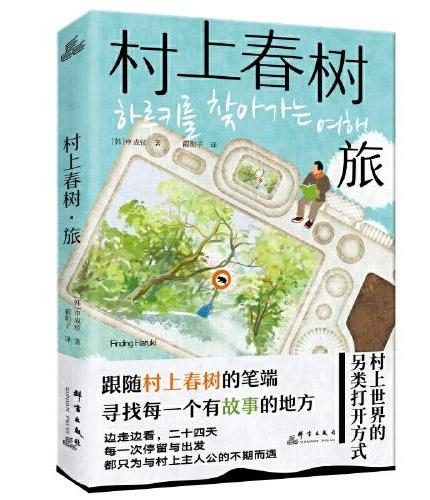
《
村上春树·旅(一本充满村上元素的旅行指南,带你寻访电影《挪威的森林》拍摄地,全彩印刷;200余幅摄影作品)
》
售價:HK$
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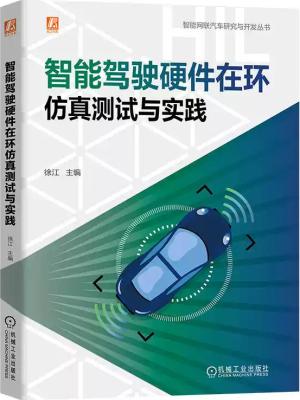
《
智能驾驶硬件在环仿真测试与实践
》
售價:HK$
1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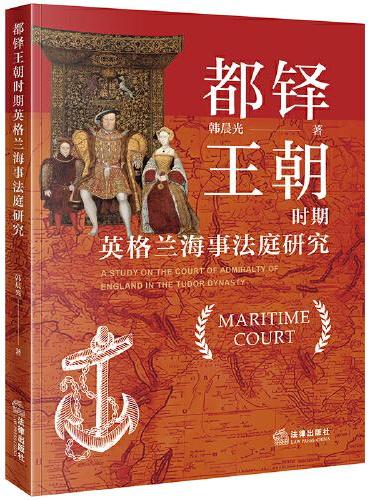
《
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海事法庭研究
》
售價:HK$
87.4

《
中年成长:突破人生瓶颈的心理自助方案
》
售價:HK$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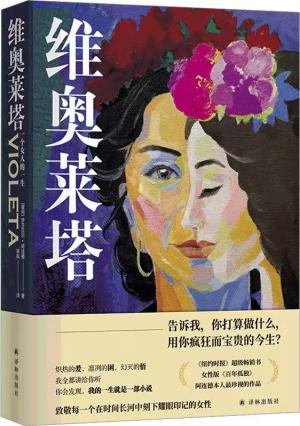
《
维奥莱塔:一个女人的一生
》
售價:HK$
76.2

《
商业银行担保管理实务全指引
》
售價:HK$
144.5

《
信风万里: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研究(全二册)
》
售價:HK$
178.1
|
| 內容簡介: |
|
本书原名《屠宰厂的潘金莲》。为当代小说作品,作者借《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外壳写了当代某小县城中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屠宰厂的种种荒唐经历,将古今两个故事串连在一起对比叙事,反映了当下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其中对原有小说中人物一反传统的颠覆性描写无疑是对现实世界有力的反讽。
|
| 關於作者: |
|
房伟,1976年生人。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作协会员,山东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艺术学院特聘研究员,山东当代文学学会理事,曾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诗刊》、《山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及诗歌、小说计120万余字,曾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小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著有《批评的表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屠刀下的花季》(济南出版社)、《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三联书店)等,获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铜奖,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曾任山东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室副主任,现执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该小说为作者长篇小说处女作。
|
| 內容試閱:
|
一
十几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我大学毕业,去一家大型肉类食品厂工作,一直到几年后离开那里。我们厂规模很大,占地近百亩,就横亘在城乡结合部的一块地方。那里的天总是灰蒙蒙的,我们高大的厂房也是灰色的。下雨的时候,从远处看去,食品厂就像一个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庄严、肃穆,充满了神秘的气息。它有两扇特制的大铁门,送活猪活牛的车队浩浩荡荡地从门里开进来,又浩浩荡荡地把变成火腿、烤肠等肉制品送出去。我不干活儿的时候,常蹲在门口看那些车出出进进。在我的想象中,这些车都是些英俊的高头大马,神情高傲突兀,披着厚厚的黑色马甲,只露出两个马眼看清楚敌人和前方的路。有时候,这些马带着骑士们出城,我就是欢送他们的号手,为他们吹响满怀信心的出征号角。有时候,这些马上都是些掠夺归来的骑士,马背上是别人领地的猪牛羊和漂亮女人。骑士们一只手拉着缰绳,另一只手抓住猎物放在马鞍上。女人们被捆得很精致,她们惊恐而疲惫地环视着四周,姣好的面孔紧贴在骑士们沾满血迹的冷冰铠甲上。骑士们都保持着风度,虽然他们很疲倦,有的还被砍成牛排般血淋淋的模样,但他们还是郑重地放下黑色面罩,扶正头盔,整理好帽缨,绝不会像那些不成器的强盗一样大喊大叫,而是有次序地排好队,在领主的带领下举行进城仪式。而我或许就是一个城堡中受领主庇护的小农奴,眼睛红肿,头发蓬乱,身上还沾着昨夜喂马时留下的燕麦,一副可怜兮兮穷小子的样子。我满怀崇敬地守在城堡门口,双手举向天空,向勇敢的骑士们欢呼,并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他们。其实,最令我眼馋的还是那些马背上的女人,那些女人无意裸露出的酥胸和粉白的大腿,都让我心神荡漾……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想象。一般说来,我的空闲很少,而厂里只有过年过节,才会有大规模的车队出入。大部分的时间,我或是推着一辆挂满香肠的货车,表情庄重,行动有力,仿佛推动着一车进贡给皇上的珠宝;或是推着一辆空无乘货的钢架车,纤徐地绕着厂子那灰白的水泥地走过。车声辘辘,轻盈而洒脱,洒在空旷的地面,如同一朵肉粉色的小花,飘落在苍凉的食品厂大地。通常,我需要从后门的冷藏库走到前门的分割间,再把分割好的肉推到食品加工车间,或者是把做好的香肠挂在车上,从加工车间推到包装车间。所以,能有闲暇蹲在门口看车来车往,实在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我蹲的姿势很古怪,几乎就要坐到地上了,屁股和地面的距离就差横放一条小火腿肠的宽度,本来就粗短的脖子几乎缩到了胸腔里,而我的眼神却变幻莫测、充满着神奇的光。在外人的眼里,这个穿着工装,傻傻地蹲在门口的家伙,神经似乎有些问题。可他们哪里知道,在这个热火朝天的现代化肉食品厂,我的精神已经进入了一个中世纪燕麦小子的冥想状态,那里有我的城堡,我的骑士,我的贵妇,我的骏马,我的梦。在我混乱不堪的想象中,燕麦小子跑到中国,变成了武松,最终成长为英雄,并独自打死了一头猛虎……
这种冥想状态的结束,常归于两种情况,一种是仿佛晴空霹雳般的粗暴女声:“刘建民!你这个孬种!怎么干活比我们女人还会偷奸耍滑!”随着这美丽的吼叫,一条仿佛孙二娘似的粗壮身影在“移步换形大法”之中,快如闪电一般出现在我的面前。看到这种情形,我会马上苦笑一下,勾着头站起来,乖乖地跟着她回车间干活,丝毫不敢有逃走的念头。她是我们分割车间的头领之一,闺名唤做胡美丽,名义上为分割三组组长,手下有刀手三十名,也是名震我们食品厂的“四大刀客”之首。该婆娘是本地人氏,原为临时工,后因工作勤奋,得以转正,成为食品厂的正式工。胡氏生得眼似钢铃,头如麦斗,声似炸雷,嘴唇边有一圈黑短汗毛,干起活来不知疲倦,被我们分割车间戏称为“女版李逵”,或曰“升级版孙二娘”。但胡头领不让我们这样称呼她,甚至只要听到“李逵”、“二娘”,或者“逵”、“娘”这样的字眼,都会暴走发飙,好似一个喜欢文字避讳的帝王(当然,“头领”也不行)。她最喜欢的就是别人叫她“小胡”,或“胡小妹”,每当听到别人这样称呼她,她总是妩媚地回过头,粗声说:“谁在叫人家呀?”让人不寒而栗。
如果运气好,胡美丽小姐正在勤奋地分割着一头猪,没闲暇工夫理会我,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时空的可能性,那是一个古朴苍凉的声音:“小刘哇,跟某家杀上一盘去!”接着,一个胖大的身影,飘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打断了我的白日梦。我讪讪地看了该老者一眼,说,高大爷,我忙着呢,不行咱们改天再下棋?而那个胖胖的高大爷,却不依不饶,继续对我拉拉扯扯,直到把我拽到门卫的小房里为止。门卫原来由退伍兵组成的治安小队负责。他们每天早上在厂篮球场上穿着迷彩服练擒敌拳。这些曾经的正规军,脱离了部队的教育,顽强勇猛的作风,现在只剩下了装模作样,以勾引食品厂的女工。后来,在保卫科的安排下,他们和厂里的未婚青年组成护厂队,天天晚上巡逻。再后来,食品厂的效益越来越差,工资发得也不及时了,这些人就慢慢散去。有的给有钱人当保镖,还有的进了黑社会。退伍兵走后,我们厂的门岗就施行轮班制,有时就是那个60多岁的独眼老头高大爷。高大爷,胖手胖脸,秃头长胡子,自称是解放前国民党某少将的弟弟,看来当年也是一条好汉,而后来和我下棋老耍赖,丝毫没有什么英雄气概,他经常在门岗上坐着椅子晒太阳、打呼噜,哈喇子流到了胸前。有时,高大爷有事,门岗上就是一个怀孕妇女,也坐在椅子上晒太阳、打呼噜,不过也偶尔织个毛衣什么的。
到了中午,大门口才开始热闹起来,三三两两的工人从这个大门走出去。在我的记忆中,它不是黑色的,而是红褐色的,因为上面长满铁锈;它也不灵活,而是笨重的,推开和关闭,都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到了饭点,厂里的广播室还会播放一些音乐,比如香港四大天王的歌曲。伴随着这些咿咿呀呀的歌,我夹着一个饭盒,拖拖拉拉地走向食堂。我去食堂打饭,总要穿过篮球场。当企业效益还好的时候,午饭前,一些大学生就和穿红背心的保卫们抓紧时间热热身。他们有些人并不会打篮球,特别是那些退伍兵。他们简直将篮球当成了大号的飞镖,“嗖嗖”地在前场和后场乱丢,可就是放不进篮筐。大学生们好一点儿,好歹还会个三步上篮、勾手什么的,就这几招已把那几个身强体壮的退伍兵搞得像熊瞎子一般团团转。我经过操场,经常被他们其中一个抓住。我在学校挺喜欢打篮球,技术还不错。可是我不喜欢和这帮人打球。我提不起兴致。那帮学生中有人知道我投篮很准,就起哄让我投几个。我本不想投,可总有一个浑身腱子肉的小个子湖南籍退伍兵向我挑战。这小子打球时嘴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个没进化好的猩猩。我们都有点儿怕他。他通常也不说话,只是抓起球,向我手中一塞,然后用倔犟又愚蠢的目光看着我。我无奈,只好投上几个三分,然后在一片喝彩声中,懒洋洋地看着那个退伍兵撅着屁股做俯卧撑。那个退伍兵的屁股很结实,又很紧凑,如果我是同性恋,一定会心动,热泪涟涟地爱上他。可是,我不是同性恋,就残忍地看着退伍兵喘着粗气做俯卧撑。我那时还年轻,刚刚走出某名牌工科院校的大门,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正是不知忧愁的年龄。我整日浑浑噩噩,游手好闲,从没有为将来打算,甚至有一点儿安心做一辈子劳动人民的想法。而这种想法,一直到我遇见王梅,才发生了改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