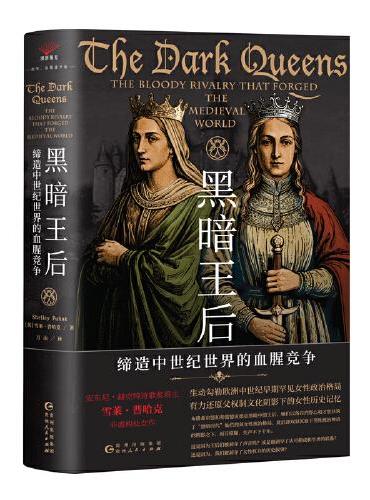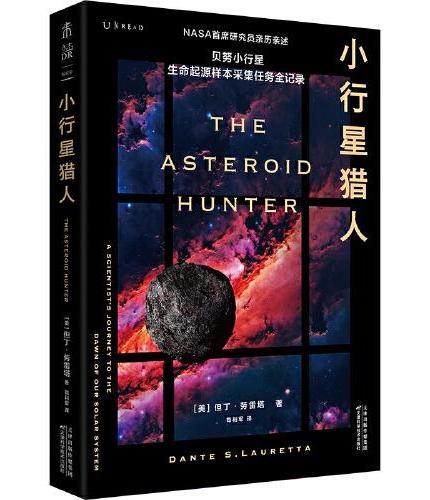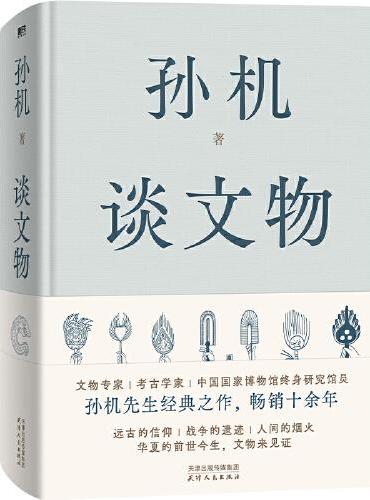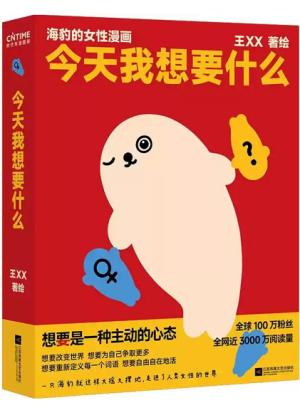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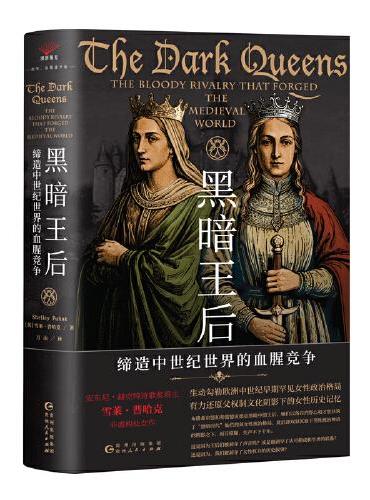
《
黑暗王后:缔造中世纪世界的血腥竞争
》
售價:HK$
1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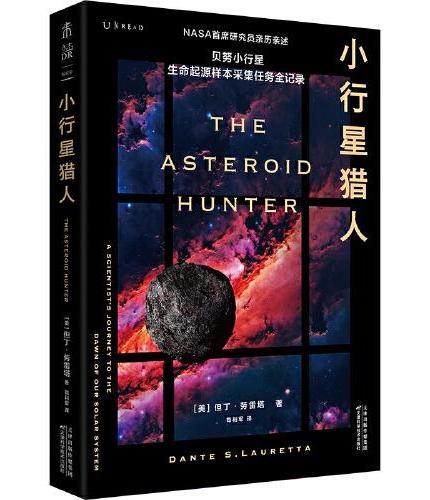
《
小行星猎人:贝努小行星生命起源样本采集任务全记录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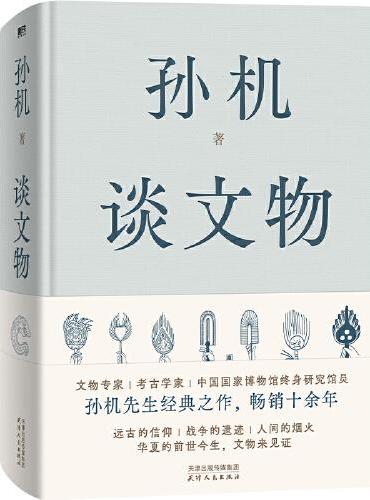
《
孙机谈文物
》
售價:HK$
118.8

《
诡舍(夜来风雨声悬疑幻想震撼之作)
》
售價:HK$
54.8

《
讲给青少年的人工智能
》
售價:HK$
52.8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107.8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HK$
3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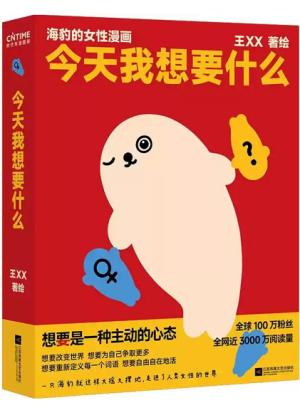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中国国家地理》是最具文化气质和历史厚度的地理读物,以其具有卓尔不群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气质,被中国“驴友”奉为“旅行圣经”。
《中国国家地理》的执行总编单之蔷
百万级畅销书《风声》《风语》的作者麦家
新浪5000万人气旅游博主风同学
——联袂推荐
随波逐流的浏览毕竟浮浅,深沉细致的行走才显雍容。
万千浮夸的脚步背后,还有聂作平,带你领略真正的中国,带你领略大地深沉的细节——历史的千般模样,风物的万种风情,陌生人群的新鲜故事,旧物新缘的深情交汇,边城远地的无限旖旎……
慢下来,用心行走,途经美好的遇见,途经盛放的钟情……
|
| 內容簡介: |
秉承《中国国家地理》的雍容大气,彰显人文中国的壮丽深沉。
《中国国家地理》“十周年文章贡献奖”得主聂作平,用文字引领你,一起领略大地的细节,一起一路钟情。
全分为名川秀水、雄山奇峰、旧物新缘、古迹重寻、优雅之旅、边城风光六个部分,讲述了聂作平10年以来游历祖国山河大地的钟情之旅。聂作平在钟情的路上,横跨古今,纵览历史,于祖国之风光,既能从大处欣赏其雄奇壮丽,又能从小处领略其优雅灵秀;既能从古迹中挖掘出尘封故事,又能从新城中发现些生活奇趣……
领略大地细节之美,自然一路钟情!
|
| 關於作者: |
|
聂作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资深撰稿人,2008年《中国国家地理》改版10周年之际,与马丽华、王旭峰、范晓等人同获“中国国家地理10周年文章贡献奖”。已出版作品30余部,主要有《历史的B面》《1644:帝国的疼痛》《天朝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等。部分作品被译为外文。
|
| 目錄:
|
名川秀水
呼伦湖:北方第一大泽
逝者如斯:一条河的灿烂与落寞
图们江:一水两岸三邻邦
黑龙江:从内河到界河
雄山奇峰
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河南
横山,隐者的高地
盘旋在云端的隐秘通道
旧物新缘
追寻杨贵妃的荔枝
洋浦盐田:阳光与海水的千古传奇
构皮纸:唐朝工艺的时尚再生
干窑:京砖是这样炼成的
腌菜:弥漫中国的古老滋味
冬虫夏草:一只昆虫创造的奇迹
古迹重寻
大中国的海上走廊
江,生者对死者的访问
湖州:丝绸之路零公里
蜀道:那条深入四川血脉的路
锡林郭勒,从皇家牧场到肉篮子
优雅之旅
成都:优雅的市井
建水:追忆似水年华
故乡赵化古镇的几个片断
莫干山:中国第一度假地
三多寨:细雨中的梨花古堡
时光之上的华安土楼
边地风光
漠河,北极光下的边城
呼中:落叶松抒写的秋色赋
遮蔽的福地
玉树:离唐朝最近的地方
一个石渠,两个关键词
|
| 內容試閱:
|
成都:优雅的市井
如果成都距离汶川再远一些;如果成都所处的扬子地块不和活动频繁的龙门山板块比邻;或者,再干脆一点,如果“5?12大地震”推迟50年;那么,至少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们将缺少一个更加精准地认识成都的机会。但这些如果都只是事后的假设,事实上是,成都距离汶川实在太近,近到只有几十公里;而成都所处的扬子地块和龙门山板块,它们已经做了亿万年邻居;而天崩地裂的“5?12大地震”,它选择了2008年这个微风吹拂的初夏。
如同登临平原尽头的山峰眺望这片熟悉的土地——当薄雾轻轻散去,平原上那些绿树环绕的村庄和溪流,就小心翼翼地浮现在大地深处。当时间开始慢慢医治大地震带来的创伤,成都的生活在继续——和以往不同的是,人们更加认识到这样一种客观存在:这座距离震中最近的大都市,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它的生活依然生动而鲜活。
我以为,成都生活的特质是市井,倘若要给市井加个定语,那就是:优雅。
宽巷子:历史深处的人间气息
慵懒的雨水有气无力地打在梧桐上,间或有风,摇动着梧桐树下那盆孤苦无依的雏菊。一张古旧的茶几,上面摆着一只青瓷茶碗,茶碗里,热气袅袅。远景则是悠长寂寞的老巷,两侧的房屋,高耸着飞檐和风火墙,院落深深。在街的那一头,一条大黄狗吐出长长的舌头,忧郁地看着越来越密集的雨,两个窃窃私语的老人,他们的两颗头碰到一起,那些铺天盖地的白发,比一个世纪还要惊心——这是我记忆中的宽巷子景象。或者说,每当想起宽巷子,我的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一幅已然过去了好些年的画面。
尽管人们常爱说成都几千年城名未变,城址未变,但可怜得紧,成都其实已经很难找到哪怕一百年以上的成片建筑了。动荡的世事和功利的商业正在给传统一记记劈头盖脸的重拳,它把先人的遗留更改得面目全非。幸运的是,宽巷子——宽巷子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地名,它往往还包括与它比邻的窄巷子和井巷子——则是不可多得的老建筑。具体地说,它们都是曾经的少城的残留。少城是清代的满城,那是作为清朝统治民族的满人的聚居地。
如果从空中俯瞰少城,它的主要街道布局极像一条巨大的蜈蚣:将军衙门是蜈蚣头,长顺街是蜈蚣身子,东西向密集的街道和胡同则如同蜈蚣身上众多的脚。这是一条精美典雅的蜈蚣。自从满清覆亡,越来越多的权贵和有钱人进入了这座原本不许汉人居住的城中之城,一座接一座的公馆拔地而起。那时候,高大的黄桷和银杏遮掩的街道两旁,不时有高大威严的石狮怒目而视,不用说,石狮身后一定是一座气派的公馆。
正像我从前在一篇短文里说过的那样,这样的公馆往往会有一些相同的细节:总是有青砖砌成的围墙,墙头牵延着金银花或是爬山虎之类的植物丝蔓,若是春夏,一些淡淡的小花便漫不经心地开在墙头,让墙外行人也有机会领略什么叫做“满园春色关不住”。若是经过后花园外的幽深小巷,或许还能听到从里面传来的女子的娇笑,让人想起“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宋词。
世事变幻如同白云苍狗,很多年过去了,那些公馆大多被拆被毁,惟独宽巷子里那些朴实的普通民居还留存了下来。虽然风火墙已经破败,旧梧桐已经衰老。但身处成都市最中心地区的宽巷子,还保存了几分老成都的市井姿态。就在不久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这几条宽不盈丈的小街,集合了众多“最成都”的茶馆、旅店和小吃,节奏缓慢的宽巷子仿佛被时代故意遗忘,下午到宽巷子喝茶便成为一种写意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我常去的那家小茶馆,迎街的老墙上,挂着一帧格瓦拉的黑白肖像,很多人都不清楚这个遥远的古巴人和成都这条破落小街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清楚。我只是坐在他的目光下喝茶,谈天,或者有一眼无一眼地看闲书。更多时候,我愿意把目光送给那些从街上款款走过的女子。至于龙堂,那是宽巷子里一个著名的去处。那里,常常聚合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的一个同窗来成都,五星级宾馆不住,偏偏指名去龙堂。其实,龙堂的设施很普通,普通到粗糙。当然,我知道,这位同窗看中的是那份潜藏在深巷中的古意与质朴,那是一种离成都民间最近的稀有之物。
无疑,宽巷子那些古旧门宅里的生活是细屑的,琐碎的。但正如历史记录看起来平淡如水的年代才是幸福年代一样,真正的幸福生活也一定是细屑的,琐碎的。
后来,宽巷子就因地处市中心而面临拆迁的危险。好在,主事者最终没有把这片有历史有生命的老建筑拆掉,另建一些冰冷的水泥盒子,而是把它改造成了如今的宽巷子——大地震之后刚刚一个月,当许多地方还处在草木皆兵的余震中时,宽巷子就紧锣密鼓地开街了。
那天有雨,我没去看热闹。不过,从电视上看,来来往往的人流,把那几条小小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我选择了另一个夏夜前往宽巷子,曾经有过的那家小茶铺不见了,更多的,是时尚的酒吧和咖啡馆。在恋旧的人看来,这未免是一种遗憾,但我却从那些怡然漂浮于店堂深处的脸上感觉得到,其实,生活更需要的是一份淡定与悠闲,至于这份淡定与悠闲,到底是用小茶铺的青花茶碗还是用咖啡馆的咖啡杯来表达,那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既然天底下最忙碌的小蚂蚁,也总是有时间参加每一次野餐,那么,到宽巷子喝一杯茶,饮一瓶酒,品一壶咖啡,都是人生这篇漫长文章中必需的几个小逗号。
生活像美女,就是用来泡的
我的朋友何小竹写过一本关于成都茶馆的书,书的名字就叫《成都茶馆》。我还记得,我和何小竹最初的几次见面,其中有至少两次,都是在一座茶馆里不期而遇。那座茶馆位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在一个叫大慈寺的古老庙宇里。外面是肃穆的红墙和森严的大门,但只要穿过了那几间面容严谨的大殿,你就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春夏时分,头上是密密麻麻的葡萄架,下面是石头方桌,间或还有几棵开着黄色小花的桂树。方桌四面,随意排放着最多只值10块钱一把的竹椅子,屁股刚挪上去,椅子就会吱吱呀呀地唱歌。茶是花茶,全都用流行于四川民间已经几百年的茶碗盛装,送茶的伙计一盏接一盏地甩到桌子上。茶客们就坐在随时可能飘落下一片葡萄叶、一阵蝉鸣声或是一颗鸟粪蛋的园子里,消磨着似乎永远也消磨不完的光阴。
即便走遍全世界,你也难以找到第二个城市,拥有成都这么多茶馆。以前的一个统计数据说,仅仅三环路以内的不到100平方公里的主城区,就有大大小小几千家茶馆。这些茶馆,高中低各个档次都有,它们与荡漾着民间呼吸的居民区和威严矜持的政府衙门,以及熙来攘往的商业场所相生共处,就像一支交响曲的各个乐章,必须有起承转合才能和谐动听。
何小竹在《成都茶馆》里说,朋友们去找杨黎,就是把他从楼上喊下来,到附近的茶馆里泡上半天。对成都人而言,茶馆很多时候具备了客厅的功能。朋友,甚至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见面,首选一般都是茶馆。成都人似乎特别喜欢茶馆的那种喧哗与热闹,一个例证是,生意越是火爆的茶馆,它的客人往往也越多,而那些冷清的茶馆,生意会越来越冷清。说到底,我有点搞不明白的是,到底是成都的悠闲生活催生了遍地茶馆,还是遍地茶馆催生了成都的悠闲生活?曾经有沿海的朋友对成都这种以茶馆为核心的散漫颇为不解,我就给他讲那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大企业家到海边晒太阳度假,遇到一个当地的穷小子也在那儿晒太阳。大企业家就教育穷小子,你为什么不去努力工作,挣更多的钱,开很多公司?穷小子反问,做了这些,接下来干什么?大企业家说,那时,你就可以像我现在一样,到海边晒太阳度假。穷小子笑了笑说,我现在不已经在晒太阳度假了吗?
除了客厅功能,成都茶馆也是不少人的工作场所。尽管茶馆的近亲——比如咖啡馆,在成都也渐有燎原之势,提着笔记本到咖啡馆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到茶馆工作的人也没有减少的势头。于我,我的许多文章——包括您正在读的这一篇,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因此,成都本土或从成都走出去的文化人,他们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写到给他们的生活打下了深重烙印的茶馆,从李人到巴金,从沙汀到流沙河,概莫能外。
在家里泡一壶茶,那叫解渴;到茶馆要一杯茶,那才叫生活。成都人在说到茶馆时,爱用一个词,叫做泡茶馆。一杯茶,坐上那么几个时辰,这就叫泡,否则只是牛饮。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和生活都像美女,都是用来泡的。
神经般遍布全城的茶馆,它对成都人性格的影响无疑潜移默化,它使这座城市的人健谈、风趣、和善,同时也带有程度不同的狡黠。当然,更本质的可能是,这种缓慢的节奏,使他们对生活总是抱有常人难以理解的通达和乐观。
必须说到近几年声名在外的几家很文化的茶馆,比如悦来茶馆。我以为,它们已经从原初的那种属于市民阶层的悠闲与淡定,被商业化成了供外地人观看的模具,它与真正意义上的老成都茶馆和老成都生活方式已经产生了遥远的距离,就好比一朵精致完美的塑料花和一朵被风雨吹打得有点憔悴的野花之间的距离。因此,最成都的茶馆其实不需要那种业已沦为江湖杂耍的变脸或吐火之类的表演,它只需要清清的茶和闲闲的心。以我为例,我常去的是一家叫柳浪湾的茶馆,巨大的落地窗户铺向府南河,垂柳的垂发一直垂到茶桌旁,庭院里,树木荫郁,小鸟闲鸣。别人打牌,我打字——无论打牌还是打字,一旦搬进同一座茶馆,生活的面容都同样亲切得一塌糊涂。
那些为滋味折腰的文化人
很多年前,具体地说是1600年前的晋朝,一个叫常璩的四川崇州人,写过一本叫《华阳国志》的地理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给四川人把了脉,认为“蜀人好辛香,尚滋味”。转瞬之间,1600年,差不多也就是60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天地玄黄,巨变沧桑,但四川人对于好滋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却一点儿也没变。
诸种菜系之中,与粤菜、鲁菜、淮扬菜相比,川菜是最草根的,它所采用的原材料,几乎没有特别贵重之物。但与此同时,川菜也是最民间的和最具生长性的——有多少悲伤的胃,因为远离了故乡,从此就把对川菜的怀念当成对故国的追思呢?
在成都,有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尽管川菜很底层、很草根,但与其他菜系相比,川菜可能也是与文化人关系最亲密的。年代久远一些的,像杨慎、曾懿、李调元、傅崇榘等,他们都有与饮食相关的著作。至于“老成都”李人,他既是一个因多种原因一直没得到真正认可的大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川菜美食家和精明的餐馆经营者。上世纪40年代,他在成都开办的小雅曾经名噪一时,入川的大多数文化名人都是其座上客。甚至,像闹革命的车耀先烈士,也开过一家叫努力餐的川菜馆。直到今天,这家已有70多年历史的餐馆仍然在营业,仍然在把那些叫回锅肉,叫鱼香肉丝,叫糖醋鱼的家常滋味整治得风生水起。
可能正是潜藏了这种君子近庖厨的传统,在当代,成都仍然是文化人涉猎餐饮业最频繁的城市。
李亚伟是著名的莽汉派诗人代表,想当年,他以一首《中文系》震动诗坛时,不过20多岁。后来,李亚伟漂流北京,做了独立出版人,出版过不少精彩的或者不那么精彩的书。在做出版人的同时,圈子里的朋友都知道,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位于华西医院背后的香积厨的老板。那是一个有池塘、假山和小树林的所在,经营菜品以川东菜为主。前来这里的客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成都或外地的诗人、艺术家。如果把这些人的名字排列出来,很可能就是一部诗坛加艺坛点将录。
现在,李亚伟的香积厨已然化蛹为蝶——从居民小区的包围圈中撤退到修葺一新的宽巷子。仿古的院落里,立着一些竹子和石头水缸,所有的窗户似乎都通向古意盎然的旧社会。没人的时候,你极疑心从那扇古色古香的木门之后,就会走出一个名唤翠娥的丫头,彬彬有礼地对你道一个万福,用黄鹂的声音说,“公子,请到堂上用膳。”
大概是为了和这份古意相吻合,李亚伟说他的香积厨主要经营古代的菜。什么是古代的菜呢?就是古人爱吃的菜。他那几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大师傅,他们的拿手好菜,都是从袁枚老师的《随园食单》里偷师学艺来的。最近一次去香积厨,是一个有月光的晚上。夜已深,偌大的庭院里还有几个人在喝酒,房顶高耸,如同受惊的猫的脊背,月光就从上面跌下来,摔得满院子都是。如果台湾那个姓林的作家在这里,一定会嚷着要温一壶月光下酒。然而我以为,与其温月光,还不如炒几个古代的菜下酒更“成都”。
与李亚伟多年来钟情餐饮,甚至最后关了文化公司,一心一意经营香积厨不同,早年也写诗的杨路,其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某文化公司老总。不过,一不小心,他也经营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小众的,甚至可以说是私密的。它有一个很牛叉的名字,叫木星16。木星16大概是成都最高的餐馆了,它高高在上,从它的窗口,可以俯瞰小半个成都南城。当你写意地举起酒杯,不经意地往窗外一瞥,下面是绿的树,细的街,以及蚁群般的人流,那种奇妙的感觉,也许就是“欲知酒中意,勿与醒者言”了。
木星16很小,小到只有四间屋,两张桌子。“小的是美好的”,这句话本是著名的舒马赫说的,杨路把它奉做设计木星16的座右铭。果然,那些精致入微的细节,具体、生动,却又透出一种低调的品质,就像杨路强调的那样:“要像装修书房一样装修厨房。”现在你也许明白了,在一个装修得像书房一样的地方喝酒,那酒才能叫做小酒,也就是从前那个叫白乐天的家伙写给好哥们儿刘禹锡的诗里表述过的意境:“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李亚伟的香积厨和杨路的木星16之外,成都文人开办的餐饮,众所周知的至少还有翟永明的白夜——它是一个酒吧,已经有10年历史,不少外地人到了成都,如果是文青的话,多半会一路嗅着酒香而去。石光华的上席——石光华是写诗的,后来写川菜,再后来就开始经营餐馆了。他的搭档,是来自凉山的诗人吉木狼格,他有能力在酒后唱一支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歌。刘承志的味典——这是一家经营四川小吃的特色餐馆,刘承志同时也是成都最著名的贩卖古老的商业街锦里的操刀者。
四川文人的老祖宗司马相如先生和他的女朋友卓文君小姐,也曾经干过开酒店的勾当。当然,据说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丢卓文君小姐的爹的脸,以便迫使老人家承认他们那桩始于以琴调情的私奔。当代四川文化人经营餐饮当然不在此例,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一群为滋味折腰的人。为了曼妙的滋味,他们不惜一折腰,再折腰,三折腰,当他们的腰折得像虾子时,他们仍然是一些面带微笑的虾子。无疑,这些散布在街坊之间的文人餐饮,除了提供具体的吃喝之外,还提供了一种情调,那就是让这座城市到处都弥漫着商业时代罕见的文人气。
埋伏在民间的艺术群落
有过下厨经验的人都知道,川菜里,花椒是绝不可少的重要调料。必须有,但又不能多。因为它只是调料,是用来提味的,分量要恰到好处。少了,起不到提味的作用,多了,喧宾夺主。显然,这么说,我并不是要介绍烹调经验,而是仅仅想借用这一烹调经验来说明一个浅显的道理:对于成都,对于这座市井味十足的城市,如果没有艺术这种花椒来为它提味,那它就与我所界定的“优雅的市井”八杆子打不着,就只是一座只有物质没有精神的空心城市。幸好,“花椒”给成都这道地道的川菜提了味,这花椒,就是那些埋伏在民间的艺术群落。
鹿野苑这个名字听上去充满中国古典的诗情画意,事实上却是从梵语转译的。因此,通往鹿野苑的路才那么曲折通幽,如果是春天的话,你得穿过几千亩金黄得让梵高看了都会流泪的油菜花,穿过由几千株柳树、杨树和桉树成行排列的乡村公路,还得穿过几道石头砌成的小桥,才能抵达那座位于成都近郊的以佛教石刻为核心的博物馆和与它一墙之隔的度假村。
鹿野苑位于郫县徐堰河畔,收藏有从远古到明清时期的石刻艺术品1000多件,以汉代到唐宋时期的佛教石刻艺术为主。这是一座掩映在河滩上的杂树和竹林之间的博物馆,它的设计者是曾经写过小说,还曾经演过戏的建筑师刘家琨,而向来以笔法诡异著称的诗人钟鸣,曾是这里的馆长。
佛教的出世与现实的入世一墙之隔:左边,是大量佛教石刻作品,佛法西来,这些艺术品描绘的故事和形象深入民间;右边,一个同样名字的度假村或者叫会所,则吃喝拉撒一应俱全,尤其打眼的是立在空旷草坪上的几根粗大的木头,它们是拓展训练用的。我前去z鹿野苑时,
正好遇到一群年轻男女在这里接受培训——佛光见证了年轻人的成长。
据说鹿野苑是刘家琨最著名的作品。这个显然带有小众化倾向的设计师,他还给四川的几个著名画家设计过工作室,其中包括罗中立和周春芽、何多苓这样的大腕。大腕是难以接近的,他们的工作室当然也就不在向公众开放之列。不过,比这些大腕资历更老,大腕们见了都得唱个喏叫声老师的叶毓山,他的工作室不仅是工作场所,同时还附设有一个个人作品陈列馆。
那个地方在牧马山。那里,据说是刘备牧马的地方,是出现在平原南缘的第一列浅浅的山丘。古木参天的庭院,立着几栋建筑,除了两栋用于居住的小楼外,其他则是叶毓山的创作室、工人生产的厂房、办公室;最起眼的,是门前立着两尊巨大雕塑的叶毓山作品陈列馆。在这座陈列馆里,安放着这位中国最优秀的雕塑家的大多数作品,其中自然有叶毓山的成名作——翘着二郎腿的毛泽东。据说,这一作品当时有不少批评的声音,认为不应该把领袖塑造得如此随意。一个脑袋里有贵恙的人固
执地认为,领袖每时每刻都要严肃地绷着脸,而在四川人叶毓山的视野里,伟人也应该有这样淡定的休闲时光。就像成都人一样。
神奇的是,由于有一条小溪环绕叶毓山的庭院,每天总有几百只白鹭飞到他的院子里觅食。因此,叶毓山每天必做的功课之一,就是给这些活泼的精灵喂泥鳅。那些泥鳅,全是花钱从市场上买来的,每年需要将近10万元。
离群索居于平原一隅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如今已然成了众多外地来蓉者必须前往的地方之一。这个以抗战题材著称的博物馆位于大邑县安仁镇,安仁镇从前最有名的是大地主刘文彩,如今,建川博物馆成了它的地标。
创始人樊建川以前的身份是政府官员,现在是地产商。据说修建这个博物馆聚落,最初源于他的个人爱好,个人爱好而成事业,樊建川是成功的。这个占地几百亩的博物馆群落,由一系列的博物馆组成,除最核心的抗战博物馆外,还包括民俗博物馆、红色年代博物馆,以及最新的因收容了那只困在地下30多天而得名“猪坚强”的猪而闻名的地震博物馆。这些鳞次栉比的博物馆似乎暗示了一种可能:无论何种身份,无论何种文化的前来者,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从鹿野苑到建川博物馆,再到集结了诸多艺术家的画家村,以及分别以郭沫若和巴金命名的艺术院和文学院,这些埋伏在成都民间的艺术群落,它们似乎从来都不曾占据过主流,但它们却又是一种沉默的、不可忽视的存在。对成都生活而言,这些艺术群落,它们是花椒,是盐,是一封上万言的情书中,在作了万千的比喻、引用、暗示和排比之后,终于忍不住写在纸上的那三个字。
因此,在成都,你可能会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现象:上午,男人带着儿子和女人,开着那辆不超过10万元的小车,驱车前往建川博物馆——其他博物馆亦然,给儿子讲解那些年代久远的事情,专业得好像他一生下来就是讲解员似的。中午,他们要选择一家有特色的小餐馆,要一桌川菜,男人还得喝两口。下午,儿子可能被送回了外婆家,或是去了艺术学校,男人呼朋唤友,在府南河边的茶馆里,喝茶,斗地主;女人则
和女伴一起,前往宽巷子或是春熙路。真实生活的气息就这样扑面而来,以至于我敢断定,哪怕走遍世界,我也能从无数种迥然不同的生活中,一下子嗅出哪一种叫“成都”。
结语一二三
结语一:关于成都生活,赞赏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虽然当事者根本不把这些赞赏或批评当成一回事。来自批评者的声音中,最大声的莫过于批评成都人小富即安——有了一点小钱就耽于享受。一个例证是,成都街上奔跑的私家车,大多是10万元以下的微型车。批评者认为,既然你有能力挣10万的车,你为什么不更加努力,今后挣50万甚至100万的车呢?这批评自然也是有道理的。可是,对生活的理解,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下的人是绝对不同的。对大多数我所熟识的成都人来说,积极向上固然好,但及时享受生活更重要。好比挣钱,你能挣得过比尔?盖茨大哥吗?你不能,所以,你不如就在有限的条件下,积极经营你的生活。你没有比尔?盖茨那么多钱,但你可以过得比他更快乐。就像莎士比亚借他笔下的人物之口喊出的那样:“上帝啊,即使你把我关在一个胡桃壳里,我也要把自己当成拥有无限疆土的君王。”
结语二:我敢打赌,宽巷子原定的开街之日一定不是地震后的6月,因为开街之时, 不少工程尚未竣工。之所以会选择在余震阴影里开街,那么多人冒雨前来,这其间,自然有政府部门为了集合人气的需要。但更多的,它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暗示,它暗示着安稳了多年的成都人,在面临大地震带来的短暂慌乱后,他们对优雅的市井生活的向往和追随,使他们迅速镇定下来,企图通过一条新街的开放,让生活尽快恢复它从容的常态——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希望狗日的生活再舒服一些。
结语三:敬请读者补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