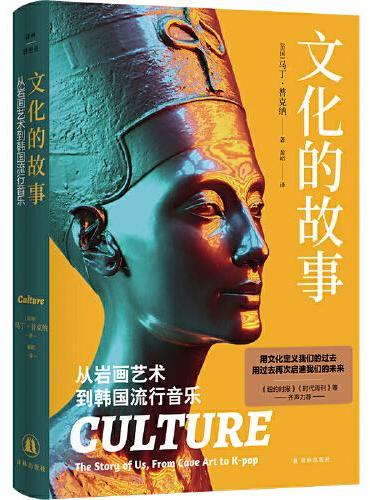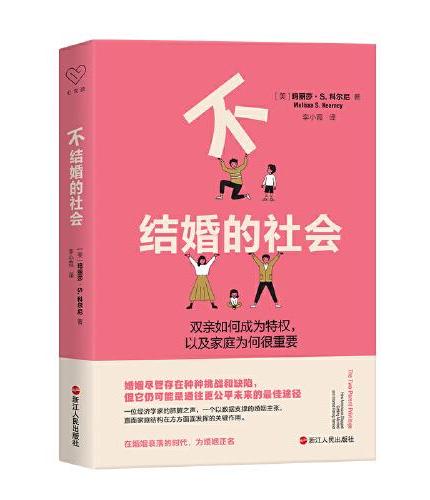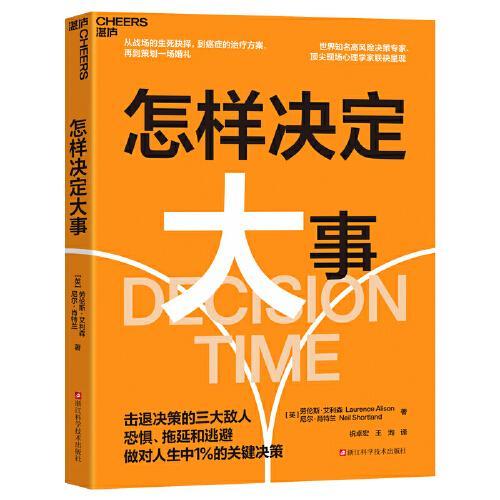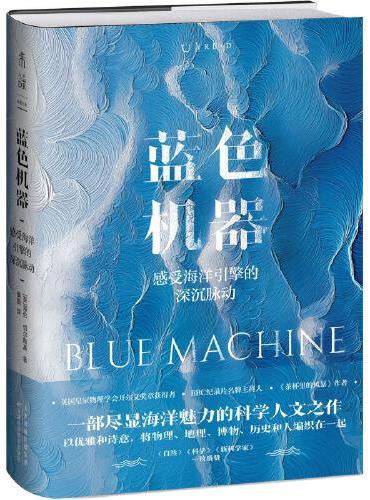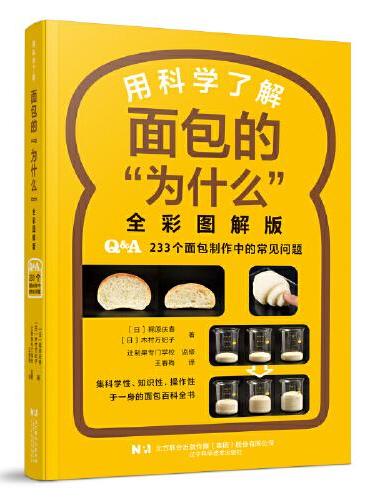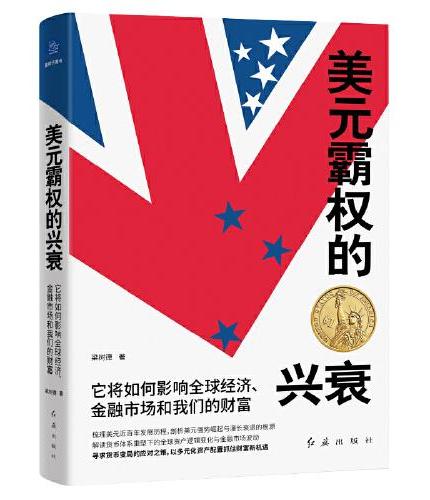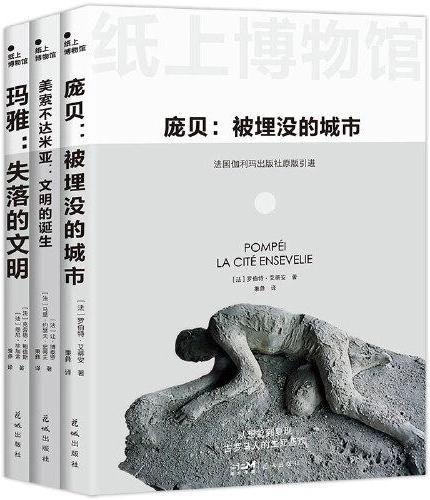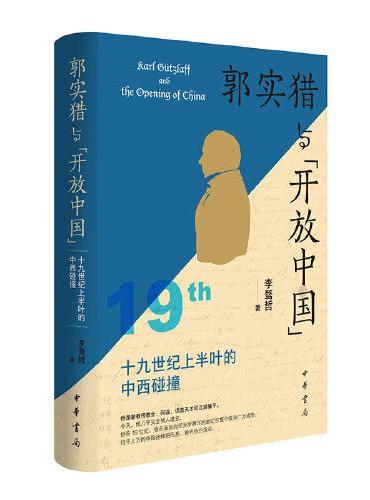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文化的故事:从岩画艺术到韩国流行音乐(译林思想史)哈佛大学教授沉淀之作 获奖不断 全球热销 亲历文化史上的15个关键点 从史前艺术到当代韩流的人类文化全景
》 售價:HK$
85.8
《
不结婚的社会:双亲如何成为特权,以及家庭为何很重要
》 售價:HK$
63.8
《
怎样决定大事
》 售價:HK$
109.9
《
蓝色机器:感受海洋引擎的深沉脉动
》 售價:HK$
96.8
《
用科学了解面包的“为什么” (全彩图解版)
》 售價:HK$
96.8
《
美元霸权的兴衰:它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和我们的财富(梳理美元发展历程,剖析崛起与衰退的根源)
》 售價:HK$
63.8
《
纸上博物馆·文明的崩溃:庞贝+玛雅+美索不达米亚(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450+资料图片,16开全彩印刷)
》 售價:HK$
279.4
《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精)
》 售價:HK$
74.8
編輯推薦:
1.极具爆炸力的思想和批评,富有穿透力的记忆和分析,一篇篇来自我们熟知的文化名家刘瑜、易中天、周有光、周云蓬、胡舒立、甘阳、刘再复、林贤治、钱理群等人的最新力作,交织成对这个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深度解读。
內容簡介:
《博文001》,以开放、自由、平等、谦卑的人文姿态,秉承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原则,通过对当下社会百态的深度关注,来寻思文化思想与制度的关联,见证当下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在网络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我们更加呼吁书桌前的独立思考,多种角度的审视,更呼唤对于社会的关心,一种富有生命实感与力度的人生意识。因此,摆在读者面前的第一期博文,是由刘瑜、易中天、钱理群、甘阳、欧阳江河、刘再复、韩钢、张鸣、范曾、周云蓬、胡舒立、林贤治等风格迥异、不同声音结集而成的最新力作,听听他们对当下社会的新锐探测,和他们一起徜徉在史海钩沉,共同缅怀流金岁月。“博,大通也”,这不仅是我们创刊之际持有的心态,亦是对阅读本书之后理应有的期待。
目錄
Contents
內容試閱
民意与伪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