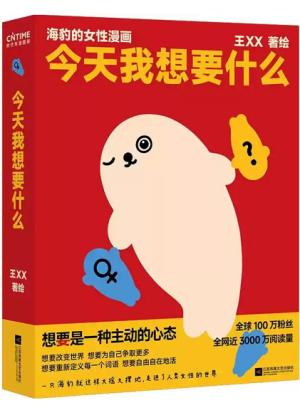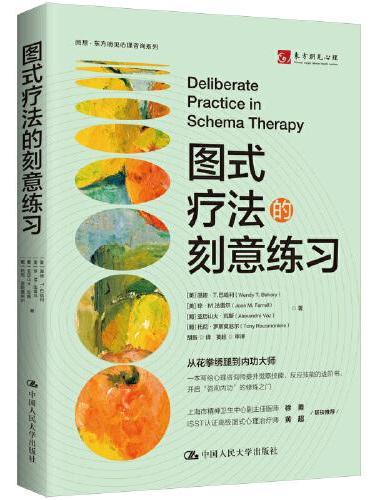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诡舍(夜来风雨声悬疑幻想震撼之作)
》
售價:HK$
54.8

《
讲给青少年的人工智能
》
售價:HK$
52.8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107.8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HK$
3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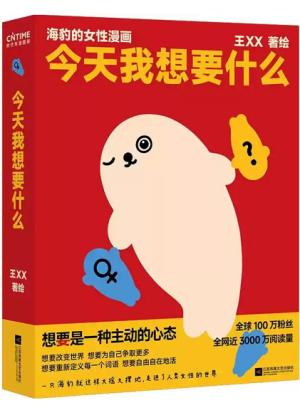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HK$
74.8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HK$
74.8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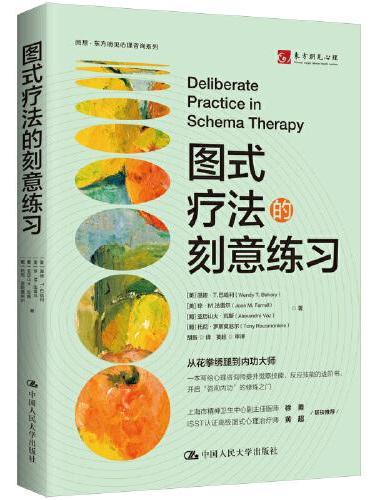
《
图式疗法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 編輯推薦: |
外国散文,浩如烟海。名家群星璀璨,佳制异彩纷呈:或饱含哲思,深沉隽永;或清新质朴,恍若天籁;或激情如炽,诗意纵横;或嬉笑怒骂,酣畅淋漓……二十世纪以降,中国广泛吸纳异域文化,许多外国散文名家日渐为国人熟识和喜爱,外国散文的写作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散文乃至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
《屠格涅夫散文》集中展示了外国散文名家屠格涅夫的创作风采。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俄罗斯文学的杰出代表。屠格涅夫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结构严整,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而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
|
| 內容簡介: |
伊·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小说、戏剧创作。第一部散文诗《猎人笔记》使他蜚声文坛。
作品以俄罗斯山川风物为背景,通过游猎间的见闻,广泛描绘了农奴和地主的群像与生活。语言优美、生动、凝炼而富有音乐感,对俄国文学语言发展有巨大影响。其散文诗,像散文一样自由,不拘格律,同时又具有诗的精炼、意境和韵味。它将抒情、叙事、写景、说理、咏怀等各种写法穿插融合,有的信手拈来,自然浑成,有的则经过长期思考,提炼出短短几句哲理性的格言。
《屠格涅夫散文》收录了屠格涅夫的经典散文作品。
《屠格涅夫散文》能够全面而深刻地展现屠格涅夫的写作特点及精神内涵。
|
| 關於作者: |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俄罗斯文学的杰出代表。屠格涅夫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结构严整,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而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
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在巴黎西郊塞纳河畔的布吉瓦尔小镇去世,永别了他深切眷恋的祖国。10月9日,他的遗体在彼得堡下葬,十万送葬者的政治示威使沙皇政府深感不安。也在这一年,他最后的作品《老年》发表了,仿佛是给世界的最后留言。《老年》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意象、诗化的语言为特色,是屠格涅夫晚年思想和艺术的缩影,也是不可多得的传世精品。
|
| 目錄:
|
霍里和卡利内奇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莓泉
县城的医生
利哥夫
白净草原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扬
总管
事务所
孤狼
两地主
歌手
约会
树林和草原
散文诗
一 SENILIA
乡村
对话
老妇
狗
乞丐
“你得听蠢人的裁判
得意的人
处世的方法
世界的末日
玛莎
蠢人
两首四行诗
麻雀
头颅骨
干粗活的工人同白手的人
蔷薇
最后的会晤
门槛
访问
]拖舍
菜汤
蔚蓝色王国
老人
二富豪
纪念尤·彼·弗列夫斯卡娅
斯芬克司
岩石
鸽
明天,明天!
大自然
“绞死他!”
我要想什么呢?
“蔷薇花,多么美,多么鲜艳
海上
留住!
我们要继续奋斗
俄罗斯语言
二 新散文诗
鸫鸟(一)
鸫鸟(二)
没有窝儿
高脚杯
谁的罪过?
爬虫
作家和批评家
当我不在人世的时候
砂漏
我夜里从床上起来
通向爱情的道路
沙鸡
Nessun Maggior Dolore
呜—啊……呜—啊……
我的树
|
| 內容試閱:
|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扬
我坐着一辆颠簸的小马车打猎归来,被云翳的夏日的闷热所困恼(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日子,有时往往比晴明的日子热得更难受,尤其是在没有风的时候),打着瞌睡,摇晃着身子,闷闷不乐地忍耐着,任凭燥裂而震响的轮子底下辗坏的道路上不断地扬起来的细白灰尘侵犯我的全身,—
—忽然,我的马车夫的异常不安的情绪和惊慌的动作唤起我的注意,他在这刹那以前是比我更沉酣地打着瞌睡的。他连扯了几次缰绳,在驾车台上手忙脚乱起来,又开始吆喝着马,时时向一旁眺望。我向周围一看,我们的马车正走在一片宽广的、犁过的平原上;有些不很高的、也是犁过的小丘,形成非常缓和的斜坡,一起一伏地向这平原倾斜;一望可以看到大约五俄里的荒凉的旷野;在远处,只有小小的白桦林的圆锯齿状的树梢,打破了差不多是直线的地平线。狭窄的小路蜿蜒在原野上,隐没在洼地里,环绕着小丘,其中有一条,在前面五百步的地方和我们的大路相交叉,我看见这条小路上有一队行列。我的马车夫所眺望的就是这个。
这是出殡。在前面,一个教士坐在一辆套着一匹马的马车里,慢慢地前进;一个教堂执事坐在他旁边赶车;马车后面有四个农人,不戴帽子,扛着盖白布的棺材;两个女人走在棺材后面。其中一人的尖细而悲戚的声音突然传到我耳朵里;我倾听一下:她正在边数落边哭着。这抑扬的、单调的、悲哀绝望的音调,凄凉地散布在空旷的原野中。马车夫催促着马:他想超过这行列。在路上碰见死人,是不祥之兆。他果然在死人还没有走上大路之前超过了他们;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出一百步,忽然我们的马车猛地震动一下,倾侧了,几乎翻倒。马车夫勒住了正在快跑的马,挥一挥手,啐了一口。
“怎么了?”我问。
我的马车夫一声不响、不慌不忙地爬下车去。
“到底怎么了?”
“车轴断了,……磨坏了,”他阴郁地回答,突然愤怒地整理一下副马的皮马套,使得那匹马完全偏斜到一旁,然而它站稳了,打了一个响鼻,抖擞一下,泰然地用牙齿搔起它的前面的小腿来。
我走下车,在路上站了一会,茫然地陷入了不快的困惑状态。右面的轮子差不多完全压在车子底下了,仿佛带着沉默的绝望把自己的毂伸向上面。
“现在怎么办呢?”最后我问。
“都怪它!”我的马车夫说着,用鞭子指着已经转人大路而正在向我们走近来的行列,“我以前一直留心着这个,”他继续说,“这个预兆真灵,——碰到死人……真是。”
他又去打扰那匹副马。副马看出他心绪不佳,态度严厉,决心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是偶尔谦逊地摇摇尾巴。我前后徘徊了一下,又站定在轮子前面了。
这时候死人已经赶上我们。路被我们阻住,这悲哀的行列就慢慢地从大路上折到草地上,经过我们的马车旁边。我和马车夫脱下帽子,向教士点头行礼,和抬棺材的人对看了一下。他们费力地跨着步子;他们的宽阔的胸脯高高地起伏着。走在棺材后面的两个女人之中,有一个年纪很老,面色苍白;她那板滞的、由于悲哀而剧烈地变了相的容貌,保持着严肃而庄重的表情。她默默地走路,有时举起一只瘦削的手来按住薄薄的凹进的嘴唇。另一个女人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岁的少妇,眼睛润湿而发红,整个面孔都哭肿了;她经过我们旁边的时候,停止了号哭,用衣袖遮住了脸……
但是当死人绕过我们的旁边,再走上大路的时候,她那悲戚的、动人心弦的曲调又响起来了。我的马车夫默默地目送那规则地摇摆着的棺材过去之后,向我转过头来。
“这是木匠马丁出丧,”他说,“就是里亚博沃的那个。”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了那两个女人才知道的。年纪老的那个是他的母亲,年纪轻的那个是他的老婆。” “他是生病死的吗?”
“是的……生热病……前天管家派人去请医生,可是医生不在家……
这木匠是个好人;稍微喝点酒,可是他是一个好木匠。你瞧他的女人多伤心……不过,当然喽,女人的眼泪是不值钱的。女人的眼泪像水一样……
真是。” 他弯下身子去,爬过副马的缰绳底下,双手握住了马轭。
“可是,”我说,“我们怎么办呢?”
我的马车夫先把膝盖顶住辕马的肩部,把轭摇了两摇,整理好了辕鞍,然后又从副马的缰绳底下爬出来,顺手把马脸推一把,走到了车轮旁边。他到了那里,一面注视着车轮,一面慢吞吞地从上衣的衣裾底下拿出一只扁扁的桦树皮鼻烟匣来,慢吞吞地拉住皮带,揭开盖子,慢吞吞地把他的两根肥胖的手指伸进匣子里去(两根手指也还是勉强塞进去的),揉一揉鼻烟,先把鼻子歪向一边,便从容不迫地嗅起鼻烟来,每嗅一次,总发出一阵拖长的呼哧呼哧声,然后痛苦地把充满泪水的眼睛眯起来或者眨动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
“喂,怎么样?”最后我问。
我的马车夫把鼻烟匣子小心地藏进衣袋里,不用手帮助而只是动动脑袋把帽子抖落在眉毛上,然后一股心思地爬上驾车台去。
“你打算上哪儿去呀?”我不免惊奇地问他。
“您请坐吧,”他坦然地回答,拿起了缰绳。
“可是我们怎么能走呢?” “能走的。” “可是车轴……” “您请坐吧。”
“可是车轴断了……” “断是断了;可是我们可以勉强走到新村……当然得慢慢地走。在那儿,树林后面,右边有一个新村,叫做尤迪内。”
“你认为我们到得了吗?” 我的马车夫并没有赏给我一个答复。
“我还是步行的好,”我说。
“随您的便吧……” 于是他挥一下鞭子。马起步了。
我们果然到达了新村,虽然右边前面的轮子勉强支持而且转动得特别奇怪。在一个小丘上,这轮子几乎脱落;但是我的马车夫用愤怒的声音吼叫一声,我们才平安地下来了。
尤迪内新村由六所低小的农舍组成,这些农舍已经歪斜了,虽然建造得大概并不久:农舍的院子还没有全部围好篱笆。我们的车子进入这新村,没有遇见一个人;路上鸡都不见一只,连狗也没有;只有一只黑色的短尾狗在我们面前匆忙地从一个完全干了的洗衣槽里跳出来(它大概是被口渴所驱使而走进这槽里去的),一声也不叫,慌慌张张地从大门底下跑进去。我走进第一所农舍,开了通穿堂的门,叫唤主人,——没有人回答我。我又叫唤一次:一只猫的饥饿的叫声从另一扇门里传出。我用脚把门踢开:一只很瘦的猫在黑暗中闪烁一下碧绿的眼睛,从我身旁溜过。我把头伸进房里去一看:黑洞洞的,烟气弥漫,空无一人。我走到院子里,那里也没有一个人……栅栏里有一头小牛在那里哞哞地叫;一只跛脚的灰鹅一瘸一瘸地向旁边拐了几步。我又走进第二所农舍,——第二所农舍里也没有人。我就走到院子里……
在阳光普照的院子的正中央,在所谓最向阳的地方,有一个人脸向着地,用上衣蒙着头,躺在那里;据我看来,这像是一个男孩。离开他若干步的草檐下,一辆蹩脚的小马车旁边,站着一匹套着破烂马具的瘦小的马。阳光穿过破旧的屋檐上狭小的洞眼流注下来,在它那蓬松的、枣红色的毛上映出一小块一小块明亮的斑点。在近旁一只高高的椋鸟笼里,椋鸟吱吱喳喳地叫着,从它们的高空住宅里带着平静的好奇心往下眺望。我走到睡着的人旁边,开始唤他醒来……
他抬起头,看见了我,马上跳起来……“什么,你要什么?怎么回事?”他半睡不醒地嘟哝着。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因为他的外貌把我吓坏了。请想象一个年约五十岁的矮人,瘦小而黝黑的脸上全是皱纹,鼻子尖尖的,一双褐色的眼睛小得不大看得出,鬈曲而浓密的黑发像香菌的伞帽一般铺在他的小头上。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而瘦削,他的目光的特殊和怪异,无论如何不可能用言语描写出来。
“你要什么?”他又问我。
我就把这件事讲给他听;他听我讲,一双眼睛慢慢地眨着,一直盯住我看。
“你能不能替我们弄到一个新的车轴?”最后我说,“我愿意付钱。
” P83-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