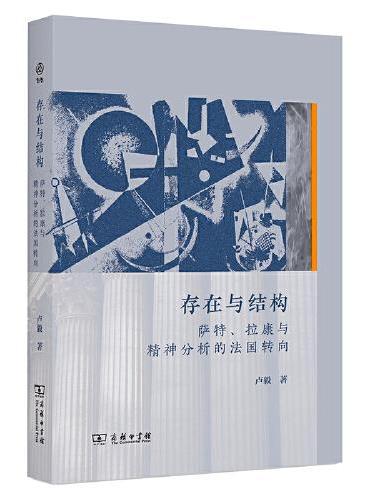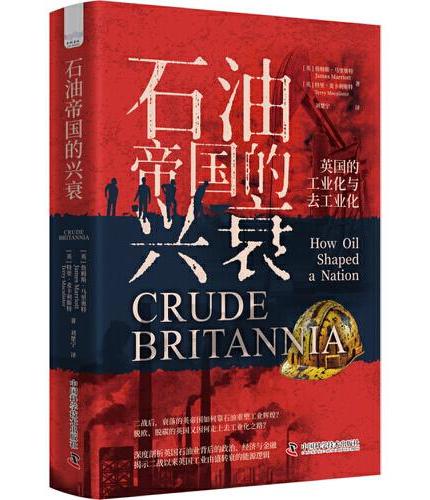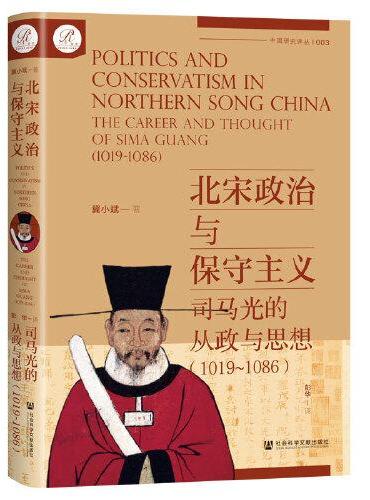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甘于平凡的勇气
》
售價:HK$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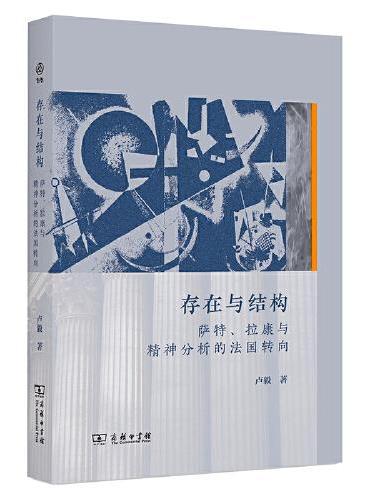
《
存在与结构:精神分析的法国转向——以拉康与萨特为中心
》
售價:HK$
52.8

《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与多模态技术应用实践指南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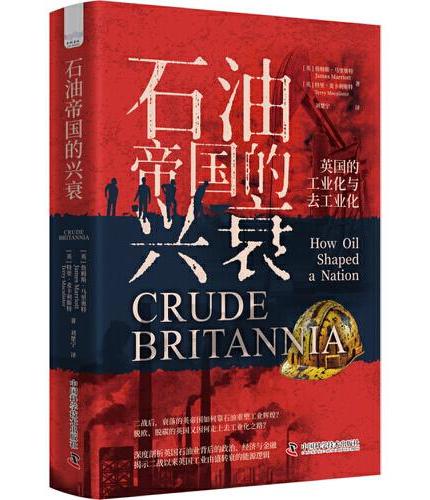
《
石油帝国的兴衰:英国的工业化与去工业化
》
售價:HK$
97.9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HK$
437.8

《
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黄老学(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HK$
1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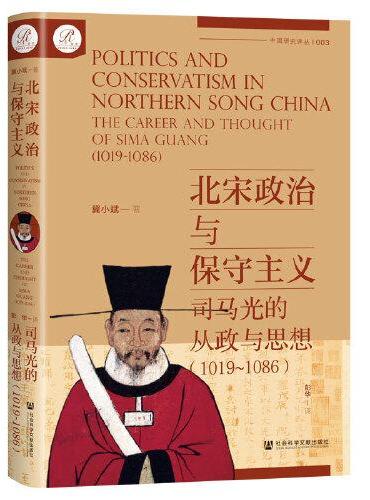
《
索恩丛书·北宋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从政与思想(1019~1086)
》
售價:HK$
75.9

《
掌故家的心事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1. 先锋派作家吕新,他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启发你对生命本质的顿悟。
2. 吕新,讷于言行却想象力丰富,他独特的艺术感觉有别于山西传统的文学创作套路,激活了民间厚土深埋着的生命种子。
3. 吕新的文字,通篇透着智者对人世的洞悟,对生命本质的疑惑,也流露出魂归何处的惘然与疲倦。
|
| 內容簡介: |
|
《梅雨》是吕新在近十年来发表的六部长篇小说之一。这部作品中,作者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发生在江淮流域的一段漫长艰难的特殊世事,以优美的文字将江南细致哀婉的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为之叫好称快。正如他在文中所说:一个人一生轰轰烈烈,大起大落,风流多情,那不算什么。一个人一生什么事都不出,窝窝囊囊,唯唯诺诺,那其实也真叫奇迹。
|
| 關於作者: |
吕新,当代作家,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与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等开起一代文学风气。从一九八六年代至今,著有中短篇小说《阮郎归》《梅雨》《成为往事》《抚摸》《光线》《石灰窑》《我理解的青苔》《中国屏风》等。曾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
、青年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
|
| 內容試閱:
|
周策田
一位瘦骨嶙峋的教员,一溜小跑出现在操场附近。我正在一道长满苍苔的高墙下慢慢走着,壕沟里的水已经积满了,渐渐漫进了小树林里。从我这个位置上望去,能看到树林里的水的反光,树上的枝桠在光影里摇晃着。
脚步声越来越近,他终于绕过操场上的沙坑在我的面前停住了。我看见他的嘴张了一下后又立即闭上了,两只脚交替着羞涩而不安地轻轻磨擦着地上的沙子,他站在那里等待着。他似乎在看着我,又像是在往别处张望,他的眼神很奇怪。时间仿佛停止了,正在某一个泥泞的地方原地转动,来回打滑。他是来找我的。
我看着这个莫名其妙的同事,他瘦得像一只春天的山羊。这样一副身躯,似乎生来就只适合教书。是的,我周围有很多选样的人,早已司空见惯了,有时乍一见到某些体肥肉厚的胖子,我会有意无意地感到意外和不适。巨大的习俗,有时不免会成为一种恶习……现在,他站在那里,似在暗自思忖,一双疲倦的眼睛在飞快地眨动着……难道……校长睡着了?这样的天气里,要想舒舒服服地打一个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突然,他不可遏制地咳嗽起来,非常响亮的喷嚏和咳嗽使他自己也惊呆了。
我从阴湿的高墙下离开,走到他的身边。他似乎有些伤风。我手里的一张报纸饱含着昨夜的潮气,软绵绵的像一张熟过的皮子。这样的阅读物,简直糟透了。他怎么了?
“啊.周校长,”他满脸通红,伸手从上表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轻轻地擦拭着脸颊和嘴角四周的地方,低声喘息着。
“是这么回事。”他说,“尊夫人打来电话,说她今天中午不回去了,让你……想吃什么,自己看着办吧。”
他飞快地扫了我一眼,表示自己说完了,很薄的嘴角开始向里收缩,自然流露出来的强烈的好奇和兴趣代替了他刚过来时的那种慌乱和不适。他现在是可以这样饶有兴趣地打量别人了,看看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需不需要自己帮他们斟酌,谋划一下,拿个主意,排忧解难。是的,很多人都乐意干这样的好事,急他人之所急,这中间不仅仅是仗义。
我看着他。在他的身后,一树肥绿的树叶正在往下滴水。
他偷眼瞧着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由于激动而遗漏了什么。他的舌头不知不觉地从嘴里吐了出来,粉红色的,短短的,形状如一瓣小金橘,轻轻地、试探性地舔了一下自己的上唇,像是在尝试一粒危险的、没有说明书的药片。上唇的温度一片灼烫,他似乎受到了惊吓,急忙将湿漉漉的舌尖重新缩了回去,不安地搓着双手,显出一副死里逃生的侥幸之色。
“啊,对了。”他终于又想起了什么,立即跳了起来,单腿着地。“一位学生的家长,”他说。“要请薛隐去吃饭。我对他说,薛老师这个时候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我这么说没有什么不妥吧?教员接受邀请,跟别人出去吃饭,在咱们学校里好像还没有先例,是吧?”
“薛老师知道这事吗?”我说。
“是的,两个电话都是我接的。”他说。他向前跨了一步.脸上露出一种不计得失,任劳任怨的笑容。“我就坐在综合办公室的电话机旁。”他说。“我刚想站起来活动活动,突然,电话响了。我拿起来,是那个学生的父亲,他是打给薛老师的,他想请她一起吃顿饭。他为什么要请她吃饭呢?我对他说,薛老师这个时候正在给她的学生们上课,我这么说没什么不妥吧?本校的教员们还没有过这种先例呢。”
“我曾经出去吃过一次。”我说。
“是吗?”他愣了一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吧?是的,那已经很久了……和那位家长说过话之后,我刚想活动活动,突然,电话又响了起来。不大一会儿工夫,怎么会有这么多电话呢?我拿起来,一听到那清脆悦耳的声音,我就知道是尊夫人打来的。她说她中午有事不回去了,让你想吃什么,自己看着办吧……说实在的,让男人们自己动手弄饭,可是够糟的。有一次,我刚把满满一锅水烧开……”
“赵老师,”我说。“上面让咱们唱的那首歌,你学会了吗?”
“你问这个?啊,快了,我想差不多了,再用不了几天就能全部唱下来了。”他又掏出他的那块手帕,拿在手里。“其实,歌词我早就掌握了,就那么几行,就像咱们国家的七律诗词或五言绝句一样。”他说。“麻烦的是那个曲子,唱着唱着,调子就跑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这很怪。”
“回去好好练练。”我说。“一定不能唱跑了调。学生们唱得都很标准,当先生的要是跑了调,那真说不过去。”
“是的。”他说。“可是,歌唱需要真挚的感情,对吧?”
“那当然。”
“我对它没有感情。我不想唱它,我连哼哼几句都不情愿。”
“赵老师,你不会不知道吧,那可是一首友谊之歌,传播的是国际感情——”
“呸!”他说。“我没看出友谊在哪里。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从词到曲,全是……”
“回去对着镜子练练。”我说。我将一只手放到他的肩上,我触到了他的骨头。我的手很热,血在指头里鼓胀。他感觉到我的手了,回头看了我一眼,顺从地点了点头。
“注意口形与喉咙的变化。”我说。
“是的,我连吃饭的时候都忘不了要矫正我的口型。”他说。“我这张嘴啊……我的妻子以为我牙疼,啊,我说她了,真是妇人之见。”
是的,我们不用心唱,只用嘴唱,甚至像戏曲那样使用假嗓。
当年,在大学里的时候,系里的一位姓陈的先生给他的女儿取名叫曼。那个叫陈曼的小姑娘,我们都叫她阿曼,小曼。她的名字有源可溯,来自于托马斯?曼。资产阶级?曼。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曼,大嫚,二嫚。
去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一场大雪刚刚下过不久,我接到了教育局俞局长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举荐信,被举荐的人是一位名叫薛隐的女大学生。俞局长在信中说,作为举荐人,让薛小姐来这里执教,他是非常满意的,于公于私,都相当不错。淑阳中学的风气像她的环境一样优美,人才辈出,随便一块砖头,一座门楼,一只书柜,都能在上面读到一段庄严的或令人警悟、令人心酸的历史。信中除了称赞薛小姐的美丽之外,并未涉及其他。为了国家——请多多关照。信的最后,俞局长这样写道。
为了国家?
多么明朗而又含糊的说法!教育当然是为了国家。撇开了国家意义的教育,只能是一种土生土长、自动明灭的山寨草莽。
我从椅子里站起来,视线落到窗外的几棵枇杷树上。天上落下来的大雪,使整个校园变得宁静祥和,仔细深究起来,还有一种隐隐绰绰的圣洁。遍地白雪,书声琅琅,火光温暖明亮,令人安心。又是一年要过去了。
是的,很快就要放寒假了。然而,俞局长在信中明确写道,薛隐小姐将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带着自己的行李与书籍来学校报到。我不免有些吃惊。这就是说,整个寒假期间,薛隐小姐将要住在学校里,安顿下来,一直等到明年春天开学以后,才能正式上课。老天!这么急着风尘仆仆地赶来,难道她是一位无家可归的姑娘吗?为什么不趁着冬闲的大好时光与自己的亲人团聚?不想团聚吗?假期是荒凉的,黑暗的,其间的困难可想而知。冷清,寂寞,无所事事,还有意想不到的危险和麻烦……
我的眼前猛烈地跳动了几下。我想到了那几间尚待修缮的校舍……伙房后面的一口水井……整个冬天里,那些破烂的窗纸常在寒风中呼呼作响……一还有每日必备的柴草……粮食,蔬菜……食用油……寒假一到,所有的师生员工皆作鸟兽散。这种时候,单独让一位远道而来的,年轻美貌的小姐守在这偌大的,空荡而萧瑟的校园里,人地生疏,凄风苦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不恰当的,万一……她自己也许想得比较简单,很少顾虑,没有意识到什么。新时代的女性,都是这样,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可是,作为从事教育数十年的俞局长,难道也不知此举欠妥吗?是的,非常欠妥。树老成精,可俞局长……有必要写一封信给俞局长,向他陈述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开门见山,水落石出。薛小姐一身光芒,能屈尊来这里从教,我在欢迎之余倍感荣幸。剔除老秀才,输入新血液,我早有志于此,只是此举目前来说还只是一股暗流,一道地气,其清晰度远不及一根皮下的血管。是的,愿望和变化都有,只是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另外,这里不适宜大刀阔斧的砍杀,一切都得慢慢来,否则会引起其它的变异和意想不到的飘移。青梅煮酒,以温暖动人。咄咄逼人,不可一世,那是多么令人憎恶。这里的环境嘛,说平静也平静,说不平静,也绝非违背事实。寒假日渐临近,学校里近来人心浮动,波光摇曳,一种涣散的,分崩离析的没落情调在雪后的日子里悄悄地延伸着,不知不觉地扩散着。寂静而不安的校园,耸立的枯枝令人惆怅。
薛隐小姐,她为什么不能等到明年春天再来呢?选择一个河水回暖,草木泛绿的日子,搭船或者乘车,那时候来……
南边一带的刺眼的积雪上站着两头牛,喂牛的老头正低着头在一片树篱前仔细逡巡,似乎丢失了一件什么要紧的东西。那是学校里养的两头牛。除此之外,学校里还有几匹马,一百多亩地——都在郊外——每年雇人耕种收获,补贴学校的开销。需要重新物色一名会计。
拎着皮箱的薛隐小姐和俞局长的回信几乎是同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握过薛小姐的冰凉的小手之后,我打开了俞局长的信。信中说,薛小姐自己都不在乎,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样瞻前顾后,婆婆妈妈,你知道你怎么了?你老了。是的,你的一举一动,都在说明你他娘的已经老了,往日的锋芒全不见了。我将一位美丽的小姐推荐到你的身边,你却一味地退缩,战战兢兢,你要退到哪里?什么意思?
是的,我这是怎么了?我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我真的老了吗,更何况,人已经来了,戴着眼镜,拎着皮箱,打着雨伞……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浴室的里面亮着灯,张芸正在里面洗澡。我告诉她,学校里今天新来了一位小姐,是教育局俞局长推荐来的,人长得很清秀,很漂亮,很优雅。
一阵水声消失后,张芸从闷热的蒸气中走出来,她从浴室的门口走到镜子前,在那里停留了一阵后,来到我面前。
“你有病吗?”她说。语气是关切的,芳香扑鼻,暖风拂面。
“我没病。”我说。
晚间的沐浴使她看上去容光焕发,咄咄逼人。她将头发向旁边一甩,水珠溅到我的脸上。“需要我帮你擦背吗?”我说。
未置可否。不需要。她已经洗完了,走到那边开始梳理头发。她的头摆来摆去,浴衣在身上飘扬。从孩子5岁以后,她开始当着我的面换衣服了。那不是因为结婚多年的原因,而是因为她目中无人,目中无物,没有什么值得避讳的东西。美丽与经验可以压倒一切。我的请求明显落伍而不合时宜。人们都说已婚妇女没有廉耻,我不这样看,我认为那是她们的勇气大于一切,有了那样的无所畏惧的勇气和信心,相信她们什么事情都能办妥,什么样的难关都能攻得下来。床上堆满了张芸的衣服。丝带。胸罩。连裤袜。衬衣。银灰色的折边。一只经过长途跋涉后的皮箱……我刚把它拎起来,薛小姐的戴着手套的手忽然伸了过来。谢谢,我能行。她说。是的,她能行。还有她。她们都是了不起的女性,能够独自撑起一片晴空,化干戈为玉帛,点石成金。
我松开手……我很想洗一个澡,就用张芸用过的水,仅仅是为了多少浸泡一下。我来到浴室门口,看到浴缸里飘满了白色的泡沫,大团大团的白色泡沫,像北方地区的那些正在解冻的河流……
凌汛……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而可笑的。整个寒假期间,薛隐一直住在寂寞的学校里,安然无恙。是的,真正的安然无恙。她有时出来买书,与书店老板也很能谈得来,有时到河边浏览两岸的景色,在弯曲的小桥和斜仄的石级上闲逛。
一个人一生轰轰烈烈,大起大落,风流多情,那不算什么。一个人一生什么事都不出,窝窝囊囊,唯唯诺诺,那其实也真叫奇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