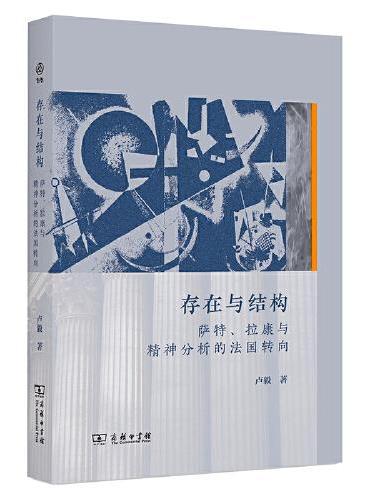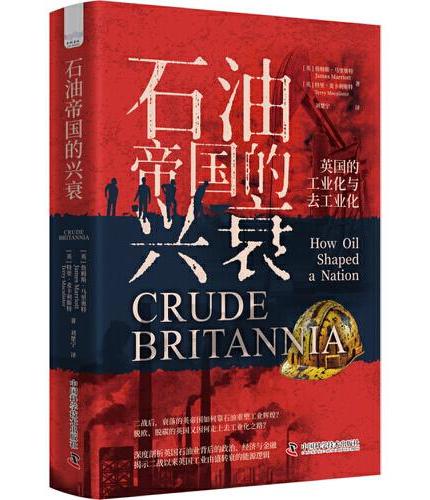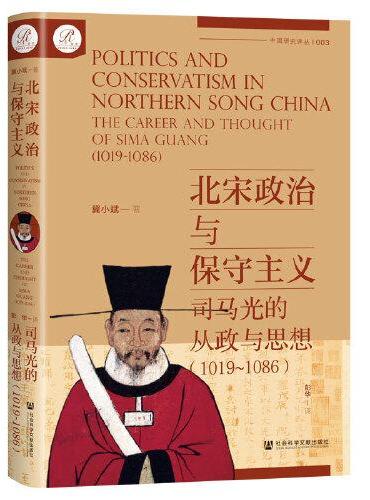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甘于平凡的勇气
》
售價:HK$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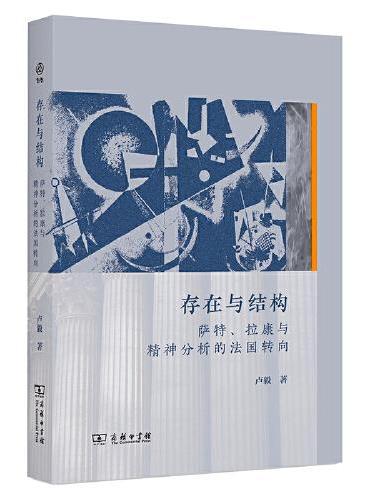
《
存在与结构:精神分析的法国转向——以拉康与萨特为中心
》
售價:HK$
52.8

《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与多模态技术应用实践指南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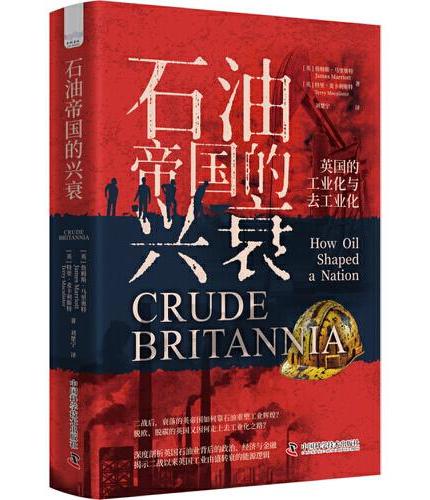
《
石油帝国的兴衰:英国的工业化与去工业化
》
售價:HK$
97.9

《
古典的回響:溪客舊廬藏明清文人繪畫
》
售價:HK$
437.8

《
根源、制度和秩序:从老子到黄老学(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HK$
1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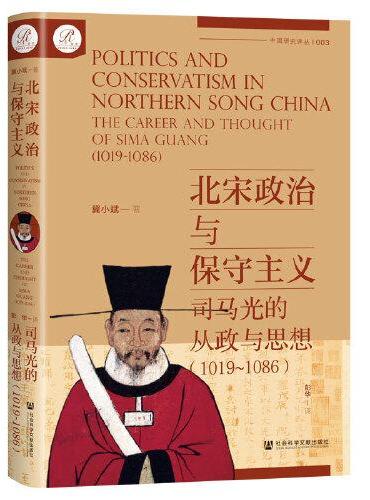
《
索恩丛书·北宋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从政与思想(1019~1086)
》
售價:HK$
75.9

《
掌故家的心事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阮郎归》不是第一部以词牌名命名的小说,但是它却是第一部将现实与虚幻完美结合的作品。小说中两个等待轮回的孤魂,或历史典故,或野史传说,被作者巧妙的转换、融合,人物心理入微,一气呵成,读来身临其境,回味绵长。
本作品故事简单好读,但也引人掩卷深思,关于生与死,透悟着生命的本质,与佐野洋子的畅销绘本《活了一百万次的猫》一样,引人深思。
|
| 內容簡介: |
《阮郎归》讲述的是一个横跨古今千年的故事,主要是以四叔与我两个死去的魂灵在阴间相遇,各自叙述过往,其间塑造了不同年代、不同性别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在叙述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江南的盐商、城门的侍卫、修建皇陵的铁匠、交欢时死去的高僧、弑君的臣子、奇异家族短命的孩童还看到了苏小姐(萧红)与鲁迅的交往片段到了叔侄两个这一辈,一个是乡村干部,一个是潦倒的大学教授,无论是乡村干部间的权力争斗,还是学术界的黑幕,结果仍然是殊途同归
|
| 內容試閱:
|
第二章
远的就先不说了,说近的吧。
康熙年间,四叔姓吴,不,严格地说,应该是我姓吴,那时我还不是你的四叔。我是淮南的盐商,富得要命,一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钱。现在可以这么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在当时不行,当时不敢这么说,明知道真的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也不能说出来,怕被人们以为是一个傻子,你一傻,不要紧,别人不傻,就会有人动心思、钻空子,所以,你不想胸有成竹也不行。
府内自然是人丁兴旺,大约有三四百口,也有可能是四五百口,具体有多少人,对于我这个一家之主来说也是个谜,完全不清楚。我常想,管他多少呢,多了总比少了好吧,又不是养活不起,支应不起,谁想来就来吧,我都欢迎,我对谁都是一样的。
经常会看到一些生面孔,像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都是谁呢?我不知道,我也不去管他们,按道理都应该是我府里的人,想必也是。有时候,你正坐着,一个孩子忽然跑过来抱住你的腿,喊你爷爷。我问他:你是谁?孩子说:我是伏龙,你的孙子。伏龙?我的孙子?是谁给这个孩子起了这么个名字?我眼前那个雾啊!没有世事人烟,前后左右、方圆多少里以内全都是白茫茫的大雾,像我的盐呢。
我有五六处园林,但也有人说是九处,这一点,我也不敢确定,因为我很少到那些地方去,有的甚至从来都没有去过。有时候累了,会在某一个园里喝一杯茶,听一段戏,或者舞几下剑。舞得也并不好,就不可能好么,我又不是专门靠剑吃饭的剑客,可就是那样,每次总会有人在旁边大声地喝彩、叫好,被认为是世间一流,天下无双,这样的无风起尘般的夸奖和赞誉,连我本人都时常觉得有些羞愧和无耻,可是他们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说那种话的人,就用那种话来进行交换,然后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我常在心里说,这就是世道啊,世道就是这样的啊,一千年前和一千年后都是一样的,身上穿的衣裳不一样了,名字也不一样了,但做事情的办法却还是一样的。
我似乎没有理由活得不好,皇帝那个人也算是够能活的了吧,可是,他却也死在了我的前面,在我还很健壮的时候经过了国丧,他死的时候,我一把年纪还给他戴了孝。有一天,我正在沁园里舞剑,舞得热气腾腾,忽然听说皇帝驾崩了。我到街上去看,街上都挂了白,到处都白茫茫的,连河里的船上也挂着孝,河水好像也成了白的。
新皇帝我们都不熟悉。忽然又有一天,我正在桂园里喝茶,新皇帝又死了。
一年一年地下来,眼看着那些比我年纪小的,甚至小很多的人,都呼啦呼啦地走了,都噌噌地走了,而我还活着。至于当年那些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人,更是早就都走得没有了踪影。街上的人,码头上的人,也都又不知换了多少茬新面孔。那时候,我就常在心里想,这不对呀!你认识的人,几乎没有了,从前和你打过交道的那些人,也都早已经不在了,不管是朋友还是仇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的年代好像已经过去了,没几年的工夫,皇帝都走了两个了。一个人活到这种时候难道还有什么意思么?我在桂园里一边喝茶,一边回想着那些早已远去了的烟雨迷蒙的往事。我想起一个仇人姜十堰临死前对我说过的话,他眼泪汪汪、满含悲愤地对我说:吴老爷,你有本事,你厉害,你就好好地活吧!你能活一千年,一万年呢。我后来经常会想起姜十堰临死前说过的这句话,原来一直以为他说的是气话,直到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心中有所顿有所悟,不禁吓了一跳,啊呀,姜十堰让我活一千年,一万年,他这纯粹是在害我呀!纯粹是没安好心啊!姜十堰啊,和我斗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砍砍杀杀,明里暗里地斗,临走也没忘了给我挖个坑,设个局,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像庄稼一样纷纷倒下了,死去了,他却只让我一个人坚持活着,还得活一千年,一万年,一千年活下来,满世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那该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啊。
乾隆年间,我终于死了。我没有上姜十堰的当。
那年冬天,江南大雪,梅花开得正艳,我想去踏雪寻梅,但是被儿孙们拦住了,他们把我按在一张太师椅里,只让我用眼睛看雪,用鼻子闻梅花的清香,却不让我到处去走动。于是,我就只好用眼睛看雪,用耳朵听雪,看见雪像丝绸一样在飘舞,漫天飘舞,飘到哪里,哪里就响成一片。梅花下面有歌声,十分纤细的歌声,不用心听是听不见的。有人在我的脸前低声说:爷爷,看看就回去吧,天又阴了。我在心里说,不回去,就不回去,我还没看够呢。回去干什么呢,回去也是个睡觉。远处的雪地上也有一些人在观赏梅花,还有人把梅花拿在手里,放在脸前。我认出那些人里有巡抚钟文焕、蓝进士、翟总兵,还有姜十堰,他穿着一件丝棉袍子,站在雪地上,一副站不稳的样子,但脸上却浸满了笑容。是的,那个把一枝梅花拿在手里,不时地又放到脸前的人就是他,姜十堰。他们几个人站在一起,让我觉得有些吃惊,远远地看着他们,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像是在哪一点上出了毛病?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但我一时又觉得有些理不大清楚,雪在我的脸前轻纱一样地挂着,从上至下地垂挂着,我等了好久,一直没有人能替我把我脸前的那道轻纱掀开,撩起来。
有人对我说:爷爷,该回去了。
说的正和我想的一样,我点了点头,也觉得是该回去了。
在外面看了两个时辰的雪,回到屋里后却倍感燥热,都已经是十二月的天气了,怎么会这么热呢?我想了半天,想不明白。我让他们脱去衣服,但燥热还是没有退去,依旧在热昏昏地生长着,还要不时地爆出响声,噼的一下,嘭的一声。听见有人说:这个冬天真冷啊!这话从何说起呢,我倒没觉得。梅花一枝跟一枝地飘移过来,没见有人举着它们,也没有人捧着它们,自己就过来了,笑盈盈地站立着,一会儿站成齐齐的一排,一会儿又不知不觉地浑成一片,有的靠在一起,有的弯下了腰,香气在它们的中间圆滚滚地隆起,隆着隆着,最顶上的原本合在一起的褶子忽然开了,于是,丝丝缕缕地跑了出来,有的站在原地,慢慢地绕着,有的像是长了腿,安了羽翼,暴露出一身的匪气。
这就是我对那个世界的最后的一抹印象。
第三章
到了嘉庆末年的时候,我已经又是一个快二十岁的年轻人了,我只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姓倪,却不知道父母是谁。离家的时候,正值春天,一位私塾先生没有要钱,白送给我一个名字,叫倪春。他说,人活一世,哪能没有一个名字呢。来招兵的也说,得有,没有名字就不能登记造册。我有什么说的呢,我当然也盼望着有。我把那个名字反复地在心里念了好几遍,我觉得很好,念完一遍还想再念一遍,我要永远记住它。
当我念的时候,就在想:那不是别人,那就是我啊!
我从余姚乡下被招兵的招到杭州来当兵,看守城门。我和另一个名叫黄世充的弟兄共同掌管着杭州西门的钥匙,一大串如漆似墨的铁,叮当有声,哗啦作响,除了它们本身的硬质,它们发出的响声也给我这个从未出过门的人的身上增添了不少的胆量和勇气,让我比刚从乡下出来时勇敢了很多,每次手里拿着钥匙往城门口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身上布满了山脉一样的力气,在嘭嘭地鼓胀、跳动,甚至会有一种巨人的感觉,觉得杭州城的西门有我这样一个巨人来把守,多少年都会铜墙铁壁,金身不坏,万无一失。拿着钥匙的时候是这样,不拿钥匙的时候,把钥匙重新挂回到墙上,就不是这样了,明显地觉得身上的那种山脉一样的力气和胆量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样在逐渐退去,回落得很快,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一万个人也很难守得住一个城门,觉得自己缺少凶狠。每天天一黑,我们就把城门关了,上了锁。在城门口附近的一间青砖的小房子里,我和黄世充两个人轮流值日,逢单日是我,逢双日是黄世充。
西门外面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庙,经常有一个要饭的坐在那里,我在城门口值日的时候,看见他大多数的时候总是坐在庙前的空地上一门心思地捉虱子,对于周围的别的从不理会。也不知他有多少虱子,总也捉不完,每天捉,一年四季地捉也捉不完。除了捉虱子还算勤快外,他在别的上面都很懒,那种懒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甚至是能够听得见的,几乎从来也不见他出去要饭,也不知他每天都在吃什么。每次一看见他,我的心里就会觉得别扭,莫名地难过,有头发一样的东西堵在里面,又变成一条一条的愁绪,卷起来,再展开。为什么那么一个人他会让我那么愁呢?当时不明白,也没有去多想,现在想起来,我怀疑那个一年四季都坐在土地庙前捉虱子的懒鬼,极有可能是我做盐商时的一个儿子,一个曾经的花钱如流水的天塌下来都砸不醒的纨绔子弟,是的,肯定是他,不是他又能是谁呢,他娘的!他的相貌是变了,可他的底子没变,别人不认识他,感觉不到,我能感觉到,我还能认出他来。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当初一看见他就总觉得别扭,难过,什么也不是,就因为他曾经是我的儿子,冤家,人倒是转世了,可那副天生的懒骨头还没有转过来,和前世比起来,一点儿都没变,成天在土地庙前稳坐钓鱼台,神闲气定,不慌不忙,还以为他老子有用不完的钱呢。
或许是前世用去的太多了,这一辈子我的日子过得真叫紧,看守城门能挣几个钱?职责重大,报酬低微,我常想,如果把我的职责比作是一座城门,那么,我得到的报酬就相当于城门下的一捧土。我一文一文地攒钱,一吊一吊地积存,每当能够串成一串时,我都会心存感激,感天谢地,心中的恩义也在一天天地增长,会想起在乡下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他们正在田里插秧,在山上放牛,而我却在杭州城乌青的城门口站着。
铜钱一枚一枚地被我小心地串起来,透过铜钱中间的方孔,我看到世间变得十分整齐,许多的事情都在一个框子里进行,再没谱没边的事情,也跑不出那个框子里去。
我成了家,我屋里的女人叫彩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她爹是吹糖人的,成天摇着个拨浪鼓在杭州城里转来转去,每天所接触的都是市井上的街坊,孩子、女人、老太太。彩云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挺好的,每天我快要到家的时候,她总是站在门口等着我,一遍又一遍地望啊望,看见我回来了,她就放心了,脸上红一会儿,接过我手里的刀立到一边,在我洗脸洗手的时候,她已经把饭端上来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说话,我告诉她街上发生的事,告状的坐在城门口,每经过一顶轿,都要站起来向旁边的人打听一下。彩云身上的粗布衣裳常常会让我感到愧疚,我总在想,看见别的女人身穿绫罗绸缎,彩云肯定也想,怎么能不想呢?别说她这么年轻,就是那些比她年长好多的女人也还都在想呢。我对彩云说:彩云,对不起。彩云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成天看守城门,让你吃不好,穿不好,将来有一天,我要是能当上西门的提督,你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彩云听了我的话,看着我,只是笑。真要是能有那么一天,那就好了。她说。你当吧,我盼着你当,算命的说我三十岁以后有好运呢。啊,彩云这话犹如一道白光,噗的一声劈开了黑暗,照亮了我眼前的路。从那以后,再带着刀往城门口走的时候,站在城门口值日的时候,换班后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想的事情和以前就不一样了,虽然从外表看上去我还和原来完全一样,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已经不一样了,心里想的,眼里看的,手里做的,好多东西都开始变了,东一声西一声地响着,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成长着,没有人知道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多大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一种清水般的日子,也让和我一起值日的黄世充十分羡慕,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回去,都不会有人在门口等着他,望着他,对于他来说,早回去晚回去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回去不回去也是一样的,回去了是一个人,不回去还是一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么?没有。而我要是不回去,彩云就会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要是回去了,我们一下就成了两个人,这和黄世充是完全不一样的,黄世充是一只,我和彩云是一双,这就是我们的区别。有时候我看着黄世充,我想他羡慕我是对的,要是换一下,假如黄世充过着的是那样的一种日子,我是黄世充,我也会心生羡慕的,这个世界上,有谁不想好呢?看见别人有出处,有归宿,成双结队,如胶似漆,怎么会不觉得好呢。所以,照眼前的情形来看,我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了,一个守城门的小兵,还要怎么样呢?杭州的知府大人、总兵大人,浙江的巡抚大人,很难说他们就一定活得比我好,他们的麻烦,我们只是不知道罢了。可是后来,我没有想到,这样的日子竟然不知不觉地越来越少了,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再后来,就完全没有了。黄世充也很快就不再羡慕我了,平日里,神情言语之间,倒像是处处都在可怜我,用一种我不太能够明白不大能看得懂的眼神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疑疑惑惑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没有人告诉我,每天就只能把那种如同刚刚拱出来的草芽般的疑惑带在身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别看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并不轻松,比直接在身上背一个包袱或口袋更让人难受、吃力。当我回家的时候,再也看不见彩云站在家门口等我了,想起以前的那些情景时,竟觉得像是一个梦一样,一醒过来,颜色褪尽,荒芜一片。不等就不等吧,我想,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一个哪能天天站在门口等另一个呢,那是多么胡闹,多么孩子气!而过日子是不能有孩子气的,更不能胡闹。彩云不再在门口等我,有什么不对么?没有。我想,不对的应该是我,是我不对,我没有弄清楚过日子的含义,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过,自以为明白,实际上却什么都不懂,只是在装模作样地瞎混。是的,就是这样。我回到家里,看见彩云一个人坐着,也没有做饭,还有的时候是面朝墙躺着,一动不动,像是在那里躺了有几百年了。问她,她也不说,扳她的肩膀,她也不动。一开始的时候,我还努力地说一些笑话,搜寻一些街市上的觉得好笑的事情,想让她高兴,但很快就发现,不知是那些事情本身不好笑,还是彩云根本就不想笑,无论说多少,她都没有笑过,反倒是说笑话的人本身变得有些好笑和可怜。我没办法了。我拿着刀从家里出来,往城门口走的时候,一路上我都在想,彩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突然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呢?每天我都在想,站着想,坐着想,躺着想,甚至连睡着以后也还在想,但没有一次能想清楚,反倒是越想越糊涂,越不明白,眼前和心里的浓雾般的重物越堆越多。在城门口值日的时候,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我在心里说,彩云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我是干什么的,我活在世上,有一多半就是为了听你说的,听你像柳絮一样慢慢地飘舞,慢慢地说的。窗前的竹竿上晾着她的衣裳,我忽然想起有一回看见她一个人站在那几件衣裳下面,眼里含满了烟水一样的东西。或许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觉得世上最难懂最不好琢磨的莫过于女人了,一看见一个女人,我就会从心里发抖。为什么发抖?还能为什么,当然是怕她们,让她们吓得。
在杭州的这一辈子,我只活了二十几岁就死了,严格地来说,那也不能叫做一辈子,因为从头至尾,满打满算也只有那么二十几年。守了几年城门,突然就死了,对于杭州的大营来说,少了一个兵,和没少的时候一模一样,西门那边很快就又有人补上了,一个长着一张红扑扑的脸的年轻后生提着刀出现在那里。我说突然,是因为我对我的死完全没有料到,没有想过,事先一点儿准备也没有,我没想到我还那么年轻就会死,而且是真的说死就死了。穷我不怕,命不好也不怕,我已做好了要活下去就必须要受苦受罪的准备,但是,突然一下,就什么也不需要我再准备了,准备好的也都用不着了。
我是怎么死的?二十多岁的人,那还能怎么死,肯定不是老死的,当然是被害死的。是的,就是被人害死的,害死我的就是这些年来我在杭州城里最亲近也是最熟悉的两个人,就是彩云和黄世充。
正是一年中的端午时节,杭州城里飘满了粽子的香气,彩云和黄世充在粽子里包了毒,他们为我准备了七个粽子,但我只吃了两个就不行了。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我不知道。每个月里,逢单日我在城门口值日,逢双日是黄世冲当值,当我在城门口站着的时候,黄世充就到我的家里去,在我的家里坐着,躺着这是黄世充亲口告诉我的。在亲眼看着我吃完两个粽子以后,他像搬一件东西一样把我搬到一张席子上,然后笑了一下。
我在城门口站着,他们在家里躺着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觉得整个杭州城都变了颜色,彤云密布,大雨滂沱,全城像一艘千疮百孔的船,到处都在漏水,我听见我前面的院子里在咕咚咕咚地冒泡,房后在跑水。我说:外面的雨好像越来越大了黄世充说:大不大和你也没有多少相干了。我又问他:彩云呢?别让雨把她淋着。黄世充说:这个也不劳你费心。听到这些,我不再问了,我闭上了眼睛。
彩云又有了笑脸。或许正是因为看到彩云的笑脸,我才从来没有给他们两个人托过那种布满鬼影的噩梦,也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屋里吓唬过他们,这样的事情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亲眼看到,他们活得也十分不易,我要是每天躲在一个角落里或哭或笑,他们也会活不下去,光是吓也吓死了。黄世充还在西门的城门口值日,每天天还没黑的时候,他们就早早地关了门,他们开始活得拘束,小心,两个人甚至连日常的笑话都不敢说,尤其是彩云,一听见门外有响动,立刻就会吓得面色如土,手里的勺子或剪子像受了惊的马一样突然跳起来,窜出去,叮叮当当地叫唤起来,这是家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要是黄世充在,情形稍微会好一些。但是,彩云不知道黄世充的心里也暗藏着麻烦,当黄世充在城门口站着的时候,他总担心会有人像他曾经那样逢单日或双日在他的家里坐着或躺着,担心往日的情景会重现,作为一个过来人,他本人尤其明白这些,深知其中的弯弯和道道。回了家,又担心我会找他报仇。
人世间与我已没有瓜葛,我终于能够旁观这些了,当我在杭州城里到处飘荡的时候,我就像一缕风,一片叶子,一面圆圆的小镜子。
有时候,夜深人静时从我原来的家门前经过,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进去了,再也不能在那里吃饭睡觉了,不管有多熟悉都不行了。我看见我的那个小院子,两间房子,一砖一木,房檐下挂着的干鱼、腊肉、霉干菜、坏了的蚊帐,还有那个我亲手一锹一锹一锄一锄地开辟出来的小菜园子和花畦,里面的腊梅还活着,芍药和凤仙花也活着,但玫瑰和美人蕉却都已经死了,菊花也死了,像我一样地死了;看见门楣上方的用白纸包着的一包南瓜籽还在,没有人动过;看见我们的两扇门静悄悄地关着,门上的门神几乎没有了,右边的尉迟敬德连人带兵器都不见了,左边的秦琼只剩下一张脸;看见屋里亮着灯,彩云和黄世充在吵架。
看见他们在吵架,扔东西,我很难过,拼死拼活,两个人好不容易到了一起,为什么又要吵呢?看见黄世充那样对待彩云,我很着急,也很生气,我也很想害死他。可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死了,如果黄世充再死了,那彩云怎么办呢?此前,我的那位辛辛苦苦地吹了几十年糖人的岳父也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样一来,彩云就再没有一个亲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人。我们都死了,把她一个人剩下,撇在那里一想起这些,伤心就会来找我,就会像杭州城里的月色一样,像端午天粽子里的毒药一样,渗进我的眼里和心里。
有一天,我终于走了,永远地离开了那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