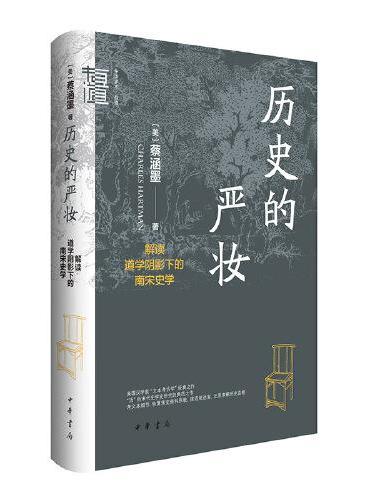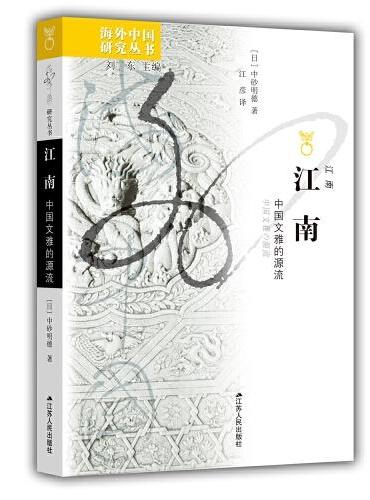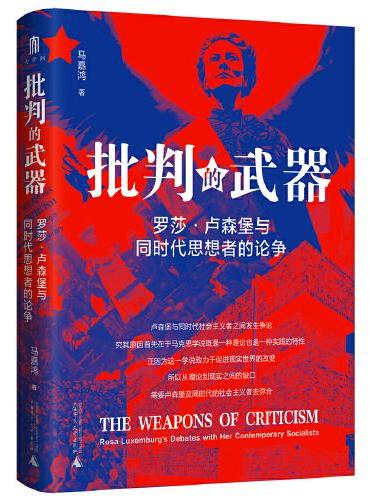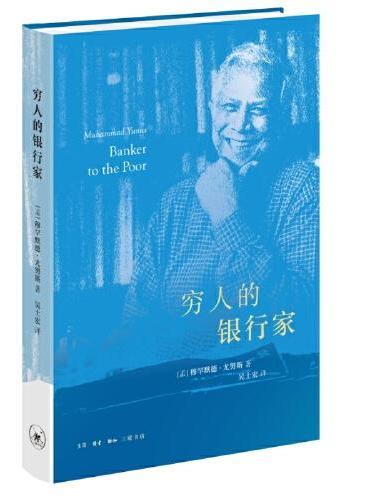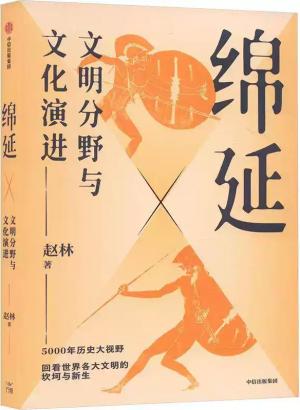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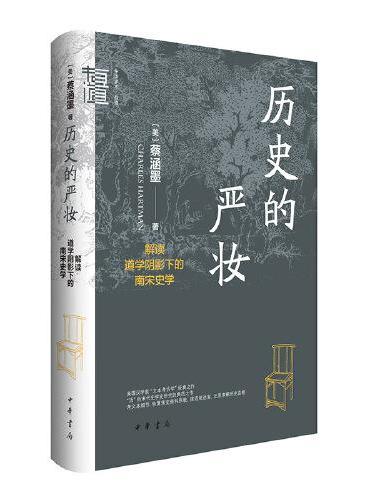
《
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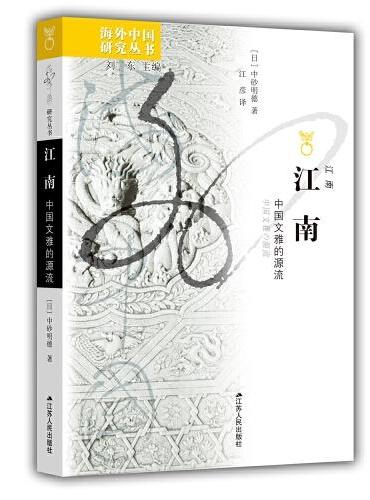
《
海外中国研究·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
》
售價:HK$
76.2

《
迟缓的巨人:“大而不能倒”的反思与人性化转向
》
售價:HK$
77.3

《
我们去往何方:身体、身份和个人价值
》
售價:HK$
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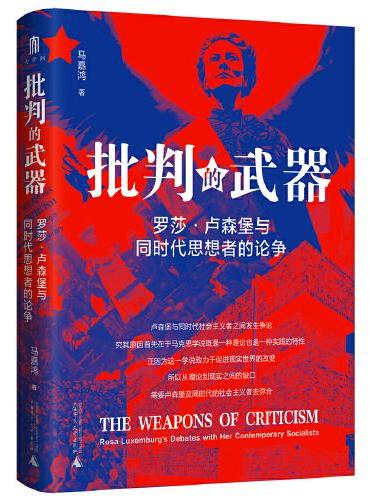
《
大学问·批判的武器:罗莎·卢森堡与同时代思想者的论争
》
售價:HK$
98.6

《
低薪困境:剖析日本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
》
售價:HK$
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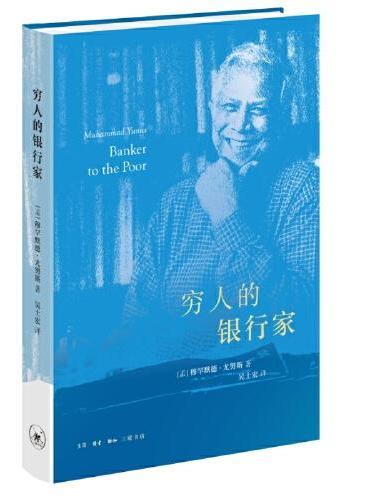
《
穷人的银行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自传)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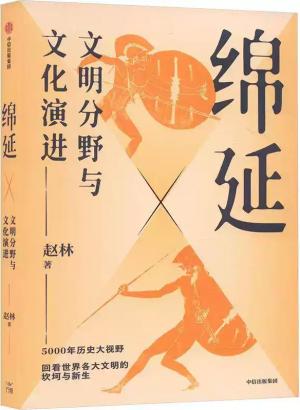
《
绵延:文明分野与文化演进
》
售價:HK$
66.1
|
| 編輯推薦: |
|
陈子善教授挖掘出的又一值得纪念却被忽略的一位戏剧家。他是中国话剧史上值得纪念和研究的“先知先觉”。
|
| 內容簡介: |
|
本书选录了作者关于中国戏曲、西洋戏剧和现代话剧的并不过于专门的论述,以及序跋和若干回忆性散文。附录乃宋春舫之子宋淇(笔名林以亮)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此文详细考证毛姆与宋春舫的那段文字交,并对宋春舫的戏剧观作了精彩的阐述。
|
| 關於作者: |
宋春舫(1892-1938),别署春润庐主人,浙江吴兴今湖州人,王国维的表弟,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是我国现代剧坛上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戏剧及理论的一位学者。他在旧剧改革,新思潮的引进和介绍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理论思想和剧作在中国话剧史上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创作的剧本有独幕喜剧《一幅财神》,三幕喜剧《五里雾中》和《原来是梦》。
宋春舫又是一位藏书家,1931年,宋春舫“斥金四千,始建褐木庐于青岛之滨”,将平生所收集的戏剧图书囊括其中。
|
| 目錄:
|
北平
我不小觑平剧
中国戏剧社的回溯
看了俄国“舞队”以后联想到中国的武戏
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
论戏剧的对白
戏院观众纵横谈
谈戏剧杂志
话剧的将来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褐木庐藏戏曲书写目》自序
《宋春舫戏曲集》第一集序
《五里雾中》之经过
《原来是梦》序
宋家弄
从“家”忽然想到搬家
海草
附录:毛姆与我的父亲 林以亮
|
| 內容試閱:
|
北平
这是十数年前的回忆!民国十二年正月十八日那一天,北平美育社,假座真光剧场,开歌舞大会,目的是筹款救济北京四郊的贫民。无论哪一社的中坚分子,总是女性居多,美育社当然也逃不出例外,如唐宝潮夫人,陆小曼女士,陈贯一夫人等,不消说个个都是旧都社交上数一数二的人物,我因平日喜欢研究戏曲,居然也忝附骥尾,当了美育社社友来凑热闹。我第一个感想,“预演”即英文之Dress
Rehearsal两个字。在当时可以算得一个时髦名词。何谓时髦名词,为普通人十中有九是不知道的。至于预演与排演,完全是两件事,吾国戏院,向来只有排演,没有预演,他们平日所登的广告中,有“排演成熟,择吉开演”便是一个绝好的证据。正式开演与预演,手续上讲起来,却毫无区别。性质上呢,“正式开演”是公开的,“预演”却是私人的。历来欧美各戏院,每逢新戏登场前一天的晚上,发帖邀请各报馆的评剧主任,及记者,以及国内的名流巨绅,文学大家,社交明星等等,近年来,或者因为经济状况困迫的缘故,也有临时卖票的,票价是不消说,比平时便宜数倍,而观众却都是知识阶级中人,大学学生,占大多数。那一次美育社的预演,也是如法炮制,票是卖的,只卖给学生们。预演的目的,是有两种:第一,预演是带些广告性质,评剧家及新闻记者,看了以后,翌日必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一番议论,引起一班人的兴味,这本来是他们的天职呀!第二,也是预演与排演不同的地方,在排演的时候,只有极少数人——在欧美是只有舞台监督——在那里监督。预演的时候,观众都在那里监督。“袍笏登场”“十目所视”,心理上的作用,当然不同,而演剧者,亦不肯像排演的时候,那样敷衍了事,至于观众一方面,预演既然是非正式的,舞台的布置,伶人的唱作,即偶有不妥,也不去求全责备,尝试者既有此种种精神上的鼓励,更可奋勇从事了。我第二个感想,就是北京人看戏的程度实在是比上海人高得多。这一次不是男女合演么?在一个男女尚且要分座的北京城中,男女合演居然能成事实,而且演戏的时候,不必挂什么
“奉警厅谕禁止怪声喝彩”的木牌,也没有人来“好吗,好乖乖”的高声叫好。报上记载,都说“大家闺秀,粉墨登场,为破天荒之盛举”云云,以如此这般的鼓吹,在社会上,那个时候却并没有引起丝毫反响,而同时素称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一个徐太夫人出来唱了几出昆曲,就闹了一个满城风雨,不亦乐乎,这毕竟是此胜于彼了。吾末后一个感想,并且是一个最普通的感想——就是法人米落霸那本《六二八》书中所说,米先生是在彼国最先有汽车的一人。有一天他很高兴自驾了他的那一辆第“六二八”号汽车,到处乱跑,经过了不少村庄和国境,他书中有一段,说:“最煞人风景的,是红日归山时候,忽然从路旁窜出一群村犬,先向着那车头乱吠,接着又想和汽车比赛,一口气便跑了一里左右,它们才觉得有些力乏了。一会儿,他又遇到了一群白鹅,很规规矩矩的排了队,在那里羊肠路上走,好容易,费了许多劲儿,才跑过他们面前,但是不到五分钟,他又遇到一群绵羊,平日绵羊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到了那时,不知如何他忽然心头起火,忍不住,说了一句Nom
de
Dieu,刚巧他的那句话出口的时候,那赶羊的老头儿,手里拿了一根棍儿,远远地向他扬着,仿佛想和他来要决斗一般。”“鸡,鹅,羊”在开驶汽车的人方面说来,都是很可厌的,但还不如人来得讨厌。至于我呢,觉得人在世界上,不做事则已,如果要做些事,须学着米落霸的口吻,“天下各事,都容易对付,惟有人,却最不容易对付的。”你看十八日那天晚上,正在锣鼓喧阗,戏码将到大轴的时候,剧场里忽然冲出一个人来,口里不住的喊道,“反了反了,男女合演,是何等的伤风败俗,中华民国,照这样下去,是立刻要没有的了,警厅一定得来禁止,否则……”但一头说,一头就要警厅的电话,叽哩咕噜,闹了好一会,警厅那里,也没有人去理会他,他兀的面红赤颈的,仿佛猴子在那里戴那帽儿唱戏文一般。后来我们一位招待员看了他可怜,便问他:“你到底闹些什么?”他说:“我么,只要你们将票钱还我,便了。”
原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人间世》第八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