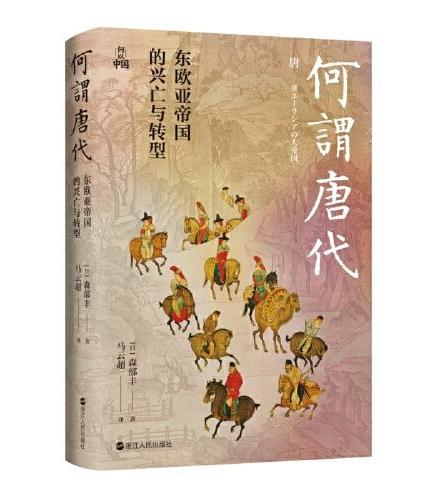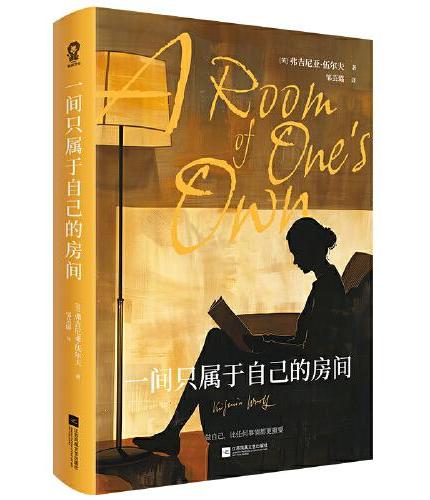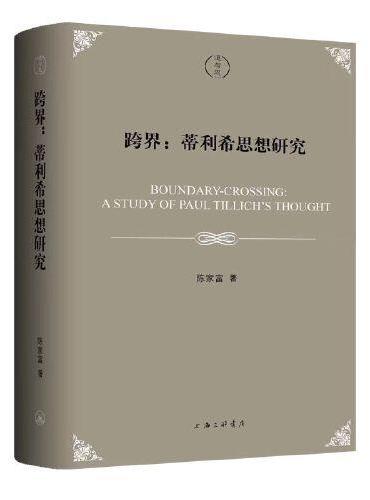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 售價:HK$
55.2
《
何以中国·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 售價:HK$
89.7
《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代表作 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象征,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 售價:HK$
45.8
《
泉舆日志 幻想世界宝石生物图鉴
》 售價:HK$
137.8
《
养育女孩 : 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1.8
《
跨界:蒂利希思想研究
》 售價:HK$
109.8
《
千万别喝南瓜汤(遵守规则绘本)
》 售價:HK$
45.9
《
大模型启示录
》 售價:HK$
115.0
編輯推薦:
一部讲述19世纪英俄“大博弈”的国际关系史著作。殷之光、章永乐、魏磊杰推荐;作为一部通史,以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为主轴,将大量史实脉络清晰地串联了起来。英俄冷战,跨越近一个世纪,涉及中亚汗国、奥斯曼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众多国家,史实庞杂。本书以通史的写作方式,将零碎的史实串联了起来;聚焦19世纪的地缘政治,阐释其中的权力逻辑。英俄冷战,恰是19世纪最强大的海权国和陆权国之间的对抗,本书阐述了这一时期各种著名的地缘政治思想,如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地理枢纽论等,并通过梳理两国的军事、外交等行为揭示其不同时期的战略思想;为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横向比较历史视野。本书讲述了“大博弈”背景之下具有相似遭遇的土耳其、埃及等帝国与晚清中国,将晚清中国置于全球视角之下,探讨世界局势对晚清政局、边疆的影响,为我们认识晚清局势和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更丰富的视野;含有殷切的现实关怀,对理解当今国际关系具有借鉴意义。本书的写作始于强烈的现实关怀,目的在于以19世纪发生于中亚的英俄冷战,为理解今天的国际局势、国家关系及国家战略提供借鉴;逻辑清晰,语言生动。本书逻辑清晰、详略得当地讲述了英俄“大博弈”近
內容簡介:
从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初,海洋霸主英国与陆上强国俄国进行了一场长达近百年的较量,即“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也被叫作“大博弈”。本书以“大博弈”中的两个焦点——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为脉络,梳理了英俄双方在“大博弈”中的军事与外交行为,生动描绘了这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力量角逐,并聚焦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阐释其中的权力逻辑,讨论了19世纪的地缘政治思想。本书将晚清中国置于全球视角之下,为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横向比较历史视野,也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现代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义,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视角。
關於作者:
傅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著有《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等。
目錄
导论
內容試閱
导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