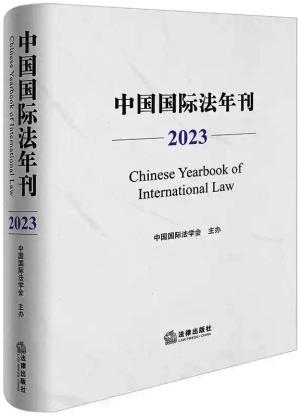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壹):《命训》诸篇
》
售價:HK$
92.0

《
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导论(光启文库)
》
售價:HK$
66.7

《
虚弱的反攻:开禧北伐
》
售價:HK$
92.0

《
泰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法国汉学经典译丛)
》
售價:HK$
81.4

《
花外集斠箋
》
售價:HK$
151.0

《
有兽焉.8
》
售價:HK$
68.8

《
大学问·明清经济史讲稿
》
售價:HK$
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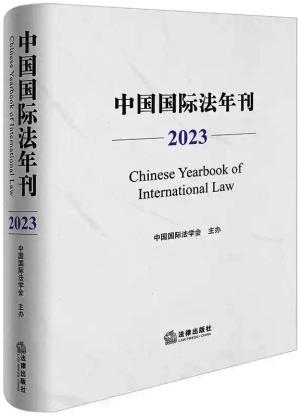
《
中国国际法年刊(2023)
》
售價:HK$
115.6
|
| 編輯推薦: |
|
? 本雅明的纯文学作品,临终前交巴塔耶保管,四十年后才由阿甘本发现
|
| 內容簡介: |
|
《十四行诗》是瓦尔特?本雅明非常罕见的文学作品,一共八十首。本雅明在一九四〇年自杀前,将诗作连同其他手稿一齐转交乔治?巴塔耶保管,存放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直到一九八一年才由吉奥乔?阿甘本重新发现。这八十首诗均创作于作者的青年时代,是作者思想转型时期的重要见证,对理解、研究本雅明和德语诗歌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
| 關於作者: |
|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批判理论家、美学家、散文家。他本人的思想极难归类,常与德国观念论、浪漫主义文艺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犹太神秘主义等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具备了高度的原创性。他的思想对后世的美学理论、文艺批评、历史唯物论等都有着重要影响。
|
| 內容試閱:
|
|
精彩内容节选生与死之环, 梦与歌之链——本雅明《十四行诗》校译者序 李双志 谁如果曾在他以巴洛克悲苦剧为题而营造出的文字迷宫里逡巡,谁如果曾在消失的灵晕与拱廊街的发达资本景观前惊叹他的思想的吉光片羽,谁如果曾追随他以轻灵的步态游荡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柏林,也许对面前这些诗行会感觉诧异与疑惑:这也是瓦尔特?本雅明吗?的确,他留给后世的文名,是跳脱出学院拘囿而笔墨纵横的评论家,是兼有敏锐洞见与卓尔文风的思想家,或者,如阿多诺所言,是一流的散文作家,但唯独不是诗人。当然,他无疑是爱诗也爱写诗人的。他所写的都是诗人中的诗人:歌德、荷尔德林、波德莱尔。可他自己确实也写过诗,他写诗远在他写出众多广为人知而回响不绝的理论著述与散文作品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世人与学界多以为这些年少的诗作早已湮没,一九八一年却有人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里找到了它们,从此本雅明自己的文字星空里补上了一角奇特的星丛。这些重见天日的本雅明的诗歌都是十四行诗。其中七十三首是他自己集为一个整体的组诗,都是悼亡诗,所悼者也是同一人: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海因勒(Christoph Friedrich Heinle),朋友称其为弗里茨?海因勒。一九一三年,本雅明结识了同在弗赖堡求学,小他两岁的海因勒,两人成为挚友,都参加了当时在德国盛行一时的青年运动,并一起换到柏林大学就读。本雅明一直钦佩海因勒的诗歌天赋。一九一四年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因勒陷入绝望,与自己的女友携手自杀身亡。为了纪念亡友,本雅明自一九一五年开始写十四行诗,断断续续写到了一九二五年,写成者都未发表,只以手稿留传下来。从情感缘起而论,这组十四行诗无疑是私密的,是作者构造出的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也是生与死的对话,这对话起于绵延不绝的情谊,终于绵延不绝的记忆。本雅明的研究者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在这些诗作中寻找本雅明评论过的诗人前辈的影迹。尤其是荷尔德林,必定在此留有余音。本雅明自己就将荷尔德林的《帕特默斯》中的一节用作了自己的诗作的题词。而他阐释荷尔德林的两首短诗《诗人之勇气》和《羞涩》的论文就写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节选的《帕特默斯》行便从死亡写起,而落于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空茫。《诗人之勇气》倒是从生写到死,不过这里是诗人之死,是一种圆满之终结,是真正成就了生命的死亡。诗歌后一节是: 同样也会消逝,如果到那时间,精神权利不减,以那时生命的庄严同样也会死亡,我们的欢乐找到美丽的完结。 正如本雅明自己在论文中所写,诗人之死是诗人与世界的同一性的显现,死亡在此开启了混沌时空的无限而非消寂于个体的终结:“在死亡这一诗人世界之中,所有被认识的关系都联合为一体。存在于死亡之中的,是境界的无限形象和无形性、时间的立体性和空间的存在、思想和感性。”而在本雅明的十四行诗中,诗人/友人之死,也同样在引发悲痛之际开启了广袤的宇宙空间供生者逡巡。不过,从悼亡诗的性质来说,本雅明更直接继承了他在评论荷尔德林时也引用过的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诺瓦利斯写组诗《夜颂》,触因之一也是其未婚妻索菲亚的早逝。然而悼亡的哀思却逐渐融入了对基督的崇拜与爱,诗中化用了《圣经?雅歌》的婚恋隐喻,引入了希腊诸神,进一步指向神、自然、人的交会感应。本雅明的十四行诗首先就动用了夜与死亡和思念的联动关系,比如第十四首开篇“我与古老之夜结盟/变得同它一样苍老”。夜在此同样不是黑暗与寂灭,而恰恰是亮光与生命流溢的空间。世间之“我”对亡故之“你”的思念如此热烈奔涌,已成为一种联结生死的爱,并在十字、颂祷、玫瑰、百合等大量《圣经》意象的环绕下,在诸神现身又离场的宇宙舞台中央,升华为此世与彼岸的情感与精神的衔接。被爱者成为引领者,在回忆中释放出灵启,爱恋者成为追随者,体验并传扬所爱者的圣名。这种对亡故青年的圣像化,这种带有准宗教色彩的深挚爱恋,以及在肉身与宇宙之间建立的对应关系,都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当时声名盛极的德国大诗人施蒂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后者在一九一三年发表的《联盟之星》就是将十六岁去世的美少年马克西米利安?克隆贝尔格(Maximilian Kronberger)树为美与光明的化身,精神的引路人,照亮颓废末世的未来之星。“星”恰巧也是本雅明在诗中频频用来指涉所恋所念之“你”或“他”的核心意象。本雅明自己也曾承认,他这一代出身德国中产阶层的少年,很难不被格奥尔格这位美学领袖的个人魅力和诗歌才华吸引。格奥尔格对他的诗歌创作和情感修辞至少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然而本雅明纪念海因勒,终究不同于格奥尔格以马克西米利安之名构建诗歌想象意义上和现实意义上的联盟。本雅明的十四行诗还是私人化的,是在虚空、哀伤、追怀、爱慕、崇拜之间来回震荡,而非仅仅往着高蹈出世的境界飞升。与这私人情感的流转奔涌相对应,本雅明的《十四行诗》也有着与歌德、荷尔德林等德国诗人一脉相承的自反观照:以诗写诗,诗中悟诗。只不过,这里更多地是以歌和梦之名。所爱者即所逝者,这是一面,而另一面是:所歌者即不朽者。梦境则成为生与死的一个通道,让消逝和永恒能在歌的媒介中融为一体。梦,当然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梦,而是尼采的悲剧哲学意义上的梦,是艺术形式的塑形功能。而歌,便是诗,是十四行体,正如其更为文雅的译名“商籁体”所暗示,是音韵之美。梦与歌都是诗这一艺术本身的化名,它们在诗中的出现,昭示了一种美的自我救赎,在这个悼亡语境中又是人与世界的美学救赎。如此来看,本雅明的《十四行诗》多少也可视作里尔克的《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的先声,正如第十二首点睛之处: 死亡或友谊,无所区别万物皆在这歌里至美之物,踏入其中。 若就十四行诗的形式而论,本雅明的这些诗严格遵循了莎士比亚时代以来的古典韵律要求,甚至到了古板的地步,而传情达意的图像和话语也往往不出浪漫派激情书写的旧制,与他日后在散文作品中的挥洒、灵动、别具一格、不落窠臼大相径庭。在现代诗歌史上,不论是他自己深入钻研的波德莱尔,还是与他同时代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诗人,都已将诗人本雅明远远抛在后面。只不过,这种保守的形式风格,或许又从另一个层面上呼应了他自己所追求的一种对亡故者的持守和对消逝者的永忆。这是少年本雅明的衷肠心曲,这又何尝不是现代性的另一面,那个不断追怀,那个渴望永恒的一面?就如第四十九首的结尾之语: 正如诗人将回忆入诗你们须能体会,爱之永恒如何被温柔回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