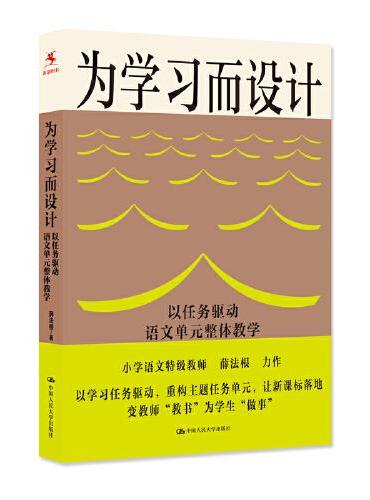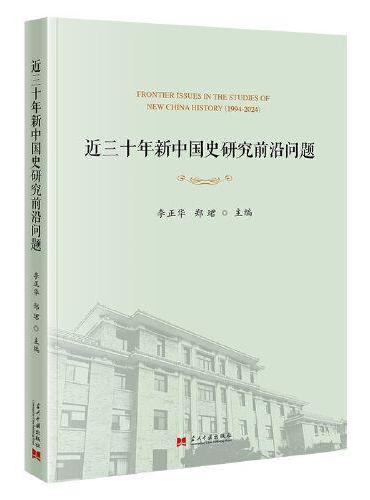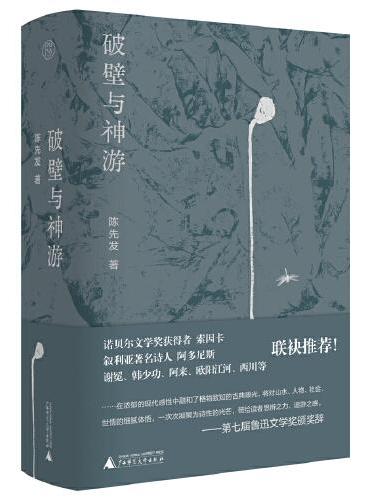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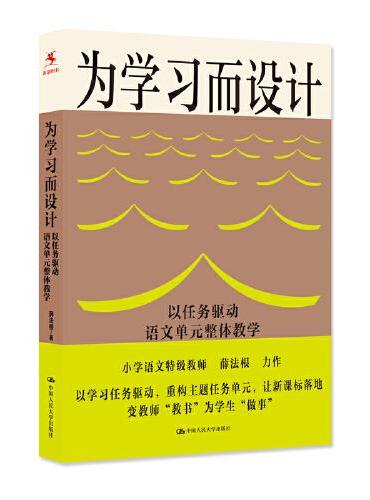
《
为学习而设计:以任务驱动语文单元整体教学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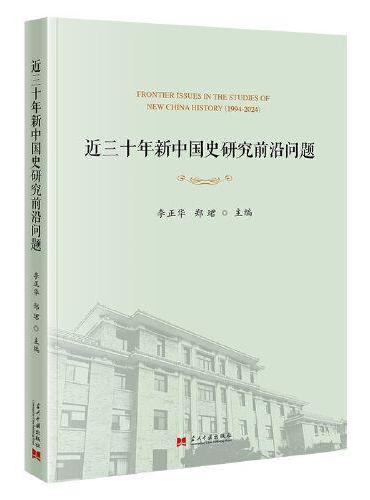
《
近三十年新中国史研究前沿问题
》
售價:HK$
107.8

《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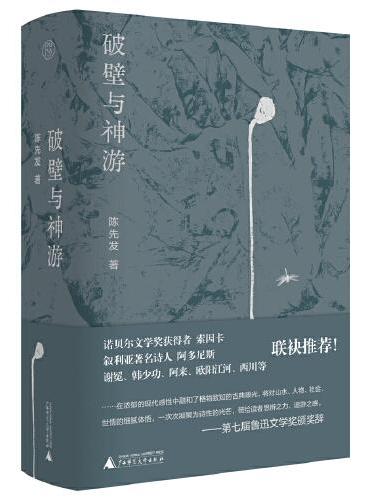
《
纯粹·破壁与神游
》
售價:HK$
90.2

《
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新版)
》
售價:HK$
96.8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
》
售價:HK$
61.6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HK$
140.8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
《信使》是一篇关涉情感和解的长篇佳作,没有在报复决绝中走向人性的绝望,而是给人以温暖的力量。作者刘荣书以“一种同情心同理心去贴近人物,走进其内心深处,了解其最为幽微隐秘的心灵深处的悸动,捕捉人物生命升华的每一个瞬间。”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正面人物退休警察曹河运、女主人公江一妍、信使男孩儿,还是反面人物谢主任、谢战旗、陆家良等,一方面展现了大时代背景下的命运浮沉与生存境遇,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了内心深处最为隐蔽的心灵悸动以及造成这种悸动的深层次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欲望,有的是因为原生家庭,有的是因为婚姻,有的是因为爱情,有的是因为救赎。信使男孩儿、曹河运、陆家良都在曾经的沉沦中极尽可能地救赎他人、救赎自己,作者写出了人类共通的故事、共痛的情感体验,共思人生的意义。
|
| 內容簡介: |
|
《信使》讲述了一个生动曲折的案情故事,通过对一桩陈年旧案重新走访与追索,各色人等相继出场。女主人公江一妍在即将举办婚礼前突然决定返回曾令她伤心欲绝的故土——黑山县,她的父母都死于当地的一桩大案之中——风河谷案,想同过去的生活达成和解。侦办警察曹河运,虽然通过此案的侦破获得了晋升,却从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心灵包袱,希望通过对当年案件的再次梳理、侦破,要将真凶缉拿归案。当所有的案情都指向了当年送信的男孩儿——“黑暗信使”时,故事却出现了反转,此“黑暗信使”却是“光明信使”……
|
| 關於作者: |
|
刘荣书,满族,河北省滦南县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多种文学期刊,著有长篇小说《党小组》《望烽烟》《一夜长于百年》,中短篇小说集《冰宫殿》《追赶养蜂人》《溯河春醒》,其中《党小组》被改编为谍战剧《前行者》,《枪毙》《扯票》等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
|
| 內容試閱:
|
我细算了一下,一九九○年秋天以后
我再没有收到过一封信
我也,再没有寄出过一封信
我觉得这些年生活空白的部分
是因为信使不知所踪
——雪舟《信使》
第一章 对一宗命案的回忆
一
故事开始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
那一年,曹河运五十岁,已到知天命的年纪。以前,他只是黑山县下辖某乡镇的一名治安协理员,每天在乡下,管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三十二岁时来运转,抽调到县公安局,参与一起命案的侦办工作。因为表现出色,被县公安局领导看中。一纸调令,将他调到黑山县刑警大队,成为一名正式警员。户口问题、家属的“农转非”问题,随后都给解决了。
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立志要在工作中干出名堂,“要对得起身上的这身警服”。这不是誓言胜似誓言的话,只是遵从了他做人的本分。他从一名普通刑警做起,任劳任怨,直至升任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一职——就是在这样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上,再也看不到事业上升的机会。
众所周知,干刑警这一行,凭的是资质和精力。资质无须多谈,精力对曹河运来说,似已达到上限。过了四十八岁,留给他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他开始脱发、失眠,和老婆一两个月也没有一次性生活……但这些极易挫败中年男人自信心的生理现象,并不能让曹河运感到沮丧。令他深感沮丧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天早上,他去早市买菜。碰到一个小偷,笨手笨脚正从一位大爷的裤兜儿里顺钱夹子。擒贼是他的本分,自然不会含糊。他咳嗽一声,意图对那小偷发出警告。
黑山县区域范围内的惯偷,大多和他是老相识了。有时在街上碰到,单看表情,也能揣摩他们是否具备作案动机。有时,他会跟他们打声招呼:“咋样?最近手痒没痒啊?”对方并不介意,觍着脸说:“痒倒是不痒。有您在,痒了只能往墙上蹭蹭。”若有小偷正在作案,被他撞个正着,无须动手,只需一个眼神,一个具有震慑性的动作(比如一声咳嗽什么的),小偷便会如避猫鼠似的,束手就擒,主动交出赃物。
可这个小偷,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听到那一声咳嗽,非但没有收敛,反而瞪了他一眼。无疑,这应该是个二愣子货,外地过来的流窜犯也说不定。
曹河运二话不说,上前薅住小偷的手腕,欲将其制服。不料,却被那小子反手挣脱。对方顺势将他推倒在地。他撞翻一篮子鸡蛋,又用胳膊肘戳烂了另一篮子鸡蛋。
那天,幸好穿的是便服,不然人可就丢大了。路人看曹河运,只见他浅灰色褂子上沾满蛋液和蛋壳,抬手抹脸,又弄了个满脸花。一位熟人打此路过,大呼小叫道:“老曹,这,这是咋了,谁欺负你了?”
曹河运绷着脸,一声不吭,瞄住小偷的背影,奋力追了上去。三番五次,每次将要赶上,只余两三步的距离,却只顾手扶膝盖,停在原地喘气。小偷最终看穿他的本事,不像刚开始那样怕了。跑几步,便会停下来,扬着下巴颏儿,冲他挤眉弄眼。只待他起身再追,这才拔脚跑开。本来一场“猫抓老鼠”的捕猎,成了一场“老鼠戏猫”的游戏。一条无人的巷子里,小偷冲着曹河运跷了跷小拇指,打一声呼哨,扬长而去。
待到曹河运缓过劲来,去找自行车,却被卖鸡蛋的大嫂扣住。他糟蹋了人家两篮子鸡蛋,不赔钱,人家断不会放他走的。他嫌丢人,没敢提自己的身份,只能拿家里的半个月菜金赔钱了事。
那个秋天的早晨,无疑是曹河运从警以来遭遇到的最为不堪的一次羞辱。由此,他也便看清了自己的命途——作为曾经的一介农民,一无学历、二无背景,能干到副大队长一职,“也算你家祖坟冒青烟了”(这是他妈常对他说的一句原话)。此后,若不能侦办几宗在警界叫得响的案子,只能成为一枚弃子,转到一个不疼不痒的岗位,慢慢熬到退休,混吃等死算了。
偏偏,他并非一个庸人,对升不升迁的倒不怎么看重。他看重的,是每遇一桩棘手案子,作为一把手的指挥权和调度权。之所以会有如此感触,只因他在单位受够了窝囊气。
就拿刚刚调走的大队长来说吧,虽说他读过正规的警察学校,却无半点儿实际办案经验,只是将一个如此重要的岗位,当成步入仕途的跳板。工作中,从来听不进别人的半句谏言。或许是读书读坏了脑子,往往会将一起简单的案子,想得过于复杂。而对一些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案子,意气用事,非常武断。等走过不少弯路,撞过几回南墙,这才会回到别人事先指明的方案中来。当有领导来听取汇报时,功劳自然不会旁落,别人的名字他自是提也不提……在这样一种糟糕的工作环境中,曹河运的境遇可想而知。他白白消耗着大好的年华,脾气又不好,不懂圆融。不像另一位与他平起平坐的副大队长,工作能力虽然欠缺,却是个地道的人精——和这样的领导、同事共处,曹河运的刑警生涯注定不会顺利。
但他却不肯放弃。十几年的时间下来,非但对工作没有半分敷衍,还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了《刑事侦查学》《犯罪现场勘查》《法医学》《犯罪心理学》等专业书籍,《福尔摩斯探案集》《施公案》这类探案小说,也多有涉猎。他在沉寂中等待。他常常将自己想象成一头隐伏山林的豹子,冥冥中觉得,总会等来一次啸叫山林的机会。
奇怪的是,自从他正式干上刑警这一行,五十多万人口的黑山县,再没出过一宗像样的案子。
就是在这一年,一九八六年的六月,曹河运记得非常清楚。他负责对一封联名举报信展开调查,起初并未怎么上心,却没想到,这正是他命运转折的一个开始。
在更早一些时候,黑山县少年宫的管理方贴出过一张出租广告,将一间三百多平方米的舞蹈教室面向社会出租。至于出租后具体做了什么,已无赘述的必要。到了这一年的四月,几经转兑,曾经的舞蹈教室,改为对外营业的舞厅,问题随之而来。
舞厅这种东西,在当时黑山县人的心目中,应该算是一种新鲜事物。
据举报信中所说,这里每天歌舞声不歇,男盗女娼之辈闻风而来,全无风雅之态,是对书声琅琅、琴音袅袅的少年宫的肆意践踏。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承包者毫无道德底线,在厅内隔出数间包房,招来一些不三不四的女子,专为客人提供陪酒服务。真是造孽呀!衣着暴露的陪酒女,大白天的也敢在少年宫大院和客人亲嘴儿。有一次,几个醉醺醺的男人走错了地方,竟然闯进正在上课的美术班教室,当着孩子们的面,嚷嚷着要找小姐。小姐是什么玩意儿?那可是旧时代的产物。在新的时代,属于糟粕……举报信的最后,联名举报的孩子们,以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这样痛心疾首地写道:“警察叔叔,救救我们吧。我们的琴房和厕所过道,就在舞厅楼下,那里到处都扔有用过的卫生纸、避孕套、卫生巾之类的脏东西,我们不敢从那里经过。一怕摔倒,二怕染上脏病,更怕被这些糟粕玷污了我们幼小而纯洁的心灵。”
曹河运走进少年宫小剧场。演出已开始,没人会注意到他。实际上,他出现在这里,也属于临时起意。
这场由全县小学生参加的“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有他二女儿的身影。起初,二女儿是合唱队的一员,由于排练期间感冒嗓子肿了,被老师放弃,为此不开心了好一阵子。直到演出进入倒计时阶段,又接到通知,可以登台,不用发声,只在台上对对口型就好了。女儿虽没有邀请家长来观看演出的意愿,可在曹河运想来,若出其不意,对女儿的表演做一番客观又中肯的评价,说不定会给女儿带来意外的惊喜。
一个小合唱节目结束之后,曹河运也没能在舞台上找到女儿的身影。此时,整场文艺演出已接近尾声。候场的间歇,前排坐着的孩子们不时会发出一阵“嘤嗡”的低语。只待报幕员离场,一束椭圆形灯光自上而下,悬置在舞台中央,周围瞬时变得安静下来。曹河运不禁感到一阵恍惚。直到前排的孩子们再次发出一阵“嘤嗡”的低语(那显然是一种崇拜的表现),这才看到,一个神态端庄的小女孩儿,身形款款,从舞台深处走上来,站在舞台中央。
他已“老眼昏花”,虽能看清女孩儿身上衣服的颜色,却无法看清她的脸;他能看清光柱里浮荡的尘埃,如银亮细小的箔,却仍旧看不清她的脸。只是觉得她的出场,令人眼前一亮。她身上穿着一件粉红色连衣裙,在灯光的照射下,如一团迷雾氤氲斑驳。如今想来,更像一个不太真实的幻梦。是的,是一个幻梦。要不然,他怎么会从台下那一张张稚气未脱的面庞中,找出一张男孩儿的脸呢?他凝神看着他,看着那双因痴迷而显得过于沉醉的眼睛。要知道,在当时,他可是坐在剧场的后排,不可能面对观众……这种发现,更像一个悖论。在其后的无数次回忆中,曹河运还会拨开时间的迷雾,与正处盛年的自己相逢——为此他会忧伤不已。他怜惜地看着那个胡子拉碴、神情落寞的中年男人,看着他时而眉头微蹙,时而茫然四顾,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我们的生活多愉快,娃哈哈娃哈哈,我们的生活多——愉——快。”
女孩儿嗓音稚嫩,表演略有浮夸之嫌。唱功虽不敢恭维,发出的“快”字音节,高音部分根本挑不上去,唱成了破音,却有足够的表演经验。用一个花哨动作,将唱功上的瑕疵轻松掩饰过去。她脚上穿一双在当时十分罕有的皮鞋(其他参演的孩子们,穿的可都是白球鞋),黑鞋、白袜,鞋尖杵地,左点一下,右点一下,以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旋转动作,给整个表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后凝神伫立,胸腔起伏,十指微跷,托住脸腮,恰似一朵沐浴在阳光下的祖国的花朵。
剧场内响起的掌声,将曹河运从恍惚中惊醒。受了感染,他也跟着拍了几下巴掌。
此时,警员小马躬身凑近。见曹河运一改往日做派,不禁笑了,俯在他耳边,低声说:“曹队,都整明白了。说得一点儿没错,仨男的,一人搂着一个女的,刚才进了包间。”
曹河运收起巴掌,仍神情专注地看着舞台。见那位穿粉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儿打头,一群孩子从舞台上雀跃而下,演出显然进入文艺汇演的高潮部分——给领导献花的环节。那群孩子当中,他一眼便看到了自己的女儿,不禁有些激动。意犹未尽地嘀咕一声:“还没晌午呢,这就结束了吗?”
小马听得有些不明所以,“没结束,他们刚进去……”又问,“要不,咱搂草打兔子——顺便带几个回去?”
曹河运摆手,站起来,小声说:“不急,咱先上去看看。别再逮不着狐狸,惹一身臊。”
舞厅内,二人刚找好位置坐下,只见一位留长发的青年,给邻座开完一瓶啤酒——他开啤酒的样子,看上去着实特别:两手各抓啤酒一瓶,像拎着两枚手榴弹,左右晃动,用其中一瓶啤酒,顶住另一瓶啤酒的瓶颈,掌心磕击瓶底,只听“嘭”的一声,瓶盖如一枚子弹,弹射到天花板上。这要伤了人可咋办?曹河运“咸吃萝卜淡操心”地想,看着酒液从瓶口汩汩涌出,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听到那男青年问:
“喂,啤酒,还是格瓦斯?”
“啤酒多少钱一瓶?”
“十块。”
小马或许真的渴了,或是看曹河运眼馋的样子,伸手去裤兜儿里掏钱。但他很快停手,看了一眼曹河运,显得不好意思。
“头儿,我忘带钱了,你带没带?”
曹河运更是感到难为情。在单位,他可是出了名的穷酸,总是兜儿比脸还干净。这种场合,又怎能丢了面子,便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架势,摆手将小马制止:“不喝,咱不喝那玩意儿,咱喝不惯……”说说这样的话也就算了,偏偏,他又犯了爱管闲事的老毛病,瞪一眼男青年,咋呼问道:“喂,啤酒——外面才一块钱一瓶,你们这儿卖十块?这不是哄抬物价吗?”
长发青年瞟他一眼。大概,他觉得曹河运这样的年纪,来舞厅着实有些不靠谱,况且他的穿着、长相,怎么看怎么土气。
“嫌贵?你们家自来水儿便宜。”
这样噎人的话,曹河运有肚量,听了不会动气。小马却不经事,也有为领导争面子之意,拧眉斥道:“你咋说话呢?瞧瞧你那德行。”
长发青年一愣,抬手,一巴掌扇在小马脸上。小马被打得猝不及防,二人随即动起手来。
小马虽身为警察,却是个刚来的,还没学到多大本事。况且个儿矮,动起手来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直到他亮明身份,这才稳住态势。随即报复性地,从包间内揪出一对衣衫不整的男女。
曹河运一直冷眼旁观。面对一地狼藉,却猛地意识到,一次随意性的调查,若真的查不出问题,砸了人家场子,可不太好收场。想到这儿,赶忙吆喝一声,带上两个“现行”,想迅速脱身。
二人刚走下楼梯,却被堵在大厅门口。
观看演出的领导尚未退场,大批学生蜂拥而至。只见一帮穿戴时髦的男女,紧随在二人身后。他们从楼梯上退下一步,对方便紧逼一步,嘴里叫嚷:“警察咋啦,警察就没王法啦?喝不起啤酒,还打人哪,还想把人带走哇!”
孩子们受了惊吓,整个大厅变得更加混乱。
一位瘦长脸、面容还算年轻鬓发却染霜白的女人,本已走到厅外,听到动静,回头张望,迈步朝这边儿走来。边走,边舒缓地撩着鬓发。她腹有乾坤的样子,一眼便看出曹河运的身份,略过小马,径直走到他面前,和颜悦色地问:“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
曹河运刚想回答,却被一群孩子挤得连连倒退。那位在舞台上见过的小女孩儿,恰好扑倒在他脚下,被他一把拽住。女孩儿扽着裙子,娇气地叫着:“我的鞋,我爸刚给我买的鞋……”曹河运弯腰,替她捞起皮鞋,这才顾得上抬头,冲那女人说:“我们……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
女人并无问责之意,只是认真地看他两眼,似惋惜,像提醒,摇头说:“你们执法,也该挑个时候呀。你看这么多孩子,真要造成事故,影响多不好啊。”说罢,神情冷漠,转身朝大厅外走去。
曹河运怔怔地看着她的背影,一时说不出话来。
小马凑过来问:“头儿,这女的,谁呀?”
曹河运摇头。
直到后来,他才知晓了她的身份——她和他即将侦办的一宗命案中的几个关键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整个故事来说,更像一个特殊的符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