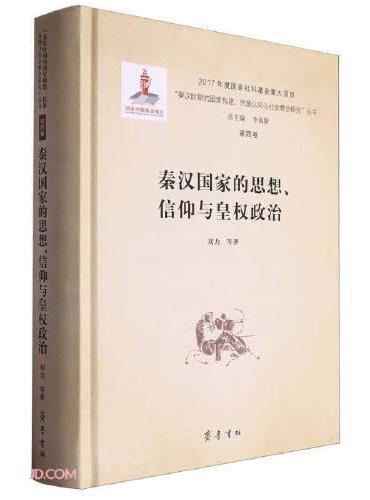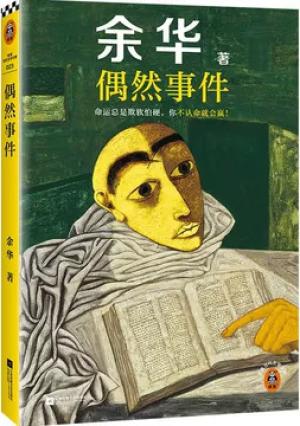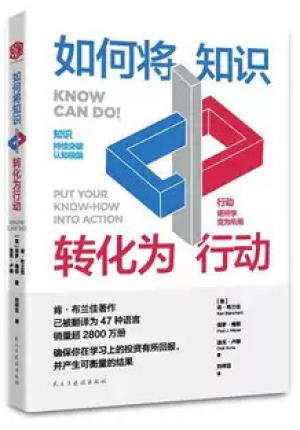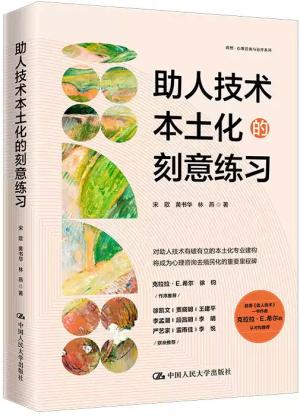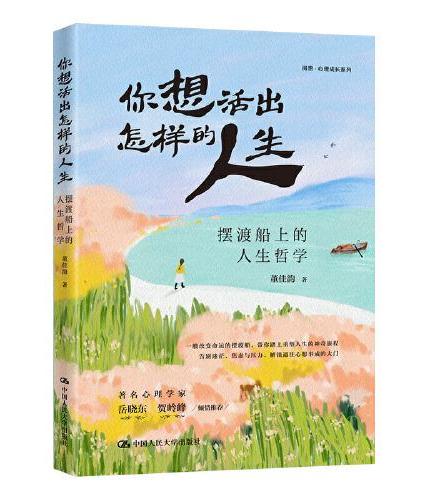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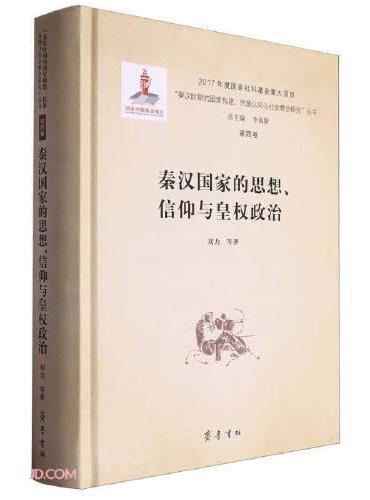
《
秦汉国家的思想、信仰与皇权政治
》
售價:HK$
215.6

《
反卷社会:打破优绩主义神话(一本直面焦虑与困境的生活哲学书!)
》
售價:HK$
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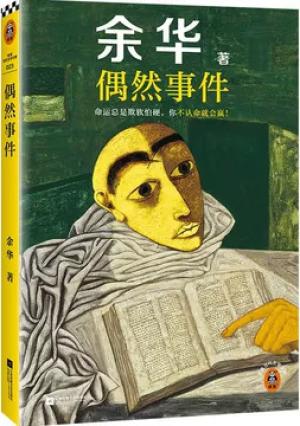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HK$
54.9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HK$
2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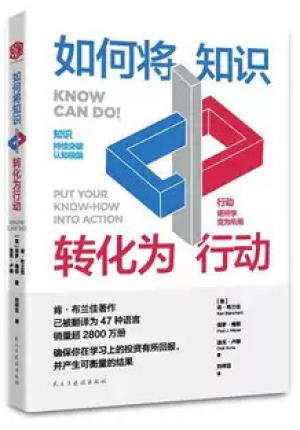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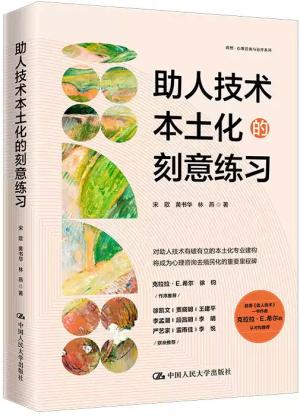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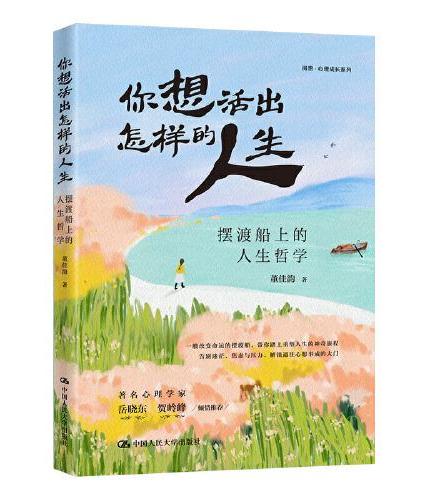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HK$
65.9
|
| 編輯推薦: |
外界危险残酷,
姐妹俩只有把自己关进摇摇欲坠的城堡,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斯蒂芬·金的启蒙导师、尼尔·盖曼的文学偶像哥特小说女王雪莉·杰克逊生前最后一部长篇
同名改编电影由泰莎·法米加(《美国恐怖故事》)、亚历山德拉·达达里奥(《白莲花度假村》)主演
|
| 內容簡介: |
|
18岁的康斯坦斯?布拉克伍德与和她性格迥异的妹妹玛丽凯特以及病怏怏的叔叔朱利安住在一幢与世隔绝的大房子里。六年前,一场离奇的下毒案夺走了其他家人的生命。人们怀疑康斯坦斯是凶手,但没有证据。他们三人反复重温过去的创伤,不断抵制变化,回避对自我的认知。村民们对他们充满了敌意。有一天,姐妹俩的堂哥查尔斯来访,其真实目的可能是姐妹放在保险箱中的家族遗产。查尔斯的到来打破了原本三人微妙的平衡。一天晚上,一场意外的大火点燃了大房子。然而,村民们并没有救火,反而朝屋中扔石头发泄恨意。逃出房子的姐妹俩在森林中互相说出了秘密。
|
| 關於作者: |
|
雪莉?杰克逊(1916-1965),美国小说家。在其所处的年代,她被认为是一个被贴有“恐怖小说家”标签的作家,但近年来,她受到批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作品已被归入美国经典文学之列。她影响了尼尔?盖曼、斯蒂芬?金等后辈作家。她的短篇小说《摸彩》是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长篇小说《邪屋》是兰登书屋“现代文库”读者票选20世纪百大英文长篇小说之一。美国中学课本至今仍有雪莉?杰克逊的文章。
|
| 內容試閱:
|
导 读 雪莉?杰克逊城堡内(外)的人生
乔纳森?勒瑟姆
十几二十年前,我常跟人玩这样的一个小把戏;我好奇它是 否依然奏效。当有人问我,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时,我会说“雪 莉?杰克逊”,并预计大部分人会说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她。这时, 我便会装模作样、洋洋得意地回答:“你读过她的作品的。”当我 的谈话者表示怀疑时,我就会描述《抽彩》 ——它依然是历史上入选文集次数最多的美国短篇小说,我打赌,肯定也是《纽约客》 发表的最具争议和最受声讨的处女作——不出所料,几秒钟内我 的“受害者们”就会惊讶地瞪大眼睛:他们不但读过它,而且永远都忘不了它。然后,大家夸我懂“读心术”,我便会欣然接受这种称赞,虽然这个小把戏实在是太过简单了。但我不认为它会失效。
杰克逊是美国小说界一种难以言说的存在,她的成就太重要了,所以不能把她称为文学界的幽灵,她的作品依然在出版销售中,所以谈不上“被重新发掘”,然而她就这么隐匿在众目睽睽之下。她既始终被低估,又始终被错误地归类为一个写高档恐怖小说的作家,事实上,她的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包含了超自然的元素(亨利?詹姆斯写了更多的鬼故事)。尽管她在写作生涯中始终受到评论者们的赞扬,但她从未被欢迎进入任何经典或流派; 她不是任何主流批评家的心头之好。杰克逊技艺上佳,备受阅读她的作家们的激赏,但称她为一名“作家眼中的作家”却显得太自以为是了。其实,雪莉?杰克逊自发表作品以来,就是一名成功的“读者眼中的作家”。她最著名的作品——《抽彩》和《邪屋》 ——比她本人更出名,而且已经作为永恒的艺术品融入了大众的文化记忆,它们似乎比实际要显得古老,像神话或原型一样让人产生共鸣。她的作品犹如民间传说般为人所熟知,哪怕是她相对不出名的作品:《查尔斯》 和《有花生的寻常一天》 (你读过这两个故事中的一个,虽然你不一定记得),以及她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
尽管杰克逊轻描淡写地间接解释过她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中的巫术元素(早期一则印在她的书勒口上的作者生平曾把她称为 “一名身体力行的业余女巫”),但她的主要题材则恰恰是超自然灵异的反面。她的作品——六部完成的长篇小说和二十多篇风格强烈的短篇小说——其不可否认的永恒核心却是一种漫无边际、触手可及、来源于日常生活的邪恶,种种平凡的人类完形 构成了这些故事的病态背景底色:一座村庄,一户人家,一个自我。她挖掘出常态中的恶毒,记录编目从众和压抑是如何沦为精神错乱、 迫害和偏执,转变成残忍、受虐和自残。像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和帕特丽夏?海史密斯一样,杰克逊的主旨是共谋和否认,以及在人与人之间奇怪流动的内疚。她的作品犹如一部此类状态的百科全书,而且能让她的读者产生一种共谋感,无论他们是否喜欢这种感觉。当然,这点在《抽彩》所引发的惊人反响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一包包谴责故事“令人作呕”“变态”和“恶毒” 的仇恨邮件,无数取消订阅的要求,还有让杰克逊永远也不要去加拿大的警告。
以《抽彩》宣告了她创作的主旋律后,杰克逊在发表《抽彩》 前刚刚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穿墙而过的路》 问世了——杰克逊致力挖掘内心深处让她自己感到恐惧的感觉,并从内部对它们发起探索。杰克逊的传记作者朱迪?奥本海默 说,在杰克逊太过短暂的人生的最后阶段,作者几乎完全沉沦在怀疑和恐惧之中, 尤其是一种悲惨且不可理喻的“广场恐惧症” ——这有点像是对她自身角色的可怕嘲弄,无论是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她文风轻快、埃尔马?邦贝克 式的畅销书《与野人同居》和《抚养恶魔》 中,她都是一名家庭主妇。然而,无论杰克逊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是多么痛苦,她的作品却变得越发凝重,从《抽彩》对狡诈权威的揭示逐渐沉淀蜕变为呈现道德的暧昧、情绪的不安和自我审视。 她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变得越来越怪异和个人化,也越来越有趣, 《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是这个转变的顶点,我认为它是杰克逊的一部杰作。
《抽彩》和《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互相交织的主题就是发生在新英格兰小镇里的迫害;两者中的小镇,都颇具辨识度,被认为是佛蒙特州的北本宁顿 。杰克逊在那里度过了她的大部分成人岁月,她是文学批评家斯坦利?埃德加?海曼 的妻子,斯坦利在附近的本宁顿大学教书。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杰克逊到佛蒙特州时就已经分身两人。一个人是战战兢兢的丑小鸭,成长过程中被一个对礼仪偏执的市郊母亲 吓坏了。这一半的杰克逊是她从一开始就才华横溢地写进短篇和长篇小说里的鲜活人物:一个羞涩的姑娘,个性难以捉摸。杰克逊的另一半是孤傲的叛逆者,她与海曼的婚姻让她不再害羞——海曼本身就是一个滔滔不绝的自负之人,典型的1950年代纽约犹太知识分子,养育四个吵闹的高需求小孩所带来的内在震撼也让她无法沉默。小镇害怕和厌恶这个雪莉?杰克逊,偶尔甚至迫害她,最后这点取决于你相信哪一个版本的故事。小镇居民对大学有种天然的排斥,作为古板狭隘乡村里的一名怪异新来者,杰克逊注定要承受大家的反犹和反智态度。乡下人的敌意帮助成就了杰克逊的艺术创作,这一过程最后产生的反作用是,后者的成功助长了前者的敌意。《抽彩》取得丑闻般轰动的成功之后,小镇上便有了一个几乎肯定是假的传说, 说的是杰克逊有一天被小学生们扔石头攻击,然后她就回家写了《抽彩》的故事。(大揭秘:1980年代初我曾在北本宁顿住过几年, 跟杰克逊在二十年前有过节的几个当地人依然在镇广场上闲逛, 《抽彩》的传奇故事正是发生在那 里。)
在《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一书中,杰克逊再度写到迫害,这一次她在强劲的笔力中融入了一些欢欣的情绪,把故事从客观的社会批评领域抽离出来,变成了一则个人寓言。杰克逊用了一个她从开始写作便致力完善的策略,即把她自己的方方面面投射到同一个故事里的不同人物身上,杰克逊把她自我的两半委派给了古怪“残缺”的两姐妹:姐姐康斯坦丝?布拉克伍德,过分敏感,整日担惊受怕,不能出门;妹妹玛丽凯特?布拉克伍德,则是一个任性、精力充沛且爱好恶作剧的人,她了解自然,适应四季更迭,习惯于死亡,显然是毒死布拉克伍德家族所有其他成员(除了朱利安叔叔)这桩未破罪案的元凶。
三名幸存者——康斯坦丝、玛丽凯特和虚弱却忙于起草书稿的朱利安叔叔——一起住在他们位于小镇外围的大房子里, 反复重温过去的创伤,不断抵制变化,始终回避对自我的认知。康斯坦丝严格按时烧饭打扫,仪式般地纪念着已经消逝的过往家庭生活;玛丽凯特则在树林里实施她的魔法,去危机四伏的镇中心购物,在那儿与村里小孩们的恐怖嘲笑作战,小孩们把布拉克伍德家的下毒案编成一个节奏单调的校园传奇故事到处宣扬。朱利安叔叔全靠康斯坦丝的照顾,他一直在慢慢地写书稿,一部家庭历史,试图以此来理解那桩让他的小世界家破人亡的事件。朱利安有点像是小说读者们的代言人,他提出 问题(“为什么砒霜没有被放在兔肉里?”),并提供对问题的推测(“我的侄女不是一个狠心的人;此外,当时她以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尽管我该死——我们都该死,难道不是吗?—— 我觉得轮不到我侄女来指出这点。”),这引发了我们对事件的好奇心,玛丽凯特,我们的叙述者,似乎特别急于忘掉这些 事件。
玛丽凯特的叙事语态——不加修饰,肆无忌惮,剃刀般尖锐——是本书的成功之处,也是贯穿这个欢乐解体的小寓言的主线。虽然玛丽凯特在全书第一段就说明自己十八岁,但她感觉上年纪更小,她的语态类似于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中的弗兰琪 ,或查尔斯?波蒂斯《大地惊雷》中的玛蒂 :一个典型的没有性经验的野丫头。不过,玛丽凯特要令人不安许多,正是 因为她已经是一名成年女子了;正在她体内升华的东西不再会被青春期化解。的确,杰克逊的特点就是,书里几乎完全不会写到性,因而不用说,性的缺失却让性无处不 在。
这是一个平静被打破的故事,原本布拉克伍德家剩下的三个人犹如壁缘 上的雕像,在大房子里过着静谧的日子。玛丽凯特把她的家庭变成了一潭死水,家庭成员就像她钉在树上的书,永远都无人阅读。堂哥查尔斯到来时,显然是为了寻找布拉克伍德家隐藏的财富(不过跟书里的其他每样东西一样,钱财像是一封失窃的信 ,就藏匿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他带来的一波混乱却并非完全是他自私的谋财任务所导致的。当朱利安叔叔提到他们的年龄时,他把我们引到了一种猜想的边缘:堂哥查尔斯三十二岁, 康斯坦丝二十八岁。没有人——玛丽凯特尤其是不可能——会说康斯坦丝类似于艾米莉?狄金森,靠一丝不苟地操持家务、庇护残疾的叔叔和危险的妹妹来淹没她的性欲,但毫无疑问,查尔斯真正象征的是:男性原则。(朱利安叔叔显然是娘娘腔,可能还是同性恋——可以确定的是,正是因为他毫无威胁性,他才被允许在下毒案中存活下来。)
玛丽凯特娴熟于交感巫术 ,她用自然界人类存在前的原始元素来对抗自然发展规律所带来的危险:先是把泥土和树叶撒在查尔斯的床上,然后是放火——把女性的堡垒烧成灰烬,也比让它被侵犯要好。在消防员抵达大宅救火的场面(“男人们拖着消防软管,大脚踏进我们的门槛,把污秽、混乱和危险带入我们的房子”“彪形大汉们从前门闯进去”“在我们前门进进出出的黑色身影”)中挖掘出一番弗洛伊德式的潜台词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就像在亨利?詹姆斯的文字中挖掘弗洛伊德式的潜台词一样简单。从奥本海默写的传记中,我们了解到雪莉?杰克逊严厉反对这类诠释,亨利?詹姆斯肯定也会反对,但我们却可能应该代表他们这么做。问题不是杰克逊的叙述没有嵌入这个题材;问题在于这个题材的内嵌具有本能的诱导性和复杂性,是很多层意思中的一层,于是把这种诠释宣扬为理解如此细腻文本 的关键会背离它原本丰富的模糊性。这本书里,性并不是唯一被升华的主题。另一个被升华的是伟大的美国禁忌——阶级地位:在《抽彩》里,潜在的阶级蔑视被冷静地具体化;《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一书中,奇怪的布拉克伍德一家意识到他们对村子的不屑一顾,也意识到他们所遭受的迫害证实了他们高贵的自我形象。
这种双重认罪是杰克逊构思的典型圈套:对她笔下的很多人物而言,沉溺于伤害之中是一种狂喜,遭受放逐、远离墨守成规的乏味群体——或家庭——不仅暗示着道德上的胜利,而且是一种波希米亚式的高人一等: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外),我们不想要任何其他生活方式。杰克逊,作为一位有名的母亲和一个痛苦的女儿,也把一个未解决的育儿争论像密码一般写进了她的小说里。在最危急的时刻,玛丽凯特撤退到了凉亭,想象她被谋杀的父母重新坐在家庭餐桌边,他们纵容她:“玛丽?凯瑟琳应该拥有她想要的一切,亲爱的。我们最爱的女儿,必须拥有任何她喜欢的东西……玛丽?凯瑟琳永远也不该受罚……玛丽?凯瑟琳必须被保护和珍爱。托马斯,把你的晚饭给你的姐姐吃,她想要再多吃一点……向我们钟爱的玛丽?凯瑟琳低头致意。”
这个场景有一种复杂的恐怖感,因为我们怀疑这些幻想既是消遣,也是对过往现实的重温。在别处,朱利安叔叔自言 自语说,不知道太过受宠的玛丽凯特是否有良心。这个主题 把《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跟二十世纪中叶那波隐含女权主义的“恶魔儿童”故事联系在一起,比如《坏种》 和《罗斯玛丽的婴儿 ,还有以两姐妹为主角的恐怖电影《兰闺惊变》 。但杰克逊的这本书更像是被品特或贝克特改写过的《坏种》——的确, 杰克逊把人生视为一座衰败城堡中的无谓传承,这让人想起两幕戏剧《快乐的日子》 中的前后对比,贝克特的维妮先是被焦土埋到腰,然后又被埋到脖子,但她自夸道:“正是这点让我感觉好极了。人改变自我适应环境的能力。人定胜天。”随着康斯坦丝和玛丽凯特的世界逐渐缩小,她们变得越发叛逆自我,随着威胁元素被彻底清除,她们的城堡越来越像一个精确代表(双重)自我 的模型。最后当村民们忏悔他们的残忍,并开始在城堡门口的台阶上留下做好的饭菜和烘焙点心作为礼物时,局面成了玛丽凯特在凉亭里的假想的真实写照——只是这一次,摆在她脚下的献祭是现实,而非虚构。众人示好,为玛丽凯特加冕。她的帝国重回静滞。
注释:
《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选摘:
我叫玛丽?凯瑟琳?布拉克伍德。今年十八岁,我和姐姐康斯坦丝一起生活。我经常在想,要是我更走运一点的话,我可能生下来就是狼人了,因为我两只手的中指完全一样长,但我必须学会知足。我不喜欢洗澡不喜欢狗也不喜欢噪音。我喜欢我的姐姐康斯坦丝,喜欢理查?金雀花,也喜欢“毒鹅膏”——就是毒蘑菇“死帽蕈”。我家的其他成员全都死了。
我最近一次浏览厨房架子上的图书馆书籍时,它们都已经逾期五个多月了,假如我早知道这些是我们从图书馆借的最后一批书,它们将永远留在我们厨房的架子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选择借些不同的书。我们极少挪动东西;布拉克伍德从来都不是一个不安分的活跃家族。我们打交道的都是暂时放在外面的小物品,比如书籍、鲜花和勺子,但在这些之下我们的生活始终是一种稳定的固守。我们总是把东西物归原位。我们掸灰清扫桌椅、床铺、照片、小地毯和灯座下面,但我们不会挪动它们;我们母亲梳妆台上的那套玳瑁梳妆用具的摆放位置从来都是分毫不差。布拉克伍德家族一直居住在我们的房子里,他们的生活总是井井有条;新嫁入布拉克伍德家族的女人一搬进来就会有一个放她自己东西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房子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布拉克伍德家族的资产,这些资产让我们的房子在这世上岿然不动。
我是在四月底的一个星期五从图书馆把这些书借回家的。星期五和星期二是很糟糕的日子,因为我必须去村里。总得有人去图书馆和食品杂货店;康斯坦丝从来不会去她自己花园之外的地方,朱利安叔叔则出不了门。所以让我一周两次去村里的不是自尊,甚至也不是固执,我只是单纯出于对书籍和食物的需求。我在回家前总会去史黛拉店里喝一杯咖啡,这或许是出于自尊;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了自尊,于是不论我是多么想立刻回家,我都不会不去史黛拉的店,但我也知道假如我不进去的话,史黛拉也会看到我经过她的店,她可能认为我在担心害怕,这个想法让我无法忍受。
“早上好玛丽?凯瑟琳,”史黛拉总是一边说一边伸手用一块微湿的抹布擦拭台面,“你今天好吗? ”
“很好,谢谢。 ”
“康斯坦丝?布拉克伍德呢,她好吗? ”
“很好,谢谢。 ”
“那么他怎么样? ”
“和你想得一样好。黑咖啡。谢谢。 ”
假如其他任何一个人走进来在吧台边坐下,我会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