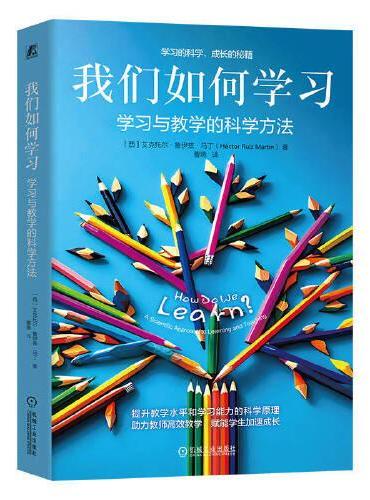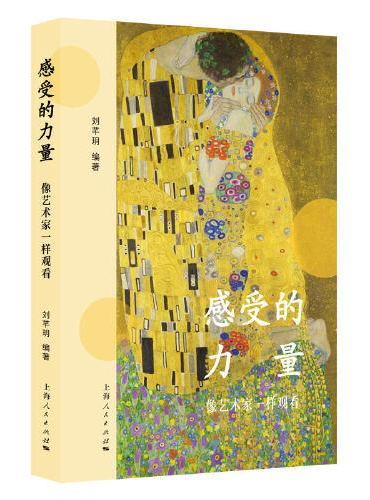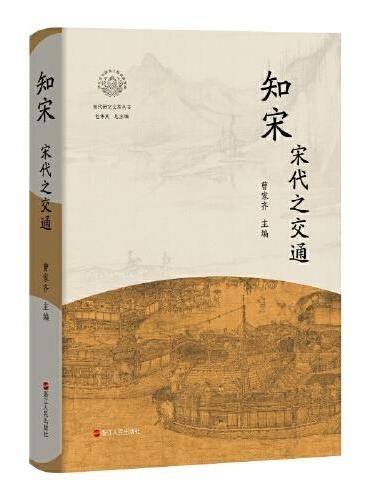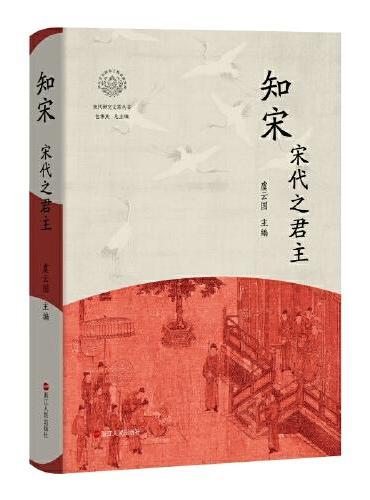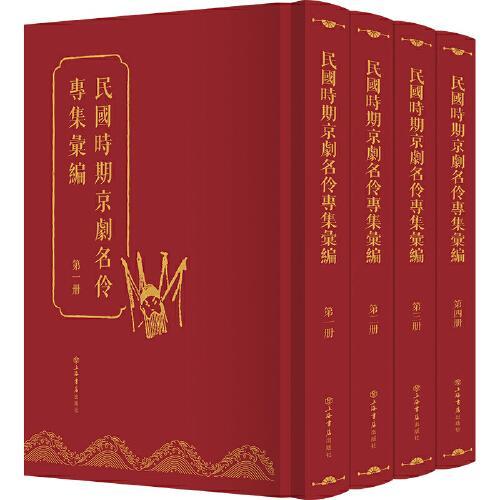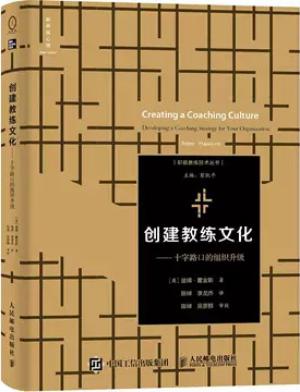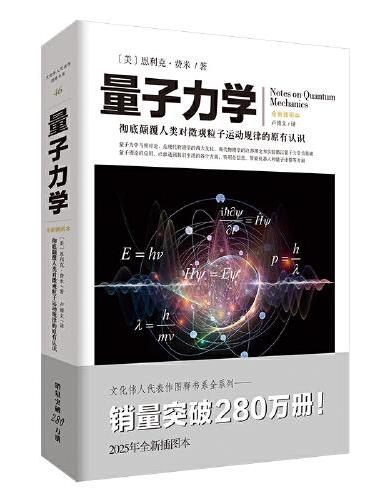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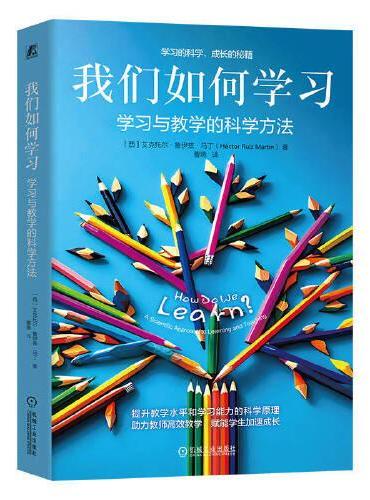
《
我们如何学习:学习与教学的科学方法 (西班牙)艾克托尔·鲁伊兹·马丁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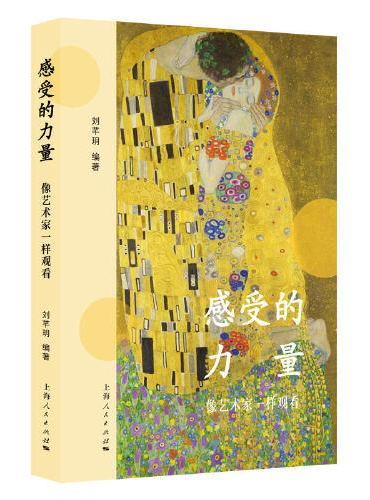
《
感受的力量--像艺术家一样观看
》
售價:HK$
57.2

《
诗词串起中国史:按照朝代顺序用诗词串起一部中国通史。
》
售價:HK$
2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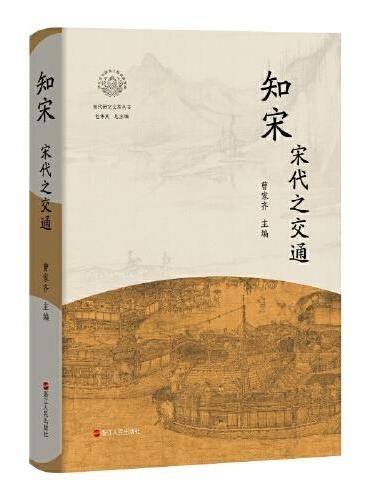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交通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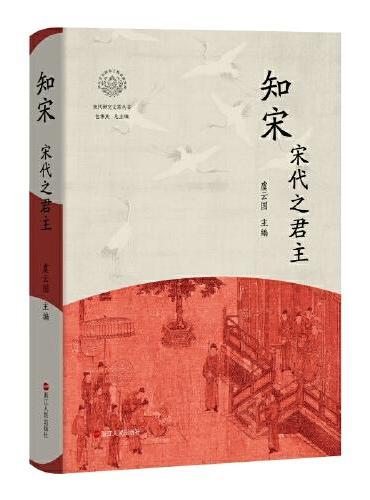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君主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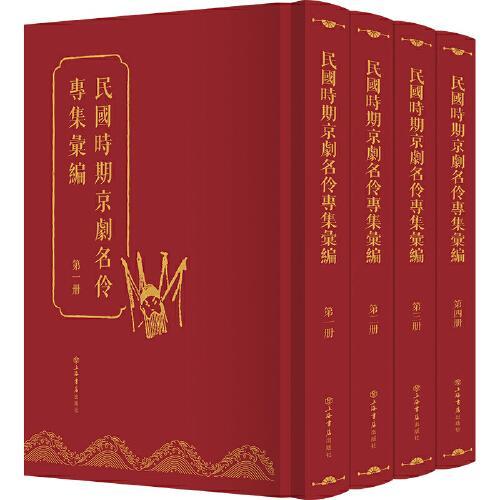
《
民国时期京剧名伶专集汇编(全4册)
》
售價:HK$
437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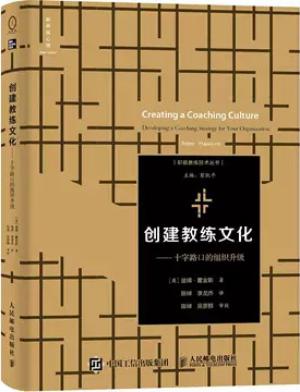
《
创建教练文化:十字路口的组织升级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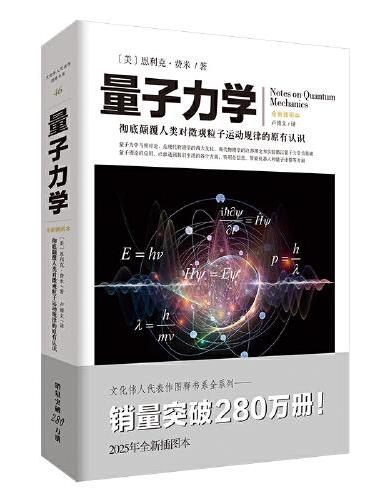
《
量子力学 恩利克·费米
》
售價:HK$
52.8
|
| 編輯推薦: |
约翰·契弗:影响美国文学的巨匠,开启《纽约客》短篇创作的黄金时代,深受哈罗德·布鲁姆、余华推崇,深刻影响雷蒙德·卡佛、杰夫·戴尔等后辈作家
对新英格兰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和生活的关注,对郊区社会与文化含义的关注,使契弗成为美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作家。
契弗对生活在郊区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心理了解十分透彻,他每每用非常幽默的笔触描写他们内心的矛盾、他们的虚荣和他们的痛苦。他的小说反映了20世纪初中产家族在日益工业化的美国生活中的命运。
约翰·厄普代克:“在美国当代小说家中没有人能与约翰·契弗匹敌。”
余华:“约翰·契弗是我的青春记忆,他把平凡写成了不朽。”
约翰·契弗樶具批判性的长篇代表作,基于自己的真实经历,是“人生的一个总结”:以一座监狱,描写“一切都乱了套”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人生与美国社会
在契弗所有的小说中,《猎鹰者监狱》是樶具有批评性的。
20年代70年代初期,契弗曾经在辛辛监狱教授过两年英语写作。在监狱耳闻目睹的情景使他十分苦闷。1974年到1975年,契弗作为英语创作课的访问教授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其时,他患上了抑郁症,耽于酗酒,不得不被送往纽约州一家酗酒康复中心诊治
|
| 內容簡介: |
|
法拉哥特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大学教授,因谋杀兄长而被判入狱。在监狱中,他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犯人,其中有杀人犯、小偷、强盗、绑匪,也有百万富翁、部长和副州长。在罪犯们的叙述中,美国中产阶级伪善面具下的真实被一层层地揭开……监狱就像是一面镜子,通过对监狱里同性恋、婚外恋和自恋的描写,契弗揭示了真实社会中人类的虚伪、虚荣、好色,以及无处不在的歇斯底里。
|
| 關於作者: |
约翰·契弗(John Cheever)
美国小说大师,尤以短篇小说著称,被誉为(美国)“城郊的契诃夫”,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樶重要的短篇小说家之一”。《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获得1979年普利策小说奖和全美书评人协会奖,第一个平装版再度获得198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除闻名于世的短篇小说之外,契弗还创作了五部长篇小说:《沃普萧纪事》(获1958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沃普萧丑闻》(获1965年度威廉·迪恩·豪厄尔斯奖)、《欢迎来到弹园村》、《猎鹰者监狱》以及《恰似天堂》。1982年4月27日,就在他逝世七个星期前,美国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授予契弗国家文学奖章,以表彰其一生的文学成就。
雷蒙德·卡佛认为,契弗对美国短篇小说的复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译者介绍】
朱世达
当代翻译家、作家、学者。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室主任。译有《青年艺术家画像》《绝望》《幸福国的故事》《沃普萧纪事》《沃普萧丑闻》等多部英语文学作品。
|
| 內容試閱:
|
1
猎鹰者监狱的大门是犯人、探监者和职员进出的唯一通道;大门上面装有一面盾饰,盾饰上描摹着象征自由与公正的女神像,在两个女神像之间,镶嵌着显示政府至高无上权力的徽记。自由女神戴一顶头巾式女帽,手持一把长矛。表明政府作用的是一只象征联邦的鹰,鹰爪抓着橄榄枝和狩猎的箭。公正女神则是通常的那种形象,蒙着眼,手握着一把生死予夺的剑,在她那紧身的长袍里隐隐地透露着一种情欲。这浅浮雕是铜制的,但如今也晦暗了——跟没有光泽的无烟煤或缟玛瑙一般的漆黑。多少人从这盾饰下面走过,他们大多数把这盾饰看成是人类竭力用图像来阐释监禁神秘性的最后的纹章。人们猜想,从盾饰下面也许走过了上百人,上千人,也许上百万人。在盾饰的上方是这座建筑各种演变的名称:猎鹰者监狱,建于1871年;猎鹰者教养院,猎鹰者联邦反省院,猎鹰者国家监狱,猎鹰者行为纠正所,最后一个名称谁也弄不明白:黎明院。现在里面住的是罪犯,狱吏全是些混蛋,典狱长统管着一切事务。名声往往是名不符实的,老天,但是,以有限的设施收容着两千名歹徒、恶棍的猎鹰者监狱跟新兴门监狱一样的有名。不再有水刑、一式的条纹囚衣、锁步和铁球脚镣;而在绞刑架曾经竖立的地方,则是一个垒球场。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奥本监狱还在使用脚镣。这你可以从奥本监狱犯人的吵闹声中得知。
夏末的一天,法拉格特(杀兄罪,判十年有期徒刑,编号734—508—32)被带进这古老的、带有铁窗的房子。他没有戴脚镣,但和其他九个犯人一起上了手铐,其中四个是黑人,全比他年轻。囚车的窗很高、很脏,他看不清天空的颜色,看不清灯光,看不清他正离别的这个世界的任何模样。三小时之前,有人给他扎了四十毫克的美沙酮,浑浑噩噩,他真希冀瞅一眼天光。他注意到司机在红灯前停下来,按喇叭,爬陡坡时踩刹车,然而似乎他们和人类其他成员仅仅只剩这些关联。人的难以估量的羞耻感似乎震慑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但是,铐在他右手的那个家伙却毫不在乎。他是一个瘦削的人,油光光的头发,一脸的疖子和酒刺,使他的面庞非常可怕地变形了。“我听说监狱里有个球队,只要有球可打,我就没事儿。有垒球打,我就能活下去,”他说,“能打垒球,对于我来说就够好的了。我不懂记分。我就那么着投球。大前年,我在北埃德蒙斯顿队自始至终不让对方得分,离开投球区的土墩,听见观众对着我直欢呼时,才明白过来。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个娘儿们睡过觉,从来没有过。我有时花个五角,有时花五十美元呢,我从来没有不花钱找到个娘儿们。我琢磨这跟不懂记分是一回事。没个娘儿们愿意顺着心跟我睡个觉。我认识好几百个男人,他们全没我长得帅气,可总是不花一个子儿就能找到娘儿们,我从没碰到过。我真想不花一个子儿来上那么一次,哪怕一次也好嘛。”
囚车停下来了。法拉格特左手铐着的是一个十分高大的人,这人一步跨下囚车,将法拉格特绊倒在院子地上。法拉格特爬了起来。他第一回瞧见那盾饰,他想,也许也是最后一次
吧。他会在这儿撒手闭眼死去的。然后他瞅一眼蓝蓝的天,竭力想将自己的存在和那蓝蓝的天联系在一起,和亵渎的语言联系在一起,亵渎、污秽的语言已经在他写给妻子、律师、州长和主教的信中开始出现了。有一小群人瞧着他们快步穿过院子。他清晰地听见有人嚷道:“这些家伙瞅上去倒蛮不错!”那些人也许是没犯什么大罪的,只是一时迷了路而已;法拉格特听见一个穿制服的嚷嚷道:“转过身子去,说不准他们中有人身上揣着把剃刀。”这些没犯大罪的说的是对的。囚车和监狱之间的那片湛蓝湛蓝的天空,他们中有些人有好几个月没瞅见过了。多么的不同寻常,天空看上去是多么的纯洁!它们永远不会再显得如此动人、如此美好了。天际的光亮映照在囚徒的脸上,显现出一种十分丰富的目的感和无辜感。“他们宰人,”看守说,“他们强奸妇女,他们将小孩儿往火炉里塞,他们会为了条口香糖勒死自己的娘。”然后,他把脸从那些迷路者转向囚犯们,开始嚷道:“你们要做个守规矩的人,要做个守规矩的人,要、要做个守规矩……”他直着嗓子号道,好像火车的鸣笛声,好像猎狗的狂吠,好像深夜孤寂的歌声或呐喊声。
他们一个拖着一个地爬上楼梯,走进一间破旧的房间。猎鹰者监狱显得十分破败。人们所见、所触摸、所闻到的一切都表明这地方被人遗弃的程度。这地方的腌臜劲儿使人迅即得到一种印象,简短地说,那就是,虽然这儿北边有一座租借的死囚行刑前的班房,这地方肯定是强迫苦行赎罪等死的场所。铁栅栏好多年前上了白瓷漆,但是,在囚犯本能地手握的齐胸的那部分,珐琅早脱落了,露出了铁面。在一间远一点的房间里,那个嚷着让他们规矩点儿的看守打开了他们的镣铐,法拉格特跟大伙儿一样,因为能自由自在地伸胳膊伸腿、耸耸肩膀而感到深深的快乐。他们全用手揉着手腕。“什么时候了?”那长酒刺的问道。“十点一刻。”法拉格特说。“我是问几月几号?”这人说,“你有只日历表。我想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嗬,让我瞧瞧,让我瞧瞧。”法拉格特摘下他的贵重的手表,递给那陌生人,那陌生人一把塞进兜里。“他偷我手表,”法拉格特对看守说,“他刚才偷我手表。”“哦,是吗?”看守说,“他真的偷了你的手表吗?”然后他转身对着小偷问道,“你这次出去待了多久?”“九十三天。”小偷答道。“这是你在外待得最长的一次吗?”“上一次我在外面待了整一年半。”小偷说。“这种怪事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完呢?”看守问道。这一切,以及以后的所见所闻,使法拉格特渐渐失去了活力,他除了瘫痪和恐怖之外什么都视而不见。
他们被赶进一辆老掉牙的卡车里,上面放着几条木板凳,车沿着围墙里的一条路开走了。在路的拐角处,法拉格特瞧见一个穿监狱灰鼠色号衣的人在用面包皮喂十几只鸽子。这一情
景在他心中唤起一种非凡的现实感,预示着一种神志清楚、精神健全的生活。这人是一个囚犯,他、面包和飞鸽,与环境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因为某种连法拉格特自己也无法解释的理由,这人与鸽子分享面包皮的形象回响着遥远的古代的风习。他站在卡车里,尽可能久地观望着一切。走进一幢建筑物,他瞅见在天花板高处,水管上有一只业已晦暗的银色圣诞花环,他又一次激动起来。这里所包含的讽喻是陈腐的,但是,跟喂养鸽子的那人的形象一样,它似乎透露出一线理智的光。在圣诞花环下,他们走进一间房间,书桌椅子的腿残缺不全,木漆斑驳,桌面上横七竖八地刻着缩写姓名和污秽的画面,这些东西,跟猎鹰者监狱里的一切一样,似乎都是从城里什么垃圾堆里捡来的。最初的一次甄别是心理测验,这种测验他在关禁他的三个吸毒者纠正诊疗所已经领教过。“你惧怕球形门把手上的细菌吗?”他读道,“你乐意在原始热带森林里狩猎老虎吗?”这些问题的讽喻性,比那喂鸽子的人和挂在水管上的银色圣诞花环所包含的讽喻性,就深度和动人而言,不知要逊色多少了。他们花了半天时间回答五百个问题,然后被赶到一座饭厅吃饭。
这比他在拘留所见过的房子要陈旧、宽敞多了。屋顶上桁条交错着顶在那儿。在窗台上有一只有柄的锡制大水罐,里面种了些马利筋花,花的色彩在那种肃穆的地方犹如一团火。他用一把锡制汤匙吃酸不拉叽的食物,然后把汤匙和盘子扔进脏水里。监狱当局严禁吃饭时说话,但他们自个儿强力推行一种隔离政策,黑人待在北边,白人坐在南边,中间夹着讲西班牙语的犯人。饭后,他们审查了他的体质、宗教和职业特点,然后等了好一阵子,将他带进一间房间,在一张东倒西歪的书桌后面端坐着三个穿廉价西服的人。在桌子的两端插着两面国旗。左边有一扇窗户,透过窗户,他可以瞥见一块蓝天,在蓝天下,他想那人也许还在喂鸽子吧。他感到脑袋、脖子、肩膀开始痛起来,他走到审判席前时,佝偻得厉害,他感到自己成了一个非常矮小的人,一个侏儒,一个从未经验过、体会过或者想象过放肆的伟大之处的人。
“你是个教授。”左边的那个人开腔道,他似乎是这三个人的发言人。法拉格特没有抬头瞅他的脸。“你是个教授,你的天职是教育所有希望获得知识的年轻人。历来的经验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是不是?而你,作为教授,一个因负有智力与道德影响责任而出众的人,却在危险毒品的驱使下,犯下了可怕的杀兄的罪愆。难道你不感到羞耻吗?”“我希望咱们先说准了保证我能拿到我的美沙酮。”法拉格特说。“哦,你真不知羞耻!”这人尖声喊道,“我们这是在帮助你。我们这是在帮助你。如果你没有廉耻感,你就永远别想在文明社会中占有你的位置。”法拉格特没有回答。“下一个。”这人喊道,有人带着法拉格特到背后的一扇门边。“我是小不点儿,”那儿有个人对他说道,“抓紧点儿。我不能一整天只伺候你一个。”
小不点儿的体形真是吓死人。他长得不高,但躯干显得十分的不协调,衣服只能为他特制,尽管他吆喝着抓紧点儿,两条粗实的大腿也使不出什么劲儿,走得非常慢。他的灰白的头发剃成一把刷子似的,你甚至可以瞅见他的头皮。“你待在F牢区,”他说,“F意味着性交啦,毒瘾者啦,傻瓜蛋啦,同性恋者啦,初犯啦,跟咱一样的大屁股啦,鬼怪啦,丑角啦,宗教狂热徒啦,联邦调查局侦探啦,销赃贼啦,放响屁啦。还有好多,记不得啦。琢磨这玩意儿的那小子归天了。”他们沿着一条地道的斜坡上行,一路聚着一堆堆的人在聊天,好像在大街上一样。“依我看,你在F牢区只是个过路的,”小不点儿说,“你说起话来那么逗,他们会让你去A牢区,那儿关着副州长啦,商业部部长啦,全是百万富翁。”小不点儿向右拐,他尾随在后,走进一扇敞开着的门,来到班房。跟这监狱里的一切一样,牢房破旧不堪,杂乱无章,散发出一股股令人难耐的恶臭,但他的班房却有一扇窗户,他走到窗户跟前,瞧见一块天空,两座高耸的水塔,围墙,牢房,以及他进来时磕绊跪在地上的院子。牢房里的犯人对他的到来显得非常的冷漠。他铺床时,有人问道:“有钱的?”“不。”法拉格特说。“没毒瘾?”“有。”法拉格特说。“你口交吗?”“不。”法拉格特回答。“你被冤枉了?”法拉格特没有搭茬儿。有人在牢房背处弹起吉他,用一种走调的肯塔基州土嗓子唱道:“我奏起无辜的布鲁斯音乐,我一直怨恨在怀……”他的歌声几乎难以分辨,因为各种各样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大吵大闹—播音的啦,唱歌的啦,乐队演奏的啦—听起来就跟大街上打烊时分或者更晚些时候一样的热闹非凡。
谁也不跟法拉格特说话,熄灯之前,那个唱歌的——法拉格特从他的嗓音分辨出来——来到他班房门口。他骨瘦如柴,苍老,嗓音很轻,听上去让人很不好受。“我是小鸡二世,”
他说道,“别指望找到小鸡一世。他伸腿闭眼了。你也许在报上读到过关于我的消息。我可是一条以文身闻名的好汉,爬窗户偷东西,是我的拿手好戏,钱全花在身体艺术上啦。改日,咱们哥儿俩熟了,让你瞧瞧我的照片。”他斜瞟了法拉格特一眼,“我来就是告诉你,这是个错误,乱了套,我是说让你这样的人蹲在这儿是乱了套。明天,他们还不会明白。得一两个星期才会回过味儿来,弄清楚了,他们会后悔,会觉得没脸面,会感到对不住你,在第五大道赶着买圣诞节礼品的人群中,州长会来亲你的屁股。嘿,他们会后悔的。因为,你瞧,我们每蹲完一次监狱,即使咱这样真有罪的犯人,总会碰上一桩美事儿,比方说找到一罐黄金啦,一汪青春泉啦,看见一片大海啦,一条河流啦,以前谁也没瞅见过,至少呢,总会有一盘配上烤土豆的、大块的上等牛排吃。每次蹲完监狱之后总会碰上好事儿的,所以我想告诉你,这全乱了套啦。在你等着他们明白错误之前,会有人来探监的。哦,就凭你坐着的这神气,我敢说,你有成千个朋友啦,情人啦,当然啰,还有一个老婆。你老婆会来瞧你的。她一定得来。她要是想跟你闹离婚,必须自个儿来,拿上文件让你签字画押。所以嘛,我想告诉你——你自个儿已经知道了——这是个大错误,全乱了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