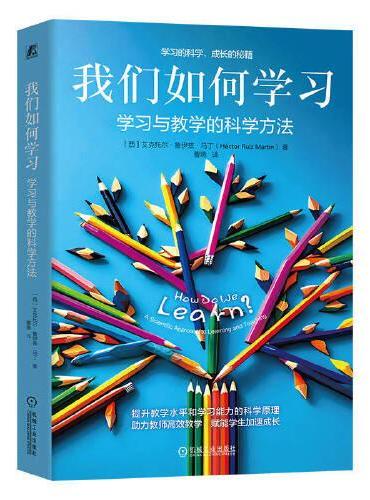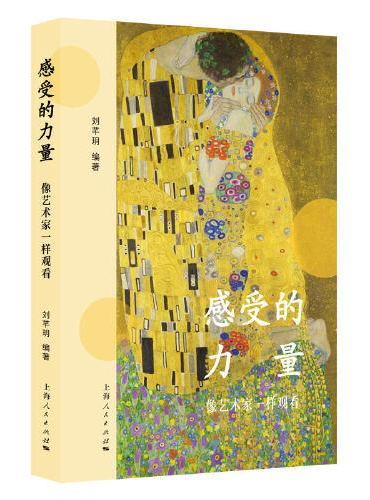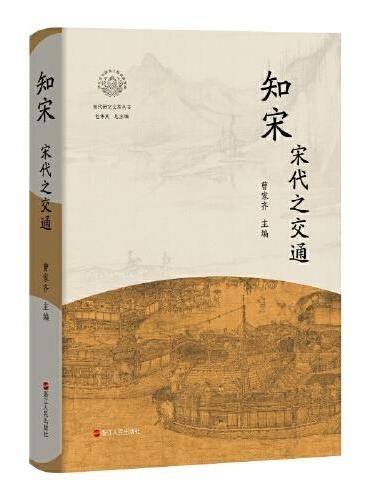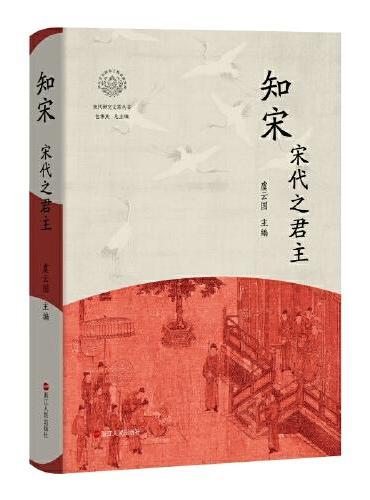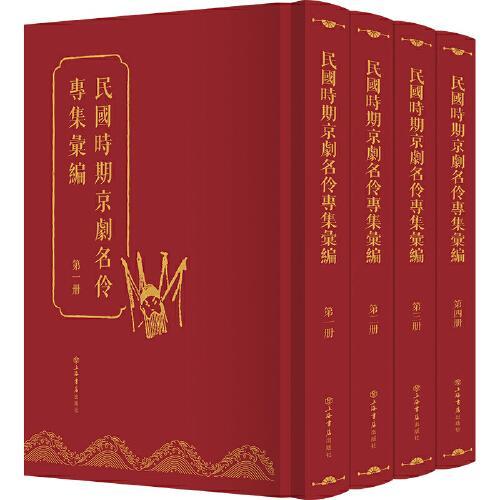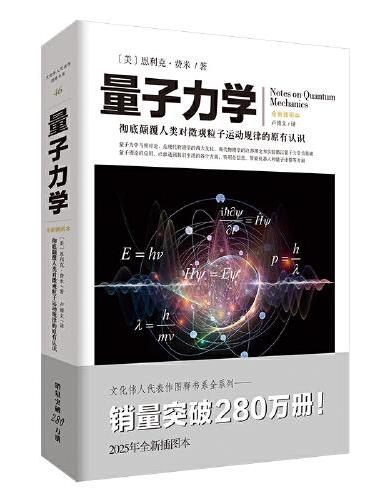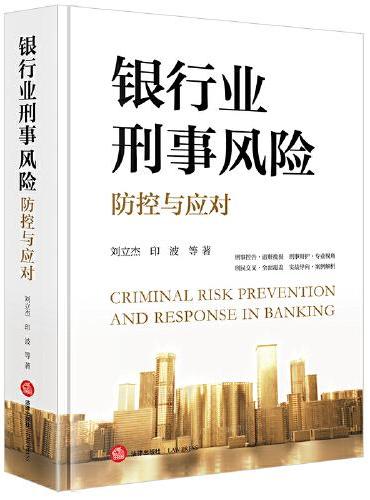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咨询
》
售價:HK$
1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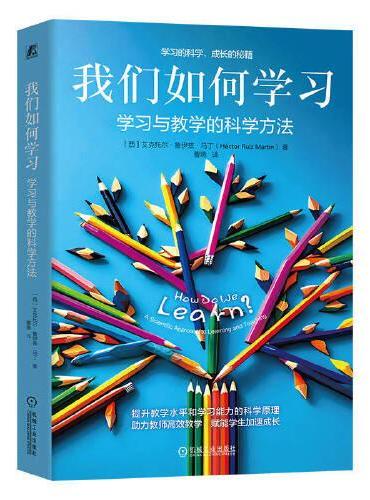
《
我们如何学习:学习与教学的科学方法 (西班牙)艾克托尔·鲁伊兹·马丁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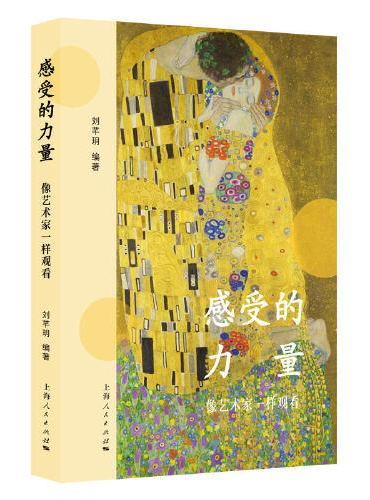
《
感受的力量--像艺术家一样观看
》
售價:HK$
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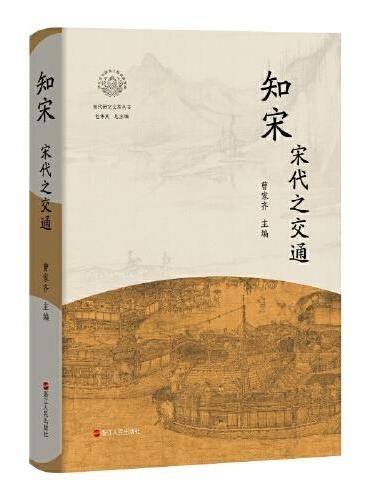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交通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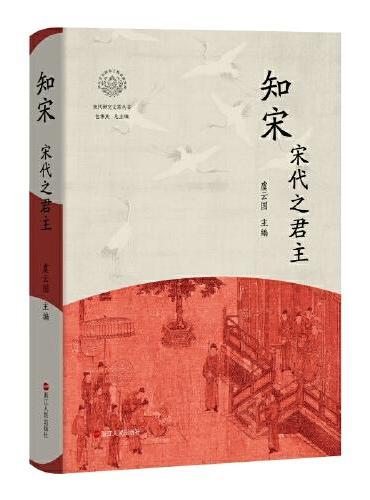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君主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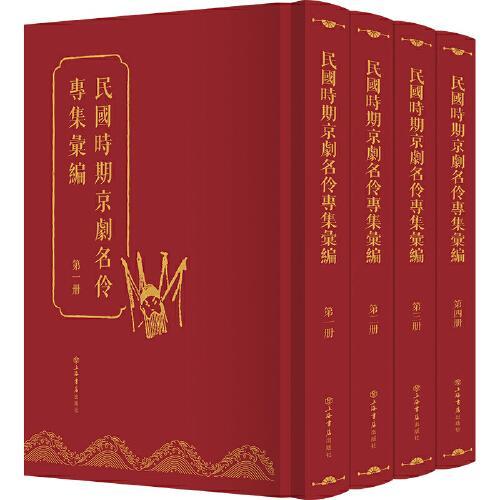
《
民国时期京剧名伶专集汇编(全4册)
》
售價:HK$
437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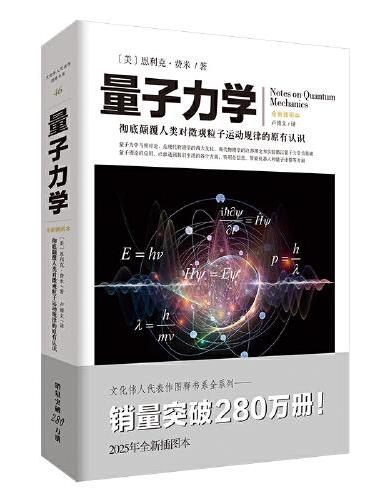
《
量子力学 恩利克·费米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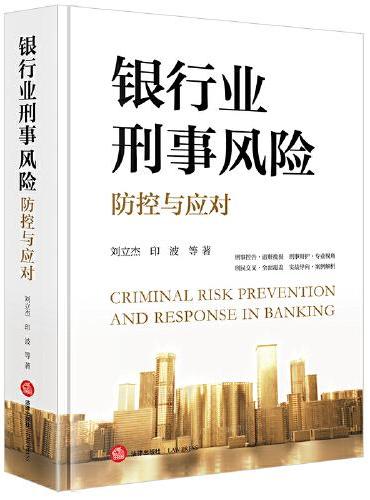
《
银行业刑事风险防控与应对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1.晋江金榜作家蓬莱客全新古风代表作
2.人生纵有遗憾,斗转星移,百代过客,这一刻,他的身边有她,足矣。
3.开疆拓土女将军VS权倾朝野摄政王
攻下南都之后,我十三岁那年见过的少年,我希望能等到他来。
4.山依旧好,昨日少年,今日却老。
5.他以天下为棋枰,上有宏图和大业。我是他枰上的棋子。但我愿意为他去做一个马前卒,心甘情愿。
6.双封面设计,外封大气水墨 磨砂UV,背封烫金。
7.新增出版独家番外《与子偕老》。
|
| 內容簡介: |
姜含元在年少时,遇到过一个让自己引路的少年。
后来啊,已经成为摄政王的少年早已忘记了引路的小兵,却为了她和父亲的将军威名,求娶她为妃。
她曾以为,除了她自己,这世间不会再有第二人知,那个快马追风、弓声惊鸿的边塞深秋的清早,也曾是她为少女时的全部荒凉梦境中的一抹亮色。
这一辈子,再不会有。
然而待到绝战前夕,她对传话之人说:
“无论他最后如何抉择,自有他的缘由。和他夫妻一场,我尊重他之所想,也不会阻挡。等到攻下南都之后,我会去我十三岁那年曾替一个少年引过路的目的之地,等那少年再来。
“我希望到了那日,能等到他来。”
|
| 關於作者: |
蓬莱客,晋江文学城签约作者。
性本颟顸,心常欢喜,窗前照有蓬莱月,我便自比月下客。
已出版作品:《辟寒金》《折腰》《表妹万福》《君侯本无邪》《归鸿书》等。
|
| 目錄:
|
上册
第一章 长宁将军 1
第二章 大婚始成 65
第三章 少年皇帝 127
第四章 悬崖死斗 197
中册
第五章 命定之人 251
第六章 心意初通 313
第七章 宫中塞外 372
第八章 少年重现 443
下册
第九章 风起青蘋 505
第十章 战况频变 568
第十一章 心有灵犀 625
第十二章 天下长宁 698
番 外 与子偕老 751
|
| 內容試閱:
|
精彩文摘
第一章 长宁将军
野阔草黄,霜天孤雁。
姜含元站在一道岗坡上,望着北麓远处的那个村庄。
村庄里的火已经灭了,但过火的民房只剩一片残垣断壁。来自北方旷野深处的风悲鸣着,穿过村庄的上空,抵达坡顶,带来了一阵忽高忽低的啜泣之声。
这个地方在今日的黎明时分,遭到了北狄人的劫掠。
一支近百人的游骑队伍于昨日深夜避开了有重点守备的边乱地带,越过距此处几十里的常规望哨段,潜了进来。
负责那一哨段的燧长和这村中的一个寡妇搭伙过日子,今年得了一个女儿。昨夜他恰好私自离燧回村,烽台只剩下两人值守。因那一带长久无事,留守的人便懈怠了,趁机偷懒喝酒,等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是晚了。
狄骑在黑夜的掩护之下,长驱直入,拂晓至此。
这种北狄游骑惯常伺机而动,抢完之后,带不走的便烧。
短短不到半个时辰,整村民房过火大半,货财被抢,妇女被掳走十数人,十来个逃得慢的男丁也丧命在了马蹄之下。
姜含元恰巧行经此段。她这趟出来本是要去云落城祭拜亲人,为早日抵达,今早四更便上了路,黎明时分路过这里,远远地见对面浓烟滚滚,冲天直上。
虽然烟束和她熟悉的烽烟不同,但出于本能,她还是停马前去察看,见状,便派人去召本地驻军李和部,命其火速驰援。随后她没有片刻停顿,带着随行二十四骑,循着狄骑在北逃途中留下的痕迹追咬上去。
等到午后,狄人自觉已到了安全地带,松懈了下来。
这些年,大魏边军遇到类似的零散劫掠,倘已叫狄人得手逃脱,考虑到各种因素,通常是不会花大代价去追击的。这也就成了狄人肆无忌惮、屡屡伺机越界犯禁的原因之一。
再说了,魏人即便真的来追,也不可能这么快便追上。一夜奔袭,饥渴乏累,这队狄人纷纷下马解刀,趁休息间隙,又对掳来的妇人施以兽行取乐。
其正猖狂之时,姜含元一行如神兵天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是一箭射杀头领,继而策马列阵,纵横冲杀。狄人毫无防备,一时间人仰马翻,仓皇应战,伤亡惨重,又不知对方后援还有多少,很快便放弃对抗,奔窜逃命。
一名满面须髯、身材壮硕的中年军官快步登坡,停在了姜含元的身后,禀道:“带回的财物已悉数发放完毕,女人也被各家接了回去,李和跟进善后之事。村民十分感激,方才要来叩谢将军,卑职代将军拒了。”
这个中年人名叫樊敬,是姜含元的心腹。
“七郎他们的伤情如何了?”姜含元转头问道。
虽然白天的追击大获全胜,不但救回被劫走的女人,还令这支骄狂的狄骑死伤过半,除了逃走的,剩下全被割了头颅,但是对方也都是凶悍之徒,加上占了人数之利,她的人也伤了七八个。
“问题不大,方才都处置好了。”樊敬顿了一顿,“不过,那名燧长熬不过去,刚断了气。他的女人抱着娃娃来了。”
燧长自知死罪,为求弥补,请求同行,伤得最重。
“两个误事的燧卒也被绑来了,请将军处置。另外,李和也一并来请罪。”
坡下,一个女人跪在燧长的遗体旁痛哭。那女婴未及周岁,被放在地上,懵懂不知发生何事,手脚并用地在近旁来回爬行,口中发出“咿咿呀呀”之声。
随从聚在近旁,一个刚包扎完伤处的娃娃脸小将愤愤不平,大声抱怨道:“大将军常年就只会命我们防着、防着!叫我们龟儿似的全都窝在关里!太窝囊了!关外大片的朔州、恒州、燕州叫北寇占去了不说,最可恨的是他们竟还越界杀我百姓、掠我妇女!到底何时才能杀出去大战一场,把这些狄人赶回他们该去的地方?杀出去了,便是死,也值!”
同伴们本也群情激愤,但听他言语中提及大将军,又不敢出声。
随后赶到的本地驻军将领李和知眼前这些激进彪悍的少壮军人都是姜含元麾下青木营的人,尤其是这个娃娃脸小将,名杨虎,字修明,小名七郎,精通骑射,还使得一手好戟,有斩将搴旗之勇,曾在一场近身战里几度来回突阵,一战便斩取敌首二十余颗,狠勇好斗、悍不畏死的名声全军皆知,因此还得了个“拼命七郎”的绰号。杨虎出身也不低,祖父曾位列郡公,如今虽家道败落,要靠投军来挣功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李和有一项监察失职之罪,在这里哪有说话的份,便沉默不语。
“住口!”樊敬大喝了一声。
杨虎扭头,见大胡子樊敬伴着主将来了,这才悻悻地闭了口。
李和惶恐跪迎,连声称自己失职,请求降罪。
女人向姜含元叩首,悲泣求告:“是我的罪!全是我的罪,和他无关哪!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是我托人捎信,让他回来一趟看看女儿的。是我害了他啊!是我害了他……”
女人哀恸欲绝,趴在地上俯首不起,哭声充满了绝望和痛悔。
残阳摇摇,坠入原野,四周昏暗了下去。野风骤然疾吹,卷得姜含元那染着血污的衣袍下摆翻飞鼓动。
女婴被衣袍吸引,以为是姜含元在逗弄自己,便朝她爬去,伸出手攥住她的衣袍下摆,晃动着胳膊,发出了“咯咯”的快乐笑声。
女人惊觉有异,抬目见女将军的脸上带着血渍,双目盯着脚下的婴孩,神色阴晦。
女人忽然想起,眼前这位女将军素有“女罗刹”之名,腰间那一柄环首刀杀人无数,又有传言道她幼时以狼为母,是为狼女,至今月圆之夜仍要嗜血,否则便会现出獠牙狼身。
对这样的传言,女人是深信不疑的,否则一个女子怎可能如男子那般鏖战沙场,令无数敌人饮血刀下?
女人哪敢再泣,慌忙求告,手脚并用地爬去想阻止女儿。却见姜含元已弯下腰,在女人惊恐的注视下伸出一手,慢慢地握住了女婴攥她袍角的小手。
这只手布满刀茧,掌与指皆极为粗粝。许是感到了疼痛,女婴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女人恐惧万分,又不敢夺女婴,只颤抖着身子,不停地磕头求饶。姜含元一顿,撒手松开了女婴,转身而去。
“燧长虽戴罪立功,但其罪,战死仍不足以全赦。二燧卒以军法处置,立斩,拟文书,告全军,以儆效尤。至于李和之过,非我能定,叫他自己去向大将军请罪!”
姜含元说完,接过一名手下递来的马缰,偏脸望向跟随在旁的樊敬:“樊叔,还要劳烦你留下监察善后,将这一带的全部边防再检视一番,务必确保没有疏漏。”
“明白。将军你放心去。”
“还有,”姜含元略略一停,望了一眼远处那个仍抱着女儿跪地哭泣的女人的背影,低声说道,“给她母女双倍抚恤,从我的俸饷里出。”
樊敬一怔,回头看了一眼,随即应诺。
“今日受了伤的,全部自行返营!其余人随我上路!”她最后下令,翻身上马,单手一拢马缰,策马欲去。
杨虎急了,一跃冲上,拦在了她的马头之前,晃着自己刚包扎好的胳膊:“将军,我好着呢!皮肉小伤!我要随你!”
“给我回去!”姜含元低低呵斥一声,策马从他身旁绕过,去了。
剩下没受伤的十几人笑嘻嘻地冲着杨虎做了个手势,顷刻间悉数上马,呼哨一声,跟着疾驰而去,剩下杨虎和那几个受了伤的兵士立在原地,满心懊恼。
杨虎望着前方将军那道越来越模糊的背影,越想越气,忍不住冲着前头一个上马离去的同伴破口大骂:“张猴子你这王八羔子!今日要不是我救了你,替你吃了那一刀,你已经挺尸了!你倒好,自己跟着将军上路了!你给我等着,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那被唤为“张猴子”的同伴连头都没回,还催马加速,转眼便不见了踪影。边上几个一道被留下的同伴不免幸灾乐祸,又不敢笑,忍得颇是辛苦。
“行了行了!照将军的吩咐,你们晚上休息一下,明早就回去!”
对着这个由女将军亲自选拔出来、似还被偏爱几分的刺儿头,樊敬也是有点儿头疼。自然了,他是绝对不会表露出这一点的。他绷着一贯的严肃大胡子脸,沉声重复了一遍姜含元的命令。
杨虎只能作罢,沮丧地瞥了一眼这趟来的方向,不料却见一匹快马载着传令兵,正从远处疾驰而来。
“长宁将军可在?大将军有急令,命长宁将军即刻火速归营——”
那传令兵远远看见樊敬几人,迎风踩着马镫,在马背上直立而起,高声呼道。
传令兵带来了大将军姜祖望的命令,姜含元只能中止行程,掉头回她父亲常驻的位于雁门西陉关附近的大营。
数日后,她于深夜时分赶到营中。
这个时辰,西陉大营四周漆黑无光,除了夜哨,将士都早已安寝入梦了。
姜含元穿过一座座营帐,来到父亲所在的大帐前,见灯火从帐门缝隙里透出,没直接进去,停在帐外,叫守卫前去通报。
“将军请进。”守卫很快出来,恭声说道。
姜含元入帐。帐内只有她父亲一人,穿着一袭军中便衣,端坐于燃着灯烛的案后。
大将军定安侯姜祖望虽战功卓著,却并非如一般人以为的武将那般生得燕颔虎须、雄壮过人。他容貌周正,剑眉凤目,年轻时当是位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只是现如今风霜侵鬓,即便此刻灯火并不明亮,也掩不住其面容里透出的憔悴老态。
他早年曾中过冷箭,伤及肺腑,险些丧命。后来他虽凭己身压制了伤势,但随着年岁渐长,加上边地苦寒,旧伤时有复发,折磨实在不轻,只是他素来刚强,极会忍耐,因而知道的人不多。
看见女儿进来,姜祖望立刻从案后站了起来,朝她走去。
“兕兕你到了?路上劳累了吧?若是疲乏,先去歇息,明日再说不迟。”他唤着女儿的乳名,眉头舒展,脸上也露出笑意。
姜含元领兵驻在从此往北几百里的青木塞,青木塞几十里外便是魏军和北狄的冲突频发之地。平日若非有军情,她与姜祖望碰面也不多。
她行了一个军中下级拜见上级的常礼,随即站直身体,用恭谨的语气问:“大将军急召我来,何事?”
姜祖望停住脚步,顿了一下,缓缓坐了回去。
帐中一时寂静无声。夜风从帐门的缝隙里钻入,吹得灯影摇晃。
姜祖望再次开口,脸上的笑意已经消失:“李和已向我请罪了。只是,你未免太过托大,不等援兵赶到,竟那样追了出去!你们才多少人?对方多少人?便是晚些,那些妇人也不至于丧命!纵然你在军中几经历练,就能以一当四?我本以为你不是这样鲁莽的性子!”
说到最后,他语气已是十分严厉。
“是,妇人们大约不会死,但我若等李和的人到了再追出去,她们恐怕已是生不如死。”姜含元平静地说道。
没有约束的普通狄兵,兽行能至何等地步,姜祖望自然清楚。他这般斥责女儿,其实也是出于一点儿私心,是担忧焦虑所致。被女儿一句话驳了回来,他一时沉默,待再次开口,神色也随之缓和下来。
他转了话题,问道:“含元,阿爹要是没记错,你也有二十岁了吧?”
他的目光从女儿落满尘土的肩上,慢慢移到那张和她母亲肖似的脸庞上。
“大将军何事?”姜含元没回答,只重复问道。
姜祖望一顿。
朝廷派遣使者——宗正卿贤王束韫北上,见到姜祖望,一番寒暄过后,再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询问他的女儿长宁将军姜含元。
“七年前,当今摄政的祁王殿下还是安乐王,曾代武帝来此犒军,当时你也在。你应当还有印象吧?”
姜含元的睫毛微微一动,她用略带戒备的眼神盯着父亲,没有接话。
“这一趟是贤王束韫亲自来的。你知他此行目的为何?”
女儿仍没应声。
他一咬牙:“贤王是受摄政王所托来向为父提亲,摄政王意欲立你为妃。”
空气仿佛突然凝固。
姜祖望看着女儿,苦笑:“阿爹知道,这消息实在太过突然,你大约毫无准备。莫说你了,便是我也如此。不过——”他将话锋一转,再次从案后站了起来,面带微笑,朝表情略微发僵的女儿走去,“不过,摄政王乃人中龙凤,才干当世无二,论姿貌风度,更是万里挑一,你从前应当亲眼见过的。何况,你毕竟不是男儿身,幼时便罢了,如今年岁也不小了,不好总这样在军营中蹉跎年岁,该当觅一良人……”
“父亲!”姜含元忽然开口,“您真觉得,束慎徽为女儿之良人?您真觉得,如我这般,适合嫁人?”
她连问两声。
姜祖望顿住了,和女儿那双如其母的眼眸对望了片刻,心中忽然涌出一阵浓烈的羞愧乃至狼狈。他甚至不敢和女儿对视,避开了她直直投向自己的目光。
大帐里陷入沉寂。片刻后,还是姜含元再次开口打破了沉默,语气已转为平淡。
“罢了,我也知您不易,您应了便是。”她说完,未再做片刻停留,转身出帐而去。
她大步走在深夜的大营里,朝营外而去,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最后径直走出辕门,解了拴马桩旁的坐骑缰绳,翻身上马。
“将军,大将军召你何事?哎,你要去哪里?等等我!”
杨虎方才不肯去休息,抱着受伤的胳膊硬是等在这里,见状,立刻拍马追了上去。
姜含元的坐骑是匹枣红大马,名天龙,是她外祖送她的大宛神骏,若放开了奔驰,寻常马匹根本无法追上。杨虎才追出去没多远,前头的一人一马已彻底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看不见了。
姜含元纵马狂奔,一气奔到了十几里外的铁剑崖,直至绝了路,方停了下来。她下马,登上崖顶,立在崖头之上。
雁门西陉一带,崖体多为黑岩,天晴时远远望去,犹如座座铁山。她此刻立足的这座崖也是如此,因其高耸笔直而得名“铁剑崖”。
今夜乌云密布,头顶无月,亦无星光。
她迎着边地秋寒深重的夜风站了许久,忽然蹬掉靴子,纵身一跃,跳至崖下。
这是她自幼时便常来的地方——她曾无数次从这里跃下。崖下是口泉潭,此刻水面黑漆漆的,如一张张开的巨人之口。她人亦如石,入水后笔直地沉到了宛如地底的潭底。
世界在这一刻彻底无声,心脏也仿佛彻底停止了跳动,她闭着双目,在水底紧紧蜷成一团,如藏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静静不动。
良久,姜含元倏地睁开眼睛,松了手脚,赤足足尖在近旁的岩上一蹬,身子便如一条灵蛇,迅速从水底浮了上去。“哗啦”一声,她猛然破水而出。
她随意地抹了把脸上的水,套回靴子,打了声呼哨,召来天龙,再次纵马疾驰而去。
天亮时分,杨虎带人找到铁剑崖下,在水边的地上看到了两个用刀尖划出的字:勿寻。
贤王束韫还在营里,姜祖望召回樊敬商议。樊敬本是姜含元母家那边的人,十几年前就跟过来了,视姜含元为小主君,对她的忠诚恐怕还要胜过对姜祖望的。此事,姜祖望自然没必要对他隐瞒。
樊敬这才知道束韫此行北上的目的,内心之震惊可想而知。
“大将军应了?!”他诧异万分,只是话刚脱口而出,便领悟自己失言了。
对方摄政朝堂,与君王实无两样,既开了口,还遣束韫亲自前来,姜祖望身为将臣,何来推拒余地?
何况再想,这件事虽突然,却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本朝高祖本为北方诸侯之一,几十年前以秦雍之地为据,在群雄割据的大乱之世创立国基。随后继位的圣武皇帝更是雄才大略,在位二十余年,南征北战,终于在十几年前灭掉了最后一股割据势力,彻底结束了中原长达百年的战乱分裂,一统天下。
但与此同时,中原的长久内乱也给了北方狄人绝佳的南侵机会。
当时的北方以两个大国为主,以黄河中游为界,河西为魏,河东为晋。魏晋之间曾有过旷日持久的拉锯对峙,但后来随着魏国不断崛起,晋帝期望能和北狄这个北方外邻结盟对抗大魏,因而面对北狄的侵犯,一再退让,舍地饲狼,最后非但没能保住基业,反而令本属晋国北方门户的朔州、恒州、燕州等大部悉数落入北狄之手。
内乱平定、大业告成之后,武帝将目光聚向北境,谋划北上,夺回重要门户——朔、恒、燕等地。不料在出兵北伐的路上,武帝旧伤复发,卧床不起,计划就此折戟。
武帝于数年后驾崩,太子继位,是为明帝。
明帝为太子时,在弟兄当中固然显得平庸,但自小宽厚有德,继位乃是人心所向。偏他在位的那几年,先是天灾不断,后又出现皇子争储之乱,明帝心力交瘁,亦是无力兼顾北方失地,于去年病重而去。十二岁的皇子戬奉上嗣大位,成为大魏的第四代君主,次年,也就是今年,改年号为天和,便是当今之少帝。
少帝尚未及冠,不能亲政。明帝临终前,指自己的三弟祁王为摄政亲王,将少帝托付给祁王和另外一位辅政大臣。
樊敬虽驻边多年,但也隐约知晓现如今的朝堂局势有些微妙。
祁王早年被封为安乐王,母家高贵。圣武皇帝在世时钟爱此子,缠绵病榻之际,还曾派祁王代自己到北境巡边犒军。当年那位少年安乐王的风采令樊敬印象深刻,虽过去了多年,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但言及祁王摄政,以他的资历和年纪,恐怕未必人人信服。
早些年,朝廷重心不在北境,守边二十余载的姜祖望也就被人遗忘了。但这几年,随着北境问题日益凸显,他自然重获关注。以他如今的声望,在这个时间,摄政王择其女为妃,目的显而易见。
姜祖望默然。
樊敬忙告罪:“大将军勿怪,实在是……”
他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好在……好在摄政王……才俊,和将军……堪称良配……”最后,他只好这么喃喃道,连自己也觉得这话实是软弱无力。
姜祖望摆了摆手:“你长年在她身边,她和你或比和我还亲。她可能去了哪里?”
樊敬立刻替姜含元辩白:“将军自小稳重干练,不会出事的,大将军尽管放心。她许是一时没想通,自己去散心了吧。她这次本就是要去云落城的,或许又去了那里?”
姜祖望紧锁眉头:“我没想到含元对这事的反应如此之大……怪我疏忽了。你即刻带几个人去云落城看看。”
“遵命!”樊敬匆匆离去。
姜祖望独自出神良久,忽然咳嗽起来,面露痛楚之色,手扶住案角慢慢地坐了回去,神色委顿。
半个月后,十月乙亥,秋高气爽,京城西郊皇家护国寺迎来了特殊的一天。
禁军将军刘向昨日便清完寺院,驱走一切闲杂人等,今日一大早又亲自统领五百禁卫来到这里,布在寺院前后以及周围,戒备之森严,连只苍蝇也休想越墙。
禁军之所以如此慎重,是因今日乃当今少帝母后兰太后的寿辰。太后倡俭抑奢,又笃信神佛,是护国寺的供养人,是以护国寺为她绘制了一幅壁画贺寿。今日,太后带着少帝来此,为壁画揭幕。
不但如此,同行之人还有以摄政王为首的诸王百官。此刻,一众人等虽已入寺,刘向依然不敢有半分懈怠。
寺院内外各处早已安排妥当,但刘向还是抽空亲自出来,又前后巡查了一遍,见确实没有纰漏才放了心。
他在寺院后门外匆匆叮嘱了手下几句,正要入内听宣,忽见对面山路的尽头走来一人。那人着青衣皂靴,头戴斗笠,因笠檐压得低,加上未到近处,他一时看不清脸,但从身形判断,年纪应当不大。
刘向立刻示意手下前去驱赶。那人便停在山道之畔,和到来的禁军士兵说了句话。
刘向见手下折返,而来人竟还不走,不禁恼怒,大步走去,厉声呵斥。
“将军,那人说与您相熟,请您过去,有话要说。”
刘向一怔,再次打量了对方一眼,见来人依旧立在路旁,身影沉静,实在想不出这会是谁,皱了皱眉,走到近前。
“你到底是何人?不知今日此处戒严?快走!”
对面的人举臂,略微抬高笠檐,露出了斗笠下的脸庞——年轻干净,眼眸清澈。来人朝他微微一笑,说道:“刘叔,是我,含元。”
刘向一怔,端详对方片刻,突然惊喜地出声:“小女君!怎会是你?”
刘向早年是姜祖望的部下,驻守北地雁门郡一带,与姜祖望同袍同泽。直到十几年前,两人才分道:姜祖望继续做安北都护,持节绥靖边郡,刘向则因旧伤解甲,后来入京做了禁军将军,掌宫门屯兵、内外禁卫。
当年武帝一统九州的战事催生了无数的武人功臣,但刘向那些年一直跟着姜祖望在北境服役,并未建过什么大功,能获得如此机会,离不开姜祖望的举荐。这些年,碍于内外不相交的禁忌,他们虽没机会再见,但对自己的老上司,刘向一直是怀着敬重感恩之心的。
至于姜含元,就更不用说了,刘向在军营里是看着她长大的。
刘向认出了来人,态度立刻变得亲热无比。
“小女君怎会突然入京?大将军可安好?哎呀,一晃多年没见,小女君竟也这么大了!我虽人在京中,这两年也时常听闻小女君的捷报,真是将门之后,武曲下凡,羞杀我等一干混吃等死之辈!”
他又上前,要向姜含元见礼,被她拦了。
“不敢当,刘叔不必客气。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找刘叔,是有事想请刘叔帮忙。”姜含元含笑说道。
刘向立刻点头:“小女君有何事,尽管道来。只要你刘叔能帮得上,绝不推辞!”
姜含元望了一眼护国寺的方向。
秋木掩映,自高墙寺宇的深处,随风飘来隐隐的佛唱声。阳光下,那一对高高立在雄伟大殿屋脊两侧的金碧琉璃鸱吻,闪烁着斑斓的光芒。
“那就多谢刘叔了。我想进去。”
刘向愣住:“这……”
他顿时期期艾艾,说不出话来。
姜含元微笑道:“我自知所求无理,实在是为难您。但请您放心,我不会给您惹麻烦的。”
倘若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就算是至亲提出这个要求,刘向也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但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姜祖望之女……
“敢问小女君,今日入寺所为何事?并非刘叔不愿帮忙,而是……小女君你也知道的,我职责在身,不能有半分差池。”终于,他开了口,小心试探。
“我想看一眼摄政王。”她语气很是寻常。
刘向再次一怔,想起一事:摄政王年二十又四,却至今未曾娉内,王妃之位空悬。
几个月前,刘向听到一个不知真假的传言。
摄政王入宫探望武帝朝的老太妃。太妃心疼他身边至今没个知冷知热的知心人,催他立妃,他便笑称自己仰慕姜祖望之女,若能娶其为妻,则当无憾。
姜祖望的原配早逝,他只有一个女儿,那便是从小被他带在身边的姜含元。
刘向又听闻上个月,宗正卿贤王老千岁束韫出京北上了,无人知晓老千岁此行的目的,但那个传言愈盛,都说老千岁是去替摄政王求亲了。
今日姜含元在这里现身,且看这一身装束,分明是悄然入的京城。
看来传言是真的。刘向暗暗松了口气。
原来如此。小女君在沙场上虽不让须眉,但终究是女孩儿家,想看一眼未来郎君的模样,也是人之常情。
祁王摄政后,宵衣旰食,孜孜不倦,常理政至深夜乃至通宵达旦,为方便常宿于宫中,外人想入宫窥其样貌自是不可能的。今日确实算是极为难得的便宜机会。
刘向又暗暗打量了一番姜含元,只见她气定神闲、泰然自若,料她知道轻重。这一点,他是绝对相信的。
退一步说,就算不考虑自己和姜家的旧情,日后她若真成为摄政王妃,必居于京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过这样一个要求,他怎能不应?
刘向不再犹豫,低声道:“也好,今日我就为小女君你破例一回。方才已观毕供养殿的壁画,摄政王伴着太后及陛下去了罗汉殿,在听法师讲经。你可扮作我的亲兵入内,以暗语通行,来回无阻。只是,小女君牢记,切勿惊动他人。”最后他靠近些,用略带调侃的亲切语气,促狭地道了一句,“摄政王姿貌无须近观,小女君只消远远看上一眼,便有数了。”
“多谢刘叔,我有数。”姜含元丝毫没有忸怩,只微微躬身,笑着道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