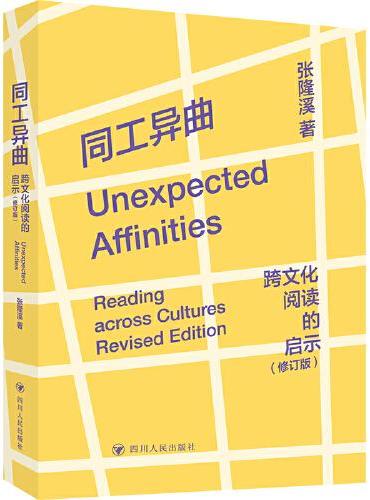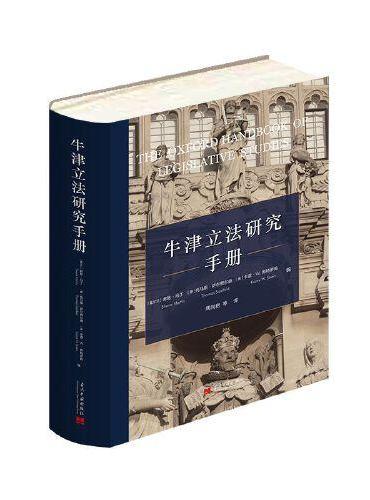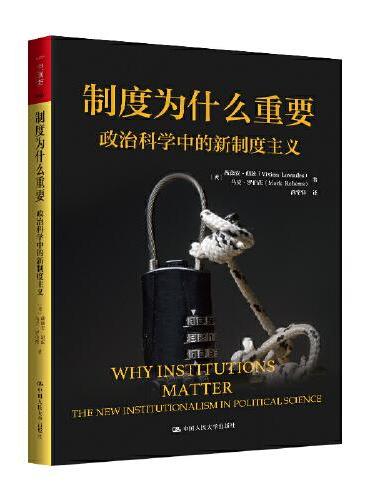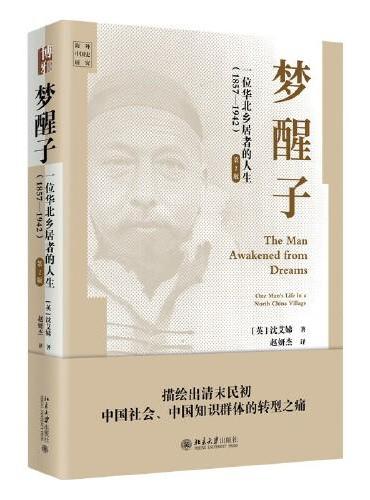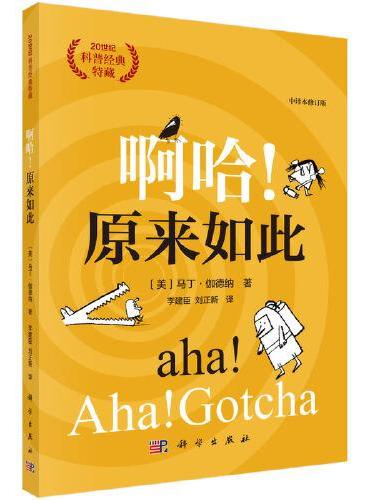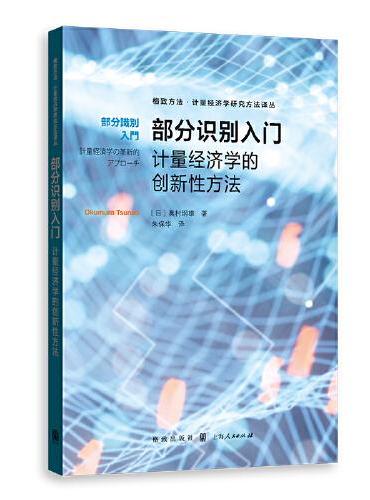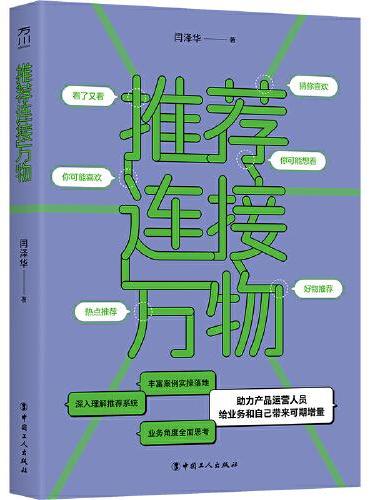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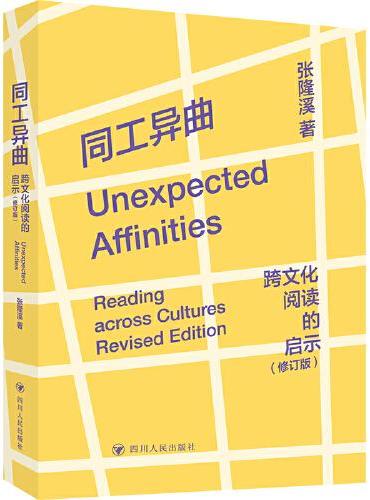
《
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修订版)
》
售價:HK$
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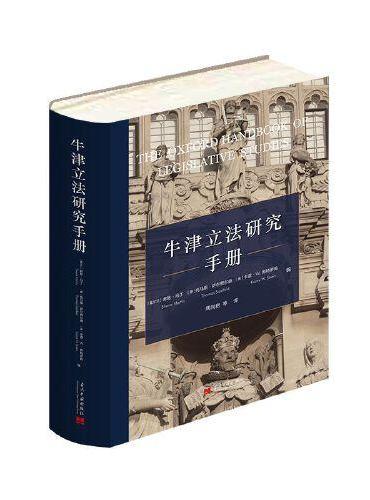
《
牛津立法研究手册
》
售價:HK$
35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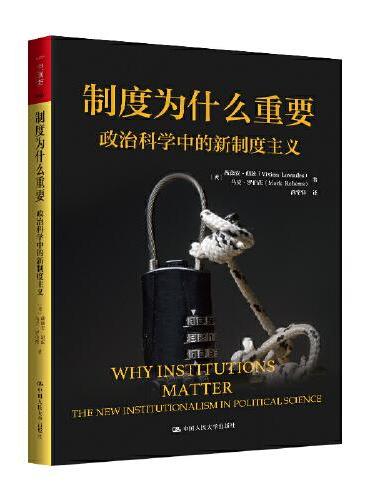
《
制度为什么重要: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人文社科悦读坊)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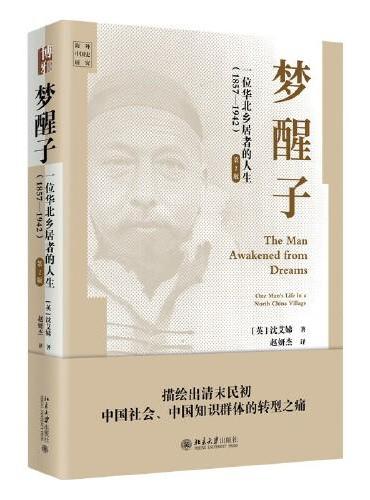
《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第2版)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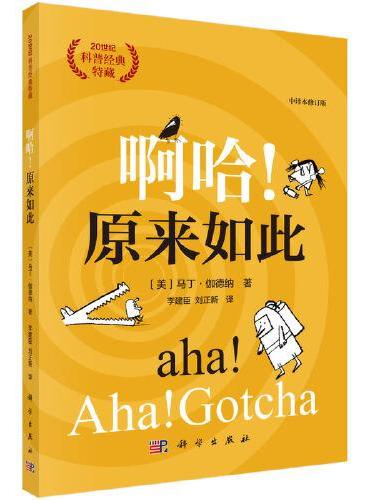
《
啊哈!原来如此(中译本修订版)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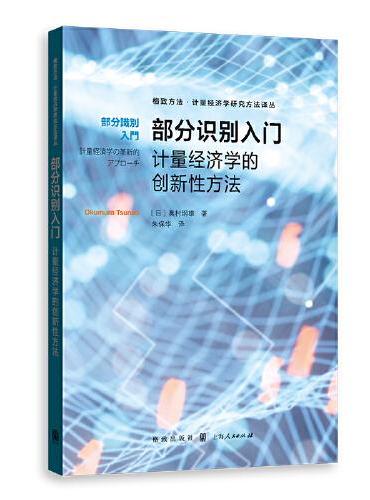
《
部分识别入门——计量经济学的创新性方法
》
售價:HK$
75.9

《
东野圭吾:变身(来一场真正的烧脑 如果移植了别人的脑子,那是否还是我自己)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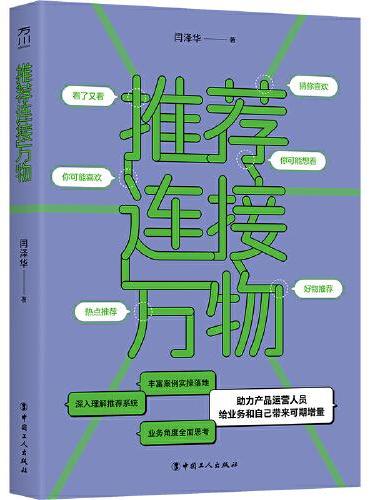
《
推荐连接万物
》
售價:HK$
63.8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为一本简明的史学史著作,扼要介绍了从《尚书》到《文史通义》的数部中国史学名著。作者从学科史的角度,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比照中见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精神与大义。
|
| 關於作者: |
|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
| 目錄:
|
自序 /
《尚书》 /
《春秋》 /
《春秋》三传 /
《左传》(附《国语》《国策》) /
《史记》(上) /
《史记》(中) /
《史记》(下) /
《汉书》 /
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 /
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 /
《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 /
刘知幾《史通》 /
杜佑《通典》(上) /
杜佑《通典》(下)(附吴兢《贞观政要》) /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 /
司马光《资治通鉴》 /
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
郑樵《通志》 /
马端临《文献通考》 /
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全谢山的《宋元学案》 /
从黄全两学案讲到章实斋《文史通义》 /
章实斋《文史通义》 /
|
| 內容試閱:
|
欧阳修《新五代史》
现在讲到宋代。讲中国学术史,宋代是一个极盛时期。上比唐代,下比明代,都来得像样。唐代富盛,明代亦然。而宋代衰贫,讲国势当然宋不如唐,也不如明。但是学术恰恰不同,唐朝只是佛学大盛的时代,宋不能及。若论文学,唐诗宋诗各有长处,唐诗并不一定就是在宋诗之上。如讲古文,虽然由唐代韩柳开始,可是宋代的古文盛过了唐代。经学、史学各方面,唐朝都远不能与宋相比。明代也一样不能同宋相比。今天我们对于所谓“宋学”,大率有两种错误的见解。一为清代学者的门户之见,他们自称为“汉学”,以与宋学分立门户。尤其是乾嘉以后,是看不起宋学的。民国以来,接受了清代人这一种门户之见,还加上了一套浅薄的实用主义观点,认为若是宋代学术好,为何不能救宋代的衰与穷。这话其实讲不通。孔孟儒家,乃至于先秦诸子百家,也并没有救了春秋战国。我们现在佩服西方人,但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并没有救了希腊。罗马帝国后来也已经遵奉耶稣教,但耶稣教也并没有救了罗马。像此之类,可见我们不该用一种浅薄的实用主义来批评学术。孔孟儒家乃至先秦诸子的学术,自有它的价值。纵算不能挽救春秋战国时代之乱,但为后来中国学术史上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宋代的学术,固然也不能救宋代之衰亡,但亦为宋以下的中国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等于我们讲希腊这几位大哲学家或者耶稣教,也不专在希腊罗马时代发生作用,它们的作用还要在后发生。这些我们暂时不多讲。
我们要专讲到史学。再回头来看看以前,周公的《西周书》此刻也暂不讲。中国史学从孔子《春秋》一路下来,经过《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到太史公《史记》,这一段是中国史学的极盛时代,正是起在乱世。当然,学术史的年代,同普通史的年代,不能划得恰平,中间有些参差不齐的。如太史公《史记》,已经到了汉武帝时,可是我们可以把史学从孔子《春秋》一路到太史公《史记》,这是中国史学的一段黄金时代。而此一段黄金时代,则正起在春秋战国衰乱之世。
第二段就是上面几次讲的,根据《隋书·经籍志》从东汉末年一路讲到唐初刘知幾《史通》这一段。从普通史讲,又是中国的一个中衰时期,然而史学在那个时期则很盛。我们能不能这样说,时代衰,史学会盛。好像一个人,跑到前面无路,发生了问题,会回过头来看看,那就是在衰乱世史学会盛的一番理由了。自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一路下来,是一个中衰时期,而史学确盛。只是那时史学虽盛,但不够理想。对于当时,乃至后世,并无甚大贡献,这我已在上面讲过。
第三个时期就是宋代。拿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个大时代来讲,宋代最弱,也可说宋代在中国历史里边,是一个比较中衰的时代。所以这时代能有史学复兴了。而这一时期的史学,比较上,他们能针对着时代要求,在史学上有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贡献。较之东汉末到隋唐统一一段,宋人的史学确要好些。但为何宋代还是不行,这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乃是另一问题,不能把普通史来一气抹煞了学术史。再下,到了明代末年,清室入主,那时候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大的转变,而那时又有史学兴起,新的史学又见曙光。可惜下面满洲政府政治上的高压力量使我们这一番新的史学只见萌芽而又不能发旺滋长。后来乾嘉以后,时代是盛了,而学术反走上了一条不理想的路,史学也一样。
我们讲到第五个时期,应该是清末民初我们的现代,这正是我们国家民族又在一个艰苦多难之秋了,又是一个时代的大转变。照例,我们在这个时期也该有史学兴起。换言之,我们又该要回头看一看啊!我们到了今天,该要回头看一看我们这两千年四千年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这个回头看,便是史学兴起之契机。可是我们现代这一段史学,可说并不能满足人的想望,而只有使人失望。到今天,我们这时代的史学,并未能对国家社会有些好的影响、大的贡献。反而横生枝节,发展出很多坏影响。关于此明末乃至民初的两段史学,我们到以后再讲。今天我们下面几讲,则都是讲宋代的史学。
宋代学术,不是单单史学一项,只是在全部宋学中有了史学一项。我在宋代史学中,想首先举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来讲。我们去年讲了四史以后,不再讲此下的许多所谓正史了。因其在体制大节上,没有什么可讲。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则不然。我们要拿一大题目讲宋代史学,那么首先就该提到它。而且从唐代以后中国人修史,都是属于官修的。至于私家著史,则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这一部。上面所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都不是官修的。欧阳修《新五代史》,则是后代惟一的一家私人著作。他生存时,这部稿子并不曾送上朝廷,也不是朝廷要他写的。等他死了以后,朝廷上才下诏把他这部稿子在国子监开雕出版。这是第一点值得我们提出的。第二点,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上法《春秋》的。后来人批评此书,说它“褒贬祖春秋,故义理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又说“史官秉笔之士,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惟欧公慨然自任迁固”。这是说一般正史,从四史以下文章都写不好,也没有一种高的观点,足以成为标准的著作。只有欧阳修《新五代史》,可谓迁固以来未之有。这都是极端称赞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文章比《史记》,而书中义理又是学孔子《春秋》的。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以前,已有了薛居正的《五代史》,这是奉政府命编修的。欧史一出,就变成了两部。一部称曰《旧五代史》,就是薛居正写的。一部称曰《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写的。就两书的篇幅材料来讲,《旧五代史》比《新五代史》多得多。也有人对此两书作了各有得失的批评,说是:“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谷》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此是说薛史像《左传》,从头到尾纪事详细。欧史是学孔子《春秋》讲义理,褒贬分明而记载多不可靠。这话好像很公平,但拿薛史比《左传》,拿欧史比《公》《谷》,实际上是比拟不伦。即论纪事,欧史也不能同从前的《公》《谷》相比。《公》《谷》确是记事很疏,欧史所记,只能说他简洁严正,多所删略,不能说他都有错。欧史当然亦有记载错误处,这从太史公《史记》一路下来,从前的历史都如此,没有一部历史从头到尾没有错。当然不必专讲薛居正的《五代史》。所以我们要有“考史”工夫。但历史不单是一堆材料,清代讲史学的人,就有人赞成《新五代史》,有人赞成《旧五代史》,把此两书来详细比较。诸位也可自己把此两书仔细去对看。但史学上更重要的,是写史人的义法所在,这可说《旧五代史》根本不能同《新五代史》相比。
赵瓯北的《廿二史劄记》,比较似乎推尊《新五代史》。他说:“不阅薛史,不知欧公之简严。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寓春秋书法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薛史网罗一大堆材料,当然记载是详了,可是写史还得应该“简”。赵瓯北说欧史文章干净,直追《史记》,而他的纪传里边都有《春秋》笔法,连《史记》也不能及,可见是很看重《新五代史》的。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则似乎有许多地方偏重《旧五代史》。甚至即在宋代,司马温公的《通鉴》,写到唐史,也比较多用《旧唐书》,少用《新唐书》。《新唐书》就有欧阳修在内。他对于五代史,也比较多用薛史,少用欧史。照这样讲,岂不是司马温公在史学上也并不很看重欧阳修吗?这问题到下边再说。总而言之,《旧五代史》是一路跟着上面从四史以下的诸史来,他只是网罗材料归纳起来便是。而《新五代史》则有写史的一套义法,不是归纳一堆材料就算历史的。这一点,我们觉得该特别看重。
我们且把欧阳修《新五代史》里所谓写史的“义法”举几点讲一下。五代是梁、唐、晋、汉、周。梁代第一个本纪是朱温,后来唐朝赐他名字叫“朱全忠”,薛史开头就称朱温为“帝”,而欧史则开头称他是“朱温”,后来唐朝赐了他名字,才称他“朱全忠”,再后来封了王,然后始称他是“王”,更后来他篡位做了皇帝,那才称之曰“帝”。单举这一点,诸位把此两书比看,就是一个大不同。薛史也有它来历,如从前南史宋齐梁陈四代,每一个皇帝,本纪一开始就称“帝”。而欧史则是学的《史记》,沛公到后来才称“帝”,为沛公时不称“帝”。最先也不称“沛公”。若我们只读薛史,正名定义都称“帝”,一读新史,才知本末。朱温本是一个很下流的人,然而还好。更有外国人跑来在中国做皇帝的,诸位一读欧史,原原本本、清清楚楚,都知道。这些只读本纪就知。所以欧阳修自己说:“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春秋是个乱世,然而孔子《春秋》里面,有一种书法,故说因乱世而立治法。但到欧阳修写史,那时是已经有了治法了,孔子以下治国平天下岂不已有了大纲大法吗?孔子《春秋》是因乱世立治法,现在欧阳修写史,乃是拿孔子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大法来正这些乱君。我从前就最喜欢拿欧史本纪来同薛史两面对读,一个一个皇帝,在这边都见得清清楚楚,在那边则都是“帝”,只做了皇帝,一开头就是“帝”了,岂不这两书的高下一看就见了吗?
五代很短,一个时期,就有八姓十三君,只有梁、唐两代,每一代有三十多年。此外的各代,都只几年、十几年。因此在五代时做臣的,很少只在一个朝代做,普通都是一个人做了几代的官。倘使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好像这个人做了清朝的官,又做袁世凯时代的官,又做国民政府的官,或许再做到共产政府的官,这是一个乱世现象。薛史则只要这个人死在哪一朝代就写在哪一朝代里,好像此等事不成一问题,这就把五代史所应有的特殊点没有把握到。欧阳修的《五代史》,若其人专是一朝之臣,就入梁臣传、或入唐臣传。但这样的人少得很。梁臣传、唐臣传中所收真是极少。一个人都做几个朝代的官,历事数朝,欧史便把来另立一个“杂传”,乱七八糟地拉杂作传,这真是多。也有人批评说:这样写法,只看目录,便感到不好看。怎么每一朝代只有两三个臣?这种批评,实是可笑。一部《五代史》,真是一段漆黑的历史,难得有几个人在一个朝廷做臣,而一个人兼做了五代之臣四代之臣的,却很多。那我们岂不只看目录,便可想见了这一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了吗?这亦可说是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创例,为从前所没有。
照旧史之例,一篇传后有论、有赞。而欧阳修的《五代史》,则论赞不苟作。每篇后有论赞,都是很重要的一篇大议论,不是随便循例而写。最有趣的一点,在欧史写的传赞里,每以“乌呼”二字开头。先叹了一口气,再往下讲。也就有人批评说,从前历史传后的赞,没有拿“乌呼”两字开头的。这种都是学的刘知幾,只在小处批评,而并不了解写史人的特别宗旨。欧阳修自己说:“此衰世之书也。”既如此,那有什么可“赞”,但照例史传到最后要赞几句,他却不是在“赞”而在“叹”。所以欧阳修又说:我用《春秋》是用其法,师其意,而不学其文。其实有许多人,是可“叹”而不可“赞”的。在五代这个时代无可赞只可叹,那有何不可呢?我小孩时,在小学里读书,写了一篇文章,先生大为称赞。那时我在初级小学,有高级小学年纪大的学生就围着这先生说:他写的文章先生说好,但文章总没有开头就用“乌呼”两个字的。先生说:你们不知,欧阳修的《五代史》,开头就用了“乌呼”二字。当时的小学先生,学问也博,多能读过史书。那时在我脑里就有了个欧阳修。其实我那时也没有读过《五代史》,不晓得怎么开头就用了“乌呼”二字。但在欧阳修以前,是没有人用“乌呼”二字作文章开头的,所以有人要批评我,而那位先生可以替我辩,说欧阳修就这样。但若有人批评欧阳修,那又有什么办法呀!
诸位读史书,于“考史”外,又要懂得“论史”。不仅要知从前人对其当时及以往的一切批评,还要有眼光针对自己时代作批评。不能人云亦云,前人如何批评,我也如何批评,该要有新意见,新批评。但也不能像五四运动以来那样信口批评,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一笔抹杀了全部历史,那实无所谓批评。到今天,已到了全部历史更无可批评了,遂只有作搜集材料的工夫。但搜集这些材料又有什么用,若使一部二十四史全是帝王家谱,全是专制政治、封建社会,那么还要读什么中国史?可见“评史”不能省,但批评历史要能有见解,要知道从前人的批评,还要能来批评从前人。我们且随便再讲几点欧阳修的《五代史》。如说军事,五代正是用兵时代,欧史用攻、伐、讨、征四个字来分别记载。两军相交,处在同等地位者称“攻”。以大压小,一大国攻打一小国,或中央政府的军队攻打一地方,这叫“伐”。对方确实有罪称“讨”。天子自往称“征”。这就是春秋笔法。只看他用哪个字,便知是哪样一会事,很简单。兵事成果亦有不同。用兵获地,或称“取”,或称“克”。易得曰“取”,难取曰“克”。又如敌人投降,以身归称“降”。带着他辖地来归称“附”。你只看一“降”字,便知他一人来,或仅带着家,乃至随从少许人。倘见“附”字,便知他带着地方一并投降。又如“反”与“叛”。“叛”是背叛了这里归附到那里,在此称“叛”,在彼称“附”,如背梁附唐。若在下反上,不是归附到别人那里去,只在里边作乱、造反,这是“反”。又有“自杀”与“死”不同。“死”是死节,为国为公而死,“自杀”则还不到“死”的程度。自杀当然死了,但还不够称“死”。死是一种忠节,“自杀”则仅是自杀而已。“他杀”亦与“伏诛”不同。有大罪,应该杀,这称“伏诛”。仅是杀了他,这又不同。像此之类,欧阳修《五代史》讲究这些用字,很有趣味。
诸位可看从前人讲《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显有分别,新史里有他自己的许多“例”,现在我们不看重这些,只拿书中材料来作研究。一件一件事,不分轻重大小是非得失,那就没有趣味。现在人讲历史,都只讲了下一级,不向高处寻。所以我特别要再讲《史记》《汉书》。一样都写汉代人的事,但两书体例不同,此因背后作者人物不同,学识不同。我们现在都不管,从来不去研究到整部书,更没有研究到书背后的那个人,只研究书中间的事情,而有些事情又更无研究意义。如这个人究是“死”,还是“自杀”,我们都不管,只知他死了便算。我们觉得,研究历史,只是些旧东西,只是一堆旧材料,但从前人如何来写此历史,你不能说这些不值一论。孔子作《春秋》,也是一部历史,若只看材料,当然远不如《左传》,《左传》里材料详细得多,《春秋》还有什么价值?所以孔子便远不如左丘明。那么从前人为何要推尊孔子,我们说这只是一种旧观念。这样一来,我们今天的史学,先有一个新旧观念的分别横梗在里面。我们又要拿西方人的史学观念来讲中国人的历史。但西方历史远为简单,为了这一点,至少使我们今天无法有史学了。从前人争论的问题,今天一律都不管了。什么“死节”呀,以及治乱兴亡呀,我们似乎都没有工夫和兴趣去讲究。大问题不讲,只找一些极小的题目,这就意味何在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