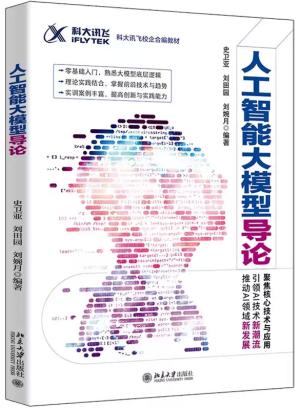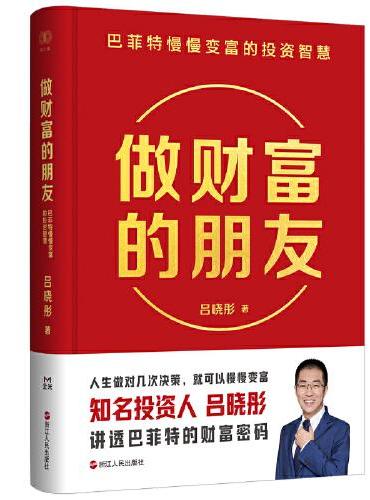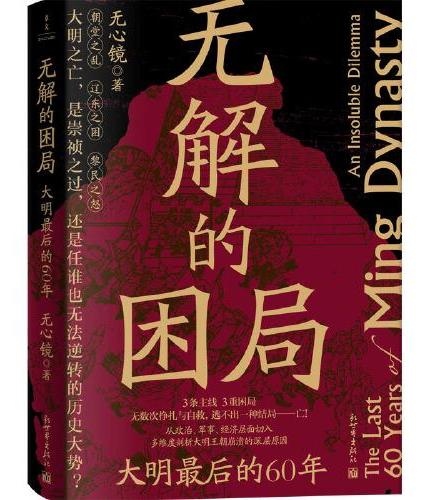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HK$
74.8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HK$
75.9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HK$
85.8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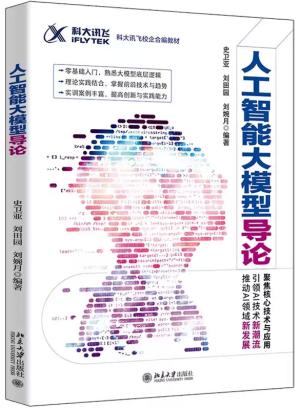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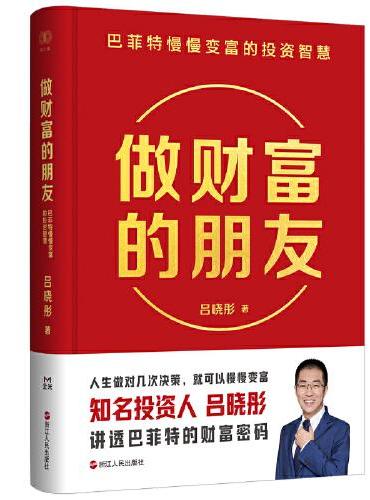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HK$
82.5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HK$
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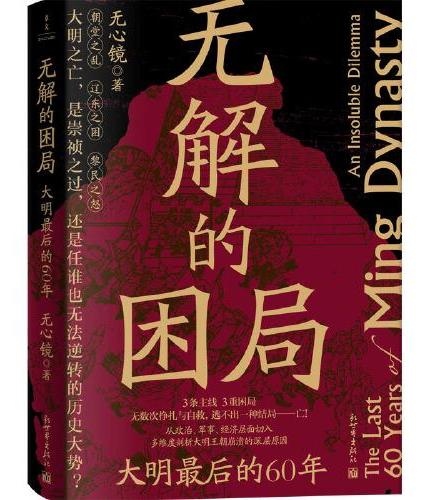
《
无解的困局:大明最后的60年
》
售價:HK$
66.0
|
| 編輯推薦: |
-社会学研究不能没有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而谈论民族问题且被收入“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中的,只有《民族与社会研究》。
-初版于2001年,费孝通先生题写书名并推荐,经典之作全面修订,新版更为深入地探讨“民族”定义,探究什么是“民族共同体”。
-11篇文章,立足不同的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族际通婚、少数民族教育、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等等,为民族问题及其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大量调研资料与理论,数据详实,文献资料丰富,是民族研究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
|
| 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了马戎在1997年至2001年期间发表的以民族问题研究为主题的11篇文章。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核心的议题就是如何把“民族”这个鸦片战争后引入中国的西方概念具体应用到中国社会。本书的中心内容即为中国学术界是如何接受这一概念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场景。其余各篇分别涉及族际通婚、双语教育、婚姻制度等族群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还有几篇介绍西方族群社会学研究概况、美国族群关系演变等课题。
本文集回顾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争论,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走向,为民族问题的社会学、人口学和教育研究等提供参考与借鉴。
|
| 關於作者: |
|
马戎,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问题、教育问题等。出版学术著作:《西藏的人口与社会》《民族与社会发展》《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民族社会学导论》《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等。
|
| 目錄:
|
新版序言 I
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 1
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28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66
关于“民族”定义 94
论民族意识的产生 118
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 128
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 146
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双语教学 209
试论历史上藏族的“一妻多夫”婚姻 244
美国社会发展中的种族与少数族群问题 268
边区开发中的民族研究 303
初版后记 327
|
| 內容試閱:
|
新版序言
我很感谢三联生活书店将《民族与社会发展》列入出版计划。
这本文集收录了我在1997 年至2001 年发表的以民族问题研究为主题的11 篇文章,曾由民族出版社在2001 年出版。虽然多为20 年前的旧作,但是我觉得这本文集的再版在今天仍然很有意义,特别是其中那些讨论“民族”定义的部分内容。进入21 世纪后,我国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民族关系出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新态势(如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2014 年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政府多次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事态的发展和中央的政策调整充分说明我国的民族关系问题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全国人民需要对民族问题给予更多关注。这本文集的内容将有助于我们回顾20 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争论,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思考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走向,这对于面临国内外风云变幻的中国年轻一代,我相信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时,最核心的议题就是梳理鸦片战争后引入中国的“民族”这个西方概念,在被具体应用于中国社会后,在人们的理解中出现了哪些不同的思路。面对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我们应当把哪个层面的群体定义为“民族”?当我们把国内汉、满、蒙古、回、藏等群体定义为“民族”时,这些“民族”与全体中国人组成的“中华民族”之间,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我们应当制定怎样的制度和政策来处理这些“民族”与国家、各“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思考和理论探索中,我们应当如何分析西欧国家或者苏联的“民族”理论与相关制度政策的设计思路,借鉴吸收其他国家“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过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实践效果,从而在此基础上思考在21 世纪,我们应当如何重新构建国内的“民族”话语和中国社会的群体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开展对话和交流。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对群体进行分类的核心概念是涵盖“天下”的“夷夏之辨”和“有教无类”,中国文化里既没有西方社会以体质和语言来界定的“种族”(race)概念,也没有产生近代西方以公民权和主权实体为基础的“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鸦片战争后,由西方传入中国而引发的以汉、满、蒙古、回、藏等各族为单元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分化中国的阴谋,完全背离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族际关系模式, 其结果导致了“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多个群体层面上的滥用。梁启超先生1903 年有关国内“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的区分(梁启超,1903/1989:75—76),1939 年顾颉刚先生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顾颉刚,1939),都曾试图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强调以国家为单位的“大民族主义”,抵制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小民族主义”。由此可见,“民族”(“国族”)的讨论是贯穿晚清和整个民国时期我国学术界民族研究的核心议题。
文集第一篇“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是我在对国内民族关系现状多年实地调查和理论思考基础上提出的重要议题,其中的核心部分特别讨论了中文“民族”一词的定义。我始终认为,在“中华民族”和56 个“民族”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层面同时使用“民族”一词是不妥的,必然会在理论和实践中造成基本概念混乱和认同意识误导。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应当“探讨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把‘国族’(中华民族)与‘民族’(汉、满、蒙古、回、藏等各族)在层次上区分开来,从而建立一个超越各族群、能够反映我国‘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的群体意识”这一世纪命题。我当时提出的具体建议是:“我们可能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从‘国族’的新角度来使用‘中华民族’这个习惯用语,同时保持56 个‘民族’的称呼;第二个是‘中华民族’的称呼不变,以便与英文的‘Chinese nation’相对应,而把56 个民族改称‘族群’,以与英文的‘ethnic groups’相对应。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有助于把在使用中相互模糊混淆的词汇明确地区分开来。”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nation”是近代欧洲用以表示现代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的重要概念,中文通常译作“民族”。在西欧社会,“state”指执政的国家政府,“nation”指的是由一国全体“公民”及以“公民的民族主义”为基本认同构成的民族国家。(Smith,1991: 11)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合众国,都是在这一认同基础上建立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更准确地说,都是“国族国家”。在中文中,如将“nation”译为“国族”,其实更贴切。“nation state”表示的是与国际法中独立的行政主权(sovereignty)和边界明确的领土(territory)等密切相关的政治实体。本国全体公民(无论祖先血缘、肤色、语言和宗教信仰等)都是“nation”成员。法兰西民族(French nation)、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在中文中如果译成“法兰西国族”“美利坚国族”“印度国族”也许更符合其本质原义,而这三个“民族”内部的种族、语言、宗教差异性并不比中国内部的群体差异小。“United Nations”(联合国)译成“国族的联合体”是适宜的。(马戎,2019:218)所以,“Chinese nation”完全可以译为“中华国族”。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第一讲即提出:“甚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诸情形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 孙中山,1924/2001:2)自20 世纪初直至90 年代,曾有多位中国学者讨论过“国族”这个概念,(袁业裕,1936:19—21;潘光旦,1995:48;宁骚,1995:5;郑凡等,1997:63)相关讨论的实质就是探讨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把“国族”(中华民族)与“民族”(汉、满、蒙古、回、藏等)在层次上加以区分,从而建立一个既能反映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又能在现实社会场景中被国内所有群体接受的新的政治认同体系。
在民国时期,“中华国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常用的概念。1949 年后“国族”一词很少使用。不仅如此,在2018 年《宪法》修正案之前的我国历次颁布的《宪法》和1984 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均没有出现“中华民族”一词。在政府文件和民众日常话语中,“民族”一词主要出现在对56 个“民族”和“少数民族”这一层面的表述上,并且与“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决”等联系在一起。20 世纪50 年代开启的“民族识别”、身份证标注“民族成分”、设立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所体现的即是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概念的使用模式以及对“多元一体”格局中56 个“民族”这一层面的重视。
文集第四篇“关于‘民族’定义”是对这一议题的进一步探讨,回溯了在国内汉文文献中“民族”一词的定义、译名以及西方文献中相关概念的使用。第一篇、第四篇与第五篇“论民族意识的产生”和第六篇“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密切相关,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西方的“nation”概念和斯大林“民族”定义传入后,中国学术界是如何接受并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场景的。可以说,这4 篇论文是这本文集的核心内容,虽然反映的是我在2000 年的认识水平,但是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和近年来杂志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李贽,2016),仍然可以感到,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核心议题至今没有取得共识,更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
1949 年后,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把中文“民族”一词译成英文时,参照苏联马恩列斯编译局的译法,把56 个“民族”层面的民族译为“nationality”, 以便和“中华民族” 译法(Chinese nation) 中的“nation” 相区别。在19 世纪和20 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和一些西方学者在讨论各国境内的少数群体时,曾经使用
过“nationality”, 但是20 世纪20 年代后这一用法已基本停用。根据今天的国际通用概念,“nationality” 是国籍,(郝瑞,2002)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护照的“nationality” 一栏填写的是“UnitedStates of America”,中国护照的“nationality”一栏填写的是“中国CHINA”。由此可见,今天我们仍然把56 个“民族”层面的民族译为“nationality”,这一译法在基本概念的理解上已不适宜。正因为如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英文译名从“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ssion” 改为“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郝瑞,2000:282)
尽管一些有关民族事务机构的英文译法做了调整,例如各民族院校的英文译名近几年改用汉语拼音,如中央民族大学的英文译名,2008 年从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改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但是国内对于中文“民族”的英译至今仍不统一。最近的例子是,在2017 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有关“民族”的官方英文译法为:Chinese nation(“中华民族”)、ethnic minorities(“少数民族”)、different ethnic groups(“各民族”)、regional ethnic autonomy(“民族区域自治”)、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各族人民”)。十九大部分修订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将“少数民族”等概念译为“ethnic minorities”。这是符合国际规范理解的
译法。但是,“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官方英文文本依然使用‘minority nationalities’而非‘ethnic minorities’来翻译‘少数民族’, 用‘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而非‘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来翻译‘各族人民’, 用‘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而非‘regional ethnic autonomy’来翻译‘民族区域自治’。”(叶江,2018:1)所以,今天对于中文“民族”这一关键词的不同英文译法,依然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译者们对于该词内涵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政治导向。自从我在文集第一篇中提出这个议题以来,已经过去了20 年,但是人们的认识仍未统一。我觉得中国学术界关于“民族”定义的争论仍会延续一段时间,读者们带着这些问题来阅读这本文集,可能会对中国当今的民族问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解。
这本文集其余各篇分别涉及族际通婚、双语教育、婚姻制度等族群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还有几篇介绍西方族群社会学研究概况、美国族群关系演变和北京大学20 世纪90 年代开展的与民族研究相关的课题。对于从事民族问题的社会学、人口学和教育研究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可能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内容。
我自己对中文“民族”一词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我过去发表的文章中,我曾把美国的“ethnic studies”译成“民族研究”。1997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翻译的一本译文集, 英文书名是Sociology of Ethnicity in the West:Theory and Methodology,但是中文书名是“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这本书的修订版时,中文书名改为“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2004 年北京大学出版了我编写的教材,书名是“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ical Study of Ethnic Relations)。我之所以至今仍然使用“民族社会学”一词,是因为国内广大读者和学生无论对中文的“族群”还是英文的“ethnicity”都比较陌生,他们长期以来已习惯于把我国族群关系的研究叫作“民族研究”。所以,我编写的教材书名和我的招生专业方向至今仍然叫“民族研究”,但是在书名副标题和英文书名中,我都清晰地将其定位于“study of ethnic relation”。
从我自己对 “nation””“nationalism”“ethnic group”等有关英文词汇内涵的理解以及自己多年来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田野调查经历中的实际感受,我觉得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多方面其实更类似于西方国家内部的“族群”。而且我相信,现有的这些称呼在将来一定会得到调整,以适应中国人应当构建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按照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方向的提法,就是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于这种考虑,在这本文集再版时,许多地方的“民族”被修改为“族群”。但是,由于“少数民族”“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地方”“少数民族教育”等已被使用了许多年,已成为政府文件和许多研究著作的习惯用语,所以,在涉及这些论述时,文中依旧保留了“民族”一词的用法。
自从这本文集出版后,我一直在我国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等)从事社会调查和相关理论问题的阅读与思考。2008 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 年乌鲁木齐“7·5”事件对我的冲击很大,这些大规模恶性暴力事件进一步推动我去系统思考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及未来改善民族关系的思路。自2012 年以来,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编了《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这套丛书已出版24 本,涉及族群研究的各主要领域和专题。在这套丛书中,由我撰写的文集有五本:《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2012)、《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2012)、《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2014)、《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族群关系》(2016)和《历史演进中的中国民族话语》(2019)。这五本文 集汇集了我近十年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读者们如果有兴趣,不妨找来一读。
关于“民族”定义
关于人们观念中的“民族”定义及有关基本理论所涉及的领域
很广,从最基本的方面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对“民族”如何定义——我们使用的“民族”一词的含义是什么?
不同的民族群体是根据什么标准相互区别开的?每个研究者在进行
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时,都必须事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即“民
族”)做一个界定,这是与前人文献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
对话的前提条件。二是民族意识的产生和传递。人并非天生而有族
群和自己民族身份的意识,那么这种意识是如何获得的?这种意识
又如何在代际之间、在人们交往过程中相互传递、延续和变化?三
是民族群体之间、各民族的成员之间在交往中的关系,这些关系体
现在哪些方面?受哪些因素影响?在这些交往中,族群意识如何具
有象征性意义并影响个人与群体行为?我们在研究群体关系的同
时,需要特别关注分属不同群体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把各
个族群内部整体与个体两个层次之间的互动和族群之间整体与个体
的交叉互动既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分。
换言之,世界各地有如此众多的人类群体,他们如何界定自身
和相互界定?学者如何来界定它们?学者进行这种界定的基础是什
么?人们出生后通过什么途径得到有关自己民族族属的意识?有了
这种意识之后,人们又如何处理自己与其他人(本族或其他民族的成
员)的关系?譬如一个汉族农民,他从南方农业区迁移到了北方蒙古
族草原牧区,定居下来,他怎样界定自身与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如何
与他们交往与共事?这些关系是如何处理的?又如在美国生活的中国
移民及其后裔,作为黑头发黄皮肤的族群,他们的族群意识是怎样获
得和演变的?他们如何与白人、黑人族群交往和共事?
无论是从宏观(群体)的层面上还是微观(个体)的层面上,这
三个部分的研究是社会学的民族研究特别予以关注的。除此之外,尚
有两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人类的起源在这个地球上是多元
的,各个群体的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是相互隔绝的,各自有着
各自的发展轨迹,形成了不同的观念系统,包括群体界定的观念,这
些观念体系之间存在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殊性,所以需要从多元的
角度来认识世界上的民族现象与民族概念;第二,民族群体的界定和
民族意识的产生、延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内涵与外延都随着外
界场景和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处于不断的变迁
之中。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有关“民族”定义的问题。
应当如何定义中文中使用的“民族”这个词汇,有关定义如何与国外
学术界使用的概念以及社会上人们通用的概念之间相互衔接,这一定
义如何能够科学地反映我国族群和民族关系的客观现实,这是我国学术界长期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定义的认识
第一,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流行的、最具权威性的定义。虽然马克
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多次谈到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但是
从来没有专门讨论过“民族”的确切定义。苏联和国内学术界长期
以来奉为经典的,是斯大林于1913 年提出的“民族”定义,即人们
今天仍经常引用的“四个特征”:“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
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
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1913/1953:294)
斯大林在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文章中,对这四条逐一加以说明,并且把“民族”区别于“种族”和“部落”,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斯
大林,1913/1953:300)。在他的这些有关“民族”的论述中,他努力
建立一套完整的逻辑和概念体系,其核心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来定义各个历史阶段的“民族”含义与性质。
同时斯大林坚持,要成为或被“定义”为一个“民族”,这四条标准缺一不可,“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这样他就把“北美利坚人”算为一个民族,他称“英吉利人、北美利坚人和爱尔兰人……是三个不同的民族”。(斯大林,1913/1953:294)同时他不承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因为犹太人“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斯大林,1913/1953:295)同时“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的日耳曼人和拉脱维亚人”也不是民族。也是基于同一理由,他坚持说中国的回族因为没有独立的语言,不能算是民族,而只能算是一种宗教集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作为一般规律来定义现时历史
时期的“民族”时,多少带有与当时俄国政治形势有关的政治性的
考虑。20 世纪初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面临“民族文化自治”和以
民族划分来分裂无产阶级政党的民族主义思潮,斯大林当时提出的
“民族”定义是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阿拉坦等,1989:31—33)
苏联建立之后,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德国的日耳曼人是一个民族,
在苏联境内的日耳曼人算不算一个民族?否则是不是也要在“东普
鲁士”(即加里宁格勒市所在的地区,俄罗斯联邦的一块飞地)成
立“日耳曼自治(加盟)共和国”呢?这种政治上的考虑使得斯大
林特别强调“共同地域”。而且用“四个特征缺一不可”这条原则,
在强调语言因素和地域因素的时候,实际上淡化了文化因素(包括
语言、宗教)和心理意识因素在民族形成和延续中的重要作用。
斯大林如此强调“共同地域”,也反映了沙皇俄国在短短200
年中从一个单一民族的内陆小公国扩张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多民族
政治实体这一过程的特点:沙皇俄国的对外移民拓展了俄罗斯的政
治疆土,但各主要少数民族仍然居住在各自传统的地域上,其他各
民族进入俄罗斯地区的移民数量十分有限。强调“共同地域”对
俄罗斯是有利的,对于其他在传统居住地域内人数较多的少数民
族(如其他建立加盟共和国的族群)也没有太大伤害,可以保持政
治稳定。同时对于境内的“跨境族群”和小族群如日耳曼人、犹太
人、拉脱维亚人,可以通过不承认他们为“民族”而剥夺其争取自
治方面的各种权利。而论断“北美利坚人”是一个民族,中国的回
族不是一个民族,不过是这种“民族”划分标准应用于其他国家的
可笑的延伸。
关于民族的演变过程,斯大林把历史上人们共同体的发展程序
表述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部族”指的是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则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形成的人们
共同体。国内把这一程序表述为:氏族—部落—古代民族—现代民
族。(马寅,1995:155)这种表述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历史进程
的划分多少带有公式化的色彩。其实,居住于不同的地区的不同族
群,面临不同的自然资源和发展条件,他们的社会各自演进的程序
与各时期的发展特点,相差可能会很大。如阿拉斯加冰原上的爱斯
基摩人,热带夏威夷群岛的土著人,北美大草原上的印第安人,云
贵高原上的少数民族,黄河流域平原上的汉人、大草原上的蒙古
人,他们的发展条件就很不相同,是否能够被套入四种社会发展形
态和“人们共同体”的四个发展阶段,完全属于应具体讨论和研究
的问题。在总结一般性规律的同时,如果对各个族群的特殊性没有
给予充分的关注,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关于“民族”的词条认为:“氏
族、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缘关
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种族属于生物学范畴,而民族则属于
历史范畴。”(1986:302)“部族”与“民族”的差别,是否仅仅是
“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之间的差别?不同民族之间差别的基
础,是否只是缘于不同的“地缘关系”?文化因素在民族的形成与
延续中扮演什么角色?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是否一定需要具备斯
大林提出的四个条件?这些也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第二,正因为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对于如何看待斯大林
关于“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国内的学术界始终存在着争议。
在争议中有一种观点完全赞成斯大林的定义,并且在这些标准
应用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方面加以拓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不
论在哪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要形成为一个民族,必须具备斯大林讲的
那四个条件(也叫四个特征),缺少任何一个条件,是不可能形成为
一个民族的”。(牙含章,1982:1)应当说,这与斯大林提出的“民
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
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
族的过程”(斯大林,1913/1953:300—301)的论断相违背。既然
使用斯大林的定义,也就必须遵守斯大林提出的该定义的前提条件。
在认定一个民族所需的各项特征方面,宁骚指出民族具有“原
生形态”和“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等,一个民族的原生形态
具有这些特征,而次生形态可能只具备其中的一部分特征。(宁骚,
1995:20)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尤其是近现代各民族交流、冲突、
迁移、混居、融合的复杂过程中,一些族群或族群的一部分很可能
丧失其民族特征的某些部分,但仍保持民族意识和部分特征,也应
当被承认其作为独立族群的存在。 关于对“原生形态”和“次生
形态”进行区分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从动态的角度在理论上认识这些
复杂的民族演变现象。
其实,真正的争议应当是对这四个条件适用性的普遍意义提出
质疑。任何概念的产生,都有一个社会历史环境,是提出这一概念
的人对自身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特点的抽象性概括。斯大林的“民族”
定义,可能主要是从20 世纪初俄罗斯族群和沙皇俄国的实际情况
中总结出来的,这一个定义,就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有几千年文化传
统和族群交往历史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也不一定适用于新兴的
移民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所以,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观
点,有的认为民族的基本特征应当有六个(增加“形成历史”“稳定
性”两条)(宁骚,1995:16—19);有的认为“共同地域”和“共
同经济生活”是民族形成的条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征(纳日碧力戈,
1990);有人认为民族具有“自然(族体)”“社会”“生物(或人
种)”三种属性(金炳镐,1994:78);还有人提出民族具有11 种属
性(吴治清,1989;郑凡等,1997:49)。这些看法反映出我国学术
界对于如何认识民族定义与民族属性的积极探索。
第三,为什么我国少数民族都统称“民族”?
我国政府把各个少数民族都称作“民族”,其理论根据还是斯
大林的定义和民族产生的历史阶段的观点。中国的这些“很弱小和
经济十分不发达的民族,他们之中有许多停滞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
段,没有具备民族的四个特征,但是他们的历史环境已经改变为资
产阶级时代了”,由于这些族群已经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卷入资本
主义旋涡中,已经不同于古代民族,而是又一种类型的现代民族”
(马寅,1995:160),所以也把他们统称为“民族”。
这里坚持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观点,
而在他的“四个特征、缺一不可”的论断上打了折扣,使用这样的
逻辑推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把我国各少数民族群体称为“民族”。这
里的逻辑是:如果认定中国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就不能
不把处于这一革命中的汉族定义为“民族”;而既把汉族定义为一
个“民族”,也就不得不把同时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其他族群也定义
为“民族”,因为从逻辑上讲,一个国度里的各个族群是生活在同一
个社会大环境中,他们之间不应该有社会形态方面的根本性的隔阂
和断裂,否则他们之间也就没有联系、没有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了。
当然,各个族群的实际社会发展水平可能会有很大的差距,如云南、
四川、西藏等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着一些
社会形态发展落后于汉族地区的情况,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各民
族确实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封建制度统治的共同历史任
务。从这一点上说,也可以把中国所有的民族族群都称为“民族”。
但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思考,则应当更进一步,突破一些“经典
著作”中提出的“民族”概念和“社会发展形态”概念这些人为思
维定式范畴的束缚。当我们对“民族”定义及其含义的理解遇到问
题与矛盾时,“没有想到在汉语原有的‘民族’一词的基础上,总
结民族识别的经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是在斯大林民族定义
的圈子里打转转,不敢越雷池一步”。(孟宪范,1988:5)思想上
的束缚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无法向前推进。
事实上,20 世纪中国各地区不同的民族群体,其社会发展的
水平阶段是不同步的。他们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资本主义的影
响,又同时共同面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但是这个大的历
史环境,并不能用来证明他们都进入或接近了资本主义社会。而
在“社会发展形态”上,也不必有明确的阶段划分,有时一个社会
当中有一些组成部分是处于两种形态混合状态或从一种形态向另一
种形态演变过程之中的,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类型很可能是多元
的,而且实际生活中的人类社会也是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的,因此
也不必把“部族”和“民族”之间划分得那么明确,各个民族族群
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和层次,民族群体的特征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
展。谁能说得清楚是在历史上的哪一天,一个“部族”变成为“民
族”?谁又能说得清楚为什么两个各方面特征很相似的族群,一个
在这个国家被划为“部族”,而另一个在邻国被划为“民族”?
总之,我们不应当拘泥于现有概念和定义的束缚,而要从活生
生的现实出发,要从多元、演变、互动和辩证的角度来分析和把握
复杂的客观事物,各种概念和定义不过是我们自己从现实中抽象出
来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客观世界的工具。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对世
界各地族群的研究中,是否需要一个如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的抽
象、统一的“民族”概念?如果需要,那么建立这一概念的努力对
于我们实际研究工作的意义何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