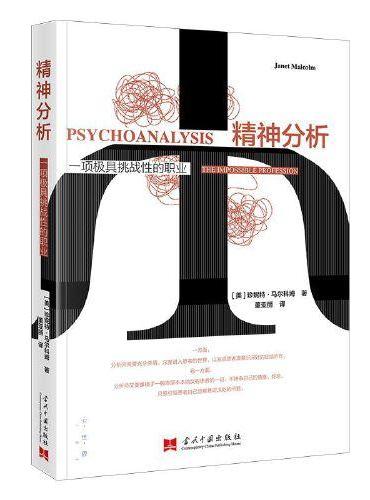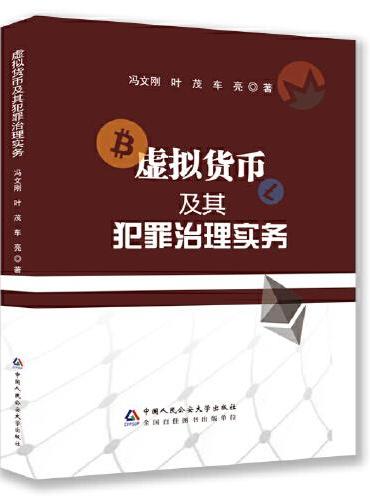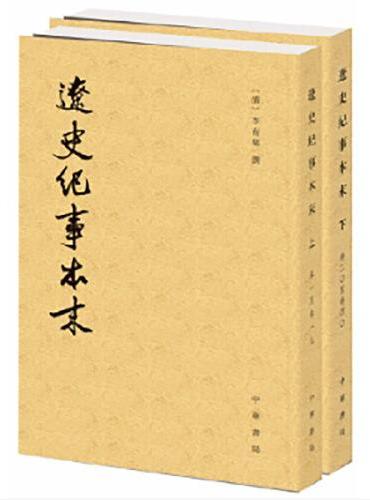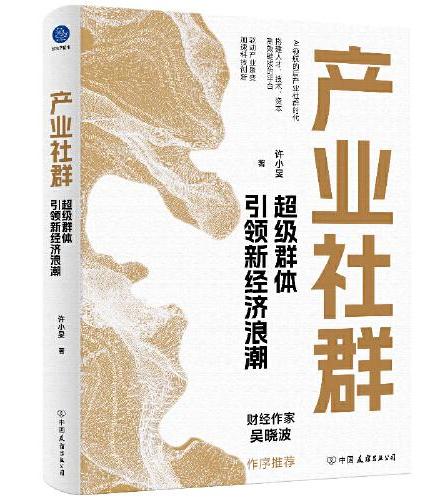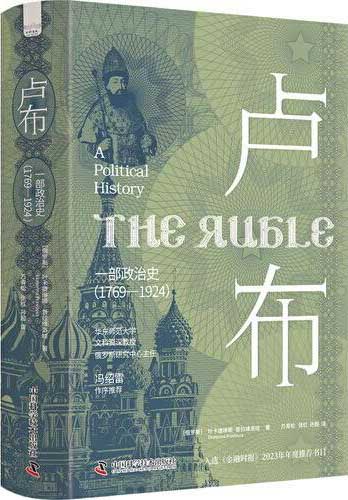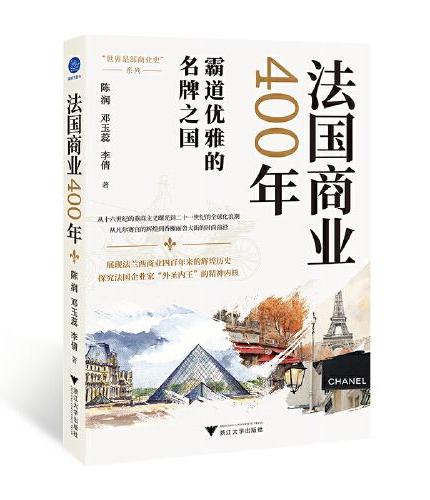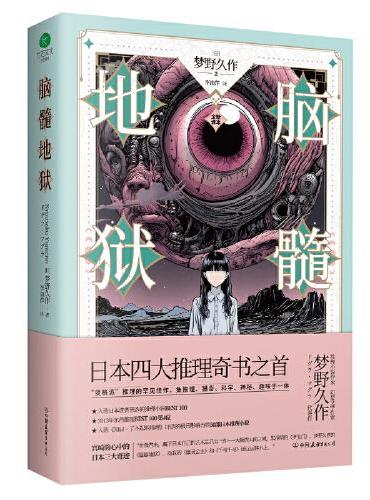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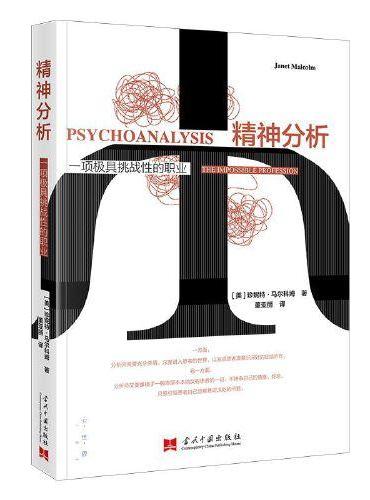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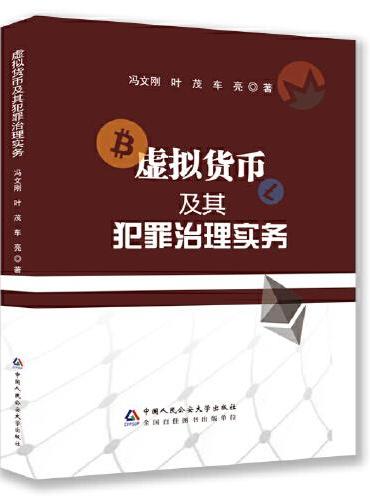
《
虚拟货币及其犯罪治理实务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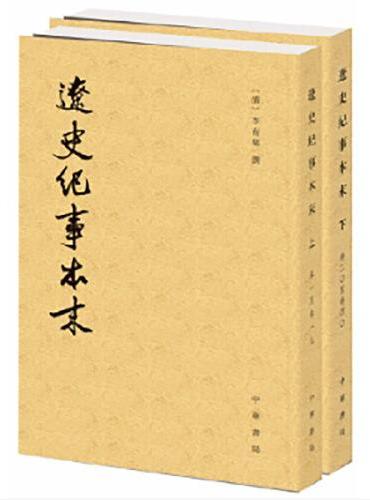
《
辽史纪事本末(历代纪事本末 全2册)新版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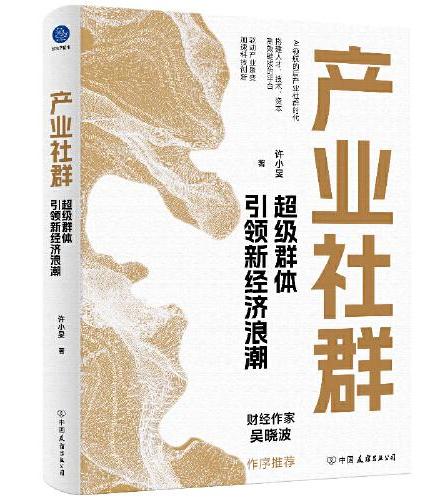
《
产业社群:超级群体引领新经济浪潮
》
售價:HK$
6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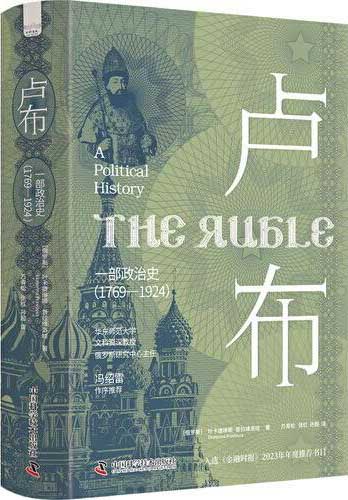
《
卢布:一部政治史 (1769—1924)(透过货币视角重新解读俄罗斯兴衰二百年!俄罗斯历史研究参考读物!)
》
售價:HK$
1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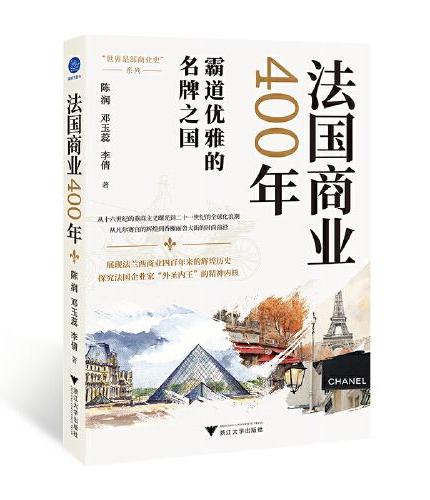
《
法国商业400年(展现法兰西商业四百年来的辉煌变迁,探究法国企业家“外圣内王”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74.8

《
机器人之梦:智能机器时代的人类未来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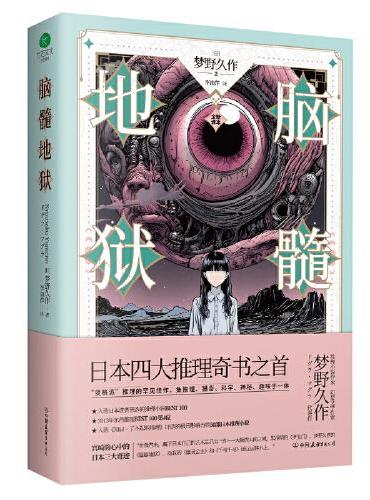
《
脑髓地狱(裸脊锁线版,全新译本)日本推理小说四大奇书之首
》
售價:HK$
61.6
|
| 編輯推薦: |
1.鲁迅文学奖获奖散文典藏书系中的一本,一本书读懂夏坚勇。
2.著名散文家夏坚勇代表作,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
| 內容簡介: |
|
《湮没的辉煌》是“鲁迅文学奖获奖散文丛书”中的一种,为著名散文家夏坚勇的散文集,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此书是夏坚勇的代表作,收录了文化散文作品《寂寞的小石湾》《驿站》《湮没的宫城》《东林悲风》《小城故事》《母亲三章》等经典作品,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审美价值。作者以畅快的措辞,深刻的思想,将历史与政治、文化与情感加以整合,在地理空间的层峦叠嶂中穿梭,俯瞰历史的烟云风尘,博古论今,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化大散文作品。
|
| 關於作者: |
|
夏坚勇,著名散文家,代表作有《湮没的辉煌》《大运河传》《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东京梦寻录》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
|
| 目錄:
|
寂寞的小石湾001
驿站018
湮没的宫城037
东林悲风060
小城故事083
走进后院107
百年孤独128
瓜洲寻梦150
童谣172
文章太守191
遥祭赵家城212
泗州钩沉236
石头记257
洛阳记276
母亲三章301
|
| 內容試閱:
|
寂寞的小石湾
一
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清英雄阎应元墓在江阴小石湾。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出几个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推举的是集忠臣良将于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而阎应元便可以算是一个。偏偏历史对他一直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叹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叹息也没用,且到小石湾找阎典史去。
小石湾依偎在要塞古炮台下。在这个升平年头,又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晖里。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讲究,但细细找过去,那些“先考”“先妣”皆名讳凿凿,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的小石碑。问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说,当年阎应元不屈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出来,偷偷葬在这里。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到底是哪座坟,搞不清了。
我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二
一个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说法,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正科级的县公安局局长。在那个民族危亡之秋,率义民拒二十四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八十一天,使清军铁骑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余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如此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黯淡而柔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
然而,江阴城沸沸扬扬的鲜血和呐喊,在史家笔下却消融得了无痕迹,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竟不著一字。倒是有一个在江苏巡抚宋荦门下当幕僚的小文人,于清苦寂寥中,推开遵命为主人编选的《诗钞》,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阎典史记》。他叫邵长蘅,江苏武进人氏,武进是江阴的近邻,阎应元率众抗清时,邵长蘅十岁左右,因此,他的记载应该是史笔。
“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守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背景图。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许诅咒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没有一点雄性的阳刚之气了。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难道还不算奇男子、伟丈夫?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史忠烈公。
就在江阴守城战两个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与清军铁骑只周旋了数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十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给史可法立传的全祖望比邵长蘅的名气可要大得多,这位在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获罪幸而免死的大学者也确是文章高手。“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梅花岭记》一开始,作者就把文势张扬得疾风骤雨一般,让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势中凛然登场。
“势不可为”是客观现实。正如后来“史公墓”前抱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践着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骁勇强悍的八旗大军挟带着大漠雄风,一路势如破竹,直薄扬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镇兵马又不听史可法调度。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很难有所作为。
史可法登场了。他的第一个亮相不是在督师行辕里谋划军事,也不是在堞楼城壕边部署战守,而是召集诸将,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也就是把他杀死,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为义子。又上书福王表明自己“与城为殉”的心迹,并当众再三朗读奏章,涕泪满面,部将无不为之动容。最后遗言母亲与妻子:“吾死,当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或其不能,则梅花岭可也。”
这就是说,仗还没有打,自己就先想着怎么个死法,如何全节。这如果是作为激励将士拼死决战的手段,本也无可非议,中国战争史上诸如破釜沉舟或抬着棺材上阵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给人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庄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想得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当年隋炀帝在扬州揽镜自叹:“好头颈,谁当斫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统率十万大军的督师辅臣,不管怎么说,十万人手里拿的并非烧火棍,即使“势不可为”,也要张飞杀岳飞,杀个满天飞。说一句大白话:打不过,也要吓他一跳;再说一句大白话:临死找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可惜史可法不会说这些粗陋的大白话,他太知书识礼,也太珍惜忠臣烈士的光环,他那种对千秋名节纯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眼前刀兵之争的创造性谋划。可以想象,统帅部的悲观情绪将如何软化着十万大军的脊梁。这支本已惶惶如惊弓之鸟的御林军,无疑将更加沉重地笼罩在一片失败的阴影之中。
到了这种地步,战争的结局只是个仪式问题了。
仪式或迟或早总要走过场的,接下来是清兵攻城,几乎一蹴而就,史称的所谓“扬州十日”,其实真正的攻守战只有一天。史可法既没有把敌人“吓一跳”,也没有能“临死找个垫背的”,古城扬州的尸山血海,不是由于惨烈的两军决斗,而是由于八旗将士野蛮而潇洒的杀人表演。弄到后来,连史可法本人苦心安排的全节,也得靠敌人来成全他,“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刀”,终于被俘。清豫王多铎劝降不成,冷笑道:“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节。”史可法遂死。
平心而论,史可法不是军事家,这位崇祯元年(1628年)的进士,其实只是个文弱的儒生。儒家历来信奉的是“修、齐、治、平”之道,这中间,“修身”是第一位的。史可法个人的品德修养毋庸置疑,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年过四十而无子,妻子劝他纳妾,可法叹息道:“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终于不纳。这样洁身自好的君子,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中相当难能可贵。若是太平岁月,让这样的人经纶国事自然没有问题,但偏偏他又生逢乱世,要让他去督师征伐,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在浩浩狼烟和刀光铁血面前,他那点孱弱的文化人格只能归结于灭寂和苍凉,归结于一场酸楚的祭奠和无可奈何的悲剧性体验。
在这里,我得说到一桩政治文化史上的逸闻。就在清军兵临扬州城下的几个月前,清摄政王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有一封回信,这封海内争传的《复多尔衮书》雄文劲彩,写得相当漂亮,今天我们捧读时,仍旧会感到那种澎湃涌动的凛然正气。可以想见,当初作者在起草回信时,必定是相当投入的。那大抵是一个夜晚——“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样的境界自然是没说的,多少文人曾把扬州的月色涂抹成传世佳句;或细雨凄迷,间离了尘世的喧嚣,将督师行辕浸润在宁定和寂寥之中,这也是写文章的理想氛围。当然,远处的城楼上会不时传来军士巡夜的刁斗声;而在北方的驿道上,快马正传送着十万火急的塘报,那急遽的马蹄声不仅使夜色惊悸不安,也足以使一个末日的王朝瑟瑟颤抖。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篇文章。此刻,史可法的文化人格挥洒得淋漓尽致。吟读之余,他或许会想到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古往今来的不少好文章都是两军决战前“羽檄交驰”的产物。首先是那位叫陈琳的扬州人,他替袁绍起草的《讨曹操檄》使曹操为之出了一身冷汗,久治无效的头风也因此大愈。丘迟致陈伯之的劝降书写得那样文采瑰丽,把政治诱导和山水人情交融得那样得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谁能相信这样清新明丽的句子会出现在冰冷的劝降书中呢?“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更不愧是大才子,他的那篇《讨武曌檄》,连被骂的武则天看了也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些千古佳话,史可法此刻大概不会想不到,因此,他很看重这篇署名文章。事实上,就凭这一篇《复多尔衮书》,后人就完全有理由认定他是一位文章高手,而忘却他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节制江北四镇的督师辅臣。
说史可法很看重这篇文章,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旁证。据说史可法对自己的书法不甚满意,便四处征求书家高手执笔誊写。当时,书法家韩默正好在扬州,便到军门应召。关于韩默其人,我知道得很少,但从史可法对他的赏识来看,大概档次是不低的。韩默笔走龙蛇时,史可法和诸将都在一旁观摩,只见那素笺上气韵飞动,从头到尾一笔不苟,虽微小到一点一画,也不离“二王”的笔法。书毕,史可法赞赏再三,这才令快马送出。
今天我们很难猜测史可法站在督师行辕的台阶上,目送快马远去时的心态。对国事的惆怅?对明王朝的孤忠?对江北四镇防务的忧虑?实在说不准。但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即对刚刚发出的这封复书的几许得意。中国的文化人总是把文章的力量夸张到十分了得,似乎一篇檄文就可以让人家退避三舍,最典型的莫过于李白表演的“醉草吓蛮书”,凭半壶水的洋文便震慑住了觊觎唐帝国版图的番邦。《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说,“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牛皮吹得还不算大。诗圣杜甫就有点豁边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一支舞文弄墨的纤纤之笔,简直有如上帝的魔杖。既然文章有这样无所不能的造化之功,人们便生生世世地重视考究起来,斟酌推敲起来,咬文嚼字起来,好像一字一词的差异,就真能演化出天壤之别的大结局来。北宋末年,靖康城陷议和,赵桓(钦宗)递降表,文中有“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之句,金将粘罕不满意,一定要叫易“负罪”二字为“失德”。讨价还价不得,战败者只好屈从。其实,“负罪”也罢,“失德”也罢,都改变不了战场上的事实。不久,赵桓父子全被敌人掳去,算是给用字之争下了一道注脚。
史可法给多尔衮复书大约是弘光甲申秋月,半年以后,清兵大举南下,扬州城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