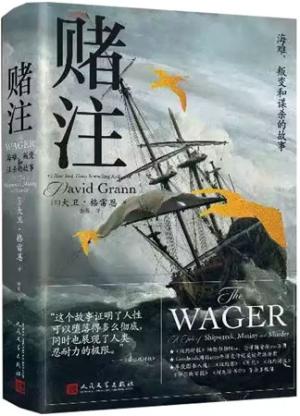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大模型智能推荐系统:技术解析与开发实践
》
售價:HK$
141.9

《
别字之辨
》
售價:HK$
140.8

《
八段锦 百岁国医大师邓铁涛健康长寿之道
》
售價:HK$
43.8

《
黄帝内经精讲
》
售價:HK$
1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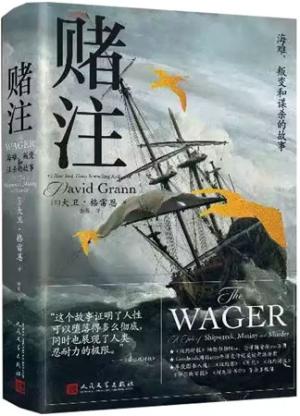
《
赌注:海难 叛变和谋杀的故事
》
售價:HK$
75.9

《
战争与史学家:李维历史书写中的汉尼拔战争
》
售價:HK$
63.8

《
古韵新声
》
售價:HK$
1848.0

《
秦汉至唐律令立法语言论要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一个了不起的原创性视觉命题(visual argument)
唤起对17世纪奇趣山水与再现山水的整体认识
西方学界中鲜有的尝试宏观思考中国绘画的造型本质问题之作
跨越近四十年的晚期绘画史写作计划,将中国古代晚期绘画视作可供西方风格发展理论进行比较反思的唯一强大对象。
海外中国绘画史研究高峰,凭借独特阅画经验与极富才情的历史感,引领现代读者以视觉方式进入历史文化深处。
几番理论思潮后,让我们重温常读常新的高居翰。
|
| 內容簡介: |
我们正是在特具原创性的中国作品里,看出画家受所接触的西洋画影响;甚至说得更确切一点,西洋影响还似乎正是造成其原创特质的重要激素之一。中国的绘画传统太健康、太肯定自己的自足性,故而难为外来的入侵文化所湮没。人类学家的刺激扩散效应观念(stimulus diffusion)或许最能够用来形容中国画史上的这种反应:本土文化撷取了外来的理念与模式,然却赋予其一个新且本土化的内涵,如此,本土文化便被驱向了一个它原先不会发展的方向。
发现西洋画与自己北宋时期的山水画有着某种神秘的相似之处,这种认知必定使中国人的注意力再度集中于中国传统中此一段久已为人忽略的篇章。一个绘画主体根深蒂固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传统之中,而另一个主体则源自中国以外的时空领域,蓦然地在此时同现于中国的土地之上。所有这一切都在一时之间,回流到了中国人所共有的形式与风格观念的资料库中,而为中国画家所撷取运用。
——高居翰
十七世纪的中国绘画,不但有其独特美感,还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气势与魄力。“即使在世界艺术史上,欧洲十九世纪以前的画坛,也都难与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坛媲美。”高居翰以《气势撼人》处理明末清初这一绘画阶段,关注绘画风格与自然经验,绘画作品与历史选择的双重关系,以张宏与董其昌的艺术对比开篇,以王原祁和石涛命运的对照终结,是西方学界中鲜有的尝试宏观思考与讨论中国绘画的造型本质问题之作。
|
| 關於作者: |
高居翰 (James Cahill, 1926-201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1997年获该校终身成就奖;曾长期担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顾问。2010年,史密森尼尔学会曾授予其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Charles Lang Freer Medal),表彰他在亚洲和近东艺术史研究中的杰出贡献。
高居翰的作品融会了广博深厚的学识与细腻敏感的阅画经验,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主要作品包括《图说中国绘画史》《隔江山色:元代绘画》《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山外山:晚明绘画》《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等。
|
| 目錄:
|
三联简体版新序
致中文读者
英文原版序
第一章 张宏与具象山水之极限
第二章 董其昌与对传统之认可
第三章 吴彬、西洋影响及北宋山水的复兴
第四章 陈洪绶:人像写照与其他
第五章 弘仁与龚贤:大自然的变形
第六章 王原祁与石涛:法之极致与无法
简写书目对照表
注释
图版目录
索引
|
| 內容試閱:
|
本书的中文译本在英文原著发行后十年,才与读者见面。在这等待的过程中,我不仅心怀兴奋,同时也有些许的惶恐。原本这即是一部颇具争议性的书,如今它以中文的版本出现,想必对中文读者而言,更是如此。
本书原本是根据我在哈佛大学时的讲稿写成,而当时我在讲演时,即已知觉到本书可能会带来一些争议。在我发表完有关董其昌的第二讲之后,一位专研明代绘画的年轻学生来到我的面前,他说:“老董今晚可说是受到重击了!”我颇有些吃惊,原来我并未想到我对董其昌特别得严苛。我当时的看法是:对于董其昌的说辞,我们不能仅单纯地照收,即使是董其昌对自己画作的说辞,我们也不能只看其皮相,而将他的说辞看作是显露他自己画作的真理;再者,董其昌的言论与别人并无太大的不同,也同样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到底他还是从某一特定的观点出发的。稍后,我的同僚约翰· 罗森菲尔德(John Rosenfield,他在哈佛大学教授日本艺术史)告诉我:“大家都认为你的讲演很精彩,但是你的观点令人感到错愕(换言之,也就是非中国式的观点)。”同样地,对于这样的评语,我首先的反应仍是为之一惊,但是,等我进一步地思索时,我愈发能够看清楚其中堂奥之所在。为了能够为明清之际的绘画注入一些新且丰富的思考方法,我当时的确是让自己从那些既传统,且已广为人所认定的中国思考模式中抽离开来,无怪乎有些听众会觉得我的观点极令人不安。
自从本书出版以来,中国学者在评论时,往往臆测更深,有时甚至认为此书是对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攻击。其中甚至有一位评论者认为这是“东方学”(Orientalism)的幽灵复现,也就是认为我用了外来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点与诠释法,强制地套用在中国本土传统之上,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根本无关宏旨的。本书当然不是为此种目的而撰写的,而有读者以这样的方式去读它,只怕也是误解了我在书中的立论。我所要辩说的,乃是:今日我们所赖以依循的论画文字,全都出自中国文人之手,也因为如此,中国文人已长时期地主宰了绘画讨论的空间,他们已惯于从自己的着眼点出发,选择对于文人艺术家有利的观点;而如今——或已早该如此——已是我们对他们提出抗衡的时候了,并且也应该质疑他们眼中所谓的好画家或好作品。我认为有许多优秀的中国艺术家——诸如本书所讨论到的张宏与吴彬两位画家,以及其他时代的一些画家等——都因为文人的偏见,而未能获得应有的认可,在此我们应该一一地重新给他们以赞扬。我同时也认为,在艺术研究的领域里,传统中国人对于自己能够自给自足的文化自信,我们也应该加以一番质疑,因为在中国研究的其他领域里,此一检讨也已经被提出。
最后,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究竟明末清初的画家是否深刻地运用了西洋画中的风格元素与“图画概念”呢?所谓西洋画,指的是有插图书籍中的那些图画与铜版画,这些图画书籍被耶稣会传教士带进中国,并用之示以当时的中国人。我个人相信这答案是肯定的。也因此,当我在书中极力主张某些晚明画家确实深刻地受到西洋图画风格的元素所影响时,也就成了备受争论的一个议题。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反驳,想要推翻或是削弱我的论证,他们指出,我所提出的那些受西洋画影响的晚明画风,都可在中国固有的绘画中找到先例,如此,“西洋的侵略”是不足以解释这些绘画现象的。但是,姑且不说这些讲法极不具说服力(不仅许多学者如此认为,我也有同感),这些反论并未像我在本书的章节中一样,提出可资对比的画例。看起来,这些反对的说法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在立意上,他们显然认定了一旦承认中国艺术与文化受到外来“影响”,便等于使中国蒙羞。1970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国际性的中国古画讨论会,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和我各有论文发表,当时与会者对我们的反应,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苏立文的论文考据说明了在晚明时,耶稣会士所传入中国的图画为何,以及中国人如何因而得见这些图画;我的论文则举证说明晚明的一些画家,如何地运用了这些西洋图画,我主要是以吴彬作为讨论的主题(也是我的论文题目)。这两篇论文,连同我们所作的一些猜测,都受到中国学者激烈的否定,他们老调重弹,重申中国绘画重精神,不像西洋是以物质为主,并且说中国画家,至少是那些优秀的画家,并无需要,而且也不会想去求助于西洋艺术中的视幻技法。
然而,我们所见到的情形却不如此,我相信任何心思客观的人一旦看了本书所举的一些图证,或是其他可能的排比,想必都会同意我的说法。正当明代的理论家议论着旧传统与美学的课题时,晚明的画家也和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有创意的艺术家一样,力图摆脱那些往往使人不知如何是好的传统包袱,并竭其所能吸取那些能够为他们所用的质素。而在接触了那些奇特且气势撼人的西洋图画之后,有些画家自然就受到了影响,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最优秀的画家。对于外来的“影响”,这些艺术家并非被动的接受者——所谓跨文化借用的说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其中暗示着一个文化强制另一个文化的观点——相反的,这些艺术家都是思虑敏捷、心胸开放的人,他们吸取了外来资源中,那些原来在中国前所未见的绘画观念,为的是裨益自己的创作。天佑这些艺术家,他们万万不会知道,数百年后,中国的“卫道之士”根本不允许他们做此种选择,但是,他们当时并不顾虑这么多,而只是一股脑地做了。如此,晚明与清初的绘画为之一搅,结果丰富了这一时期绘画的内容——正如十八世纪时,日本的绘画亦因借取了中国明清绘画的质素(早些年,这曾是我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又重新有了生命力(即所谓的南画),或乃至于在十九世纪,欧洲绘画因为接触了日本版画,而颇有裨益地受到了震荡,再或者,到了二十世纪时,美国的艺术家受到中国书法形式的激发,而以健康的态度回应,如此,产生了抽象表现主义。就好比是异族通婚,跨文化的结合,势必会繁衍出特别健壮且迷人的后裔;所幸的是,自以为是地想要拒绝这种融合,终究是无益的。
然而,此一争论想必是会持续下去的,而且,对某些读者而言,本书所呈现的,可能极不悦耳,或甚至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如果说我的书成功地凸显了一些前人所未曾真正探及的问题,且从而开启了一道讨论之门,使吾人得以突破传统的诠释方式,那么,本书便算是达到目的了。最重要的是,我想要说明:无论诠释的方式多么得正统或老生常谈,作品的意义内涵都不会因此而有所枯竭;而且,中国艺术家的伟大之处,也远非他们当时代的作家所能尽括——同时,其伟大之处,也不是今日的“我们”所能说得完全的。但是,我们仍得继续地努力;而本书便是此种尝试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