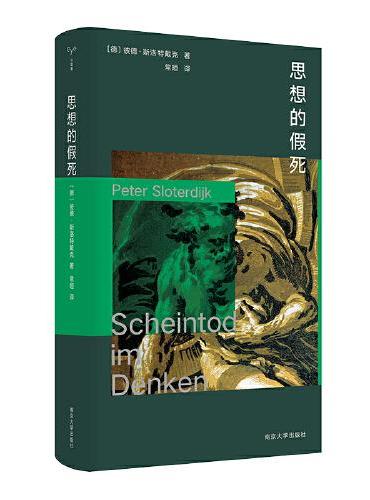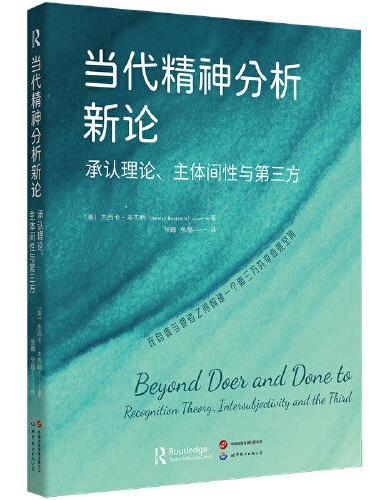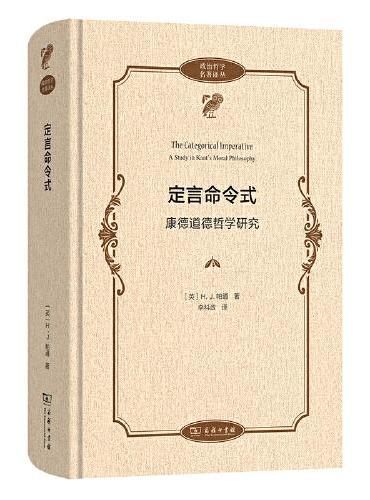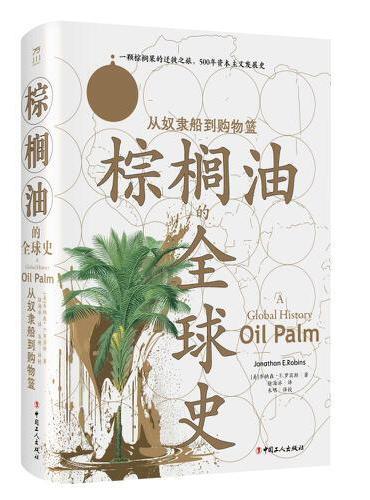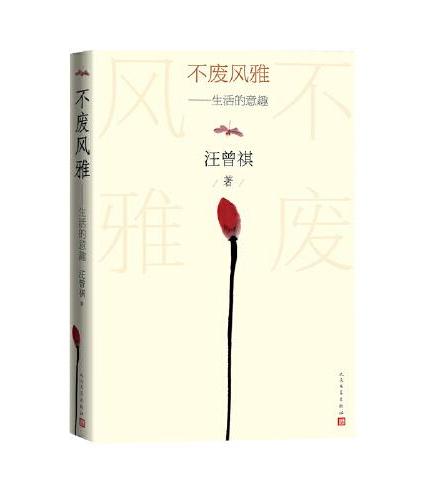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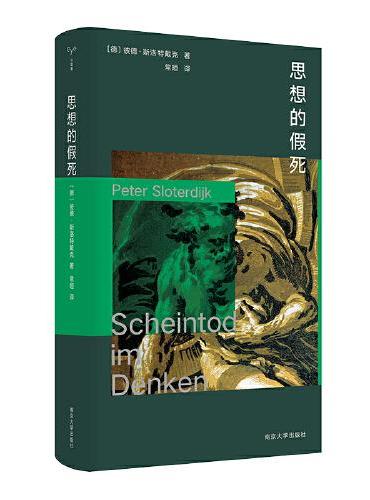
《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思想的假死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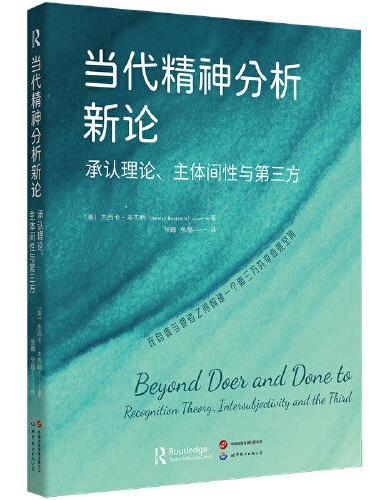
《
当代精神分析新论
》
售價:HK$
94.6

《
宋初三先生集(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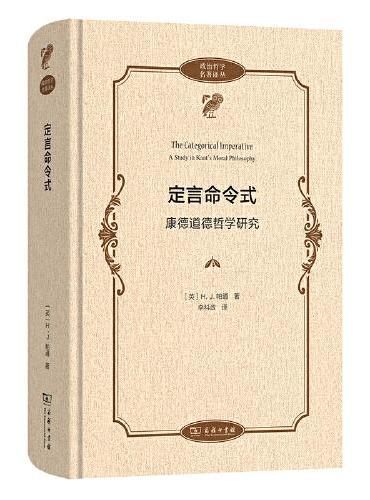
《
定言命令式:康德道德哲学研究(政治哲学名著译丛)
》
售價:HK$
1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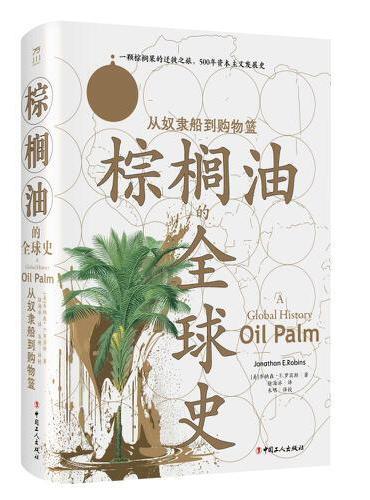
《
棕榈油的全球史 : 从奴隶船到购物篮
》
售價:HK$
96.8

《
简帛时代与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上下册)(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HK$
308.0

《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王中江著作系列)
》
售價:HK$
2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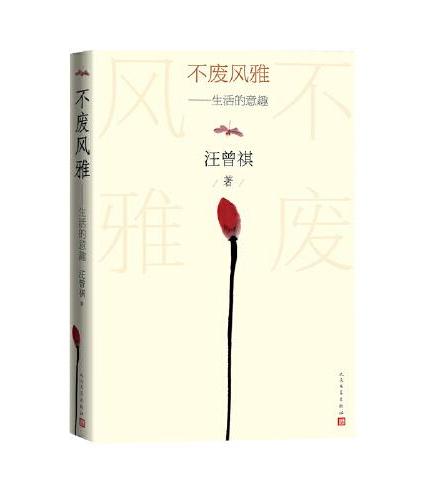
《
不废风雅 生活的意趣(汪曾祺风雅意趣妙文)
》
售價:HK$
61.6
|
| 編輯推薦: |
1. 当下,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加强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影响力,由此,更需要打造中国叙事的有效方法论。
2. 郑永年老师、杨丽君老师力作。“中国叙事”是讲好中国故事,建立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抓手,作者在长期思考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话语是“另一种制度选择”,进而详细分析“如何叙述中国经济制度”“如何正面叙述中国政治制度”“如何应对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并指出“中国叙事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瓶颈问题,兼具前瞻性和方法论特点,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意义。
3. 作者立足于中国国情与世界局势,犀利直达问题肌理,文风犀利,不拖泥带水,相信会为您提供一场良好阅读体验。
|
| 內容簡介: |
当下,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加强世界对中国的理解,而这就需要我们讲好中国故事。
那么如何讲好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如何让西方理解、接受、认同中国模式及价值?这需要一整套有效的叙事结构与方法论。
作者围绕“中国叙事”主题,开宗明义地讲述中国叙事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方法论的宏观思考,进而层层递进揭示中国话语的本质,深入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关键点、目前中国叙事存在的困境等,由此来启发读者,帮助读者理解中国叙事的常识基础,明晰把中国方案说清楚、讲明白的关键点,以及当下存在的问题与难点,更好地运用中国智慧、传递中国经验、模式、规则、理念,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提升软实力。
|
| 關於作者: |
|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IIA)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专注于社会变革和社会运动研究,日本第21届大平正芳学术奖获得者。
|
| 目錄:
|
自?序?中国叙事:从读懂中国到主动解释中国/III
第一章 中国话语:另一种制度选择
西方为什么妖魔化中国?/007
如何让西方读懂、接受和认同中国?/017
如何实现中国与西方的有效对话?/031
第二章 “世界问题,中国方案”与“中国问题,世界方案”
“中国共产党叙事”的“常识”是什么?/039
“中国问题世界化”的探索/043
特殊性和普遍性缺一不可/051
第三章 如何叙述中国经济制度?
我们该如何把中国的经济制度说清楚?/057
资本主义的前途在哪里:西方经济危机及其改革呼声/065
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西方政治经济学简史/077
经济发展是政府的责任:中国政治经济学简史/089
第四章 如何正面叙述中国政治制度?
美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围堵/109
美国内部和美西方之间可能的分化/121
西方治理危机及其根源/125
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129
第五章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制度根源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161
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衰退与西方之乱/165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创新与中国之治/177
第六章 中国如何应对中美意识形态的斗争?
当代认同政治恶化着各国内政和外交/193
美国的对华认同政治战/201
中国的应对/211
附录1?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构建中国原创性政治经济学理论/225
附录2?讲好中国故事,世界性和中国性不可分割/232
|
| 內容試閱:
|
自?序?中国叙事:从读懂中国到主动解释中国
“中国为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内部这些年也在讨论“何为中国”的问题,但这只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中国的内部认同问题和“中国”形成过程中那些恒定的因素与变化的因素。而国际层面的讨论似乎更具哲学和理论意义,即要为中国定性—中国代表的是一整套什么样的价值系统。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12月召开所谓的“世界民主峰会”就是要实现其世界“两极化”的目标,“两极”即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极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极。拜登执政之后,一直把中美关系简单地定义为“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争。人们普遍认为,拜登组织的“世界民主峰会”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冷战的“宣言”。美国的这种行为并不难理解。自登上世界舞台以来,美国的一项重要使命甚至可以说是宗教式的使命,便是把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带向世界其他地方,或者让世界其他地方接受美国的价值观。
就知识追求而言,意识形态之争毫无意义。如果从意识形态出发,知识就非黑即白,但真实的世界并非如此。在真实世界中,人们都可以找到几种主义共存的现象。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大作《经济分析史》中所详细讨论的,在资本主义成为西方主导性生产方式之前的封建社会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要素。从经验来看,简单地用“主义”来分析历史的进展并不科学,因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都可以找到被人们称为各种“主义”的因素;同样,人们所宣布的用一种“主义”替代或者消灭另一种“主义”的情况也没有发生。现实如此复杂,人们并不能用一种“主义”来概括之。
但是,人们绝对不能低估以“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忽视了各种“主义”之间竞争和斗争的历史,人们很难理解迄今为止的历史是如何造就的。就大历史而言,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两波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之争。第一波是欧洲国家内部资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围堵。西方经济史上,从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到二战以后以芝加哥学派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聚焦的是如何创造财富。而以卢梭和马克思的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学探讨的则是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前者代表资本的利益,后者代表劳动者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自然就遭遇了资本的围堵和扼杀。资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围堵尽管主要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但也是很血腥的。两者之间的对立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第二波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围堵。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把马克思主义现实化,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强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形成了直接的对立。苏联处于西方的外部,美苏冷战持续了半个世纪,最终以苏联的解体宣告结束。
今天,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转向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进行围堵。对此,我们应当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希望中国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尽管西方向中国开放是基于利益考量,但美国的这种“希望”构成了其向中国开放的政治算计。美国一旦认为中国不仅不可能变成它所希望的国家,还对它构成了挑战,就转而把中国归入“另类”,围堵和遏制中国。今天美国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和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所做的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当然,美国是否有能力像围堵苏联那样来围堵中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这个国际大背景下,人们不难理解近年来我们一直所从事的“读懂中国”事业的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往何处去有很多不确定性。一些西方国家更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逻辑强加在中国身上。所以,我们要逆转这个局面,帮助国际社会读懂中国,不要让西方把对中国的理解强加到我们身上。和西方不同,我们有中华文明自身的逻辑。尽管我们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也向西方学了很多经验,但我们不仅不会变成西方国家,反而越来越“中国”。这些年,我们提倡“文化自信”(或者“文明自信”)就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理论表述。
就我们自身而言,如果“读懂中国”主要是帮助世界读懂中国,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自己读懂中国。但这个问题恰恰是人们所忽视的,因为很多人假设我们是懂中国的。这些年来,我们在“讲中国故事”领域花费了不少人财物力,但效果似乎不是那么理想。如果我们越讲,人家越不懂,那么就表明我们讲故事的内容或者方式是有问题的。固然不管我们如何讲故事,外在世界的少数人,尤其是那些坚定的反华人物,总是“不懂”,但这一解释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人。如果我们讲的故事为外在世界的大多数人所听懂和接受,那么这些少数人的“不懂”也就不重要了。故事没有讲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讲故事者本身没有“读懂中国”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近代之初,中国实际上是从“读懂西方”开始的。那个时代,因为封闭、落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我们挨打,所以我们迈开开放的第一步就是读懂西方。就是说,尽管近代以来的第一波开放是被迫的,但就我们自己而言,这一波开放就是从读懂西方开始的。第二波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邓小平所开启的改革开放。这一波开放是主动的开放,但实际上也是从读懂外在世界开始的。在80年代,那些近代以来帮助我们读懂西方的作品,无论是翻译过来的西方作品还是中国学者自己写的介绍西方的作品,一版再版,就是一种具体表现。在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照理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优越的条件来同时读懂世界和读懂自己。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读懂世界还是读懂中国,我们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就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来说,我们自己读懂中国必须被置于*高议程。很显然,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读懂中国,那么如何帮助外在世界来读懂中国呢?
也就是说,我们更需要帮助自己读懂中国。不难发现,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我们中国本身的理解还是有欠缺的地方。近代以来的主流是西方文化,一开始我们用了大量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做中国研究。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失去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文化。西方叙事反映的是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而这些都是建立在西方的实践经验之上的。简单地用西方叙事的概念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很难把中国故事讲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的西方依然掌握着话语权,控制着世界舆论场。如果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这里便涉及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在读懂中国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释中国。如果说现在读懂中国的效果还不够好的话,那么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把中国解释好。在笔者看来,读懂中国的核心目标其实是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强大,核心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大、经济技术强,而且在于他们创造了一套建立在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因为这套知识体系能够解释西方是如何发展和强大起来的,西方人所讲的西方故事就很容易被非西方读者接受。近代以来,*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便是“知行合一”理论,就是所有理论都有坚实的经验基础,是可以验证的。中国如果要强大起来,那么随着经济的强大,也必须建立起一套能够解释自身行为的知识体系,而这套知识体系是帮助外在世界读懂中国的终极工具。在早期,很多学者往往简单地搬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发现和指出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现象,因此学界不乏批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努力,更有学者一直在提倡和呼吁要建立中国学派。然而,迄今确立“中国学派”依然是一种理想,除了“解构”西方社会科学的努力,人们少见“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的努力。
一句话,“解释中国”是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有效方法,而“解释中国”于我们来说还任重道远。根据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的说法,社会科学研究就是对“社会事物”的研究,包括对实践、政策等社会现象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的实践就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学术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研究的积累。学术的核心是概念、理论和原理。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实证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对实践(包括政策)的提炼。我们可以举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例。这是一本*为经典的政治学作品,但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基础就是古希腊各个城邦所实行的不同的政体或者政治制度,他经过比较分析,构建出一套理论。西方整个政治学体系都是建立在不同的政策或者制度实践之上的。霍布斯的《利维坦》是英国当时国家形式的反映,洛克的《政府论》也是。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从经验来看,实践(包括政策)总是先于概念和理论而存在。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有其理由的”,这句话道出了概念和理论的真谛。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对“社会事物”的解释。
对自然界各种存在的解释构成了科学或者纯理论。在这方面,中国和西方表现不同。传统上,中国所发现的自然现象也不少,但我们少有解释这些现象的纯理论,因此我们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纯科学。我们的文化强调实用和应用,但对与实用和应用无关的纯理论不那么感兴趣。西方则不同,西方文化不会停留在发现自然现象,而是还要追究自然现象出现的理由,这导向了西方的纯科学。这里以火药为例。火药是中国发明的,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就说过,中国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塑造了近代世界。但在发明火药之后,中国尽管有各种应用,却对火药本身的研究缺乏兴趣。也就是说,中国有火药技术,却没有火药科学。人们可以说,火药科学助力西方的崛起,但中国却被自己发明的火药打败了。
在社会科学上更是如此。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的每一朝代都有详细的历史记载。正因为如此,中国产生了大量的史学家。但在读二十四史和其他伟大历史著作的时候,人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那么丰富的历史记载和材料,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呢?中国方方面面的实践实在太丰富了,但这些实践并没有被提升为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
但是,社会科学家光解释“社会事物”还不够。社会科学家不仅仅是分析社会事物的工具,还有其自己的价值观,根据其价值观去塑造社会。因此,马克思认为,哲学家的两大任务便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正因为这样,一不当心,社会科学家就会构建出各种不同的“乌托邦”,希望能够在人间实现符合其理想的社会。所谓的“乌托邦”就是没有现实可行性的。人是一个道德个体,充满情感和知识想象,构建乌托邦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尽管乌托邦在一些时候助力人类的进步,但人类社会上大的乌托邦运动则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例如,自由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但发展到今天,新自由主义本身又变成了另一个极端的乌托邦。
如何避免乌托邦?我们可以引入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概念。人是社会性动物,人有立场和观点受制于文明、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因此人很难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是在解释“社会事物”的时候,必须尽最大努力来实现“价值中立”,否则就如我们平常所说,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总会出现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把社会科学家和其所生活的社会与世界的关系比喻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根据其所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给病人看病。医生的道德底线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把病人医死。如果病看好了,表明医生的知识是对的,经验足够。但如果医生医不好病,那么医生只能说自己所学的知识不够甚至不对,或者自己经验不足。没有医生会说,医不好病是因为病人的病生错了。
但今天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却认为“病生错了”是存在的。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来解释社会现象,解释得通的时候,可以说其掌握的知识是有效的,解释不通的时候,则不能说社会现象是不对的,只能说其所学的知识不够用了,需要新的知识。但很可惜,一些社会科学家在解释不通社会现象时,往往认为是社会现象本身出了问题,而自己的知识没有问题。
这绝对不是说社会科学家只解释“社会事物”,承认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存在有其理由,但有理由并不意味着合理。社会科学家是社会人,是道德体,他们诊断社会问题(例如自杀和他杀问题、一项政策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巨大政府工程对社会的影响等等),需要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像医生要把病人的病医好那样。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社会科学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从社会科学的建构来说,有两点是相当清楚的。第一,基于“价值中立”之上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所有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对“社会事物”的分析。近代以来流行各种“主义”,但它们一开始都是基于实证之上的研究,而非“主义”。一旦成为“主义”,那么就成了意识形态。第二,“社会事物”是变化的,对“社会事物”的解释也需要变化,解释、再解释构成了社会科学创新和发展的巨大动力。
不管怎样,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必须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之上。中国的崛起必须伴有自己的一套能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没有这样一套知识体系,不仅自己不能读懂中国,更难帮助外在世界读懂中国。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读懂中国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基于“解释中国”是读懂中国的基础这一信念,这些年来,笔者试图在解释中国方面做一些努力,涉足政党、政治体和政治经济系统等各个方面。《中国叙事》就是对这些研究基础的“非学术”表述,意在让读者意识到,只要我们有意识,解释中国不仅必须,也是可能的。希望《中国叙事》这本小书能够为读懂中国这项事业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