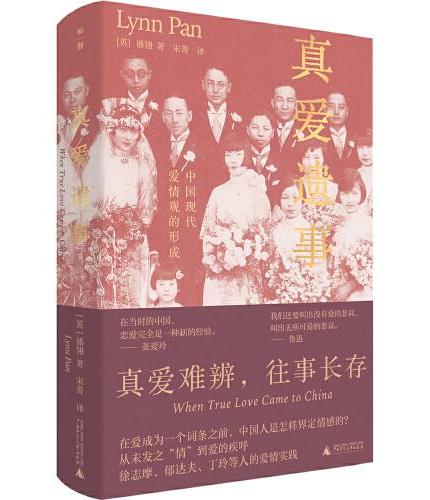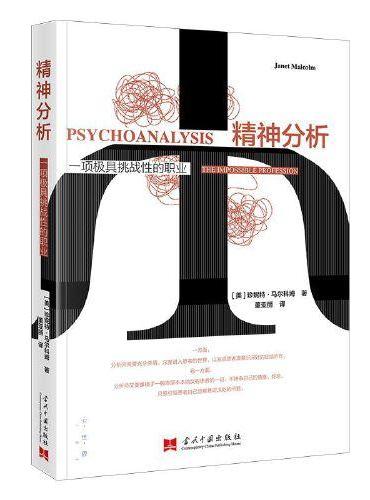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布克哈特书信选
》
售價:HK$
94.6

《
DK园艺的科学(100+个与园艺有关的真相,让你读懂你的植物,打造理想花园。)
》
售價:HK$
107.8

《
牛津呼吸护理指南(原书第2版) 国际经典护理学译著
》
售價:HK$
206.8

《
窥夜:全二册
》
售價:HK$
87.8

《
有底气(冯唐半生成事精华,写给所有人的底气心法,一个人内核越强,越有底气!)
》
售價:HK$
74.8

《
广州贸易:近代中国沿海贸易与对外交流(1700-1845)(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国际知名史学家深度解读鸦片战争的起源!)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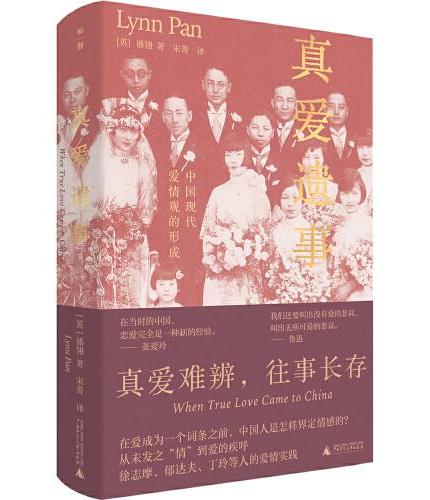
《
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
》
售價:HK$
1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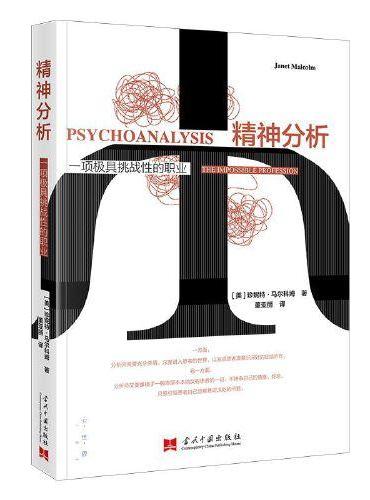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当代都市青年的呐喊与彷徨
告别星群般混沌的力量,告别虚浮麻木的日常、混沌的思索、踌躇与躁动,我们的双脚重新踏上大地
责任与自由,从来都是双生子——
“事实上,当我们感受到真正的责任后,行为才真的受到自我的限制。”
我们的生活,正如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
“那些经过艰苦训练并能把这些内容保持到生命结束的鹰,分有了人才有的某种特殊秘密。对我来说,我从那三只鹰的眼睛里看到了我的生活……枯燥、乏味、重复,但又每天不同。从那以后,我觉得我可以应对大部分难过的时刻,不失去信心,不去抱怨,不丢弃责任。”
|
| 內容簡介: |
|
本想学习驯鹰却被鹰驯服、从猎鹰身上感受到自由与责任感的摄影师何婷,长久在外创业、借弟弟结婚的机会重新适应自己家人的柳毅,用写日记和与少年时朋友见面的方式来对抗“记忆粗糙症”的斯桑凯,执着于盖一间自己的房子却在城市化进程中节节败退的拾荒人黎姐……出现在《再见,星群》里的这些年轻人,始终在努力辩识自己的路,努力将外在的世界和内在的自我融为一体。
|
| 關於作者: |
|
王苏辛,1991年生于河南汝南,现居上海。曾获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第三届“《钟山》之星文学奖”等。出版有小说集《象人渡》《在平原》《白夜照相馆》《马灵芝的前世今生》,长篇小说《他们不是虹城人》。
|
| 目錄:
|
【目录】
1 绿洲
30 猎鹰
52 远大前程
108 传声筒
151 寂静的春天
175 冰河
228 柳毅
248 灰色云龙
275 后记
|
| 內容試閱:
|
猎鹰
阿鸿提议去看草原猎鹰的时候,我刚刚拍完冰岛马回来,除了疲惫不堪,还觉得脑筋迟钝,视线中充满白色和浅灰色的小点。我没有去看医生,认定是在极昼地区待久了的缘故。疲惫几乎消耗了所有的意志和欲望,连需要人陪伴的愿望也消失了。我常常睡到半夜醒来,看见外面黑色的天,觉得十分恍惚,仿佛自己已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高强度的户外作业常给我这样的体验,但我也因此不再对任何或阶段性或长期的陌生感到恐慌,我只是偶尔觉得厌倦,发现这些需要远赴遥远国度的工作,居然也和曾经在杂志社的工作毫无区别,本质上依然是烦琐事务的累积。但“草原猎鹰”四个字到底是有吸引力的,我不禁问阿鸿——“你说的是猎杀鹰吗?”
“怎么可能猎杀?那是违法的,何婷!”
我知道条件反射的回答又一次让自己显得无知。那是一群飞翔在高空随时准备围猎小动物的“狩猎者”,既显示出强大的攻击性,又拥有高度的自控力。我直觉这是跟人十分接近的物种。
阿鸿是行动派,很快办好签证,我不得不改变休假方式,跟他一道往蒙古国去。飞机在成吉思汗国际机场降落时,我有短暂的眩晕。接着是一阵长且熟悉的滑翔,我知道自己再次进入一条仿佛被无限抛弃的跑道。似乎还没有进入猎鹰的领地,过往旅途中那阵熟悉的空茫感又袭来了,提着行李的手差点滑下去。阿鸿赶上来从后面帮我拖住行李,又告诉我朋友已经在出口等着我们,我的心才稍稍放下,开始期待起这次旅行—我把没有带摄影器材的旅途都称为旅行。也因为没有摄影任务的控制,我终于把大脑放空,只想着怎么用双眼记录。毕竟,我更无法接受手机摄影的变形,只能信任头脑。
阿鸿的朋友名字很长,但用蒙古语念出来,有一个音节接近 “ji”,阿鸿便叫他阿吉。阿吉是地道的蒙古人,刚刚二十五岁,已经是两个男孩的父亲。阿鸿退役前曾在蒙古国执行运输任务,阿吉是他们小分队的向导,帮助分队穿越雪山。退役前阿鸿的最后一次任务,是接待我和同事穿越一段常遇泥石流的山地。退役后,阿鸿把曾经用于极地训练的热情,投入到户外旅行中,我常常看到他分享在朋友圈的攻略。加之他退役后在运输公司做事,也时时需要外出,感受却不似在部队时,他常常想念曾经那种高强度的密集训练,那曾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不像现在,看起来依旧开朗,却常常被失眠困扰。
阿吉不懂英语,但因曾外祖母在内蒙古生活,他十八岁前来过几次中国,懂一点汉语,只是十分有限,多数时候要靠打手势。我享受着语言不通带来的沉默,很珍惜地望着车窗外,湛蓝的天空、昏黄的大地、稀疏的建筑物,彼此相隔甚远的树,以及距离带给我们的那丝整洁的印象。直到车子越开越快,我在半梦半醒中听见阿吉喊了声:“马上到真的高原!”
我没想到阿鸿不打算在市内休整一晚,直接就往猎鹰家族而去,惊讶中睡意全无,只是呆呆地看着远处起伏不定的山脉。直到车子越开越高,头顶的蓝天渐渐和晚霞连成一片,有几抹深蓝色藏在云层的缝隙中,从晚霞深处透出来,显出一层淡淡的蓝紫色。远处与地表连接的地方,又泛出一层慵懒的橘黄。开着车的阿吉似乎比我们还兴奋,一边唱着蒙古语歌,一边轻拍方向盘打着节拍。阿鸿说,白天只要方向不错,怎么开都可以,但现在天黑下来,就不好开了。我听着阿吉的歌声渐渐落下,直至完全消失。待我和阿鸿在手电筒的光亮中匆匆分食完一袋薯片,我们面 前山坡的尽头已经站着几个戴着圆帽的哈萨克人。为首的一位拿着手电筒,阿吉喊他“波泰”。
夏日的高原夜晚,虽然没有我和阿鸿想象中那样冷,但确比白天气温低许多。我们在波泰的带领下穿过呼呼的风声和一些分不清是狼还是犬的吠叫,钻进蒙古包内。喝了奶茶酒,吃羊肉、干芝士和面包。波泰解释说,我和阿鸿的蒙古包因狂风的缘故未能在白天搭好,只能先和他们一家挤在一起。阿鸿则表示不用另搭,除非波泰觉得住不下。波泰哈哈大笑,语气也热络起来。
和阿吉不同,波泰的汉语很流利。他曾在二连浩特做运输生意,往返于中国、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多年。直到三年前妻子生下第三个孩子,他不得不分配更多精力给家庭。我想问他为什么不考虑把家人接去山下,阿鸿摆摆手制止了我。
驾驭猎鹰,有体能要求,需会骑马。好在我和阿鸿本来就会。阿鸿退伍前接受过系统的体能和抗寒训练。我大学毕业后就在地理杂志工作,多次在国内西北部和北欧各地徒步拍摄鸟群和草食类动物,虽常常需维生素保持体力,但基本身体素质也都过关。波泰对我们很满意,第二天一早,就带我们挑选猎鹰。 起初,一只看起来有些暴躁的金雕飞到我戴着厚手套的小臂上。波泰给它戴上眼罩,它则不消十秒就吞食完我切好又洗净泡出血水的羊肉。只是波泰并不打算把这只猎鹰交给我。他建议我和阿鸿同时训练一只猎鹰,我们表示听从安排,只是担心猎鹰会不懂得如何接受两个主人。波泰则笑道,说主人无论几个,对猎鹰来说都是一个。假如我和阿鸿离开他们一家和整个部落,猎鹰也未必依然认同我们是主人。我和阿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最终,一只看起来相对温顺的母金雕,成为我和阿鸿的预备朋友。除了与它尽快建立友谊,为可能的狩猎创造机会,大多数时间,我和阿鸿都在草原上骑着马观察空中飞翔的鹰。即使作为人类的狩猎搭档,它们的自由也依然广阔。人类的喂食更像对它们辛勤工作的奖赏,除此之外,它们依然有自己的生活,比如训练子女,比如和其他未被完全驯化的亲戚们偶尔团聚。我和阿鸿一边觉得不可思议,一边察觉到其中巨大的平等和差异,激动非常。
从清晨到黄昏,我们不知疲倦地奔跑,有时,在满天星斗下躺着看像在我们眼前流动的星星。有时,在半梦半醒之间,我甚至觉得一伸手就可以直达天上。阿鸿则一如往常,在固定的时间与神秘的朋友通电话。在这样的天幕下,即使说到私密的话语, 我似乎也听而不闻,仿佛那些可能掺杂着欲火和绝望的言辞,只是为了配合广阔草原上奔跑和休憩的动物。
这样持续了几日,波泰邀请我和阿鸿围观他们的猎鹰大赛。与我想的不同,当鹰从主人的手臂上飞起,它们彼此并不产生真正的竞争,更像沿着自己本来就有的跑道,朝着目标下手。我没有见到两只鹰因争夺猎物而发生斗殴,即使有碰撞,晚一步的鹰也会毫不犹豫寻求新的目标。只是,和一些看起来缺少牵挂显得更为独立骄傲的鹰不同,我和阿鸿的母金雕,早已经是一位母亲。波泰说,它正在训练自己的孩子。阿鸿曾在与国内客户打长途电话的清晨,看到母金雕率先醒来,待波泰把它的眼罩摘下,它就往另一个方向飞去,午后准时回来。我不知道它的孩子在何处,只一次,母金雕飞回我们的蒙古包时,它身后不远处有一只小鹰似要飞向前,又似要退到其他鹰的背后。
我想,那就是母金雕的孩子了。它看起来已足够神气,只是没有母亲自信,如若不是母亲在前面站着,它还要更加胆怯,不愿意朝我们靠近。
“这已经是它的第二件羽毛衣了。”阿吉道,“上次来,它还是这样。”他比画着,试图告诉我们上次这只小鹰的羽毛,只能勉强把它的身体遮住。
“我甚至没有看清那是一只鹰。”阿吉道。
“它的底子不算很好。”波泰道,“它出生前,草原上来了坏猎人,不少鹰被电网电死……它母亲就是那时候受了伤,之后就没好起来。”
我和阿鸿感到惊讶,我们完全比较不出母金雕和其他金雕的区别。母金雕的战斗力似从没有弱于其他猎鹰。但波泰说,这就是带小鹰的鹰应做的表率。
这样又过了几日,阿鸿的失眠减轻了一点,清晨准时醒来处理工作。因此带来的好心情,似乎缓解了他和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阿鸿甚至时而露出甜蜜的微笑。
白天,我和阿鸿一起在阿吉的带领下在草原上游玩,见到过断裂的河坡、蒙古包围成的农家乐和牧民子弟学校,以及没有墓碑的荒坟。
坟十分低矮。阿吉说,牧民每迁徙一次,坟地就矮一寸。也许再过不久,这里就像其他地方一样,看不出曾有墓地的痕迹。 我不禁想起在冰岛溶洞的日子,曾和同事发现过当年的探险者留下的少量遗骸,甚至还有人说,如果那些骨头依旧长期停留在洞中,就会和洞穴长成一体。当时听到这些细节,我只觉得是一场奇观,但也并不为之所动。此番把它们再次从记忆中打捞出来,突然百感交集。那些我曾经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再次集中回到我的脚下。我不禁觉得像是悬浮在幻象之中,感到脚下的泥土竟也有一丝松软。但很快,我又觉得脚下的泥土比刚才更坚硬了。这样沉默着走了一段,阿吉突然示意我和阿鸿上马——
“风神要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在狂风中观看空中盘旋的鹰。
它们围成了一个圈,仿佛这是它们抵挡狂风的方式。我们的马在风中时而前进时而退缩,我感觉大腿两侧比往日更疼痛,一边希望赶紧回去,一边又好奇鹰群的举动。直到狂风到来,它们终于分散飞去,仅有一只小鹰依然在刚才的圈圈内飞翔。
因为曾经近距离拍摄鸟群和草食动物,我感受到的都是相对温顺的动物教育,即便争夺,也知道这是出于生存本能。可鹰不同,在这种看起来荒芜的草原上,它们即便不是最强大的,也是强者之一。它们的训练更像是为了应对某个最艰难时刻的战斗,而非只为生存。过往的户外工作,让我感到残酷的不是动物世界,而是气候和长期独自跋涉、观察的孤独。因职业的特殊性,我的许多同事在过去几年内纷纷转行。没有新的人加入,有些任务,我必须独自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前往,甚至要独自面对在极昼中跋涉的困倦带来的似是夜晚、又仿佛白天的幻象。我也不是没想过更轻松稳定的职业,可真的在办公室停留多日,我又会想念那个独自行走时的冷静自我。我只能专注于行程中的具体的艰难,否则就可能完不成任务。一切精神深处的纷纷扰扰在这个时段暂时退去,没有网络,没有热腾腾的食物,还要躲避暴风雪和个别动物的攻击,我变得十分有耐心。尽管每段路途的站点都有接应我的人,但许多时候,我只能依靠手表推测他们会在何时出现,也许是下一个路口,也许是几十个路口之后。仿佛身处一场没有队友又没有裁判,更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我只能把维生素嚼碎混着肉干和水吞下去,想着无论如何,帐篷一定不能划伤。这样一路想着,我竟跟着阿吉默默走到居住的蒙古包前。母金雕突然飞出来朝我的方向落下,只是它没有落在我的手臂上,而是落在阿吉的手臂上。阿吉没有戴手套,鹰爪直接穿过他的右手手背,我不禁惊叫一声。
波泰道:“它把阿吉认作了阿鸿。”
阿吉倒是笑嘻嘻的,甚至重新给母金雕戴上眼罩。
“幸好没伤到骨头。”波泰给阿吉拿来药,阿吉制止了他,自己清理起伤口。我这才看见,阿吉和波泰的掌心和小手臂上都有好几条疤。
“被鹰爪划伤,是驭鹰猎人的勋章。”波泰重复着他童年时祖母说过的话,“我小时候不爱学这个。但当时我阿爸去世,家里的手艺必须有人继承。我是独生子。姆妈说,‘要想活得好,除了放牛羊,还必须会一样’。我那时只想下山念书,可我家是最穷的。我就想下山打工,或者去乌兰巴托……只是也不可能。姆妈说我必须学会阿爸的手艺。我那时候没能跟阿爸学会,只好让部落里其他的长辈来教我。他们对我比阿爸对我严厉,被鹰爪穿过了手臂,也只隔三天就继续训练。我给稻草人扎上野狐的皮毛……风里,它被我们的马拖着在草原上奔跑……那时我没有属于自己的鹰,只有阿爸曾经的那只跟着我们,还有部落里其他的鹰。他们说,只要有一只鹰把猎物交到我面前,我就算它的主人了……可我在风里等了很久,马背都松弛下来……还是没有鹰那么做……”
我看着波泰红彤彤的脸上那道浅浅的疤,不禁对我和阿鸿的这位新朋友有了新的敬畏。
“……这是好事。”波泰道,“它居然主动想要迎接主人了……自从它开始训练孩子,就似乎不再对任何新东西感兴趣……跟所有忧心忡忡的母亲一样……除了必要的部分……我想,你们很快就可以一起打猎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