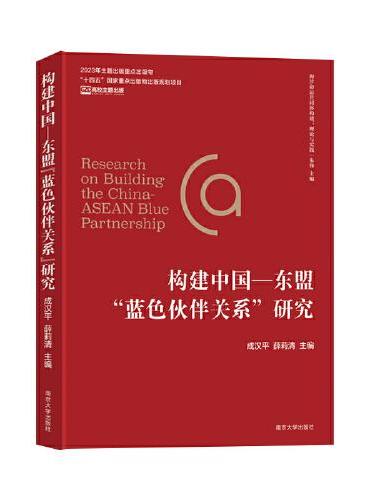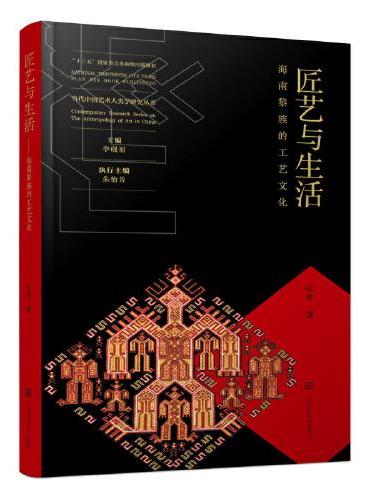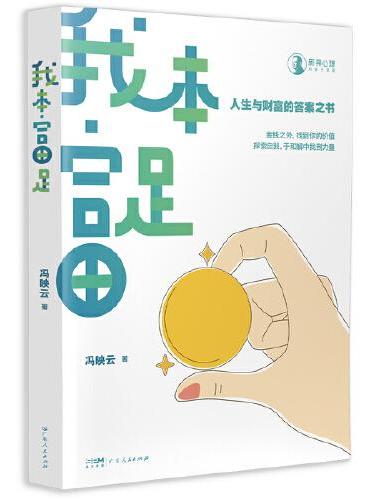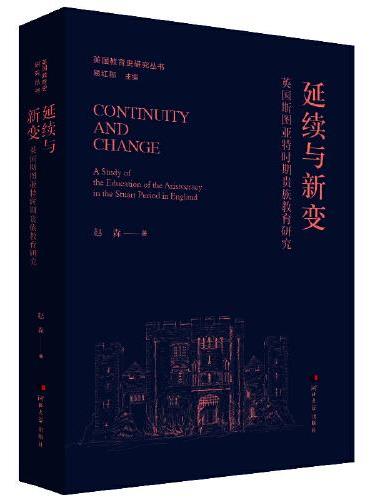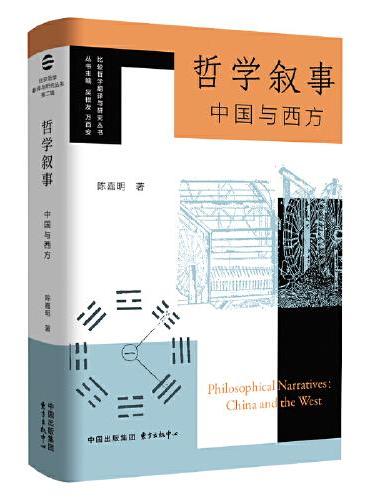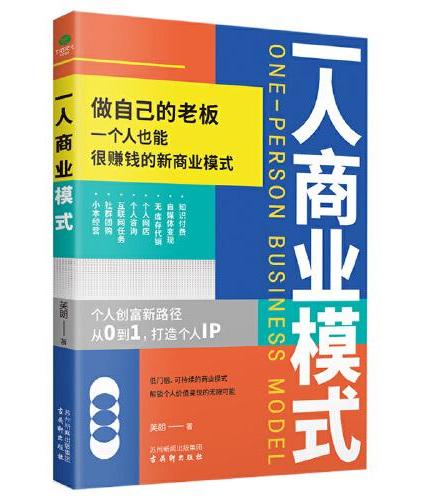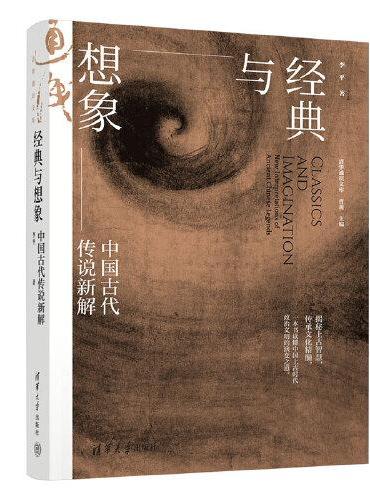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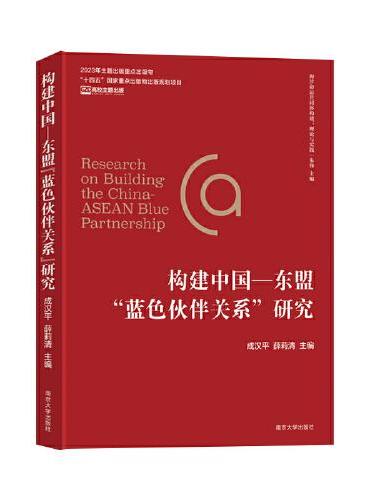
《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理论与实践)构建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研究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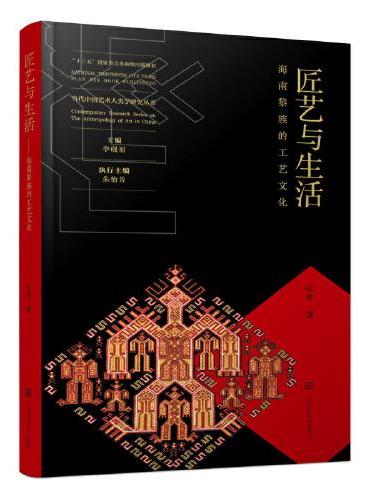
《
匠艺与生活:海南黎族的工艺文化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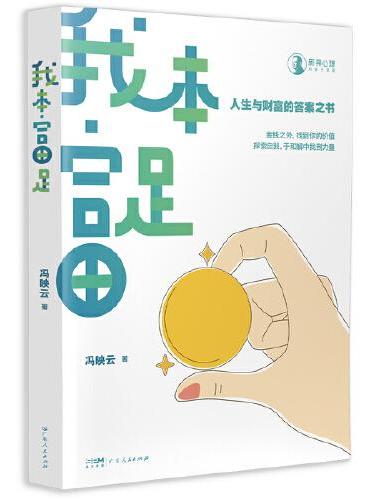
《
我本富足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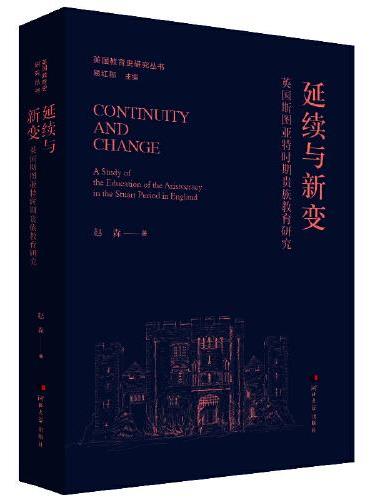
《
英国教育史研究丛书——延续与新变:英国斯图亚特时期贵族教育研究
》
售價:HK$
108.9

《
更易上手!钢琴弹唱经典老歌(五线谱版)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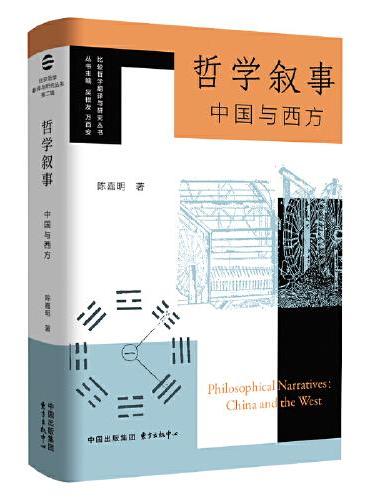
《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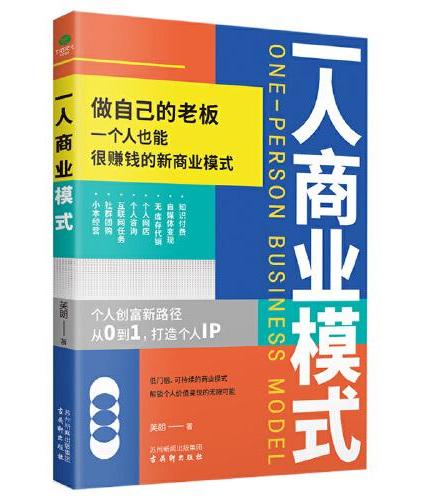
《
一人商业模式 创富新路径个人经济自由创业变现方法书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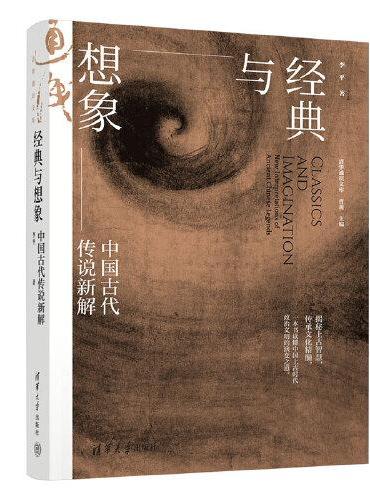
《
经典与想象:中国古代传说新解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
美剧《妙女神探》系列原著小说,双女主强强联手,惊险刺激,反转不断。荣获尼洛沃尔夫奖年度最佳侦探小说,获得爱伦·坡奖、麦卡维提奖提名全球销量突破三千万册、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斯蒂芬金谈写作》书单推荐作家——“医学悬疑女王”苔丝·格里森话题之作。“死而复生”的女尸,医院中的绑架,一场关于“美国梦”的骗局。法医加刑侦,细节生动真实。
|
| 內容簡介: |
“我叫米拉,这是我的故事。”
冰天雪地的贫瘠湖畔,黄沙漫天的墨西哥沙漠,绿意森然的独栋木屋。
哪里都不是她们的归宿,哪里都仿佛巨大的牢笼。
这牢笼由铁制的围栏、贪婪的人心和沦丧的道德铸成。
米拉和她的朋友们被困在这里,无人能听到她们的哭声。
远在波士顿,神秘女子在停尸间“死而复生”,与同伙劫持医院,即将临盆的警探简·里佐利被困其中。联邦探员迪恩为了拯救妻子,法医莫拉·艾尔斯为了营救挚友,决定一边谈判一边查明真相。然而,警方采取了突入行动!
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简听到了一句柔和却急切的低语:“米拉知道。”
来自远方的哭声终于抵达了它的归处……
|
| 關於作者: |
作者:苔丝·格里森
美籍华裔女作家。一九七五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人类学专业。一九七九年,取得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博士学位。在夏威夷檀香山担任内科医生行医多年,后辞职成为职业作家。
一九九五年,苔丝·格里森出版了第一本医疗惊悚小说《宰割》,迅速跃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列。二〇〇一年,她的第一本犯罪惊悚小说《外科医生》甫一面世便获得瑞塔文学奖。波士顿警察局凶案组女警简·里佐利作为配角首度登场,在随后的十二本小说里,她作为核心人物,与女法医莫拉·艾尔斯搭档冒险,共同探案。苔丝·格里森被《出版人周刊》誉为“医学悬疑女王”,“里佐利与艾尔斯系列”为她的代表作,后被改编为美剧《妙女神探》,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
译者:乔迪
CATTI一级笔译,一个教英语的翻译。代表译作有:《至高忠诚》《间谍的工具箱》等。
|
| 內容試閱:
|
1
我叫米拉,这是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太过精彩,该从哪里讲起呢?就让我从克里维奇讲起吧。克里维奇位于谢尔瓦奇河畔,由米亚德利镇管辖,是我的故乡,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八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十二岁那年,父亲丧命于邻居的货车轮下。但我不想讲这些。我想从这里讲起——从墨西哥荒漠讲起,那里离我的家乡白俄罗斯很远。在那里,我失去了我的纯真善良,还失去了梦想。
那是十一月的一天,万里无云,天空是我从未见过的湛蓝,黑色的大鸟疾冲向天。我坐在一辆白色面包车里,司机是两个男人。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的真实姓名。他们只是大笑着,叫我红发索尼娅。自打我从墨西哥城下飞机,他们就这样喊我。安雅说,他们这样喊是因为我有一头红发,就像《女王神剑》的女主人公索尼娅一样。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但安雅看过。她偷偷对我说,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漂亮的女战士用长剑战胜敌人的故事。现在我知道了,原来他们给我起这个名字是为了讥笑我,笑我不漂亮,笑我不是个战士。我只有十七岁,我很害怕,害怕未知的明天。
安雅和我手拉着手。车里除了我俩,还有五个姑娘。面包车行驶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穿过一丛丛低矮的灌木。在明斯克,那个女人答应我们,她会将我们送上这次的“墨西哥之旅”。但我们心知肚明,这根本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次逃离,一个机会。她说:你们坐飞机去墨西哥城,机场有人接你们,帮你们越境,帮你们开始新生活。
她说:“你们在这儿能过什么好日子?这里根本没有适合姑娘的好工作,没有靠谱的公寓,也没有靠谱的男人,你们也没有父母可以依靠。而且米拉,你的英语说得还不错。在美国,你们能融入社会,一定能。”她打了个响指,“勇敢点儿!把握机会呀!老板们还能出路费,你们还在等什么?”
等的肯定不是这个,我想。我看向窗外,一望无际的荒原呼啸而过。安雅靠着我缩成一团,车里所有的姑娘都一言不发。我们都开始思考同一件事情:我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车已经开了一上午,前座的两个男人什么都没说,但后排的那个总对我们挤眉弄眼。他总是偷瞄安雅,我不喜欢他的眼神。安雅并没注意他的眼神,她正靠在我肩上打盹。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叫安雅“小鹿”,因为她太害羞了,哪个男生看她一眼,她就脸红。我和安雅一样大,但安雅的睡颜就像孩童一样纯洁。我有点儿后悔,不应该让她跟我一起来,应该让她留在克里维奇。
面包车终于下了高速,开到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那五个姑娘蒙眬着醒来,盯着窗外灰秃秃的山。巨大的石砾散落四处,像风化千年的骨骼。这个时节,克里维奇的第一场雪应该已经落下,但这里依然四下无风,只有沙尘、蓝天和一丛丛灌木。
车摇摇晃晃地停下了,前座的两个男人转过头来。
司机用俄语说:“下车走路吧,要想过境,只能走路。”
他们拉开车门,我们一个个爬出来。在车上坐了这么久,车外的阳光有些刺眼,我们七个伸着懒腰,打量这个世界。阳光灿烂,但风很冷,比我想象中冷多了。安雅把手塞到我手里,轻轻颤抖着。
“这边走。”司机命令道。他带着我们离开脏兮兮的土路,走上一条进山的小路。我们爬过一块块巨石,穿过一丛丛带着尖刺的灌木。安雅的鞋子是露脚趾的,她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把钻进鞋里的小石头倒出来。我们全都渴极了,但领头的男人只让我们停下来喝了一次水,然后紧接着启程,沿着石头路磕磕绊绊地爬上山,越过山巅,又跌跌撞撞地爬下去,朝着山谷里的森林前进。爬到底之后,我们才看到一条干涸的河床,两岸全都是前人扔下的垃圾:塑料水瓶、脏兮兮的尿布和一只不知什么年头留下来的鞋,鞋面上的塑胶被太阳烤出断裂的纹路,树枝上还挂着一小块蓝色油布。已经有太多的追梦者走过这条路,我们七个是后来者,即将沿着他们的足迹踏入美国。一瞬间,我所有的恐惧消失殆尽,因为这里,这些垃圾,就是我们即将到达彼岸的证据。
领头的男人挥手让我们过去,我们继续前行,穿过河床,开始爬另一边的河岸。
安雅紧紧抓着我的手,拖着一瘸一拐的脚。“米拉,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她轻声说。
“你没得选。”
“我脚都流血了。”
我低头,她的脚趾满是瘀青,娇嫩的肌肤渗出血来。我对着领头的大喊:“我朋友割伤脚了!”
司机说:“别矫情!快走!”
“走不了了,她得包扎一下。”
“你们两个,要么接着往前走,要么我们就把她扔在这儿。”
“至少给她点儿时间换双鞋吧!”
领头的男人回过头来,瞬间变脸,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安雅吓得退后几步,其他姑娘僵在原地,瞪大了眼睛,好像吓破了胆的羔羊般挤在一起。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揍了一拳,瞬间跪倒在地,眼前一阵昏黑。安雅的尖叫声听起来十分遥远,然后我才意识到,疼痛从下巴处传来。我尝到了血腥味,鲜红色的血一滴滴落在河床的圆石上,又飞溅开来。
“起来!站起来!时间浪费得够多了!”
我蹒跚着站起来。安雅盯着我,眼里满是受伤的神色。“米拉,听他们的吧。”她轻声说,“按他们说的做。我的脚不疼了,真的,我能走。”
“你现在搞明白了?”领头的男人对我说。他又转向其他姑娘,扫视一周。“你们都知道惹恼我会是什么下场了吗?敢顶嘴?就是这个下场!快走!”
一瞬间,那些姑娘连滚带爬穿过河床,爬上河岸。安雅抓着我的手把我拉上来。我头晕目眩,只能拉着她的手,跌跌撞撞地跟着她,把嘴里的血腥味咽下去,惶惑地盯着眼前的路。
看起来不远了。我们爬上河岸,穿过丛林间蜿蜒的小路,转眼间就站在了一条土路上。
两辆面包车停在那里,等着我们。
“站成一排,”司机说,“快点儿!给人家看看。”
尽管不太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七个依然排排站好,精疲力竭,灰头土脸,脚上还流着血。
车上下来四个男人,用英语和司机打了招呼。他们都是美国人。一个大块头慢悠悠走过来,一个个打量着我们。就好像农夫在审视他的羊群。他戴着一顶棒球帽,皮肤被烈日晒得通红。他
停在我面前,皱眉道:“这个怎么了?”
“哦,她顶嘴了,”司机说,“就是点儿瘀青。”
“这个太瘦了,谁想要她?”
他知道我能听懂英语吗?他在乎吗?我可能是瘦了点儿,但他简直像头猪。
大块头的目光已经移到下一个姑娘身上去了。“可以,”他说,咧嘴笑了笑,“来吧,看看她们都有些什么料。”
司机看向我们。“脱衣服。”他用俄语命令道。
我们震惊地看着他。在这一刻之前,我都希望明斯克那个女人说的是真的,她真的在美国帮我们找到了工作。安雅要照顾三个小姑娘,我会在婚庆店里卖婚纱。就算司机拿走了我们的护照,就算我们在来时的小路上艰难跋涉,我依然觉得:没事,会好的,一切都会成真。
没有人动。我们依旧不愿相信,他居然让我们脱衣服。
“没听见?”司机说,“你们都想像她一样吗?”他指了指我依旧不断抽痛、青紫一片的脸,“快点儿!”
有个姑娘不断摇头,哭了起来。司机被激怒了,他抡圆了胳膊,一巴掌扇向那姑娘。那姑娘趔趄着倒向一旁,他又把她拽回来,抓住她的衬衫,一把撕开。她尖叫着推开他,可那男人上来就是一拳,直接将她击倒在地,爬都爬不起来。这还不够,他又走上前去,对着她的肋骨猛踢了几脚。
“现在,”他转过来看着我们,“你们谁还想试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