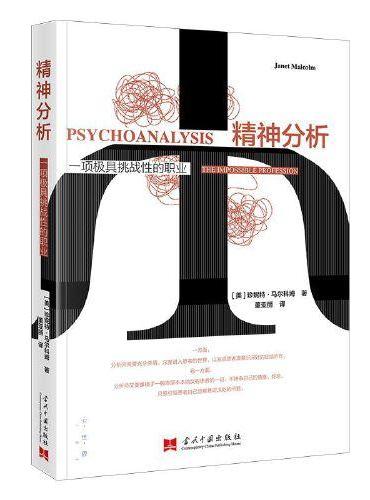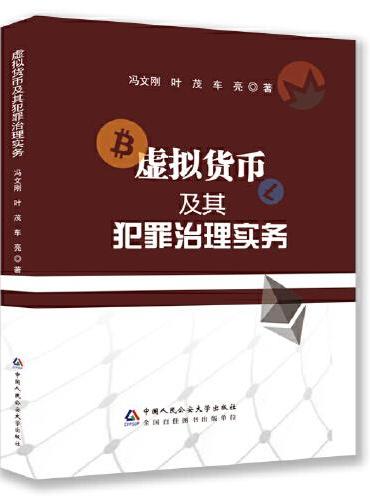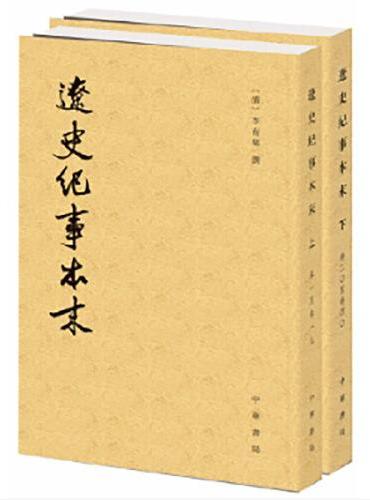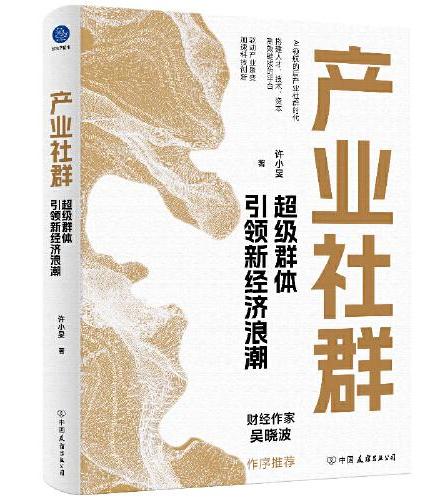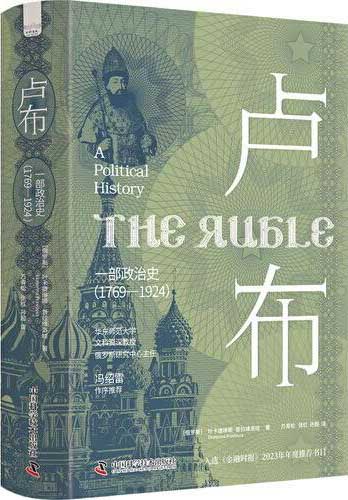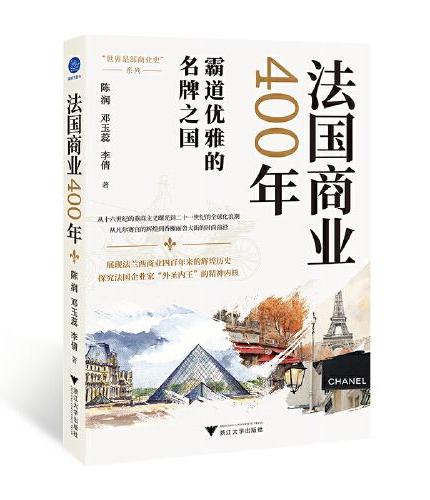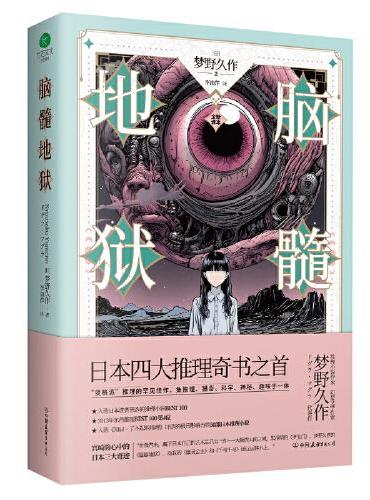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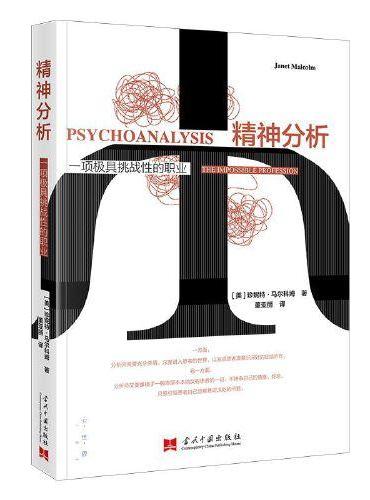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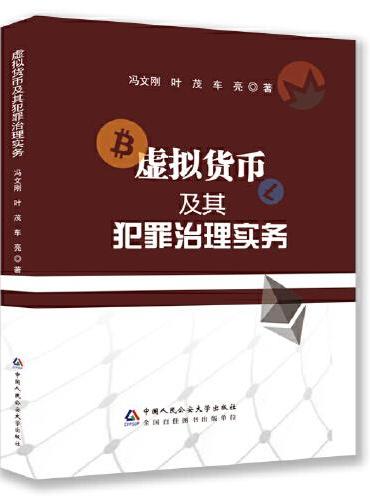
《
虚拟货币及其犯罪治理实务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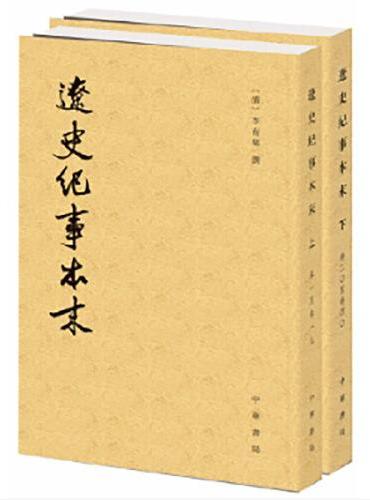
《
辽史纪事本末(历代纪事本末 全2册)新版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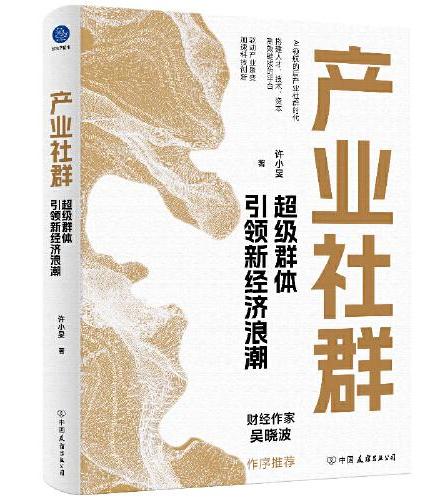
《
产业社群:超级群体引领新经济浪潮
》
售價:HK$
6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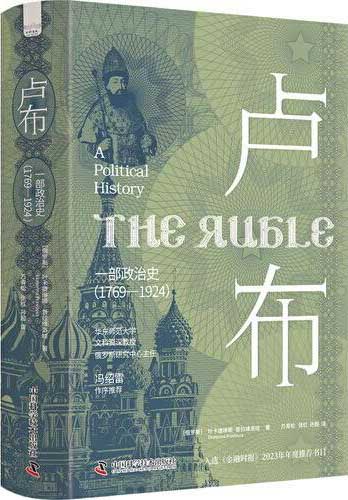
《
卢布:一部政治史 (1769—1924)(透过货币视角重新解读俄罗斯兴衰二百年!俄罗斯历史研究参考读物!)
》
售價:HK$
1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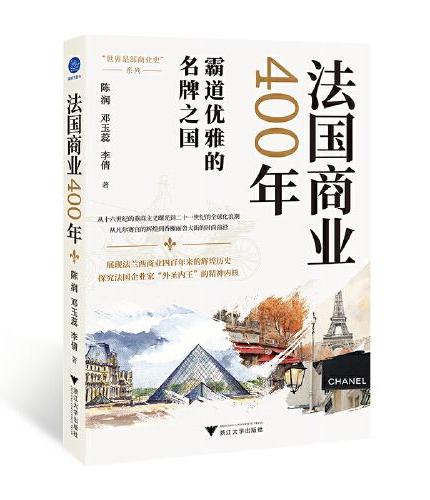
《
法国商业400年(展现法兰西商业四百年来的辉煌变迁,探究法国企业家“外圣内王”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74.8

《
机器人之梦:智能机器时代的人类未来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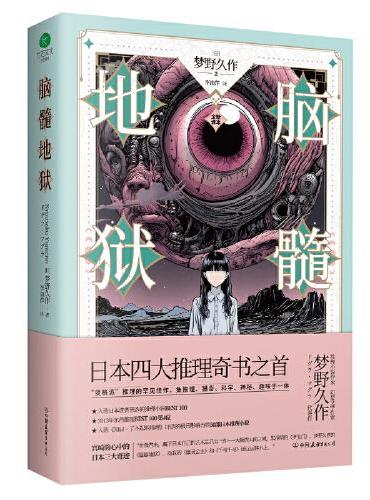
《
脑髓地狱(裸脊锁线版,全新译本)日本推理小说四大奇书之首
》
售價:HK$
61.6
|
| 編輯推薦: |
★ 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奖得主,《白老虎》作者阿拉文德·阿迪加短篇杰作集
★ 以英吉拉·甘地夫人和拉吉夫·甘地两次暗杀事件为节点,描摹当代印度社会图景
★14个短篇,刻画不同阶层多个人物,写尽理想陨落和人性污秽
★现实与虚构水乳交融,出色的当代印度编年史,媲美《小城畸人》的杰作
|
| 內容簡介: |
|
《两次暗杀之间》是阿迪加出版的第二部作品,却创作于斩获布克奖的《白老虎》之前。书里的十四部短篇小说讲述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印度南方小城基图尔。两次暗杀指的是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两次政治谋杀事件,即一九八四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遇刺与一九九一年拉吉夫·甘地被害。前一事件标志着印度以“紧急状态法”为标志的中央集权时代的结束,后一事件恰逢印度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到来。书中的故事围绕印度不同阶层、种姓与宗教信仰的人物展开,表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严酷现实,逼真地描摹出现代印度的真实面貌与众生百态。
|
| 關於作者: |
|
阿拉文德·阿迪加,一九七四年出生于印度海港城市马德拉斯,后移居澳大利亚,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与牛津大学。他在长篇小说处女作《白老虎》中,以一位印度班加罗尔的企业家给中国总理温家宝写信讲述自己人生故事的形式,反映了当今印度经济“奇迹”表相下的真实面貌,凭借独一无二的原创性获二○○八年曼布克奖。阿迪加曾任《时代周刊》驻印度通讯记者,并为《金融时报》、《独立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英国媒体撰稿。现居孟买。
|
| 目錄:
|
抵达基图尔
日(上午):火车站
小城格局
日(下午):港口
第二日(上午):灯塔山
第二日(下午):圣阿尔丰索男子高中与大专
第二日(晚间):灯塔山(山脚下)
第三日(上午):市场与广场
基图尔史
第三日(下午):天使之音电影院
基图尔的语言
第四日(上午):安布雷拉大街
第四日(下午):凉水井大转盘
基图尔:基本情况
第五日(上午):瓦伦西亚(去个十字路口的方向)
第五日(晚间):瓦伦西亚圣母大教堂
第六日(上午):苏丹炮台
第六日(晚间):波贾普
第七日:盐市村
大事记
|
| 內容試閱:
|
抵达基图尔
基图尔是印度西南沿海的一个小城,位于果阿与卡利卡特之间,西接阿拉伯海,东部与南部为卡利马河所围绕。该地区丘陵起伏,土壤呈黑色,并带有微酸性。季风每年六月光临小城,一直肆虐到九月。接下来的三个月,天气干燥而凉爽,是来此旅游的时间。这里历史悠久、风景如画、宗教众多、种族聚居、语言丰富,所以我建议您至少要在这里住一个星期才会不虚此行。0000日(上午):火车站
无论是乘坐清晨抵达的马德拉斯邮政专线还是乘坐下午到站的西海岸特快抵达基图尔,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火车站的拱门。基图尔火车站灯光昏暗、脏乱不堪,地上到处都是丢弃的午餐饭盒,不时有流浪狗四处觅食;到了晚上,这里则是老鼠猖獗的世界。
车站的墙壁上画着一个胖乎乎的大肚子男人,他满面春风,全身赤裸,盘腿而坐,非常巧妙地挡住了他的生殖器。画像下面用卡纳达语写着:“此人一言足以改变你的一生。”他就是当地耆那教的精神领袖,在这个城市经营着一家免费医院和快餐厅。著名的基塔马德维女神庙是一座泰米尔风格的现代建筑,坐落在一座古代神社的遗址上,这里祭祀着传说中的女神。从火车站步行就能到达,因此这里是游客们到基图尔旅行的站。
火车站附近的店主没有一个会雇用穆斯林。而经营印度奶茶和萨莫萨饼11萨莫萨饼是一种三角形的饼,内部馅料是马铃薯混合豆子、茴香、辣椒等香料,味道香辣,被视为印度人的点心。的“完美小店”的店主拉曼纳·谢蒂先生是个例外。他告诉齐亚丁他留在这儿工作也可以,条件是保证不偷懒,而且手脚要干净。
这个满身灰尘的小东西立刻把他的包丢在地上,手放在胸前说:“先生,我是穆斯林,我们穆斯林绝不会手脚不干净的。”
齐亚丁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脸蛋肥嘟嘟的,一笑就露出洁白的兔牙。他用一个硕大的不锈钢水壶为顾客煮茶。当茶水沸腾、溢出壶盖、在煤气火焰里发出咝咝声响时,他就会特别小心,眼睛死死地盯着水壶,生怕出一点差错。每隔一会儿,他就伸手从身边破烂不堪的几个不锈钢盒子里抓一把黑茶粉、一把白糖,或者捏一撮姜末,扔进茶壶里。他绷紧嘴唇,屏住呼吸,用左手把水壶倾向滤壶,滚烫的茶水就通过滤网流入纸板箱里的小玻璃杯里。这种纸板箱原本是用来放鸡蛋的,里面的隔缝正好用来放茶杯。
他把茶杯端到桌旁,一边将茶杯砰的一声放到客人面前,一边口里嚷嚷着:“一杯啦,两杯啦,三杯啦。”那些常到店里来的粗鲁汉子虽然被他打断了谈话,却也被他的举动逗笑了。再过一会儿,就见到他蹲在店门边忙活着:有时候把餐碟泡在装满了黑污水的大水槽里;有时候用从大学三角学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纸把油腻的三角饼包起来以便携带;有时候把过滤器里一堆堆的茶叶舀出来;有时候则用一把生锈的螺丝刀拧紧椅子后面松了的螺丝。听到别人讲英语时,他会停下手里的活儿,转过身子,用他的声音重复一遍:“周日到周一,天天没床戏!”于是整个店铺里的人便会哄堂大笑起来。
每天深夜,拉曼纳准备关门时,当地的老酒鬼廷马都会准时到店里来买三支香烟。看到齐亚丁用屁股和大腿顶住庞大的冰箱,把它一寸一寸地推进店里,他就高兴地开怀大笑。“看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他拍着手评论,“他还没这个冰箱大,却是个多么勇敢的战士啊!”
他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叫过来,掏出二十五派沙11印度等地的货币单位,一百派沙等于一卢比。放在他手心里。小家伙看了看老板的眼色,拉曼纳点了点头,于是他就合上手掌,用英语高声地叫着:“谢谢先生!”
有天晚上,拉曼纳·谢蒂把齐亚丁带到老酒鬼面前,摸着他的头说:“你觉得他有多大了?猜猜吧!”
廷马这才知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快十二岁了。他出生在本邦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家里的十一个孩子中排行老六。雨季刚结束,他父亲就把他送到了一辆巴士上,叮嘱他在基图尔站下车,然后到集市上等着别人雇用。“他们一个派沙都没给就把他打发出来了,”拉曼纳说,“这小子能留下来全是靠自己的本事。”
说完,他又将一只手放在齐亚丁的脑袋上。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的本事并不怎么大,即便是以穆斯林的标准来衡量也不过如此!”
齐亚丁跟店里其他六个洗盘子和打理茶馆的男孩交上了朋友。他们一起住在店铺后面搭建的帐篷里。每个星期天中午,拉曼纳都会关上店门,骑着他那辆蓝色和奶油色相间的巴贾牌摩托车,慢悠悠地驶向基塔马德维女神庙,几个男孩则步行跟着。拉曼纳到庙里去给女神供奉椰子的时候,六个男孩就坐在摩托车的绿色座垫上讨论庙檐上用卡纳达语写的几个红色大字:尊敬你的邻居,你的上帝。
“住在你隔壁的人就是上帝。”一个男孩得出了这样的推论。
“不对,意思是如果你真正信仰上帝,他就会在你身边。”另一个反驳道。
“不对,它的意思是,意思是……”齐亚丁也想解释解释。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让他说完:“你根本就不识字,你个乡巴佬知道什么。”
拉曼纳喊他们进庙,齐亚丁跟在其他孩子后面冲了几步,又迟疑起来,接着跑回摩托车旁边,嘴里说着:“我是穆斯林,我不能进去。”
他是用英语说的这句话。他那郑重其事的样子让其他男孩愣了愣,咧嘴笑了起来。
还有一周雨季就要来了,齐亚丁收拾好他的行李,说:“我要回家了。”他要回去承担起他对家庭的责任了,跟他的父母和兄弟们一起为那些有钱人干活;他们要在地里除草、播种、收割,每天只能赚几个卢比。拉曼纳还“额外”给了他五卢比,以确保他会回来工作(但是他摔坏了两个瓶子,每个瓶子要扣除十派沙)。
四个月后,齐亚丁回来了。他得了白癜风,嘴唇上布满了粉红色斑纹,手指和耳垂上也长满了粉红色的斑点。他的婴儿肥也在这个夏天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晒得黝黑,人也瘦多了,眼神里充满了野性。
“你怎么了?”拉曼纳拥抱了他一下,关切地问,“你不是早在一个半月以前就该回来了吗?”
“没什么。”齐亚丁边回答边用手指揉着他那褪了色的嘴唇。
拉曼纳马上叫人送了盘吃的。齐亚丁一把抓住盘子,像个小动物一样把脸埋到盘子里吃了起来。拉曼纳忍不住问道:“难道你在家里没吃过东西吗?”
大家都跑来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很多顾客这几个月天天都问他怎么还不回来;有的顾客本来都已经改去火车站附近新开的茶餐厅吃饭去了,因为那里干净一些,现在却又回到拉曼纳的店里来,就是为了看看齐亚丁。晚上,廷马拥抱了他几次,又塞给他二十五派沙。齐亚丁不声不响地接了过来,掖进裤子口袋里。拉曼纳却对着喝得醉醺醺的廷马喊道:“别再给他小费了!他现在可是个小偷!”
据拉曼纳说,齐亚丁在偷客人的咖喱角时被他抓到了。廷马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自己也不愿相信,”拉曼纳咕哝着说,“但是我亲眼看到了。他从厨房拿了个饼,然后……”拉曼纳对着想象中的饼咬了一口。
齐亚丁正紧咬着牙关,背靠冰箱,吃力地用腿肚把冰箱往店里面顶。
“可是……他过去是个诚实的孩子啊……”醉汉喃喃地回忆道。
“可能他一直都在偷东西,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发觉。这年头谁都不能信了。”
冰箱里的瓶子发出乒乒乓乓的碰撞声。齐亚丁停下了手里的活:“我是帕坦人!”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脯。“我来自帕坦,来自印度北方,那里的山上布满了积雪!我不是印度教徒,我不会干偷鸡摸狗的事情!”说完,他就走到店里面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醉醺醺的廷马问道。
店主解释说齐亚丁总是这样突然就帕坦瓦坦地胡言乱语,他肯定是在北方从那些毛拉11毛拉是伊斯兰教内用于学者或宗教领袖的称谓,多指伊斯兰教学校的教师或精通伊斯兰教义的学者以及诵经人。那里学来的。廷马双手叉腰,对着里面大吼:“齐亚丁,帕坦人是白皮肤的,就像伊姆兰·汗11伊姆兰·汗是巴基斯坦著名的板球运动员,退役后投身政治,成为印度“正义运动党”的领导人。那样;而你,黑得像个非洲人!”
第二天早上,“完美”小店经历了一场风波。这次齐亚丁被抓了个人赃俱获。拉曼纳抓着他的领子,把他拖到客人们面前,气冲冲地说:“给我说实话,你这个秃头女人养的,你到底偷了没有?要是说实话,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说的是实话,”齐亚丁一边回答,一边勾着手指搓了搓他那由于白癜风而褪了色的嘴唇。“我一个饼都没碰过!”
拉曼纳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倒在地,踢了几脚,接着又把他拖出了茶餐厅。其他的几个男孩只是挤在一起,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就好像几只绵羊在观看同伴剪毛一样。接着就听到拉曼纳大吼了一声,举起一根流着血的手指头。
“他咬我,这个畜生!”
“我是帕坦人!”齐亚丁站起来,也冲着拉曼纳吼着,“是我们来这里修建的泰姬陵和德里红堡。你怎么敢这样对我,你这个秃头女人养的,你这个……”
顾客们围成一圈,盯着拉曼纳和齐亚丁,苦苦思忖着到底谁对谁错。拉曼纳转过身对大家说:“这里再也不会雇用穆斯林了,我给他工作,他居然敢跟我打架。”
几天后,齐亚丁骑着一辆脚踏送货车经过茶餐厅,车板上的篮子里装满了牛奶瓶,乒乒乓乓地响着。
“看看,”他嘲笑以前的雇主,“卖牛奶的老板信任我!”
但是那个工作也没有干多久,因为他再一次被指控偷窃。他当众发誓再也不为印度教徒工作了。
有不少穆斯林移民定居在火车站附近,那边新开了几家清真餐厅。齐亚丁又在那里的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他在门口摆了台烤炉,卖煎蛋卷和烤面包,用乌尔都语和马拉雅拉姆语吆喝着:“穆斯林同胞们,不管你们来自世界的哪个角落,也门、喀拉拉邦、阿拉伯还是孟加拉,请到正宗的穆斯林餐馆来用餐吧。”
但是好景不长,这份工作也没干多久——他再一次被雇主指控偷窃,顶嘴的时候还挨了一巴掌。再见到他是在火车站了,他穿着红色的制服当起了搬运工,一边顶着大堆的行李,一边激烈地跟顾客讨价还价。
“我是帕坦人的儿子。我的血管里流着帕坦人的血液。听着,我从来不骗人!”
他盯着旅客,眼球突出,青筋毕露。印度的各个火车站总是有一些骨瘦如柴、独来独往的人出没。他们经常在角落里抽着自制的烟卷,眼神很活泛,似乎一声召唤就随时可以去打人或杀人。而齐亚丁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但是拉曼纳店里的老主顾们叫他的名字时,他总是对着他们咧嘴一笑。人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满脸笑容、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把茶杯砰的一声放到客人面前的男孩的影子。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了。
后来,齐亚丁跟别的搬运工打起来了,被赶出火车站后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了几天,见到长得像印度教徒或穆斯林的人就破口大骂。再后来他又回到了火车站重操旧业。几列满载士兵的火车到达了基图尔,坊间传言说在前往科钦的路上将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士兵走后没几天,货运列车随之而来,车上满载着要卸下来的大箱子。
齐亚丁闭上了嘴巴,把箱子从火车上卸下来,再搬到车站外面等着装货的军用卡车上。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都十点了齐亚丁还躺在站台上睡觉,一周的辛劳使他筋疲力尽。他的鼻子抽搐了一下,被空气中弥漫的肥皂味弄醒了。肥皂水和泡沫像小溪一样流到他身边。他看到一排瘦弱黝黑的人在站台边上洗澡。
00肥皂泡的气味刺激得他直打喷嚏。
“喂,到别的地方去洗!别吵我睡觉!”
他们笑了起来,用满是肥皂泡沫的手指着齐亚丁:“我们可不像那些肮脏的畜生,齐亚,我们中的有些人可是印度教徒呢!”
“我是帕坦人!”他嚷嚷着,“不准那样对我说话。”
正当他准备大吵一番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洗澡的人都冲了出去,吵吵着:“要苦力吗,先生?要苦力吗?”
虽然这个点没有火车进站,但还是有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了站台上。他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穿着白色整洁的商务衬衫和灰色的棉质长裤,手里拿着精致的黑色皮包,全身上下都散发着金钱的味道。那些搬运工疯狂起来,来不及擦干净身上的泡沫,就一拥而上,把那个人围在了中间,就像得了恶疾的人终于见到能够治病的医生一样。但是那个人谁都没理,而是径直走向一个身上没有肥皂泡的人——齐亚丁。
“到哪个宾馆?”齐亚丁挣扎着站起来问道。
陌生人耸了耸肩,好像在说“随你的便”。那些近乎赤身裸体、满身肥皂泡的搬运工仍然在旁边观望着,他看了他们一眼,眼中流露出厌恶之情。
齐亚丁对着他们吐了吐舌头,跟着那个陌生人出发了。
车站附近的街上满是廉价旅店,两个人就停在了其中一栋房子前面。房子上挂满了招牌,什么电器店、药房、水管维修,等等。齐亚丁指了指二楼的红色招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