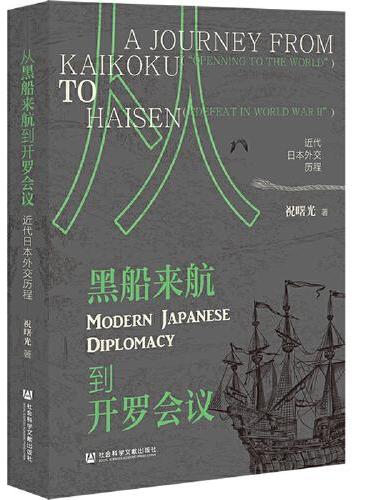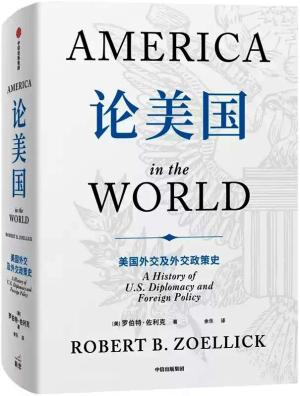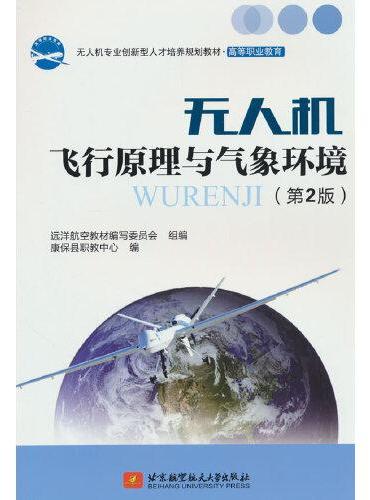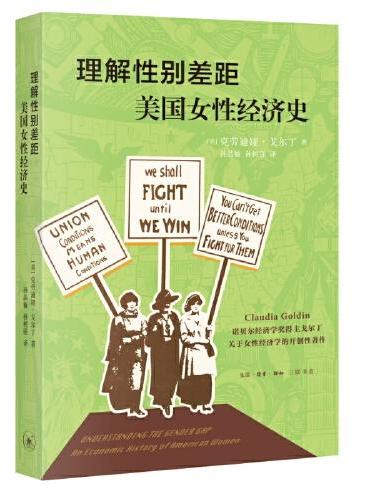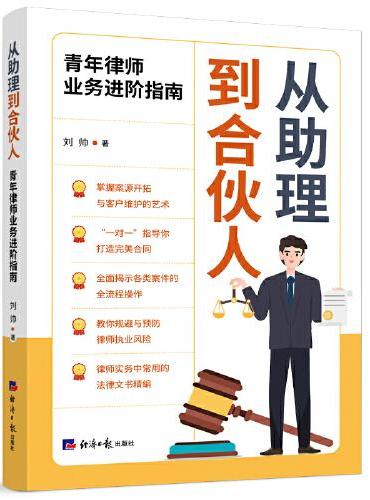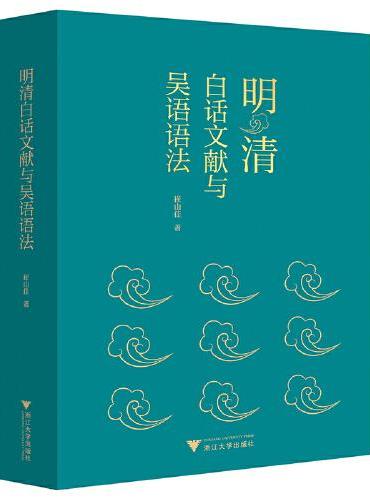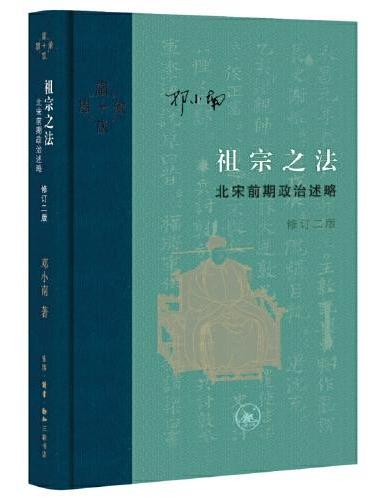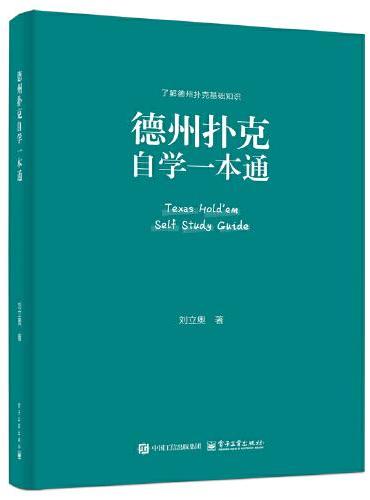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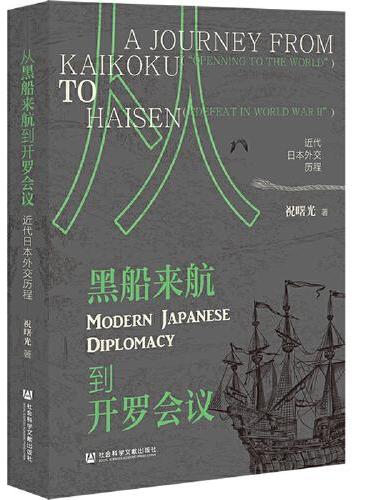
《
从黑船来航到开罗会议:近代日本外交历程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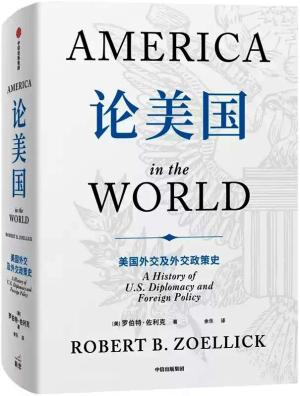
《
论美国(附赠解读手册)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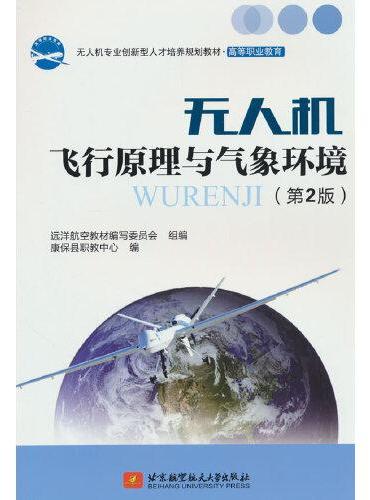
《
无人机飞行原理与气象环境(第2版)
》
售價:HK$
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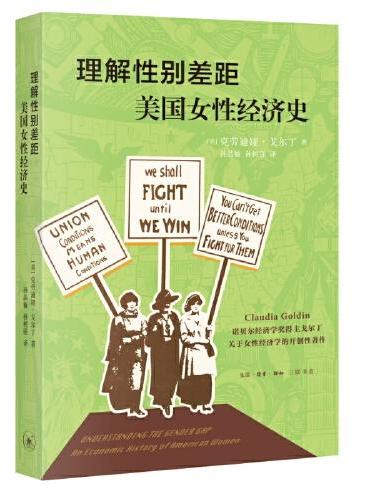
《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
售價:HK$
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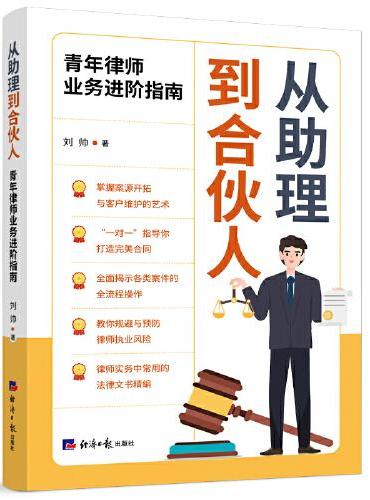
《
从助理到合伙人-青年律师业务进阶指南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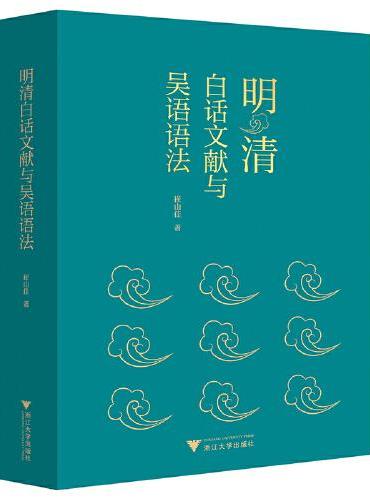
《
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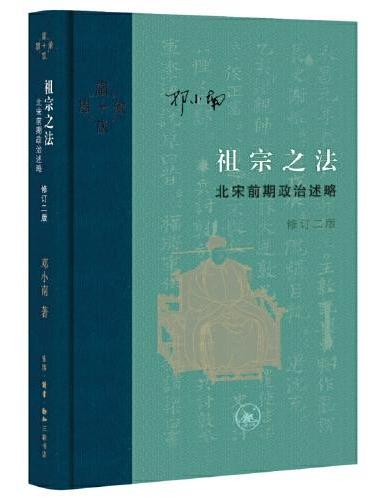
《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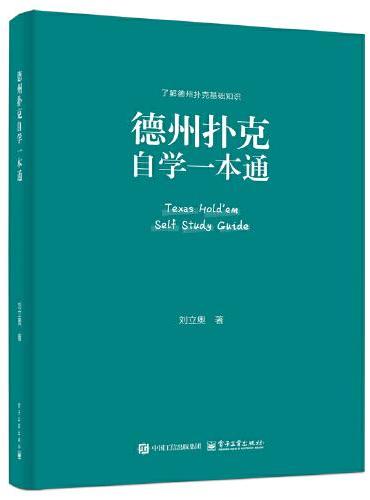
《
德州扑克自学一本通
》
售價:HK$
55.0
|
| 編輯推薦: |
奥威尔并非生而为先知。透过《一九八四》的深邃棱镜,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穿透一切人性迷雾的末日预言家。但那并非以血肉之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奥威尔。终其一生,他也曾是一个热忱的信徒,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受伤、恐惧、落魄的普通人。《一九八四》是他的终点而非起点。
《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与《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三部纪实作品就是奥威尔在人生和思想的重要关口留下的三个足印。从中,我们不难读出《一九八四》中某些似曾相识的场景与情感碎片,虽然经过了重重转换。它们共同构成了解读这位先知思想历程的一把钥匙。
|
| 內容簡介: |
《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的作者、反乌托邦的先知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一生中却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点或许会令不了解政治光谱变迁的当今读者有些困惑,但对于奥威尔来说,这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
《巴黎伦敦落魄记》是奥威尔正式出版的部纪实性作品,讲述了奥威尔本人在巴黎和伦敦自愿走入贫民窟,体验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经历。对英国殖民体制感到彻底厌恶绝望后,奥威尔的文学梦在几经挫折的情况下终于首度开花结果。巴黎和伦敦的经历可以看成是奥威尔为自己曾经为殖民体制服务的忏悔和救赎之旅。作为一名社会主义体制的忠实信徒,或许奥威尔刻意选择流浪和挨穷是对自己能否坚持贯彻社会主义理想的考验。巴黎和伦敦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繁华之地,社会底层的贫穷和困顿却令人触目惊心。奥威尔“自甘沉沦”,与劳苦大众平等相待的真诚态度在英国左翼文学作家中实属另类,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巴黎伦敦落魄记》成为一部揭露社会不公的经典纪实作品,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
| 關於作者: |
|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传世之作《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脍炙人口,历久弥新,被誉为“一代英国人的冷峻良心”。
|
| 內容試閱:
|
章
巴黎,金鸡大街,早上七点钟。街上传来几声愤怒又略带气哽的尖叫。在我住的地方对面经营一家小旅馆的蒙西太太走到人行道上,和住在三楼的一个房客吵架。她光着脚丫,趿着一双木屐,披散着一头灰发。
蒙西太太骂道:“臭婊子!臭婊子!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不要把虫子碾死在墙纸上。你以为你把整个旅馆买下来了吗?你怎么就不能和别人一样把它们扔出窗外呢?妈了个逼的,你这个贱货!”
住在三楼的女人回了一句:“母牛!’
接着,两人闹哄哄地吵了起来。街道两边的窗户都打开了,半条街的人加入了争吵之中,一直吵了十分钟,然后戛然而止,因为有一队骑兵经过,大家都停了下来,观望着他们。
我将这一幕情景记录下来,为的是让读者了解金鸡大街的风貌。虽然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单单只有吵架——不过,几乎每天早上这样的争吵起码得发生一次以上。除了吵架,还有街头小贩落寞的叫卖声和小孩子们在鹅卵石街道上追逐橘子皮的戏耍声。到了晚上则响起高昂的歌唱声,垃圾车经过时留下一股恶臭,这就是整条街的风貌。
这条街很窄——两边都是高耸肮脏的房屋,东倒西歪地堆在那儿,似乎在倒塌的时候被冻结住了。所有的房子都开设成小旅馆,住满了房客,大部分是波兰人、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旅馆楼下是小酒馆,花一先令就可以喝得酩酊大醉。到了星期六晚上,这一区有三分之一的男人会喝醉,为了女人大打出手。那些住在便宜的旅馆里的阿拉伯搬运工人总是在窝里斗,拿着椅子互殴,有时还动用了手枪。到了晚上,警察得两人同行才敢到这一带巡逻。这地方的确不太平。不过,尽管环境肮脏嘈杂,这里还是住了一些体面的法国人,从事小店主、面包师和洗衣女工这样的工作。他们只与自己人来往,安分地积攒着一点一滴的财富。这就是典型的巴黎贫民窟。
我住的那家旅馆叫“三雀旅馆”,有五层楼高,采光阴暗,几乎摇摇欲坠,用木板隔出了四十个房间。房间很狭小,而且终年没有打扫,因为旅馆里没有女工,而女房东F太太根本没有空闲。墙壁差不多和火柴棍一样薄,为了遮掩上面的裂缝,贴了一层又一层的粉红色墙纸,都已经松动了,孕育了不胜其数的臭虫。在天花板上,整天都有一列列的臭虫就像士兵列队行进一样爬来爬去,到了晚上就会下来饕餮一餐。于是,房客们每几个小时就得醒来大肆屠戮。有时臭虫实在太猖獗了,房客们就会用硫烟将它们赶到隔壁房间,而隔壁房间的房客也会点燃硫烟进行反击,把臭虫们给赶回去。这地方很脏,却很有家的感觉,因为F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好人。房间的租金一周从三十到五十法郎不等。
房客的数量总是在变动,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空手而来,身上没有一件行李,住上一个礼拜,然后就走了。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补鞋匠、砌砖工、石匠、搬运工、学生、妓女和捡破烂的。他们当中有的穷得叮当响。在阁楼的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位保加利亚学生,靠做鞋子出口到美国维持生计。每天从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他就坐在床上做完十二对鞋子,挣到三十五法郎。其余的时间他到索邦神学院上课,准备进教堂服务,那些神学著作封面朝下堆在满是皮革的地板上。另一个房间住着一个俄国女人和她的儿子,他自称是个画家。母亲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织袜子,一只袜子挣两毛五。而儿子则穿得衣冠楚楚,整天流连于蒙帕纳斯区的咖啡厅。有一个房间租给了两个房客,一个上日班,另一个上夜班。有一个房间租给了一个鳏夫,和他两个成年的女儿睡同一张床,而那两个女儿偏生又长得楚楚动人。
旅馆里住了一些怪人。巴黎的贫民窟是怪人的集中地——这些人破落潦倒,过着孤独癫狂的生活,连维持外表的正常或体面都顾不上了。由于生活穷苦,他们的行为标准无法以常理判断,就像人们一有钱就可以不用工作一样。我住的这家旅馆有几个房客过着光怪陆离的生活,几乎无法用言语加以描述。
就以罗吉尔夫妇为例吧,这对老夫老妻个头奇矮,有如侏儒,衣衫褴褛,从事着奇怪的买卖。他们总是在圣米歇尔大街兜售明信片,其中颇有猫腻:这些明信片的包装看上去像春宫图,但其实只是卢瓦尔河畔城堡的照片。等顾客们发现货不对板时已经太晚了,因此也就没有人抱怨。罗吉尔夫妇一周挣一百法郎,生活非常节约,虽然没办法吃上饱饭,却能有钱买酒喝个半醉。他们的房间脏得连楼下都闻得到,据F太太所说,罗吉尔夫妇两人已经有四年没有换衣服了。
我们再说说下水道工人亨利吧。亨利身材很高,性情忧郁,长着一头卷发,穿着他那双长靴看上去颇为风流倜傥。亨利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上班以外他可以好几天不说话。一年前他还是个待遇不错的私人司机,能攒点钱。有一次他谈恋爱了,后来那个女孩甩了他,他按捺不住性子,对她拳打脚踢,而那个女孩居然因为这样而疯狂爱上了他。两人同居了半个月,亨利攒下来的一千法郎被挥霍一空。后来那个女孩和别人勾搭上了,亨利用刀子刺伤了她的上臂,被判入狱半年。那个女孩被刺伤后反而更爱亨利了,两人重归于好,商量好等亨利坐完牢出来就买一辆出租车,然后结婚安定下来。但半个月后,那个女孩再次红杏出墙,等亨利坐完牢出来她已经怀孕了。这一次亨利没有伤害她。他把自己的储蓄全部提了出来,喝得昏天暗地,后被判入狱一个月,出狱后他成为了下水道工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亨利都不开口说话。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他会成为下水道工人,他从不作答,只是伸出双手,表示自己戴过手铐,然后朝南边监狱的方向仰了仰头。不幸似乎让他在一天之内变成了半个白痴。
还有英国人R君。他一年有六个月和父母在普特尼住,另外六个月在法国住。住在法国的时候他每天喝四升红酒,星期六喝六升。有一次他曾远赴亚述尔群岛,因为那里的红酒是全欧洲便宜的。他是个温和的宅男,从不喧闹或和别人争吵,却从未酒醒。他总是在床上躺到日上三竿,然后一直在小酒馆的角落里一直坐到午夜,安安静静地喝着酒,一边喝一边说话,谈吐很文雅,又有点娘娘腔,谈论的内容都是关于古典家具。除了我之外,这一区就只有R君这个英国人。
像这样的怪人还有很多:朱尔斯先生是罗马尼亚人,他有一只玻璃假眼,但从不承认这一点。还有利穆赞石匠福雷克斯、守财奴罗克尔——他在我来之前就去世了——但卖破烂的老劳伦总是随身口袋里携带一张纸条,在模仿他的签名。要是有时间的话,写写他们的生平会很好玩。我之所以描写住在这一区的房客并不单单是为了好玩,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故事的一部分。我要描写的是穷人的生活,在这个贫民窟我次接触到了贫穷。贫民窟的生活肮脏不堪、离奇古怪,这些描写既是贫穷的客观写照,又是我个人经历的背景。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希望能让读者了解那里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章
贫民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比方说吧,在我们“三雀旅馆”楼下有一间小酒馆。房间很狭小,铺了地砖,一半陷在地下,摆着几张被红酒浸泡过的桌子,挂着一幅葬礼的绘画,铭文是“死亡的颂歌”,束着红腰带的工人拿着折叠小刀切香肠大快朵颐。F太太是个来自奥弗涅的农妇,长得像头倔强的奶牛,整天喝着马拉加酒,说是“要治胃病”。大家玩着骰子拿开胃酒作赌注,高唱着民歌《草莓和覆盆子》和《玛德隆》,玛德隆这个女人曾说过:“我爱着整支部队,怎么能嫁给一个士兵?”甚至公然就在大庭广众下狎戏亲热。到了晚上,旅馆一半的房客聚在小酒馆里,要是在伦敦能找到一间酒馆有这里三、四成的热闹开心就好了。
在小酒馆里你可以听到有趣的对话。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怪人查理,他说话就很有趣。
查理是个年轻人,受过教育,从家里搬了出来,家里人时不时会给他寄钱,他就靠这个生活。他很年轻,脸色红润,长着一头柔软的棕发,就像一个小男孩,还长着一张鲜红湿润的樱桃小口。他的脚很小,胳膊很短,双手就像婴儿的手一样胖嘟嘟的。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手舞足蹈,似乎太高兴雀跃了,一刻也无法让自己消停。现在是下午三点钟,小酒馆里只有F太太和一、两个失业的房客,但查理并不在乎说话的对象是谁,只要能让他倾吐心声就够了。他说起话来就像站在路障上的演说家,一连串单词从他的舌尖蹦了出来,两只短短的胳膊挥舞不停,那双小眼睛就像小猪的眼睛一样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说实话,那副尊容实在难以恭维。
他正在谈论爱情,他喜欢的话题。
“啊,爱情,啊,爱情!啊,曾经辜负过我一番爱意的女人!哎,先生们,女士们,这辈子我就栽在女人手上,沦为万劫不复之身。二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注定了毁灭。但我学会了很多事情,度量了智慧的深渊!能拥有真正的智慧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让你成为品位的有教养的绅士,变得文雅而邪恶。等等等等。
女士们,先生们,我能感觉得到你们都很伤心。啊,这没有什么,生命是美好的——你们不必难过。要开心一点,我恳求你们!
‘满斟萨摩斯岛的美酒,
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沉沦!’
生命多么美好!女士们,先生们,我将以我的经历向你们阐述爱的真谛。我会向你们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真正的情感,更为高尚微妙的欢娱,只有绅士才能理解。我将告诉你们我生命中快乐的一天。呜呼哀哉,但快乐对我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再也不会回来——没有半丁点儿希望,连追求快乐的欲望也消逝了。
听我说,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我哥哥就在巴黎——他是个律师——我爸妈叫他来找我,带我出去吃顿饭。我们两兄弟总是处不到一块,但我们不想忤逆爸妈。我们一起吃了饭,他喝了三瓶波尔多红酒,醉得很厉害。我送他回酒店,路上买了一瓶白兰地,等我们到了酒店的时候,我让他喝了满满一杯白兰地——告诉他那是醒酒药。他喝了下去,立刻烂醉如泥。我把他抬了起来,背靠着床,然后搜他的口袋,找到一千一百法郎。我拿了钱立刻跑到楼下,拦了一架的士,逃之夭夭。我哥哥不知道我住哪儿——不能拿我怎么着。
有了钱男人会去哪儿?当然是逛窑子了。但你以为我会把钱浪费在那些只有苦力工人才会去的烟街柳巷吗?去他妈的,我可是斯文人!你们知道吗,我挑剔得很,尤其口袋里有了一千法郎。到了午夜我才找到要去的地方。我遇到一个帅气的年轻人,大概十八岁,衣冠楚楚,理着美国式的发型。我们去了一间远离马路的小酒馆聊天,彼此心照不宣。我们聊这聊那,探讨怎么找点乐子。过了一会儿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开车离开了。
的士在一条狭窄偏僻的小巷口停了下来,只有巷尾一盏煤气街灯还亮着。石头缝里沾满了黑泥,旁边是一间女修道院的高墙。他领着我走到一座窗户紧闭的高大破屋那里,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了脚步声和门闩的转动声。那扇门开了一道缝,一只手搭在门沿上。那只大手弯曲着,直接将掌心伸到我们的鼻子底下要钱。
那个向导把脚伸进那扇门和台阶之间。‘你开价多少?’他问道。
‘一千法郎。’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一次付清,否则别想进来。’
我把一千法郎放在那只手上,把剩下的一百法郎给了那个向导。他道了晚安然后离开了。我听到里面在数钱,然后一个穿着一袭黑裙的干瘦的老太婆探出头来,狐疑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才开门让我进去。里面很黑,只有一盏煤油灯照亮了一堵石膏墙的一小块地方,其它地方显得更加昏暗,除此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到老鼠和尘土的味道。那个老太婆什么也没说,就着煤油灯点着了一根蜡烛,然后蹒跚着脚步走在我前面,领着我穿过一条石砌的走廊,来到一条石阶的上头。
她说道:‘喏,下去里面的地窖,你想干什么都行。我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懂的——想做什么都可以。
哈,各位先生,让我告诉你们——暴力——你们知道何谓暴力吗?——那种战栗的感觉,一半是恐惧而另一半是快乐,在这时流遍你的全身。我摸索着走了下去。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鞋子摩擦石板的声音,除此之外四周一片寂静。在石阶的底部我的手摸到了一个电开关,将它打开,一盏有十二个红色灯泡的吊灯照亮了地窖。我定睛一看,原来我不是在地窖里,而是走进了一间卧室,一间宽敞华丽的卧室,从天花板到地板都涂成了鲜红的颜色。女士们,先生们,想象一下那幅情景吧!地板上铺着红地毯,墙上贴着红色的墙纸,椅子上挂着红色的长毛绒,连天花板也是红色的,到处都是红色的,侵蚀着我的视野。那种红色沉重得令人窒息,似乎光线是从盛着鲜血的玻璃碗里透出来的。在卧室的一角摆着一张方形的大床,被褥也是红色的,上面躺着一个女孩,穿着一袭红色天鹅绒裙子。看到我进来,她缩成一团,想把膝盖藏在短短的裙摆下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