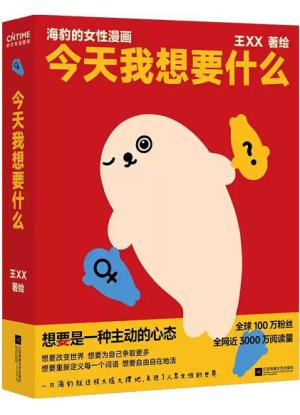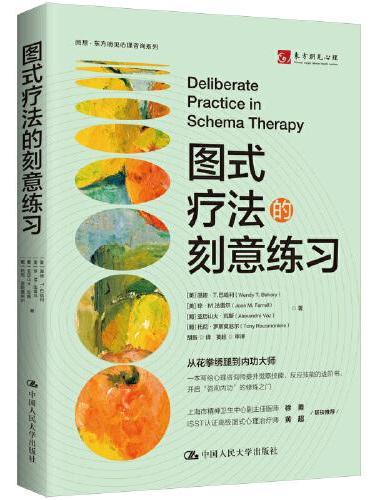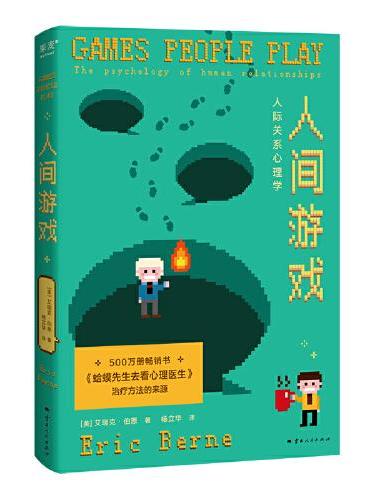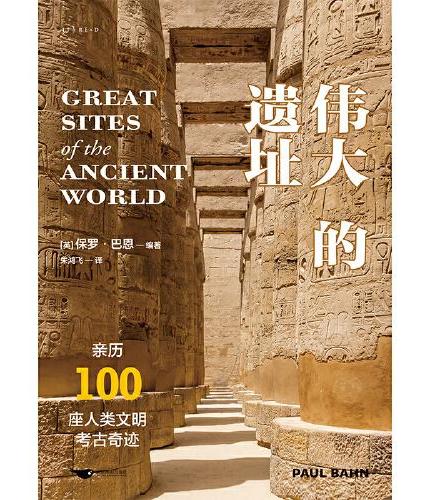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107.8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HK$
307.6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HK$
74.8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HK$
74.8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HK$
107.8
《
图式疗法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人间游戏:人际关系心理学(500万册畅销书《蛤蟆先生》理论原典,帮你读懂人际关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 售價:HK$
43.8
《
伟大的遗址(亲历100座人类文明考古奇迹)
》 售價:HK$
206.8
編輯推薦:
1. 一部全面深入追溯机器人观念演变史的佳作。
內容簡介:
机器人虽然是以纯粹科幻小说的形式走进我们的世界,但如今它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既存事实。无论是太空时代的半机械人、棋手自动机,还是我们口袋里的智能手机,机器人长期以来都是我们和我们的创造物之间令人担忧甚至令人恐惧的关系的象征。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目錄
目 录
內容試閱
引言:机器中的亲与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