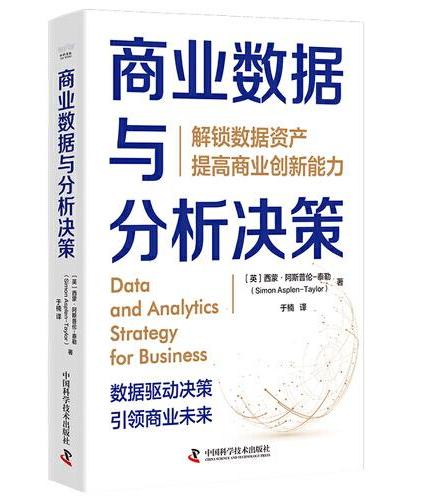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肌骨复健实践指南:运动损伤与慢性疼痛
》
售價:HK$
294.8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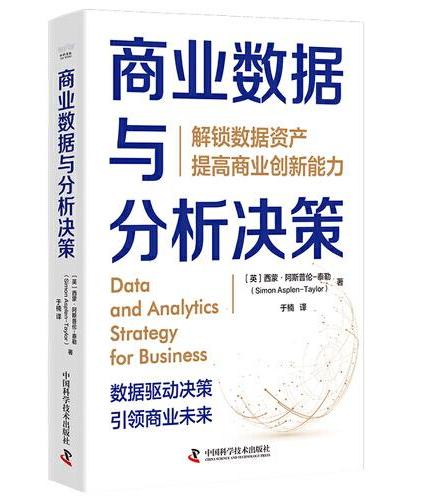
《
商业数据与分析决策:解锁数据资产,提高商业创新能力
》
售價:HK$
79.2

《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
售價:HK$
77.0

《
史学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一): 追踪谱系、轨迹与多样性
》
售價:HK$
104.5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HK$
118.8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HK$
217.8

《
东方小熊日本幼儿园思维训练 听力专注力(4册)
》
售價:HK$
88.0
|
| 編輯推薦: |
★ 知名媒体人伊险峰、杨樱首度出书,以两位工人子弟的阶层跃升,照见中国社会三十年沧桑巨变
“我们的大城市充满了废弃物,其中大多数是人。”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残酷真相。
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是什么决定了普通人的命运?一个家庭要如何维持尊严,如何避免成为“废弃物”?
★ 一个昨日世界,但你并不陌生:两个家庭、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
从闯关东到日本殖民,从苏联援建到社会主义建设,从国企改制到单位解体……百年间,东北经历了兴盛与阵痛;
高耸的坦克碑、风雨飘摇的单位、逼仄的工人小屋、终日奔波的母亲……计划经济重镇沈阳,承载着两位少年蕞初的人生。
两位作者将镜头对准学校、工厂与街巷;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重现过往;透过个人的命运流转,我们也得以窥见“共和国长子”遭遇的时代之困。
★ 近距离观察普通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浮沉与变迁,探寻当代人精神困境的社会根源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为什么精神却荒芜了?”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过山车般光怪陆离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作者携前述疑问,通过大量的采访
|
| 內容簡介: |
这部平民史诗的主题只是不要成为时代废弃物。
两个原生家庭,跨越三十年的奋斗,调动的能量,堪比战争。
张医生和王医生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家庭。在国企改制、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凭借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摆脱了掉队的命运,实现了阶层跃升。可是,虽然看起来功成名就,但他们的人生,仍充满了焦虑和疲惫。
两位作者采访数十人,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打捞过往生活图景,描摹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半生的个人成长与阶层跃升之路,并审视二人知识、尊严与自我的建构过程。与此同时,本书还以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为经纬,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东北。
阅读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故事,我们将会厘清,世纪之交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而透过个体在历史中的沉浮,我们也将窥见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
这本书的特别价值,在于以这两位医生的真实经历为线索,呈现了过去三十年令人叹息和沉默的民间社会史;更在于作者以知识人的认真态度和故事人的写作能力,描摹了上述问题的核心答案,即促使人们精神腐败的社会因素。
——作家、媒体人李海鹏
|
| 關於作者: |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2008年创办《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创办“好奇心日报”,也写东西。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
| 目錄:
|
序言“社会”与沈阳人的精神世界李海鹏
部分20世纪
章我们的主角
第二章走进奉天
第三章张家
第四章王家
第二部分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一
第五章王医生的高光时刻
第六章张医生的门诊
第三部分工人阶级子弟的成长
第七章“我们”和“他们”
第八章“社会”与奖学金男孩
第九章男性气概和它的消逝
第四部分家庭
第十章父亲的角色
第十一章母亲的社会
第五部分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二
第十二章王医生抓住了机会
第十三章“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座坟墓”
第六部分社会人
第十四章“熟人社会”
第十五章社会里的成功男人
第七部分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三
第十六章王医生的房子
第十七章张医生的爱情
第八部分知识,尊严和自我
第十八章缺失的人文
第十九章王医生重入社会
第二十章不能独自进晚餐
说明及感谢
|
| 內容試閱:
|
章 我们的主角
在万豪后面。
这家万豪在世纪交替那十几年里,一直是沈阳豪华的酒店。从桃仙机场进入沈阳,过了广阔的开发中的浑南区,还没到浑河大桥的时候,闪闪亮的金顶就已经招摇地在对岸路口翘首以待了。万豪对面是沈阳早的高级住宅区,河畔花园。1991年3月这家楼盘就在《沈阳日报》上打出广告:
中外合资 金牌工程
沈阳首座外商住宅区
时价三千多块钱一平方米,差不多是工薪阶层两年的工资。举凡有头有脸的人都应该在河畔置一套房产,大佬都住在那里,传说赵本山也是那里的住户。快三十年了,小区看起来老旧了很多,大佬们起起落落换了几茬,现在看起来衰落了不少,与对面金光灿灿的万豪不可同日而语。
往北一点点,有几个卖奢侈品的大商场。同样是千禧年前后,中国奢侈品的半壁江山号称都由东北人掌握的时候,它们都是中国零售业绩数得上的大店。现在店已不景气,但富人区的架子还在,餐馆高档而且洋气,豪华酒店还是依着惯性在这里扎堆开业。尽管与万豪的合作早就终止了,但它还是固执地叫自己万豪,大家也已经习惯于用万豪来指称它,并以它为地标。
王平医生在这里开了半天会,把我们约在万豪后面的一家日式海鲜火锅店里。我和他有五个月没有见面,在五个月之前有三十年没有见面。五个月前,我们都参加了毕业三十年的同学聚会。
这一天很紧凑。
上午,我们到了沈阳。天冷。离约定时间还早,就决定试试直接到陆军总院的机场大巴。在车上等了有一个小时,司机中间来过一次,拎了一桶热水放在驾驶位边上,又下去了。只剩下袅袅的热气和零星几个裹紧羽绒服的乘客。那趟大巴本来要开到龙之梦客运站,但走到陆军总院站人就全下去了。司机也意外,“你们都走了啊。”
下了车,发现陆军总院的名字改过了,现在叫“北部战区总医院”,人们还是习惯于叫它“陆总”,或者“总院”,过去它的全称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在楼下等了一会儿,通了电话,张医生穿始祖鸟羽绒服,从病房楼里出来。我们穿过整个总院,到另一个大门外的商场里找了家餐馆吃饭。
张医生和王医生都是我们的主角。
我们跟张医生解释了我们想做的事。大意是,我们想写一本书,事关一代人的阶层跃迁,想找几个专业人士为主人公,想来想去觉得你挺合适。
张医生,张晓刚,工人子弟,有一兄一妹。他考上第四军医大学(注: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后在三〇一医院(注: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念完了博士,如今是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
他认真地听,讲他关注的一些大事,比如中年人的翻盘机会。前半生不顺还好办,你看王平——就是王医生——刚工作时不顺,现在顺了;后半生不顺就比较麻烦,没有翻盘机会了。
他这不是拿自己当对照组。在之后一年多的数次谈话里,他从来没有不顺的任何暗示。
不过,那天他说,他应该做一些更烧脑的工作。
这不属于不顺的范畴。这是人生的大方向上的问题。
就像是深思熟虑过,他说,你这事我全力配合。说得很诚恳。
王医生在火锅店里表情严肃。
王平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主任秦浩比他大一岁,成立科室的时候挑中了王平来一起做事。王医生表示对名利很淡泊,但很在意一家名叫“好大夫”的网站上的评价。“全国二十万医生,请三百人到北京去开年会,有我一个”,“机票酒店都不用掏钱,怎么也得四星级,照顾得都很好”,“果断把双人间升级为单人间”。
王医生说现在爱忘事,眼睛花。吃饭时他突然到处找起了手机,想起这会儿应该有人给自己拿一台机器,但手机放在口袋里,振动听不见。
“你看,就是容易忘事。”
联系上了,但是他很不满意,一直埋怨送机器的人为什么不配个手提箱,七十来万的东西,就这么端着。
我们说,可能会有一些外围采访,没准会有一些说他不好的话。他想了想,很严肃地说,应该不会有他找来的人说他的坏话。他说他在原来的诊室不是一个合群的人——“做我自己的事”。
王医生看上去很板正。有问必答,答得尽心尽力,但是说到他觉得可以结束的时候,便戛然而止。讲家里的情况时是个例外。他的自我定位是一个大家庭的运转核心。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女儿,正准备考东北育才学校的高中。太太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与他同届,现在在一家有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工作。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妹妹还在二〇四那边住。妹夫在沈海热电厂。妹妹被他参谋着提前退休了,这样可以更好地照顾妈妈。
母亲这年肾上长了个肿瘤,全家人吓得不轻。“做了一夜陪护,想起小时候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张床上的日子,找到了感觉,这是家。”
王医生说,他由此意识到自己生活的重心在哪里、什么东西才是重要的。
又说到了他的女儿,青春期,经常指责他思想落后。
思想落后的前情提要是这样的。他爱他的女儿,觉得必须要安顿好她的前程,因此出国留学是考虑之一。没想到女儿激烈抗拒,认为这是不爱国的表现,这出乎王医生的预料,他本来只是考虑钱的事。“留学钱?那才几个钱。这么说吧,如果她觉得上海好,那至少得给买一套房子吧,一千万够不?”
房价是他主动发起的话题,在日后我们的聊天里,这个话题也仅仅有过一次变体:“在上海做啥工作赚钱算多?”
“房子得有。不能在这家工作不开心了,连职都不敢辞,成天担心自己交不起房租,委屈着自个儿迫不得已撅着屁股还得干下去。不能。”
“撅着屁股干”,是王医生经常说的词。他用来反问自己,质疑别人,包括我们。“你们撅着屁股干,累死累活的,说不是为了赚钱,那图啥?”
***
王平掏出一个硕大的钱包抢着付账。“请得起,到沈阳了你们得听我的。”
随后他抱着机器坐上出租车。他没有车,也不会开,在数九寒天也骑共享单车上班。“挺大一个公司,就不能给它弄个包。”他又重复了一遍。尽管我们早就想好了要写两个专业人士——医生的成长史,但我们还是准备得太不充分了,好长时间才适应,原来这机器就是手术刀。
一周以后,2018年年底,我们给张医生和王医生分头发了邮件。
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是值得记录的,也到了应该记录的时候。
总的来说,这是流动性强、人生积极、机遇完好,并且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阶层转换的一代人。
知识、专业性是决定因素,它超过了阶层和出身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相信进步带来的改变,也让这一代人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与此同时,这一代人还经历了旧企业衰落、社会剧烈转型、传统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瓦解与再造。在这一点上,沈阳和大东区都具有特别意义。
大东区除了经历大工业遗产和计划经济传统工人社区的起落之外,还有传统市民社会的转型(这是与铁西区不大一样的地方)。它包括了市民社会的瓦解和社会结构的解组。
从那天的采访开始,就不断地有人——特别是我的同学们狐疑地看着我们:写晓刚?啥?写王平?为什么写他们?这能行吗?他们不是名人。得写名人啊。马云。罗振宇。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记录有关个人成长的故事。
一个人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之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如何把握时机。
教育、家庭、学校、社会……为一个人的成长提供了什么支持。
希望为这一代人,在个人意义上和代际意义上获得更全面的评价以及赢得更多尊严。
通过个人的成长和变化,也能折射出家、家族、社区、城市的变化。
我猜想这些东西还是迷人的。作为他们的同学,我在与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亲戚一次又一次的聊天过程中,发现了更多一开始我们所忽略的东西。
在写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事儿与我们的关联度并不大,但它是一个以前未曾出现的现象,而且显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如果在音乐、小说、电影、电视中都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它对我们当然是一种启发。
有的时候,感觉我们正做的工作就像一部精神流浪汉小说一样,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两个人莽撞地闯进这个庞大的题材,试图顺着理清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我们的主人公在这四十余年中也在不断地寻找。
在那封邮件中,我们详细地列出了我们要进行对话的次数、要点和想要见到的人。
半年以后,我们终于接近了现在的想法——呈现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知识、尊严和自我的形成过程。这令我们变得有野心,而且愈发显得我们莽撞。我们的社会学训练,不论是对社会学的掌握,还是对社会学方法论的了解,都过于欠缺了。
但是这承平日久的一代,从贫穷中走出,从工人阶级转身为专业人士,在他们经历的这几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复杂而且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名词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完全变为另外的意义,“专业”“知识”“成功”“财富”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重新定义,“国企”“单位”“福利”“社区”等每一个词仿佛都换了内涵和外延……如果可以有一些机会审视并探讨个中的意义,无论如何都是极为诱人的。
在几十年间,张医生和王医生完成了知识获得,赢得了社会尊重,看起来功成名就。
在他们上升的同时,整个锈带地区在下降:东北经济的衰落、东北文化的妖魔化、东北人和“东北人”这个词的内涵的转变……这个社会发生的变化,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变化。
过去这些年,沈阳在中国的各项城市排名中不断下降,敏感一点的沈阳人都活在各种失落当中。这种失落有悲天悯人愁煞人之感,看到“024”这样一个电话区号都会触景生情,感慨起命运无常来——三位区号表示在电信业曾经发达的时段里沈阳作为“中心局”的地位,现在一些新贵城市当年可未必有这样的殊荣。因为三位区号或者“东北局大军区总部”之类的荣耀,沈阳原来还幻想过成为直辖市,直到现在心里还为争夺“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暗暗较劲。但是,一些跟增长有关的硬数字不留情面,沈阳还担了“数据打假”“挤水分”的名分,这个以往看上去手到擒来的中心地位现在也没有任何把握。这时候,连人口都成了个大问题:老龄化和人口外流——前者对张晓刚这样的医生来说倒不是什么坏事——以及前些年执行计划生育的坚定和听话,让沈阳的育龄人口比例不断降低;多年的城市化,也有人认为是东欧化,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虽然沈阳很早就想凑齐一千万人口,成为超大城市,但过了这么多年,人口只能勉强维持着增长,每年只有七八万,离大目标越来越远。
沈阳四十年的发展,前十年似乎是计划经济回光返照,那时感觉硬硬的底子都在,沈阳努力努力还可以争一争中国第四城、第五城的位置。接下来十年,完全被下岗这事打击懵了,一群掌握不了自身命运的省市领导,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大政方针转向——让一个计划经济堡垒城市失守而放弃,兵溃如山倒——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就这样任其发生:“你总得给我点解决政策吧?”结果等着等着,就等成了一直被各种人声称要挽救的对象。后二十年,靠着过紧日子挺过了贫穷,借着一些区位和贸易的优势,再加上全中国如出一辙的房地产拉动了消费,城市里还算得上富裕,但眼看着再也追不上别人,以前讲些“共和国长子”之类的陈年荣耀,现在泯然众人,发自内心地说起了自己的“宜居”——房价不贵,物价便宜,就连夜市小烧烤和鸡架都成了“网红”选题。
这几十年间,始终有两个社会交错进行:一个是张医生和王医生一点点试图融入的社会;另一个是曾经社会失序,城市景气不再,先是失落,而后负重前行的沈阳城。
过了好久,我们终于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一个出现在形形色色的对话、探讨、宣传和自我反省里的词有关:社会。这个词是如此变化多端,你可以说“这个人很社会”,也可以说“社会现在流行什么”,至于小孩,一旦做了什么事需要被说教,就会听到“等你进了社会”这样语重心长的预警。
而我们希望探讨的,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定义,不如说是一组动态的关系,关系的两端分别是“自我”和“社会”。对于张医生和王医生而言,他们所追逐的、他们背景中各个时间段里鲜明的标签、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都是形形色色社会的变体。
在此过程中,我们本来希望探讨“两位医生如何构建了自我”,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被修改成“他们这一代的自我真的完成了建构吗?成为父辈,成为中坚,成为了不起的权威教授,成为有担当的人,但他们在人生的刻度上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专业人士张晓刚和王平都曾经是一流好学生。一个只会学习的好学生是不懂得社会的——让我们换个直接的说法:一个书呆子如何在社会中立足?在粗粝的工人阶级文化中,他们与社会之间隔着一条又是怀疑又是嘲弄又是羡慕的鸿沟。“社会险恶”,几乎成为他们从小到大的梦魇。他们要摆脱那些不信任,害怕地、担心地一步一步走过,或者躲过,后成为一个社会人。
他们到现在也为这事焦虑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