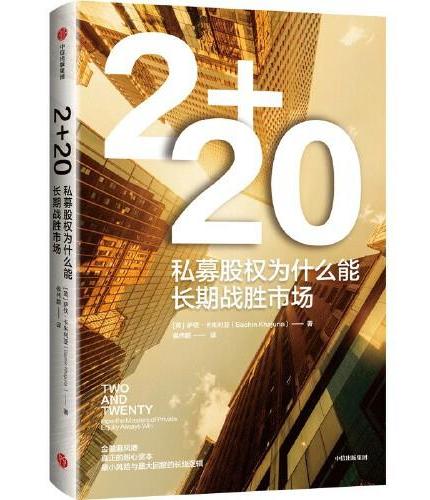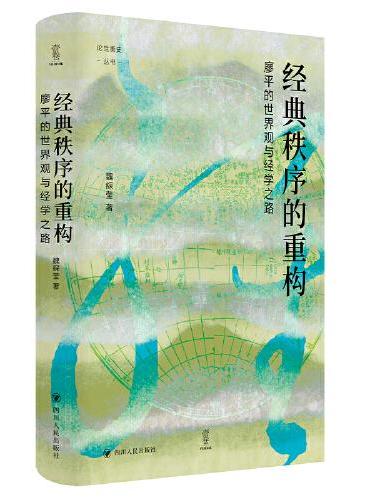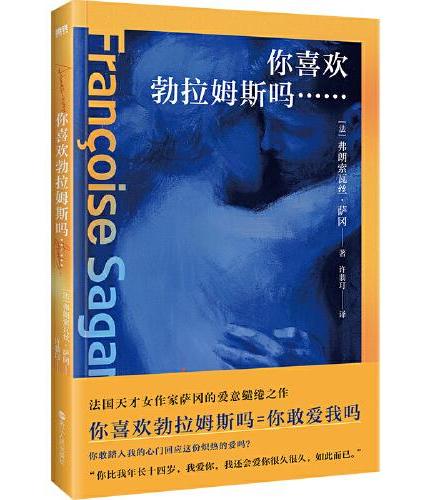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HK$
74.8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HK$
54.8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HK$
63.8

《
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看英国科普黄金时代的科学家如何担当科普主力,打造科学共识!)
》
售價:HK$
86.9

《
太极拳套路完全图解 陈氏56式 杨氏24式和普及48式 精编口袋版
》
售價:HK$
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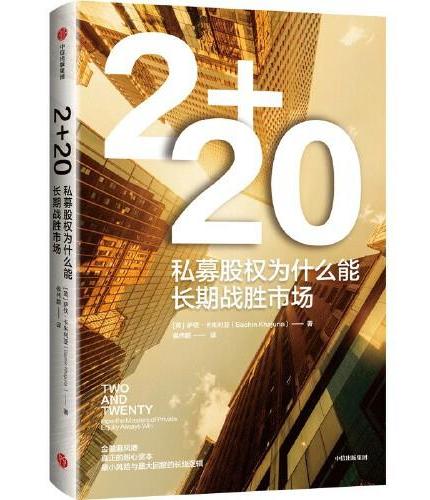
《
2+20:私募股权为什么能长期战胜市场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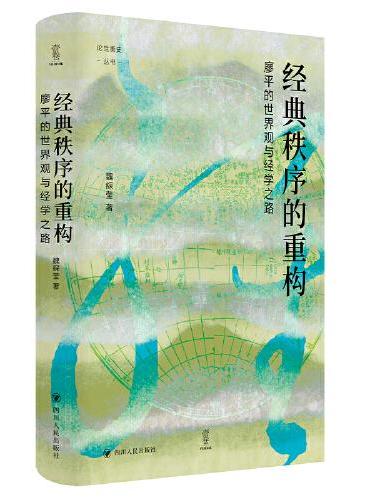
《
经典秩序的重构:廖平的世界观与经学之路(探究廖平经学思想,以新视角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西学冲击下的转型)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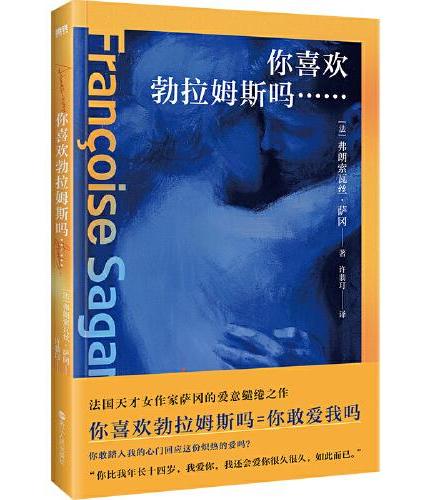
《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
售價:HK$
52.8
|
| 編輯推薦: |
?著名动物文学作家黑鹤代表力作集结出版
?著名作家、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作序
?入选IBBY(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书单的插画家九儿绘制封面美图
?新增作者序言、照片、“黑鹤动物文学小百科”等内容,提升阅读体验
?作品和作者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榕树下诗歌奖、《人民文学》年度作家奖、茅盾文学新人奖、“比安基国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十余种语言译介到国外,拥有涵盖儿童和成年人的广泛读者群
|
| 內容簡介: |
丛书代序?对黑鹤动物小说的解读① 曹文轩
黑鹤是一个独特的作家,在儿童文学领域,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家。他的写作,与流行写作、世俗写作是偏离的。他有他的自然观,他有他的文学观。就像对于我们而言雪原、草地离我们非常遥远一样,他的写作,与我们一般的写作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他似乎很喜欢这种距离。远离人群,远离大众化的文学书写潮流,是他内心的强烈欲望。安静,是他生存方式的,也是他文学方式的。
他曾这样描绘过他对森林和草地的感受:
“在森林和草地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安静。这次从山上回来,我这样向朋友们解释那种安静:在山上,我只要一转头,左耳上的两枚耳环相碰会发出轰然巨响。”
这种安静,于他而言,是一种境界,一种美学。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无数次地看到了他对安静的诗化性体会与描绘。
远离而带来的偏离,成就了黑鹤。
|
| 關於作者: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中国当代自然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庆油田作协名誉主席。
与两头乳白色蒙古牧羊犬相伴,在草原与乡村的接合部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居呼伦贝尔草原,拥有自己的营地,饲养蒙古马群和大型猛犬,致力于蒙古牧羊犬和蒙古猎犬的优化繁育,将幼犬无偿赠送给草原牧民。
出版有长篇小说《黑狗哈拉诺亥》《黑焰》《血驹》,中短篇小说集《狼獾河》《狼谷的孩子》《黄昏夜鹰》《驯鹿之国》等,长篇开放式散文集《蒙古牧羊犬——王者的血脉》《生命的季节——黑鹤二十四节气自然观察笔记》等多部作品。
|
| 目錄:
|
狼谷的孩子?
琴姆且?
斑斓?
从狼谷来?
獾? ?
克尔伦之狐? ?
冰层之下
|
| 內容試閱:
|
1.冬——每一片雪花
推开厚重的毡帘,弯腰钻出毡包,那日苏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那是一种实在得似乎拥有质感一样的冰冷。
只这一口冷气,他就被寒气呛住了,喘不过气来,他感觉自己的肺都冻住了。
他尝试着咳嗽两声,向卧着的羊群走去。
天刚刚亮,淡蓝色的晨光带着冰块般料峭的严寒包裹着这个早晨。
这是初春的早晨,几乎是草地最冷的时候。
他像往常一样清点着羊群,抬头看到巴努盖①[① 巴努盖:蒙古语音译,熊之意。
]卧在距离毡包不远的一个雪堆上,慢条斯理地舔舐着自己的后腿。
那日苏以为它只是在昨天晚上驱赶狼群时受了轻伤,没当回事。
他在羊群中转了一圈,数过之后,他松了口气——羊的数量没有少。他又穿过羊群,在羊呼出的热气腾腾的雾气中,他大略地打量了一下所有的羊。羊的身上没有被咬伤撕裂的伤口,看来,昨天晚上,牧羊犬①[① 牧羊犬:内蒙古草原牧区大型原生犬种,在蒙古国也有分布。体硕毛长、体格健壮、性情凶猛,主要用于牧区营地护卫、放牧牛羊。
]整夜的咆哮与撕咬还是起到了作用,饥饿的狼群没有侵进羊群里。
羊群边的雪地上,被践踏得一片狼藉,有些地方像被犁过一样,露出雪层下稀薄的草地。周围的雪地上满是爪印,有些是牧羊犬的,更多的应该是狼的。那日苏注意到今年冬天狼的爪印特别大,显然,这些狼似乎不是狼谷里的本地品种,似乎是从蒙古国那边翻越边境过来的。
随后,那日苏从羊群的另一侧绕过,从巴努盖的身边走过,顺便扫了它一眼。突然,他感觉巴努盖的脸上少了点儿什么。
他再仔细看,发现巴努盖的左眼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幽深的空洞,从这个伤口里倒是没有多少血流出来。
他俯下身,捧住巴努盖的头,仔细地查看了一下伤口。
它的整颗眼球都被掏掉了,非常彻底,甚至连视神经也被扯断了,没有什么残留。
这样挺好,伤口更容易愈合。
巴努盖的腿上还有几处轻伤,对于它来说,那算不了什么了。
它见得太多了,它的身上都是与狼争斗时受伤又愈合后留下的伤疤,头脸和身上这些纵横交错的伤疤上面都生了灰色的毛,使它看起来更显得凶悍。
他轻轻地按了按巴努盖眼眶周围已经冻成冰碴儿的血块,想估计伤口的程度,但巴努盖从宽厚的胸腔中发出浑厚的低吼。那是爆破般吠叫的前奏,随后,它会用自己的利齿在那日苏的身上留下恰到好处的齿痕,以示对侵犯自己的人类的惩罚。除了扎布,这世界上好像没有它不咬的人。
那日苏轻轻咒骂一声,放开它的头。但即使如此,他的动作也尽量小心,不想让它的头受到震动。
他向毡包里走过去时,卧在毡包边的两头刚刚一岁的小狗慢慢地站了起来,它们厚重的皮毛上挂满了白霜。
它们受的伤看起来似乎更重一些,那头被那日苏叫作白雪的纯白色牧羊犬身上的毛几乎都被血浸过,变成粉红色的;黑色牧羊犬丹克①[① 丹克:蒙古语音译,茶壶之意。
]的嘴肿胀得几乎有原来的一倍还大,它本来小时候长得就壮,所以那日苏给它取了丹克这名字,此时这肿大的嘴使它看起来更像一头熊。
两头狗少了往日见到他时的活泼,它们显得异常安静,似乎昨天那个狂乱的夜晚让它们身体里的某些东西永远地消逝了,它们不再是小狗了。
此时,它们的身体上笼罩着拆迁后的房屋般颓败而荒寒的表情。
走近了,那日苏注意到白雪身上只是小伤口流出的血染红的,伤得并不重,倒是丹克伤得更重一些,腿上有一些贯穿的伤口,尽管先前流出的血已经结冰,但仍然有新的血流出来。
寒冷减缓了血流的速度。
它的鼻子也豁了。
从冬天到现在经历了数次狼群的侵袭,这一次营地里的牧羊犬遭到最沉重的打击。
钻进毡包里,羊粪燃起的炉火升腾的热气扑面而来。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寒气似乎缓慢而坚决地从全身的每个毛孔里渗透出来,那日苏不禁打了个哆嗦。
正坐在炉火前修理鞍子的扎布抬起头,显然是注意到了那日苏的动作。
“冷,外面很冷。”那日苏回答。
尽管扎布什么也没有问,但他知道扎布那探究的目光是想问什么。
他不需要说话,只要目光就足够了。
那日苏坐在火炉前,伸出双手烤着火,炉火执拗地驱赶着他体内近乎凝固的寒冷。
修补这个镶有银饰的古老的鞍子,几乎是他每天早晨的例行公事,当然,也更像一种富有仪式感的东西。
扎布终于完成了他的工作。最后,他用一块发黑的皮子在银饰上擦了几下,算是完成了。
“巴努盖没了一只眼睛,”那日苏还想具体说一下是哪一只眼睛,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到底是哪只,只好告诉扎布,“另外两只狗也受了伤。”
扎布刚开始似乎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随后抬起了头。在从毡包顶泄下的微弱的光线下,那日苏感觉他脸上的每一道黑色的皱纹似乎是从他降生时就刻在那里的。
他没有再说什么。
天更亮一些,那日苏骑马赶着羊群离开营地时,看到扎布正用一块黄油①[① 黄油:新挤牛奶静置一夜,第二天将上面凝结的油皮撇下,即为奶皮子。将奶皮子熬制,即得黄油。
]小心地涂抹着巴努盖那空洞的眼眶,那鬼怪般的狗竟然顺从地任由扎布处理自己的伤口。
所有的人都知道,那狗,除了扎布,谁也抓不着。
并没有过多长时间,仅仅四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又一群狼冲进了营地的羊群。
整个夜晚,白雪和丹克都不安地对着地平线吠叫。它们知道那里有什么,不过,那些饥饿的野兽仅仅是远远地观望,它们不会轻易地发动攻击。
它们很有耐心地等待着,直到营地里的牧羊人和牧羊犬都对这种等待感到厌倦,失去耐心时,它们才会发起进攻。
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那些野兽呼朋唤友般地互相打着招呼,那高亢的嗥叫顺着谷底直上云霄,回荡在冰封千里的草原之上。千万年来,它们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经历过漫山遍野的黄羊②[② 黄羊:即鹅喉羚,隶属于偶蹄目牛科。背部毛色较浅,呈淡黄褐色。胸部、腹部和四肢内侧都呈白色,冬天的毛色更浅。
]群呼啸而过的黄金般的日子,也曾在草原围捕的洪流中落荒而逃,一直逃出国境线,进入蒙古国。
整个冬天,不止一个狼群会回到这片谷地,这是它们祖先的游猎之地。
狼嗥,是冬日草原夜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冬天的夜晚,一声遥远的嗥叫像一团从地平线后面升起的小小的火苗,微弱但清晰,很快,更多的火苗此起彼伏地燃起。当然,当这些火苗集聚在一起,并且为相互间默契的应和而沾沾自喜时,营地里的牧羊犬就开始不安了。它们略显惊恐却也颇为期待地咆哮着,围护着紧紧挤在一起的羊群,它们整夜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那日苏倒是不能想象没有狼嗥的夜晚。
在温暖的毡包里,扎布和那日苏都很清楚,只要巴努盖不发出声音,那么无论白雪和丹克叫得多么紧迫,所谓的狼群来袭也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终于,直至凌晨时分,在白雪和丹克略显疲惫的呜呜咽咽的叫声中,传出如闷雷般撼人的一声吠叫。
那吠叫声听似并不响亮,但那日苏隔着毡壁却感到自己的鼓膜被震得嗡嗡作响。
这种浑厚的吠叫声可以轻易地在空旷的草原上传到数里之外。果然,随着这一声吠叫,那些此起彼伏的狼嗥声顿时戛然而止,四野一片寂静。
根据这声穿透力极强的吠叫判断,那些对营地中的羊觊觎已久的狼群突然发现,在这营地还有另一头牧羊犬,与那两头不知轻重胡叫乱嚎的小狗显然不是一样货色。整个夜晚它都不曾发出一点儿声音,沉稳地卧在营地里,直到它们准备开始真正的袭击时,才恰到好处地狂吠一声,以示警告。
这是一头很有经验也很难缠的老狗。
但是仅此而已,饥饿的力量比一头难缠的老狗更可怕。它们决定进攻了,即使此时营地里有一门大炮在等待着它们,它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冲进来。现在它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盼着尽快冲进羊群,寻找羊肉抚慰饥饿的肚腹。
那日苏和扎布拎着枪冲出去的时候,外面一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扎布冲着天空放了一枪,伴着火光,爆裂的巨响让那日苏感觉似乎周围的空气都让这枪声吸空了。枪声的余韵像巨人远去的脚步声一样,越来越远。
那日苏举起了火把。
羊群死死地挤成了一团。
在羊群前面,巴努盖身下压着一头野兽,正狂暴地甩动着头颅。
等他们跑到跟前时,巴努盖身下的野兽正发出痛苦的呻吟,像小孩子一样的抽咽声。
巴努盖已经解决了一切。那头狼的喉管已经被撕开了,那日苏只听到像水中冒出的气泡般的噗噗声。
白雪和丹克正绕着羊群在奔跑,吠叫声中带着兴奋的颤音。显然,在羊群里还有狼没有逃走,藏在羊群的中间。
胆怯的羊在面对恐惧时唯一的办法就是紧紧地挤在一起,以无限地向身边的同伴靠近来消解自己的恐惧。
有时候,狼挤进羊群里寻找最肥美的羊只时,也会因为被挤得太紧而寸步难行。现在,就有狼被困在里面。
那日苏用力地挥舞着蘸满煤油的火把,冲着挤成一团的羊群发出像野兽一样粗鲁的号叫。
终于,在对火和人类的恐惧的双重压榨之下,两头狼一前一后地从羊群的正中间挤了出来,连蹦带跳,趔趔趄趄地踩踏着羊的背脊跳了出来。
这个冬天,看来这些狼的日子并不好过,它们瘦得似乎只剩下一副皮毛裹着的骨架,几乎是轻轻地从羊群上飘了过去。
它们落地之后,就以惊人的速度向黑暗中跑去了。
扎布的枪响之后,前面的那头高速奔跑的狼被来自它身后的更大的力狠狠地向前推去,一头扎在雪中,再没有起身。
扎布没有开第二枪。白雪和丹克已经追过去了,再开枪他怕伤了狗。
那日苏摇晃着火把高声呼唤着追进黑暗之中的白雪和丹克。
黑暗之中,是狼族的世界,在那里,狗永远不是狼的对手。
那是草原上的牧羊犬必须学习的一课,它们一旦追得太远,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还好,它们很快就跑回来了。
在这次对抗中,它们能够存活下来,就获得了宝贵的经验。越来越多的经验积累,就会让它们成为真正的牧羊犬。
火把已经快要熄灭了,那日苏回头看时,发现扎布正蹲在巴努盖身边,查看什么。
那日苏这才意识到,刚才在两头狼奔出羊群时,巴努盖竟然没有跟随过去。在这种时候,它向来是领着两头牧羊犬冲在前面的。
那日苏走过去,借着将要熄灭的火把闪烁的微光,看到扎布正掰着巴努盖的头。它右脸颊新增了一条伤口,血已经被冻得凝固,像它脸上一块赤红色的铠甲。这种伤没有什么,但是,他注意到,在伤口的上端,垂挂着像血块一样的什么东西,再仔细看,那是巴努盖已经松脱的眼球。
巴努盖一动不动地蹲坐在原地。
扎布试着抱起巴努盖,呻吟着试了几次都不成功,巴努盖对于扎布来说太沉重了。
最后,毫无办法的他站了起来,用手拎住巴努盖颈部的皮,扯着它向毡包走去。
巴努盖犹豫着,试着走了一步,显然还不适应这种行走,甚至发出略显惊恐的低嗥。
扎布呵斥一声,拖着它继续向前走,就这样将它跌跌撞撞地弄进了毡包。
那日苏拎着枪跟进毡包时,扎布正借着蜡烛微弱的光线试着将巴努盖脱落的眼球复位。在寒冷的天气里,只是暴露在空气中那么短短的一刻,眼球已经冻得像冰块一样了,根本无法放回到眼眶中去。
忙乱的扎布低声地咒骂着。
那日苏困得厉害,重新缩回到自己的被子里。很快,当炉火的温暖驱散了身上的寒气之后,他就睡着了。
那日苏在睡梦中偶尔惊醒,翻身时看到扎布还在忙碌,将白酒倒在刀上,正在火上燎烤。刀子上面的高度白酒燃烧起来,于是这把锈蚀丑陋的刀似乎在一瞬间拥有了新的生命,它被美丽的青色火焰所包围,在扎布的手中翻滚着,此时它是一把拥有了魔力的刀。
那日苏很快又睡着了,在进入睡梦的最深处时,似乎听到一声被憋进胸腔中的压抑的咆哮。
在那个夜晚,巴努盖失去了另一只眼睛。
在早晨,扎布给两头狼剥皮时,那日苏注意到这两头狼的毛色比当地的狼颜色更深一些。显然,它们是从边境的那一边过来的。
失去了双眼的巴努盖蹲坐在毡包的门前,似乎一直在向远方的地平线处观望。整整两天它几乎没吃什么,对扎布放在它面前的食物偶尔闻一闻,但没有碰一下。
那日苏以为它身上还有其他的部位受伤了,但是当丹克凑到它的食盆边偷食物时,巴努盖咆哮了一声,狠狠地咬向丹克的腰腹,丹克哀鸣着跑开了。
那群狼很快又一次来袭击营地了。
那日苏持着火把冲出去时,牧羊犬和狼在羊群前已经混战成一团。这一次,狼群连进攻前的试探都取消了。
扎布怕伤到与狼纠缠在一起的牧羊犬,仅仅是向空中放了一枪。
那咕咚的一声巨响,也许是距离那日苏太近了,他感觉自己脚下的大地都在震颤着,眼前所有的景象都在摇晃。
在一片动荡的景象中,在火把投出的光线中,被枪声吓得从一片混乱中跑走的,一共是四头狼。它们的毛色像是一种青色上有墨汁洇开般更深的颜色。
最后跑开的那头狼大得出奇。因为它们拥有与黑夜更加接近的颜色,几乎在一瞬间就消失在黑夜之中了。
这时,那日苏才注意到,其实白雪和丹克一直都是在这咬成一团的战场外面助势,它们并不在里面。
雪地上还剩下两头动物,瘫躺在那里,而那雪地上一簇簇发黑的斑块,应该是血。
扎布端着上了膛的枪慢慢地走过去。
随后,他就将枪放在一边,蹲了下去。
那日苏努力举着火把为扎布照亮,尽量不投下阴影。
两头动物是一头狼和巴努盖。
那日苏还勉强可以辨认出那是巴努盖。
但仅仅是勉强,它身上的皮被大片地揭开,一条后腿显然已经被咬断,耷拉着,脖子几乎被撕烂了,而致命的伤是腹部那道可怕的创口,腹部被自上而下地整个撕开了,几乎所有的内脏都流淌出来。
而被巴努盖压在身下的那头大狼,被巴努盖咬住了咽喉,早就窒息了。
那日苏无法想象没有视力的巴努盖是怎样迎击这些狼的,大概是跌跌撞撞地循着气味冲过去,一口咬住那头狼之后就再也没有松过口,任由其他的狼在自己的身上蹂躏,撕出巨大的伤口。
巴努盖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但仍然死死地咬着那狼的咽喉。
扎布试着慢慢地掰开巴努盖的嘴,但毫无意义,似乎已经锁死了。
终于分开之后,从巴努盖的口中发出像古老的门扇打开时的咯吱声。
巴努盖刚刚松开嘴,白雪和丹克就咆哮着扑向那头已经死去的狼,狠狠地撕咬着。
随着它们的扯动,那日苏注意到,那狼的颈骨已经断裂,而整个脖子几乎都被巴努盖咬断了,只剩后颈还有一些肉连接着。
内脏摊淌了一地的巴努盖根本没有办法直接挪动。最后,那日苏找了一条皮褥子,和扎布一起将巴努盖抬起,放在褥子上。一起放在上面的,还有巴努盖已经被冻硬的内脏。
两个人将褥子拖进了毡包。
整个夜晚,扎布用酒洗了手之后,将巴努盖脱出的内脏填回到肚腹中,又用大号的钢针将伤口缝合。
巴努盖身上的伤口太多了。当扎布终于将它身上那些大块的伤口缝合好的时候,巴努盖看起来更像一头被重新拼凑起来的狗。
在整个缝合的过程中,巴努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那日苏不时地摸摸它的脖颈,感受到动脉缓慢地律动,以确定它还活着。
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巴努盖的眼睛偶尔会眨动一下。
天快亮的时候,扎布终于缝合了最后一道伤口。他呻吟着扶着腰站了起来,整个夜晚他俯身太久了。
扎布拿起酒瓶喝了一口,然后用破布擦了擦手,就歪倒在褥子上睡着了。
昏睡中的那日苏听到了什么响动,睁开眼睛,在毡包顶透进的微弱的晨光中,巴努盖竟然已经站了起来。
他一阵欣喜,轻轻地唤了一声。
但巴努盖对那日苏的呼唤毫无反应。
它仅仅是站在那里,但似乎有些东西失去了,好像在它被重新组装的过程中,它已经忘记了很多事。
也许是因为身上的毛都被血浸湿了,它显得小了很多。
它的身体僵硬如木头,腿几乎是僵直地移动,慢慢地向前。它在试探着,但它知道背对着位于毡房中间炽热的火炉,然而它选错了方向。当它的鼻子碰到了哈纳①[① 哈纳:即蒙古包围壁的木架,以榆、柳或杨木制成。
]时,它停了下来,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用鼻子探索着哈纳,沿着哈纳的弧形慢慢地移动。
它太累了,每移动一步,似乎都要思考很久,是否还要迈出下一步。
每一步都耗费了它所有的力气,需要积聚很久的时间才能挪出下一步。
终于,它挪到了毡包的门口,将鼻子探出毡帘后,它的身体轻轻地抽搐了一下。
那日苏正想阻止它离开毡包——现在出去很容易冻伤刚刚缝合的伤口,听到扎布用鼻子发出一个制止的声音。
原来他也醒了。
就这样,巴努盖用鼻子挑开了毡帘,钻出了毡包。
一抹青色的晨光将它笼罩其中,随后,毡帘在它的身后合拢,毡包重又归入昏暗之中。
天大亮时,那日苏出了毡房。
丹克和白雪卧在毡包前舔舐自己身上的那些细小的伤口,看到他,起了身,摇了摇尾巴,算是打招呼。但是,它们看到那日苏循着巴努盖留下的爪印往草地里走,并没有跟过来。
其实,巴努盖也没有走出多远,它的爪印几乎一直在雪地上拖行。
它卧在毡包东南一个舒缓的雪坡上,头冲着营地的方向,毛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就那样冻硬了。那日苏试着将它抱起来扛回到营地里去,但它身上流出的血已经将它紧紧地冻在地面上,结实得像被焊在那里一样。
那日苏走回营地时,扎布正在剥那头狼的皮。
那日苏从他身边走过时,他并没有抬头。
已经冻硬的狼,应该放在毡包里暖一暖,否则皮根本就剥不下来。
寒冷的风吹得那日苏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听得见走在前面的扎布一样在喘息,呼出的热气一瞬间就被风吹走了。
齐膝深的雪,每一次落脚,都要等上一会儿才能拔出来,再踏出下一步。
他们在谷底下了马,剩下的路就得靠自己走了。
他们走都很费力,但扎布还扛着巴努盖,更显得艰难。
那日苏想跟上去帮帮忙,但他下马时慢了几步,所以,一直爬到山顶,他也没有跟上。
山顶的风更大,山的另一面是更加空荡无边的草原。风吹起雪花打在脸上,那日苏感觉自己的脸早已经麻木,不再属于自己了。
天很冷,但到底有多冷,那日苏不知道。
山顶也许是因为总是有风掠过,将积雪带走,所以还裸露着一些石头。
扎布喘息着将肩上的巴努盖放下的时候,巴努盖与地面的石头相碰,竟然发出钢铁与石头相碰般坚硬的声音。
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它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了。
扎布双手扶着腰在那里喘息,胡子和睫毛上都结着霜。
那日苏站在扎布身边,背对着风,感觉自己终于可以喘过气来。
他的脸已经没有感觉了。
扎布随后蹲下,抽出腰间的刀,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切下了巴努盖的尾巴。那日苏感觉巴努盖的尾巴短得有些不可思议,此时他才想起来,巴努盖的尾巴在一次与狼的争斗中被咬断过。那时,自己还没有降生呢。
扎布将巴努盖的尾巴放在它的头下,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取出一小块黄油。
他本来想试着将黄油抹在巴努盖的嘴唇上,但黄油已经冻硬了,他索性就轻轻地掰开它已经冻硬的嘴,将黄油放在它的嘴里。
仅仅这几个简单的动作,那日苏注意到扎布的手已经变成了另一种颜色。做完这些,扎布就将手掖进了袍襟里。
他站起来后想了想,似乎在判断方位,随后又蹲下将巴努盖的头调整了一下方向,重新将尾巴在它的头下放好。
那日苏不知道巴努盖的头到底冲着什么方向,但似乎是冲着风的。
他们下山。
远处,拴在谷底的两匹马已经变成白色了。
风卷过空荡无边的草原,他们骑着马回营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