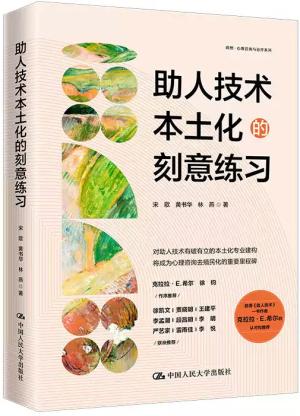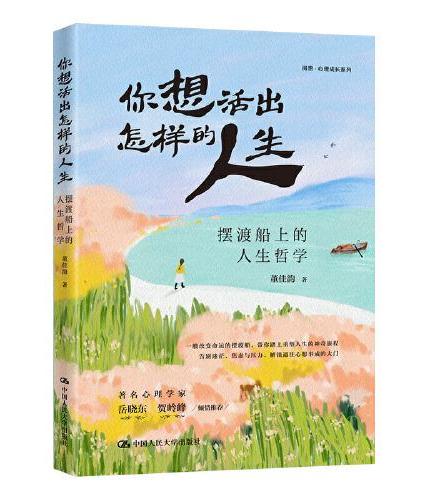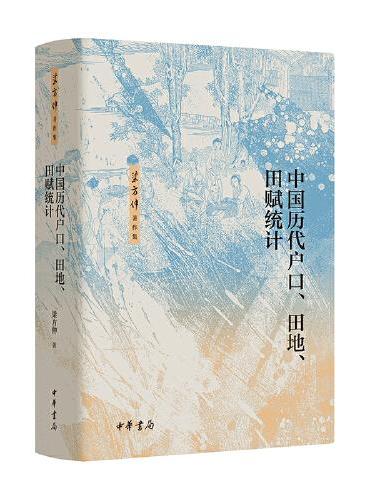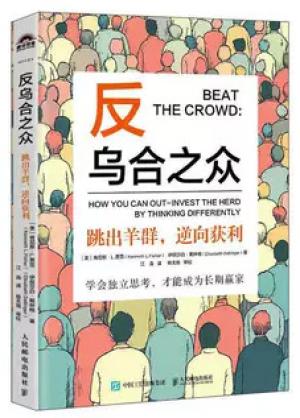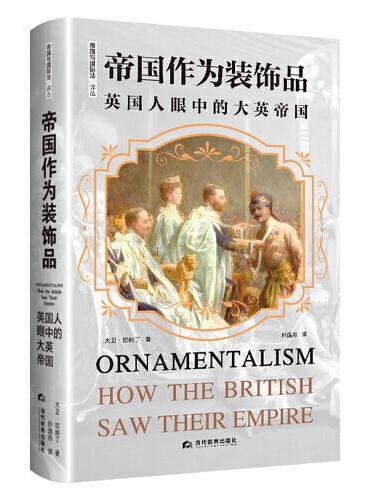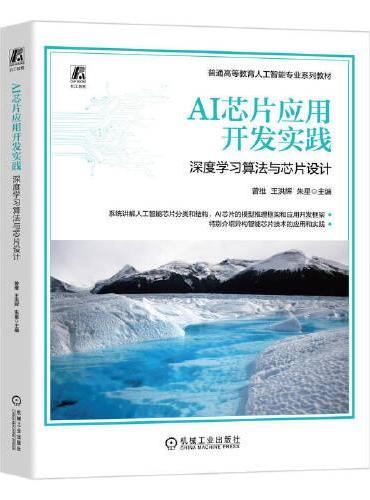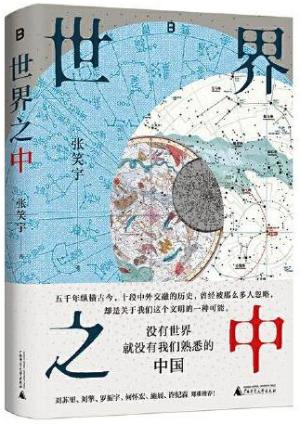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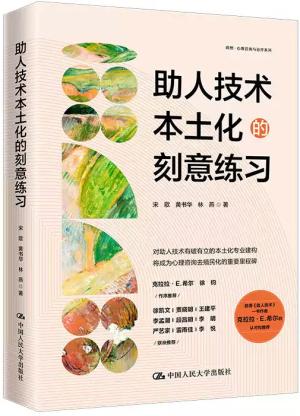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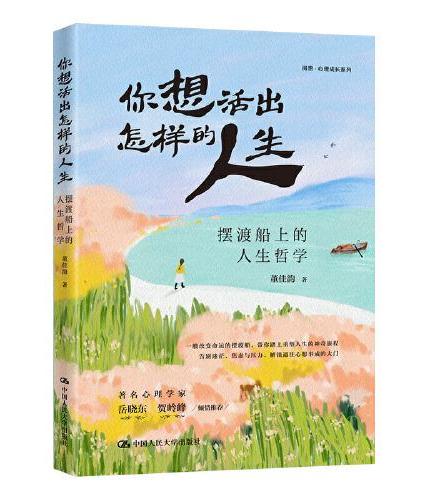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HK$
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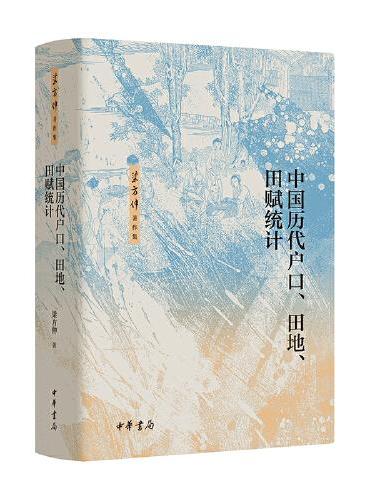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HK$
1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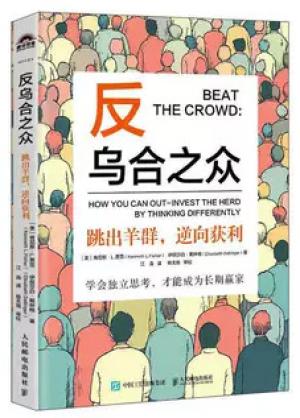
《
反乌合之众——跳出羊群,逆向获利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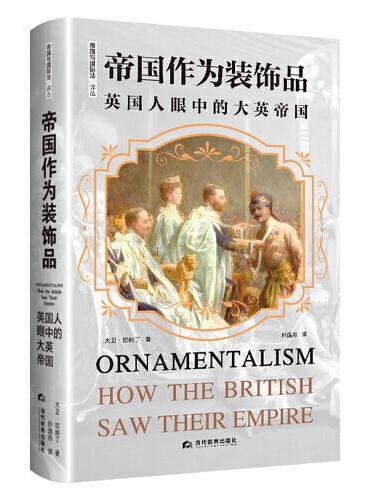
《
帝国作为装饰品:英国人眼中的大英帝国(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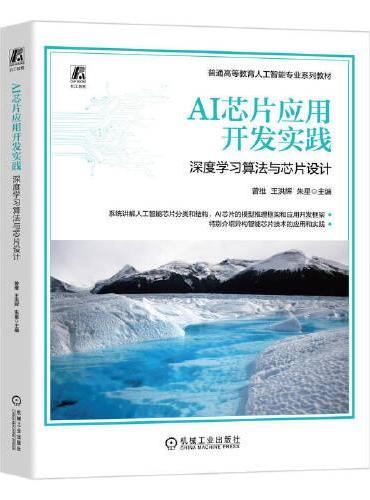
《
AI芯片应用开发实践:深度学习算法与芯片设计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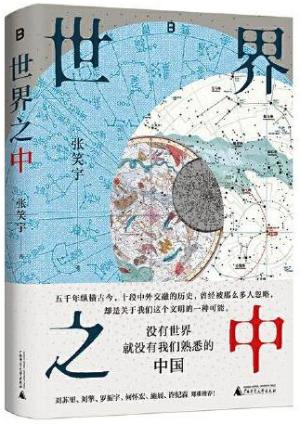
《
世界之中(文明三部曲之后,亚洲图书奖得主张笑宇充满想象力的重磅新作)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这是一部诗学随笔与诗学研究相互融合的作品。纯粹的诗学随笔容易流于随意和散乱,纯粹的诗学研究又显得过分高深和严肃,本书既有诗学随笔的亲切自然,亦不失学术研究的底蕴和严谨。它纵深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史,高屋建瓴地审视诗歌文化中的众多重要命题,梳理诗学脉络,致力于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一个古今互通互鉴的诗学样本。
1.本书内容上兼顾古典诗学和现当代诗学,将两者汇铸一炉进行锤炼和提纯,对古今诗学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和现象,做了纵深的探究,展现了作者四十年来在诗学这座迷宫里的不懈探索,以及如象罔求珠般对诗歌真谛的孜孜追求。
2.向以鲜作为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古典诗学探究中游刃有余,举例丰富,论述有条;作为当代诗人,他随着当代诗歌一同走来,亲历着诗坛潮流,论述中如数家珍,又以自身为引子,延伸出众多诗坛现象和人事。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四川大学教授、诗人向以鲜四十年间的古今诗学随笔选粹,全书分为两卷:上卷“迷宫”,讨论古典诗歌,将浩瀚的中国古典诗歌及诗学喻为一座瑰丽神奇的迷宫,里面遍布七宝楼台和暗道,如何从迷宫中获取无尽宝藏并成功走出迷宫,是所有中国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下卷“玄珠”,讨论的则是现当代诗歌,取意于《庄子》的象罔求珠传说,如何像象罔一样找到诗歌的真谛,也是每一个当代诗人想要回答的问题。全书内容涉及中国古典诗歌与现当代诗歌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试图从纷繁的诗歌史和诗歌现象中,梳理出一条来龙去脉。
|
| 關於作者: |
|
向以鲜,诗人,随笔作家,四川大学教授。著有学术专著《超越江湖的诗人——后村研究》《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诗集“我的三部曲”及“旋律三部曲”,以及长篇历史剧《花木兰传奇》等。20世纪80年代与同人先后创立《红旗》《王朝》《天籁》《象罔》等民间诗刊。
|
| 目錄:
|
上卷 迷宫
003 释“彩翠”
008 时间之诗
017 别离的笙箫
027 乡愁或唐诗
034 当杜甫遇见成都
050 宋词一啸
062 美人幻影
072 逃不开的花朵
084 焚稿的冲动
093 琼岛椰谭
099 山居闲笔
106 卧云书院
113 与其垂钓不如叩舷
127 截句断议
134 怀乡的胃
142 玻璃或影子秘史
156 我者与他者
164 溪山有多远
182 蝴蝶与奔马
下卷 玄珠
193 理想主义的夏天
202 锦江先锋精神
216 缓慢
232 神秘的陶罐
249 墨马发微
255 头发的故事
263 隐喻与超越
272 打动我的三片落叶
277 童谣里的秘密
286 圣人有几张面孔
296 烟云、革命、数学与诗歌
302 “动荡”的时间简史
312 口语诗的真相
323 火车或诗歌札记
340 我、海子和德令哈
345 星辰与大海札记
354 聂家岩在哪里
360 整体性、音乐性及物性论
370 我的书房生活
377 诗匠
|
| 內容試閱:
|
引子:
迷宫与玄珠
迷宫
哈姆雷特:啊,上帝!我可以关在一个核桃壳里,自以为是无限的土地之王。
一阵微风把残损的烛光吹灭了,什么也看不见,彻底的黑暗是多么令人迷恋啊。
我想到了一座奇异的迷宫。一座既光亮又晦暗的宫殿,其建造材料主要是古老的语言,当然,可能还有梦或星光。如果说诗人有什么异于常人的话,那就在于,诗人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可以穿越这座迷宫:既是迷宫的囚徒,也是迷宫的缔造者。
瞽者说:一个神,只应该说一句话,而这句话是完整的。它的声音不能低于宇宙,或者少于宇宙的总和。这个声音等于语言,或者可以理解为语言。它的影子或者幻影,就是人类野心勃勃的声音:全部、世界、宇宙。
一道语言的光穿越了时间、死亡和爱。
所有的诗人都将为此耗尽生命。
这儿闪闪烁烁,千变万化,它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甚至以某种方式囊括了星辰。
诗人与语言之间所形成的暧昧关系是令人费解的,语言的阴影随时笼罩着可怜又幸运的人。
保罗·瓦雷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如果有人说“我向你借一个火”或“你给我一个火”,这意思是很明白的,这句话对普通人而言,只是一句交流用语。你问我借一个火的时候,你说那几个不重要的词语时是用我们所理解的某一种语调、某一个声音、某一种曲折变化和某一种倦怠或活泼的神情。我明白你说的话,因此,我甚至想都不想,就递给你你所要的东西——一个火。但是倘若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我一直想起你这个短小的句子的声音和它的特征,它在我心中发出回音,仿佛它很愿意待在那里;我也很愿意听自己重复讲这句话。这句话已经失去它的意义,已经不再有用处,然而却可以继续存在下去,显然它此刻已经获得另外一种生命,它创造了被再听的需要。
在这里,我们跨过了诗的门槛。
这就是诗人与常人的区别所在,因此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语言的直觉而不是生活的体验。
诗人永远张开着一张虚无的网,等待着语言的昆虫扑来。
或者反过来说:诗人就是昆虫,语言就是网。
《百道梵书》:词语乃不灭之物,天道之长子,《吠陀》之母,神界之脐。
迷宫是多义的,也可能是悠久的传统(语言就是承载传统的一道河床),里面布满了七宝楼台和暗道。
玄珠
黄帝北游,在昆仑之巅失落玄珠——那颗黑色或玄秘的珠子,后来被象罔找到了。
诗人的玄珠其实就是诗歌的真谛,而象罔可能就是一个充满玄学意味的诗人?
当史蒂文斯把一只神奇的坛子置放于田纳西州的山野,群山排闼而来时,诗歌的意义猝然显现。有人说:在大海的黑夜里,穿梭的游鱼就是闪电;在森林的黑夜里,翻飞的鸟儿就是闪电。而我要告诉你的是:在昏暗的生命里,诗歌就是闪电。
当我们抬头仰望一轮明月时,我们会想到什么呢?亚历山大·冯·洪堡认为,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月亮”这个词语,虽然指称同一个对象,但并不表示相同的意义:希腊语的月亮是指月亮的“衡量”时间的功能;而拉丁语的月亮则是指月亮的清澄或明亮的状况。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生活在自己的语言和传统的月光里。
有人问我:如果你用一种东西来象征自己的诗歌,会是什么?我告诉他:水中的刀锋。是的,水中的刀锋,静静地存在于清澈之流中的淡蓝色刀锋,它所表现出来的隐秘力量甚至危险的光芒,玄珠一样的光芒,正是我在诗歌中所要表达和闪现的。你可以忽略它,无视于它,但你得小心它。在不经意的某个时刻,它可能划伤你有些麻木的神经呢。
玄珠得好好保存起来,一旦丢掉,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
因为,象罔就是虚无的人,他根本就不存在。
理想主义的夏天
我深信,时间并不仅仅如逝水,一去不复返,时间的某些面孔或波澜是轮回和交叉的,甚至可以重现。至少,我们可以通过回忆,通过梦,通过语言来实现其中的一部分,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那也足以显示时间的复杂性和温情的脉络。比如此刻,也是10月初,我坐在书房,却与32年前的秋天的那个我奇妙地重叠在一起,一颗56岁的心脏和一颗24岁的心脏,像两粒久别重逢的星星,发出同样的光芒和节奏。
我和《诗歌报》的故事,始于秋天,却在夏天怒放。
1987年10月6日,《诗歌报》总74期头版报额的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征稿启事——一则注定要载入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歌“双奖”启事,为推动中国新诗发展之大潮,《诗歌报》决定举办中国“首届探索诗大奖赛”及“首届爱情诗大奖赛”。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心怀理想的诗人们跃跃欲试。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诗歌由一幕幕大戏组成,那么《诗歌报》则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幕后推手和导演的角色。这场声势浩大的诗歌“双奖”活动,显然是其所导演的最浓墨重彩的一幕。“双奖”与之前《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一脉相承,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一次紧锣密鼓的重量级擂台赛。
整个80年代,《诗歌报》在中国诗人心中,尤其是在民间青年诗人心中,具有圣殿般的地位,其影响力远在老牌的《诗刊》和《星星》之上。如果要给当年的三大官方诗歌报刊排个英雄座次的话,名列榜首的一定是《诗歌报》,其次才是《星星》和《诗刊》。从后来公布的“双奖”获奖诗人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80年代中国诗坛的不少领军人物及重要诗人均位列其中,尤以第三代诗人为中坚。随手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杨黎、高月明、沈天鸿、尚仲敏、周伦佑、蓝马、孟原、吉木狼格、贝岭、廖亦武、南野、祝凤鸣、潘维、钢克、潇潇、刘涛、喻言、江弱水、席永君、程宝林、顾城、陈先发、海男、马及时、苏历铭、杨然、陈绍陟、雨田、李自国、韩非子、郁舟、周所同、马永波、李青松、李南、盘妙彬、聂沛、柯平、华万里、简宁、周墙等。这些获奖诗人中,很多在今天仍然是中国诗坛的主力军。我相信,在未获奖的参赛诗人中,一定还有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诗歌兄弟姐妹。如果有人对当年参加《诗歌报》首届“双奖”的全体诗人及作品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一定能勾勒出80年代壮丽的诗歌版图,并从中找到80年代诗歌繁荣的密码。
《诗歌报》“双奖”启事登出之后,不仅在诗人之中引起热烈反响,在诗歌批评界也引起诸多争鸣,尤其是《诗歌报》主编严阵先生就关于“双奖”的各种置疑进行了回答之后,更是引来一拨又一拨的批评和反对之声。矛头直指探索诗,也就是所谓现代派新诗,认为《诗歌报》所要张扬及褒奖的这些诗歌,是“皇帝的新衣”,是“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产物”,是“毒害人类审美心灵的腐蚀剂”!这其中任何一顶帽子都足以让正在旺盛生长的《诗歌报》中途夭折,让刚刚拉开序幕的“双奖”活动戛然而止。但是,《诗歌报》顶住了,并且顽强地坚守着。严阵先生为此撰写了《为青年诗人辩护》一文,刊登在《诗歌报》1988年1月6日的头版头条。我认为这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篇文献,文中所呈现的真诚、开放、风骨、洞见以及理想主义激情,将历久而弥新,今日读之,仍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是的,《诗歌报》之所以能在众多青年诗人心中拥有崇高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先锋性和理想主义。
蒋维扬先生在《大幕垂落,公正与否任评说——诗歌报首届爱情诗探索诗大奖赛揭晓》(《诗歌报》1988年6月21日)一文中袒露了他们的初衷和理想:“《诗歌报》能否导演一场场面宏伟、扣人心弦的话剧,让大大小小想当诗人,有些也许一辈子也当不了‘诗人’的人们登台亮相呢?能否在这块青年诗歌爱好者自己的领地里,搭起一个擂台,人人平等,个个无欺,一视同仁地让各路英雄或平民登台角力、一试高下呢?能否给许许多多想知晓自己的诗创作处于何种水平上的诗歌爱好者,提供一个忠实的,不看风使舵、扒高踩低的磅秤,使他们在密密麻麻的刻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小小的点呢?”这是一个真正想为中国诗歌做点实事的诗歌媒体才会说出的真心话,和今日林林总总带着各种目的各种利益以至各种交易的诗歌奖相比,《诗歌报》首届“双奖”,像一对玉树临风的孪生兄弟或冰清玉洁的姐妹,代表一个纯粹的诗歌时代,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时代。
“双奖”严谨、公正的评审程序,可能会令今天的很多诗歌和文学奖项汗颜,不仅有一审、二审和复审,还设立了罕有的互审制度,以防止因评委个人偏好而有遗珠。整个评审过程从 1988年3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至4月中旬,最终从数千篇稿件中,选取了411件作品进入终审(爱情诗215件,探索诗196件)。根据蒋维扬先生的回忆,终审结果出来后,
4月16日,组委会专门约请了4位中学教师将终审稿件重新刻印出来,那时还没有电脑排印,全靠手工劳动,刻印时隐去了姓名、地址,只保留编号,然后装订成册。5天之后,也就是4月21日,组委会正式向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八大评委寄出稿件,并附上了评审信函:“尊敬的评委: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些参赛稿都已经过了一审、二审和两次复审。希望您认真公正地评审这些稿件,几千名参赛者无一例外地全都期盼着!请遵守时间,请保守秘密——不要向您的诗友说及此事,更不能出示待评稿,请守信誉。”读着这些朴素的寄托着澄明诗心的文字,我竟然有些想落泪的感觉。
对于“双奖”评委会成员的选择,《诗歌报》也别开生面,之前没有过,之后也很少再见。评委会要求评委的年龄不超过35岁,并且是在全国范围内卓有成就的青年诗人,不设顾问,评委会及本报全体工作人员均不参赛。最终入选探索诗评委的是王家新、魏志远、陈超和钱叶用4人,入选爱情诗评委的是程光炜、陆新瑾、阮晓星和俞凌4人。为什么会特别强调35岁这个年龄呢?我想组委会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的。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借此保持《诗歌报》所强调的青春色彩和先锋实验性质。虽然年轻并不一定代表着前卫和探索,但总的来说,诗歌的革命都是由年轻人来完成的。这个事实,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由于那时的交通和邮政的落后,我读到“双奖”启事的时间,大约是在一周以后了,估计是 1987年10月中旬,一个下午或黄昏。最先看到启事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妻子可可。她知道我一向不太喜欢凑热闹,就说,这可是你很喜欢的《诗歌报》举办的呢,这场大戏一定好看。我被她说动了,就选了两首,一首参加爱情诗,一首参加探索诗。爱情诗是选的哪一首我已经不记得了,直到前几天才从《诗歌月刊》编辑刘康凯那儿得知,当年我参赛的爱情诗也入围了好作品奖,也算是一个迟到的意外收获。诗人及诗评家西渡在批评我的诗作时发现,我很少写爱情诗,认为这可能是由爱情洁癖导致的。爱情太神圣了,我不敢轻易下笔啊。至于选取写于几个月之前的《割玻璃的人》一诗作为参加探索诗大赛的作品,有一定的偶然性:从一堆乱糟糟的手稿中,忽然就看见写在一个牛皮纸信封背面的这首诗作。那个信封是我 1986年夏天从南开大学毕业时带回成都的,可可当年写给我的两地书所用,信封的正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天津的地址,这是个好兆头。我用校点《全宋文》的稿笺,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一遍,装进信封,然后投进川大校园路边一个古旧的邮筒之中。
稿子寄出以后,也就没太关心这事了。就在我差不多忘了的时候,经历一整个冬天,诗歌的奇迹正在潜滋暗长着。夏天来了,1988年,成都的夏天好像没有现在炎热。记忆中的成都总是浓荫密布,清凉,饱含丰收的喜悦。也是在一个黄昏,我正陪身怀六甲的妻子散步回家,便收到了一封来自《诗歌报》编辑部的信函。一张盖有编辑部红色公章的信笺,上面只有很简单的几句话,意思是祝贺我的参赛作品获奖了,获得什么奖只字未提,并告知请于1988年6月18日前往黄山市参加颁奖典礼。黄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3年前的夏天,我还在南开大学读书,曾与可可一同登过黄山。
我当时的着装,现在想起来是相当叛逆,并且很不得体的:一双陈旧的胶底拖鞋,齐膝黑色短裤,最离谱的是身上那件故意翻过来穿的圆口衬衫,肩头和腋下布满了长短不一的线头,背心部位还用自己的手掌拓印了两片模糊的掌纹。我当时就是那样我行我素,就想要那种效果,颓废、独特而前卫,略略有几分玩世不恭,再配上一副黑框宽边眼镜,用今天的话来说,很酷的样子。记得蒋维扬老师第一眼看见我时,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非常宽容地笑了笑说,像一个诗人。
直到颁奖之前,我只知道自己获奖了,但并不知道得的是什么奖。三等奖和二等奖的名单念完了,悬念越来越少,只剩下两个一等奖和一个特等奖。当主持人念到探索诗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杨黎和高月明时,我知道那个万众瞩目的《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奖,已经幸运地降落到我的头上,记得是严阵先生亲自给我颁发的获奖证书和奖金——1000元现金,对于那时平均月工资收入不足50元的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有经济学者做过计算,以实际购买力来看,1988年的1000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万至15万元。获奖5个月以后,我迎来了自己的女儿——因为有了这笔奖金,女儿的奶粉钱不用发愁了。因此,我曾对女儿说,要感谢诗歌和《诗歌报》,它们为你的成长做出了诗意的贡献。
从黄山返回时,诗人阮晓星邀请我和杨黎、靳晓静,还有陆新瑾等人往南京吃咸水鸭。然后又一同去南京无线电厂拜访了成都籍诗人覃贤茂(闲梦),并且约定一起创办一份民间诗歌刊物。这段诗歌的因缘,完全因《诗歌报》而起。20多年后,覃贤茂在一篇名为《那时的月,那时的怀念》中,深情地回忆道:“那是一个热血慷慨的盛夏,那是青春和诗歌日日痛饮无绪的浪漫时光,我的爱情在那时正怒放如花,而在诗歌运动中结识的友情也如植物一样蓬勃生长。1988年安徽《诗歌报》举办首次现代诗歌大奖赛,向以鲜兄以《割玻璃的人》一诗斩获特等奖。真正对向以鲜兄诗歌才华有了深入的理解和钦佩,正是因为读到他的这首诗。而我的好友,诗人杨黎,则是以其名作《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获得大奖赛的一等奖。正是因为这一年向以鲜和杨黎去安徽黄山领奖的机缘,他们一起专程来了南京和我相会,我由此结识了向以鲜兄。杨黎兄是我当时诗歌上志同道合的至交,他的到来我非常高兴就不说了。而初次与向以鲜兄相见,把酒言欢,竟也一见如故,惺惺相惜。那时的向以鲜兄,风华正茂,少年才俊,容仪如玉,风度翩翩。他送给我的油印诗集《割玻璃的人》,我至今还妥帖收藏着。虽然我们在诗歌理想上有着一些激烈的论辩,虽然已经记不清那时我们具体高谈阔论的内容,但彼此的尊重、理解,使我们彼此印象颇好,友情加深。我们无话不谈,除了文学、诗歌,我还记得向以鲜兄和我讲起的他的浪漫情感,当然我也会和他分享我的故事。向以鲜和杨黎来南京,同行的还有获奖四川女诗人靳晓静、南京女诗人阮晓星。因为我的女朋友也姓靳,所以那时她们还相约结为姐妹。那一次欢聚结束之际,我们共同策划,由我牵头筹办一份诗歌民刊,作为纪念。此后一年的时间,我与杨黎、向以鲜兄等人书信往来,终于在1989年,一份凝聚有我们诗歌兄弟情义的铅印诗刊《思无邪:89 年现代诗歌运动交流资料之二》面世了。这一本32开、只有55个页码的诗歌小册子中,除了我和杨黎的诗,还刊载有向以鲜兄的50多行的长诗《人们的梦》。此外还有上海女诗人陆新瑾的两首诗《无题》《白马黑马》,南京女诗人阮晓星的两首诗《手的爱情》《温暖的存在》。另外还有诗人钟鸣、漆维、冉云飞、梁晓明、吴非、柯江、南岛、李德成、行行、黑沨、华小青的诗,寒江雪的散文诗,柏桦翻译的T. S. 艾略特的文论《叶芝》。而诗刊‘思无邪’的取名,也是来自柏桦的建议。”
离开覃贤茂那儿,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南京火车站,分别的时候到了。南京的夏天不同成都,闷热,阴郁。我正排队购买回成都的火车票,快要到窗口时,回头看见诗人陆新瑾站在不远处,孤单而美好的样子。我立即从队列中抽身而出,来到她的面前。我们就坐在玄武湖边的长椅上,谈诗歌,谈理想,谈家庭,谈人生的幸福和虚无,一直谈到天亮。多年以后,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已不再年轻,不再轻易激动,那个湖畔夏夜,那个因《诗歌报》而带来的理想主义的仲夏夜,仍会不经意地浮现。
《割玻璃的人》一诗获奖之后,虽然没有现在的网络传播那么迅捷和广阔,但还是以惊人的方式、诗歌本有的生命方式传播开来。在往后的漫长岁月中,经常会遇见来自天南海北的诗人,大多数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读过《割玻璃的人》,还有一些兄弟会说,我抄录过《割玻璃的人》。1989年,深处大巴山腹地航天重镇的诗人凸凹,在诗歌讲座中率先将《割玻璃的人》板书出来进行讲解,那时我们完全不相识。世界真奇妙,因为有凸凹,令人惊奇的是,那次讲座还拍了照片,而且,那张照片还保留了下来。
获奖之后,《诗歌报》先后又刊登了我的诗作《狼眼》(外一首)、《水果》和《黑钻石,幻狮与父亲》,其中的《父亲》(《黑钻石,幻狮与父亲》中的一篇)还入选了《1989 年全国诗歌
报刊集萃》。在我的诗歌征途中,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诗歌报》。
3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经常会想起在黄山结识的老朋友,想起严阵和蒋维扬诗歌二先生,想起爱情诗特等奖获得者殷红,想起多年未见的兄弟姐妹们,想起与《诗歌报》结下不解之缘的点点滴滴,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
当活着的痛苦比痛苦本身更深
在踏向灭亡的途中你是个恩赐
(黄燕德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