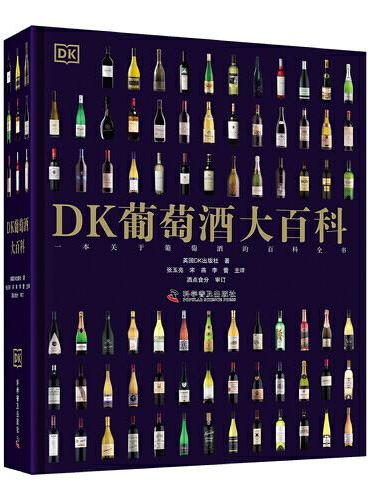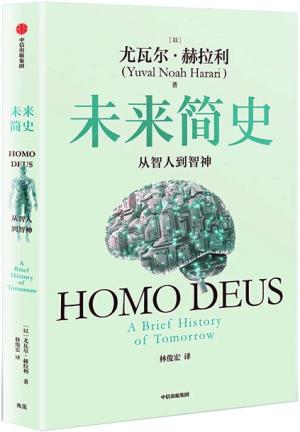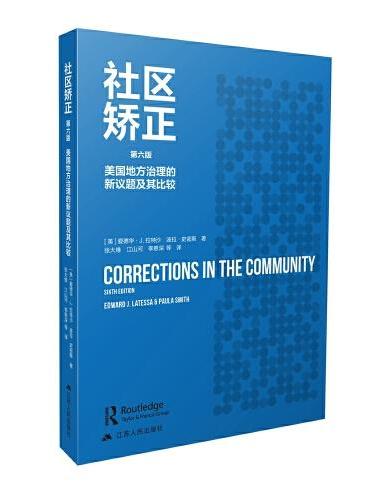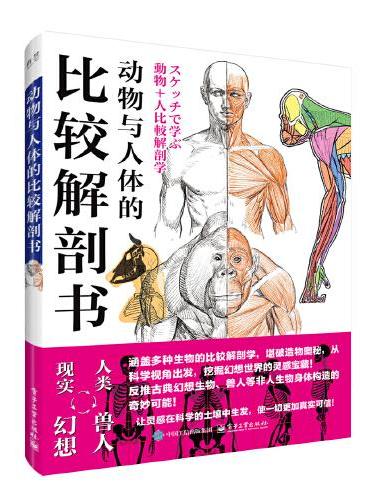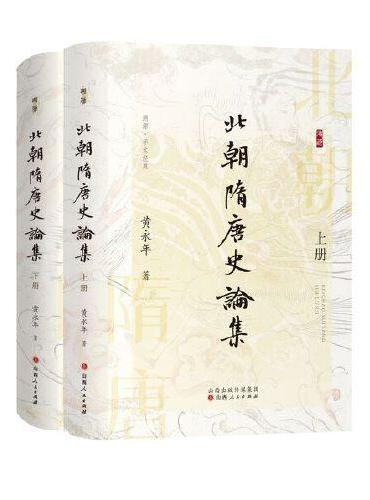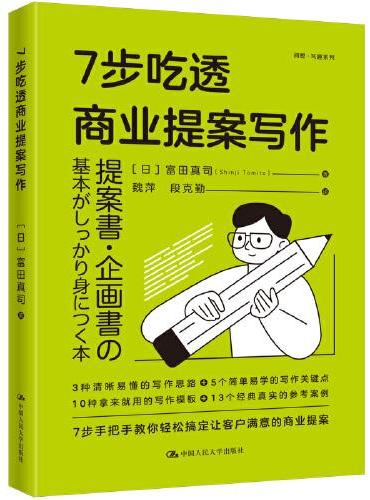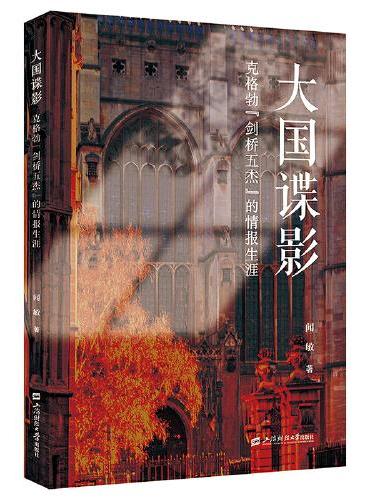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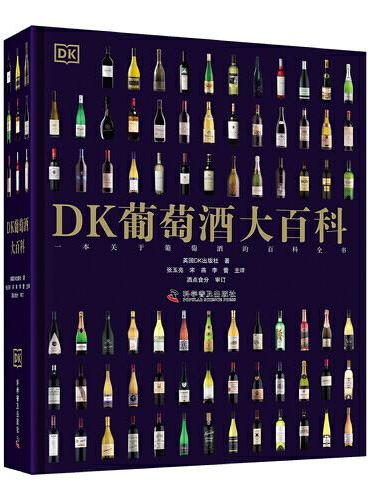
《
DK葡萄酒大百科:一本关于葡萄酒的百科全书
》
售價:HK$
54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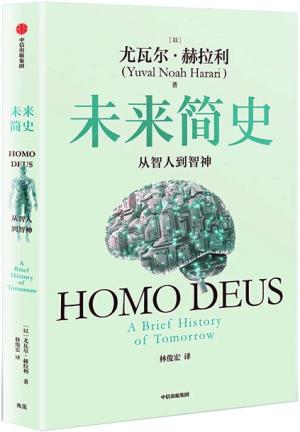
《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2025白金纪念版)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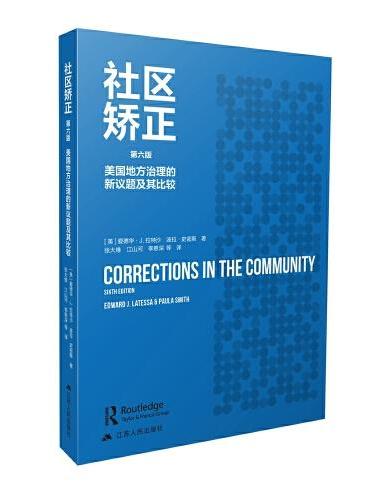
《
社区矫正(第六版):美国地方治理的新议题及其比较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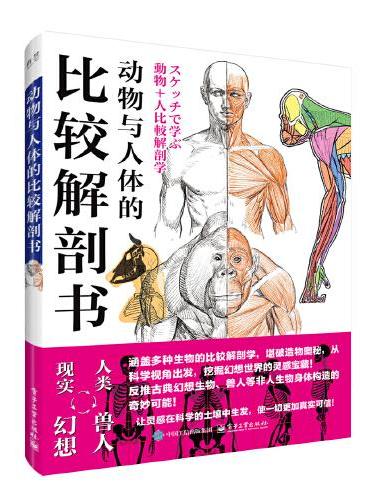
《
动物与人体的比较解剖书
》
售價:HK$
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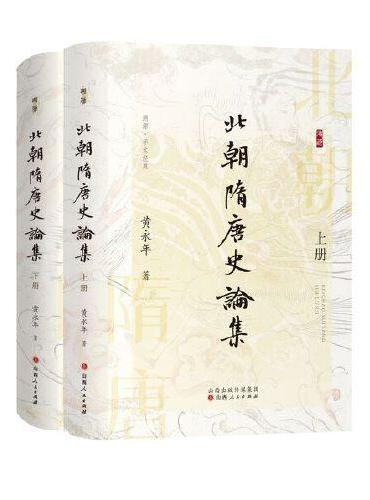
《
北朝隋唐史论集
》
售價:HK$
273.9

《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全5册)
》
售價:HK$
2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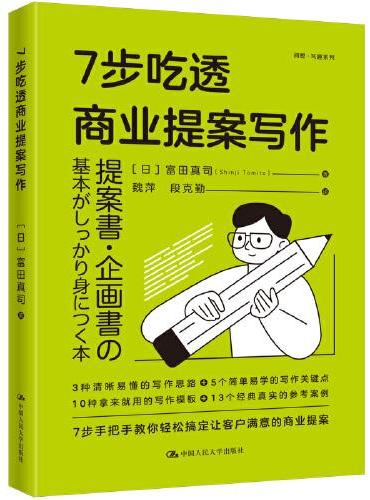
《
7步吃透商业提案写作
》
售價:HK$
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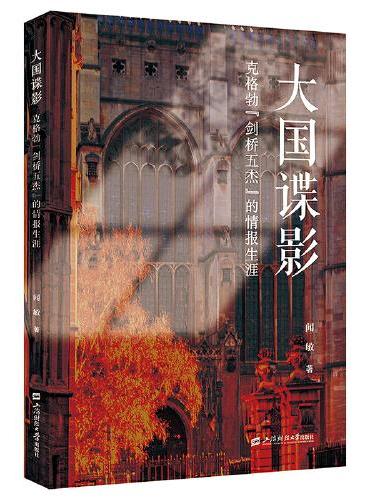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审视数字时代的《娱乐至死》,建立现代人的思想支点!抖音、电子游戏、直播、特斯拉、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当新的潮流袭来,我们真的做好迎接它们的准备了吗?他们又会给我们的认知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跟随著名传媒学者胡泳,一起解剖“流行”,展露世界的底色。
流行与时代同步,喧嚣与冷静抵牾。毫无疑问,流行是当下的产物,但每个当下,都会被卷进历史的洪流中,流行也就变成了时代潮头上的一朵朵浪花。历史告诉我们,反思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每一轮流行的大潮都向着它的未来退去,并在沙滩上留下痕迹。
|
| 內容簡介: |
什么样的东西才会流行?时代潮流的本质是什么?不论在潮流内外,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哪些东西是始终应该放在首位的?对于这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流行事物,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是积极拥抱,还是提高警惕?
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才是平衡之道。
胡泳在本书中聚焦潮流和热点问题,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论是对“顺流”的思考,还是对“逆流”的反思,都透过他的专业视角,为所有或主动或被动地置身潮流之中的我们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思想支点。
|
| 關於作者: |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
因推动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而被誉为“数字时代的严复”,研究领域为数字媒介与数字社会、网络政治学、数字经济与管理,是国内媒介生态领域最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在《财新》《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平台发表专栏文章。 2018年,被Thinkers50(全球管理领域的权威排行榜)选入“Thinkers50 雷达”名单,名列可能对未来组织机构的管理和领导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30位世界思想家之一。
译著:《数字化生存》(1996)
《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2009)
《知识的边界》(2014)
著作:《网络为王》(1997)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2008)
《数字位移:重新思考数字化》(2020)
|
| 目錄:
|
第一部分 顺流而为
流行的事物总是引人追逐。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潮流意味着成功的机遇,以及时代前进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流行并非泡沫,它的背后有确凿实在的内容。
短视频·直播·真实内容·算法·沉浸·自我定位·网红·社交资产·多频道网络·冒险·改变世界·关心人类 ·顾客至上·飞轮效应·新物种·新媒介·架构·体验与感知·模拟人生·虚拟世界
TikTok 的流行之道 _003
15 秒会造就什么? _011
未来每一位名人都是网红 _039
马斯克:钢铁侠还是魔法师? _062
贝佐斯:想大事,但从小事干起 _077
当麦克卢汉驾上特斯拉 _099
智能汽车:移动时代的里程碑 _108
第二部分 逆流而思
潮流陷阱:“风口”还是“虎口”?
“站在风口上,连猪也会飞”,无数追逐潮流的人,梦想着麻雀可以站上枝头变凤凰。但想象性感,现实骨感,盲动者往往遭遇吃人的獠牙。
元宇宙·乌托邦·流量·内容产业·伪个性化·机器学习·A I决 策·算法复杂性·量子计算·量子伦理·区块链杀手·加密术与密码解析·AIQC 契约·消费技术·社区团购·民间互助·直播电商·马太效应·金融科技·信用监管
元宇宙社会的新乌托邦想象 _134
流量密码 _159
人工智能不智能 _174
量子伦理 _184
区块链“杀手” _191
消费技术最新的“大决战” _196
直播电商从风光到失色 _205
汹涌暗流:不为人知的盲点
消费时代里,人们面对流行,如同聆听一首颂歌,唱出来的都是好听的。那些要紧的反调,像是波涛之下的暗涌,无法被轻易发现,但却影响至深。
后真相状态·信息流行病·公共利益·个人隐私·群己界限·数字排斥·数字包容·数字化养育·无屏幕生活·无媒体时间·交互式媒介使用·数字化成长·移动互联网·围墙花园·网络暴力·集体羞辱·在场与缺场·数字游牧
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_212
危机时刻的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 _242
数字弃民 _254
新数字鸿沟 _263
技术改变了青春期的面貌 _271
乔布斯:互联网历史上最大的“罪人” _274
社交媒体何以变成愤怒机器 _278
永远生活在别处 _281
第三部分 大潮反卷
流行与时代同步,喧嚣与冷静抵牾,历史告诉我们,反思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每一轮流行的大潮都向着它的未来退去,并在沙滩上留下痕迹。
知识媒介·分布式认知·个体学习·大众媒体·社交网络·失忆陷阱·人类经验实验室·最重要的世纪·存在风险·水平化·多极化·生产率悖论·技术解决主义·脆弱的世界·共同生活的艺术
互联网作为知识媒介 _287
历史的“插入语” _300
没有历史感会怎样? _303
人类历史的枢纽期 _312
全球化已在我们身后 _321
“技术解决主义”的愚蠢 _328
人类步入“危机社会” _344
|
| 內容試閱:
|
自 序 事物如何变得流行
太阳底下无新事?
流行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为什么有些歌曲、电影、游戏、应用程序或名人会爆红,而另一些则会失败?“走红”到底是运气还是有科学依据?本书虽名为“流行之道”,但并不能揭示某种单一的流行秘密——显然,如果作者知道这样的秘密的话,就会变成一个万亿级的企业家,而不是来写一本书。流行从来没有完整和完美的公式,因为假如有的话,每个人都会竭力仿效它,那么流行物反而随之变成大路货了。
尽管没有流行的成功公式,但流行背后还是有规则可循。这些规则事关我们为什么喜欢我们喜欢的东西,以及流行背后的文化是如何变化的。一个金科玉律是,消费者或用户往往在对立的紧张关系中纠结。特别是他们在“喜新厌旧”和“恐新症”之间纠结——他们中意新的东西,喜欢新的想法;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害怕任何太新的东西,不喜欢改变他们的偏好或迫使他们改变习惯的事物。
大脑对新与旧有一种奇怪的平衡:人类期待看到熟悉的、舒适的模式从新奇(但也不要过于新奇)的情况中出现,流行因此永远处于某种“半混沌”状态。单纯地模仿很少能带来成功,但把熟悉感、创新性和难以捉摸的大胆营销共同组合起来,却有更多机会。热门产品诞生于流畅性(有关事物对消费它的人来说似乎很熟悉,因此容易消化)与新颖性(该事物带来了新鲜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挑战性)的结合。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那么这一事物就会显得很无聊,从而乏人问津。但假如情况相反,人们就会感到沮丧,转而去寻求别的事物。
因此,成功的诀窍在于,在新产品中融入某些熟悉的东西,锁定“熟悉的惊喜”(familiar surprise)的甜蜜点。而这有赖于对我们习惯的、舒适的、自己喜欢的和令我们出乎意料的东西的一种精确的判断,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被 20 世纪中期伟大的美国工业设计师雷蒙德·洛伊(Raymond Loewy)归纳为 MAYA(Most Advanced Yet Acceptable)原则——“最先进但又可接受”原则。过于先进的想法不太可能获得广泛的接受,而人们能够欣然接受的东西,总是既足够舒适,又足够新奇。
例如,人类喜欢音乐,是因为我们喜欢重复。按照《大西洋月刊》编辑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的说法,“重复是音乐的上帝粒子”。重复也是流行的虚构或非虚构作品的核心——要么是熟悉的故事的重复,要么是一种能够讲故事的成熟模式的重复。同理,电影制片人提出过拍出好电影的秘诀:把任何成功类型中的 25 个要素聚集到一起,再将其中一个颠倒。
面对差不多的选项时,我们往往总会选择那些我们熟悉的或者曾经带给我们美好回忆的事情。心理学家将此称为“曝光效应”(exposure effect),它指的是人会单纯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作“熟悉定律”(familiarity principle)。通过对人际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某个人在自己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
对熟悉的事物的偏好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人认为它一定是早在我们的祖先在大草原上游荡时就写进了我们的遗传密码。对“曝光效应”的进化解释很简单:如果你认识一种动物或植物,那就意味着它还没有杀死你。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危机层出不穷的世界,不得不经常小心翼翼地去应付不熟悉的事物或情境,而这种针对不熟悉的情境的谨慎又加强了人类的生物适应性。通过与这样的环境不停地相互作用,带来危险的不熟悉之物逐渐为人所适应,对人而言也就变得熟悉与安全了。
熟悉性与喜欢的关系可以被应用在许多地方。一个例子是在线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的“发现周刊”(Discover Weekly,一个用于服务用户的个性化播放列表),每周一它会根据用户的品位为其挑选歌曲。当平台对这一应用进行内部测试时,他们希望所有的歌曲和艺术家都是新的。但意外的是,算法中出现了一个错误,让一些大家已经听过的老歌和老艺术家溜了进来。然后程序员修改了这个错误。猜猜结果发生了什么?这一应用的参与度随之大幅下滑。
更让人容易联想到的例子是电影。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将《星球大战》(Star Wars)描述为“以外太空为背景的西部电影”,他大量借鉴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系列电影《闪电侠戈登》(Flash Gordon),将人们已经熟悉的类型——西部片、英雄之旅等——以新的和令人兴奋的方式(在太空!)结合起来。汤普森将卢卡斯的电影描述为“一个原创的汇编”。卢卡斯自己则说:“它不像一种冰激凌,而是一个非常大的圣代。”《星球大战》的成功生动地证明了,对熟悉的事物重新包装,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不仅卢卡斯如此,漫威电影宇宙也如此。为什么好莱坞有那么多大片都是续集和重拍片?因为娱乐业害怕失败,厌恶风险,瞄准的是观众的熟悉感。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在过去的 16 年里,除了一部电影外,美国电影院中票房最高的电影都是续集,要么是改编自已经流行的书籍或电视节目。
流行就是产品
流行常常与病毒的隐喻联系在一起。本书中提到,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最后一章,讨论用模因(meme)来表达文化当中的各种复制的时候,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使用了“病毒式的”的隐喻。互联网模因与疾病的流行共享一个形容词,这绝对不是巧合。因为爆发需要三样东西:首先是传染性足够的病原体;其次是不同人群之间要进行大量的互动;而在大量的互动以后就会产生足够多的易感人群,即到达了临界量(critical mass),这构成了第三样东西。所以,所谓流行,就是在某一个门槛上跃过临界量,突然就从小众的偏好变成大众的流行,人人皆知,人人皆用。
现代内容创作最常见的理论是,如果你做出伟大的内容,它就会被认可、分享,并成为“病毒”。其实,现实的流行远没有那么简单。传染病模型,即人们感染他人,而他人又感染更多的人,并不是总能解释大规模的点击率。网络营销者一向声称口碑营销强大无比,但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明显的“病毒式”流行浪潮背后,总是有一个或多个影响者或组织使用的是大规模老式“广播”,这些影响者或组织本来就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关注者。因此,内容是否流行的关键依然在于广播的规模——不是一百万个一对一的模式,而是几个一对一百万的模式。
固然,要想有关事物具备流行度,对大众来说它必须是有趣的或引人入胜的,但它也必须被放置在一个可以被发现和传播的地方。所以,内容或许为王,但传播才是真正的法宝。你可以说一首歌曲是世界上最好的歌曲,或者一本书充满了有益的真知灼见,但假如没有一个有效的传播策略来触达人心,就没有人会听到这首最好的歌,或是读到这部杰出的著作。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提出了“引爆点”理论,他相信观念、产品、信息和行为方式都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和流行开来。但实际上,从文化模因到科技扩散,都并非基于一个人感染两个人、两个人感染四个人这样的指数传播,而是仰赖于想尽一切办法在现有的社会网络上“搭便车”。例如,Facebook(脸书)最初的“病毒式传播”,不是设计一个每个人都可能与其他五个人分享的产品,而是巧妙地利用现有的网络:先是将已经存在的哈佛的网络予以数字化,然后再扩大到常春藤盟校的网络。
Skype 也是这样的例子,它允许用户在广大的范围内建立偶然的联系,也可能会因此发生有趣的对话(以及大量的滋扰),但 Skype 真正的引爆点在于它连接了本来就互相认识的人。如果它不是开发了这类功能,或者没有加强这类功能,它就不可能获得“病毒式成长”。
同样的道理,微信的大规模流行并不在于产品的设计能够巧妙地实现用户之间的互动。虽然用户同用户交互的便利的确是微信的卖点,但并不因此就生长出“病毒”,因为用户缺乏强大的动力介绍他人使用产品。说穿了,微信能大行其道,缘于在开始推广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要想注册微信,要么通过QQ,要么通过手机号,这两个都是经过一层筛选的。也就是说,凡有微信账号的,已经是经过两层现有的人际关系网筛选的了。尤其是手机号,几乎一个手机号就对应一个真实的人。从微信 5.0 版本开始,注册页面连“使用 QQ 号码登录”的选项都没有了,只能通过手机号码注册。
除了“引爆点”理论不符合实情,另外一个在互联网界大名鼎鼎的理论——“长尾”理论也难以成立。毕竟,热门产品往往是赚钱的产品。如果真正的钱来自世界上每一种产品在无限范围内的持续供应,那么为何还要努力生产热门产品?完全可以不用那么费力气,可从泛在网络中轻易获得好处。“长尾效应”只是个假想,现实是生产热门产品仍然是通往长期成功的最可靠途径。虽然数字技术的进步乍一看似乎有“民主化”的倾向,但是多年以来的实践证明,它们带来的是相反的东西:促进了权力集中和赢家通吃。
是的,大热门的创作和营销可能是非常昂贵的,而且许多尝会失败。但是,正是这些主流的、大受欢迎的电影、歌曲、电视节目和产品最终会受到消费者青睐,并由此产生个人和企业的财富。
今天的消费者购买的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他们真正购买的是进入一个流行对话的入口。换言之,让消费者产生购买意愿的,并不是因为某些产品性能更优,而只是因为它们很受欢迎。在这个意义上,消费者所购买的不仅仅是产品,也是流行本身。
元宇宙社会的新乌托邦想象
随着以“移动互联”“应用生态”“全息互联网”等为关键词的新一轮数字革命的全面展开,以及虚拟现实、沉浸环境、区块链、开放源代码等媒介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加之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趣缘社群逐渐成为成熟的网络文化生产机制和主体组织方式,元宇宙“顺势而出”,在当下被历史性地定位为内嵌在整个互联网以及数字化发展序列中的新阶段,并被赋予了超脱话语层面之外的社会意义和未来想象。从其内在技术、机制和价值设想中可以看出,元宇宙作为一个依然携带硅谷话语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和社会实践,在生产与创造、认知与经验、社群与身份 3 个方面都呈现出有待激发的潜能和变革性影响。但是这种潜能和变革性影响又深受物质世界的制约,元宇宙社会也因此展现出和现实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连接。
随着马克·扎克伯格的商业布局变动和资本市场的新一轮 狂欢,“元宇宙”成为当下产业界和学术界风光无两的热门概念。然而,元宇宙并非具有历史断裂意味的“新发明”,而是一个经由 3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讨论和实践,而被我们早已熟知但不自知的“旧概念”。因此,对元宇宙的历史性梳理和学理化建构,将是对数字革命开启至今的一次管中窥豹式的阶段性总结,以及对互联网未来发展方向的展望与想象。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曾指出,20 世纪后期美国的科学文化中有 3 处至关重要的边界崩溃:首先是人与动物的界限被打破;其次是人、动物和机器之间界限趋于模糊;最后是物质世界与非物质世界的相互渗透。这三重界限的不断消弭使得“赛博格人类”的想象成为可能。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开启,这三重边界的崩溃突破了时空的限定来到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因此,当我们讨论元宇宙时,所讨论的绝不仅仅是互联网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或资本投资的下一个风口,而是一个关乎另类社会实践的可能性以及人类种群如何与技术共处、与机器共生、与代码共事的后人类境况议题。
“元宇宙”的语汇缘起与历史叙述
“Metaverse”作为一个词语和概念上的舶来品,在本土的语境中被对应为“元宇宙”这一并不具有明确意涵和具体所指的词语。除此之外,该词亦有“超元域”“后设宇宙”“形上宇宙”“元界”“超感空间”“虚空间”等翻译。而在诸多翻译中,我认为“超元域”一词相较而言更准确地指涉了这个概念的关键含义,即超越次元的场域。“Metaverse”本身就是前缀“meta”(超越)加后缀“verse”(宇宙)的组合词。因此,它的字面意思是“超越物理世界的宇宙”。更具体地说,这个“超越的宇宙”指的是数字生成的世界,同时也就与同样超越物理领域的形而上学或“精神”概念相互区别开来。
当下对“元宇宙”概念的溯源,大多回到尼尔·斯蒂芬森在 1992 年出版的科幻小说《雪崩》。此概念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被印在一张名片上:“名片背面是一堆杂乱的联络方式:电话号码,全球语音电话定位码,邮政信箱号码,六个电子通信网络上的网址,还有一个‘超元域’中的地址。”在小说中,斯蒂芬森所想象的元宇宙在形式上和操作上本质都是一个巨大的且人满为患的虚拟世界,而不是一个具有特定参数和目标的游戏环境,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与物理领域并行运作的开放式数字文化。可见,斯蒂芬森对“Metaverse”的想象依然内嵌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数字化生存”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的序列中。
斯蒂芬森对元宇宙的叙述对之后的虚拟游戏创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比如 1995 年的虚拟世界 Active World 就是基于《雪崩》这一小说开发的,2003 年的开放式游戏《第二人生》(Second Life)也受到了斯蒂芬森的影响。由此,对“元宇宙”的历史梳理就存在另一条脉络线索——虚拟世界和开放式游戏。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文本互动游戏,比如 1974 年的《龙与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和 1975 年的《洞穴探险》(Colossal Cave Adventure)就被视为元宇宙的史前叙述。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计算能力和计算机图像学的进步,基于文本层面的交互逐渐进阶为基于 3D(三维)图像和开放式社交的虚拟世界,如 1994 年的多人社交游戏 Web World 和 1995 年的内容创作虚拟世界 Active World。到了 21 世纪,大规模多人在线游戏和开放式游戏蓬勃发展,其中就有一度被西方学术领域当成元宇宙样本进行研究的《第二人生》,以及标志着元宇宙在资本和产业领域登场的《机器砖块》(Roblox)。
除了借助文学、游戏这两个领域进行元宇宙的历史叙述之外,产业视角也是进入这一概念的一个窗口。有研究将元宇宙按照虚拟沉浸体验的程度来进行历史分期,具体划分为无沉浸期(2014 年 Facebook 收购 Oculusa 之前)、初级沉浸期(2015 —2018 年诞生第一代 VR 产品)、部分沉浸期(2019 —2021 年 5G 发展、虚拟现实生态成型),同时预测,到 2026年将进入完全沉浸期,其特点是网联云控和有机融合。可见,当前产业界习惯用当下互联网平台正在进行的生态搭建与元宇宙进行类比,是持续的硅谷话语的一部分。元宇宙更像是一系 列高新技术的“连点成线”,许多科技公司联合起来,拥抱一个新鲜的、模糊的概念,就像旧日的大数据、物联网一样,听起来既充分具有未来性,又能够对喜欢大场面的投资者产生崭新的吸引力。在这套话语中,元宇宙被视作一种人类进行全面数字化迁移的生产、生活、生存的载体,也成为具有超越性力量的新型媒介。
在对元宇宙的历史发展分期的叙述中,2020 年至 2021 年被不约而同地看作是元宇宙发展的爆发增长期,朱嘉明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将其归纳为 2021 年出现了元宇宙要素的“群聚效应”(critical mass)a ,并将元宇宙现象与 1995 年互联网的群聚效应进行类比。2021 年围绕“元宇宙”这一概念出现的周边元素在产业内呈现星火燎原的态势,比如 2021 年 4 月互动娱乐公司和 3D 引擎技术商 Epic Games 完成了 10 亿美元的融资并宣布该融资将主要用于与元宇宙相关的开发。2021 年 8 月建立在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数字宠物游戏 Axie Infinity 在市场上破圈并联通 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代币) 领域,得到了产业关注度和大众认知度的提高。几乎在同期,中国的 互联网平台企业也纷纷将产业转型和升级的着陆点定位在元宇 宙上,例如腾讯提出的“全真互联网”c 的概念以及将“QQ 元宇宙”“王者元宇宙”等商标注册。基于这些产业动作,元宇宙之于我们终于不再是文学文本中的一个虚幻概念,而是切实影响到未来人类社会的变革性因素。
可以明确的是,在新技术革命经由一轮又一轮迭代的当下语境中讨论的“元宇宙”乃至 20 世纪 90 年代斯蒂芬森所处的 时代语境下诞生的“Metaverse”,无论在概念的内涵还是外延上,都具有超越性的差异。然而,在这 30 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元宇宙的讨论常常和“虚拟现实”“数码游戏”“应用生态”等相似概念缠绕在一起,比如 2007 年出版的著作“《第二人生
先驱报》:见证元宇宙黎明的虚拟小报”(The Second Life Herald: The Virtual Tabloid that Witnessed the Dawn of the Metaverse)就是围绕开放式游戏《第二人生》中的虚拟报纸《第二人生先驱报》(Second Life Herald)展开讨论的。无独有偶,2012 年关
于虚拟现实和元宇宙的论文集“虚拟世界与元宇宙平台:新的沟通和身份范式”(Virtual Worlds and Metaverse Platforms : New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Paradigms)则收录了大量以开放式 游戏《第二人生》和多人互动游戏《魔兽世界》为案例的相关研究。因此,若想辨析元宇宙所蕴含的与前列概念不同的差异性力量,就必须对元宇宙的概念和特征进行厘清和总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