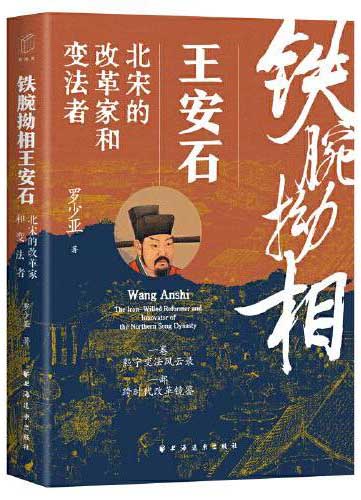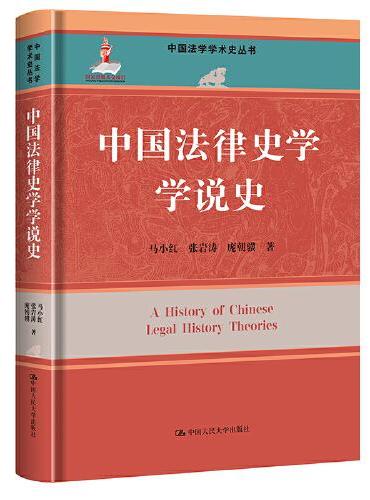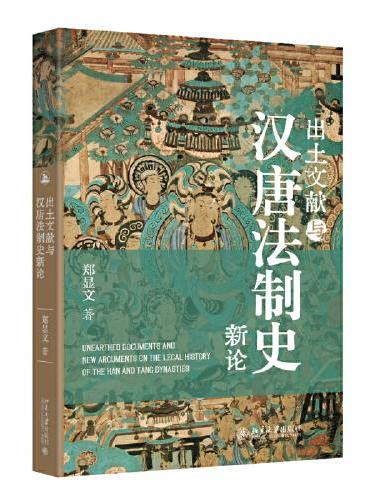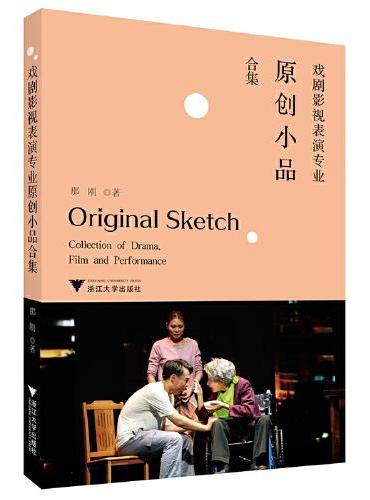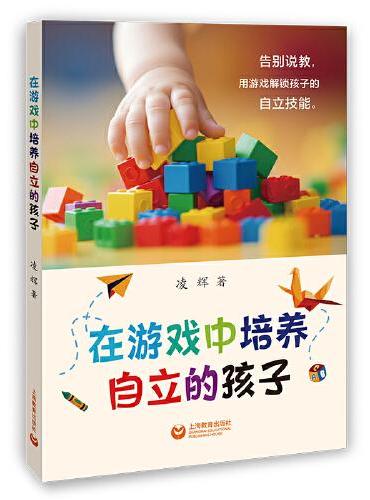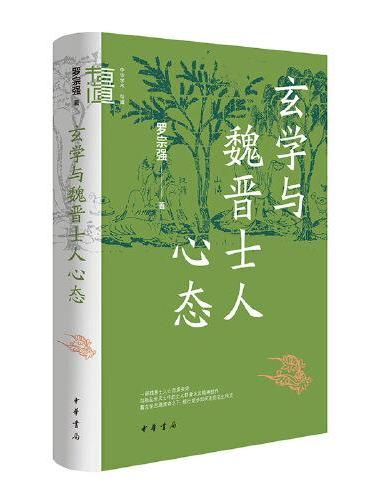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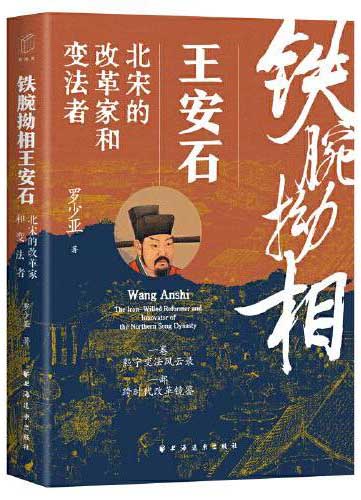
《
铁腕拗相王安石:北宋的改革家和变法者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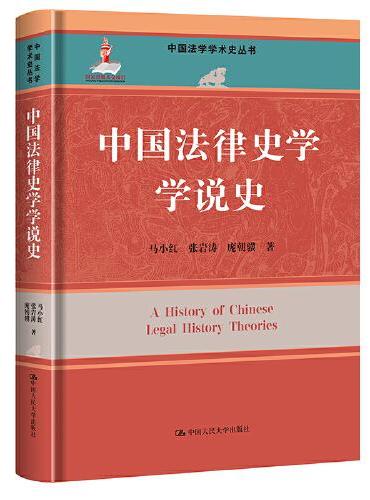
《
中国法律史学学说史(中国法学学术史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售價:HK$
184.8

《
方尖碑(全2册)
》
售價:HK$
1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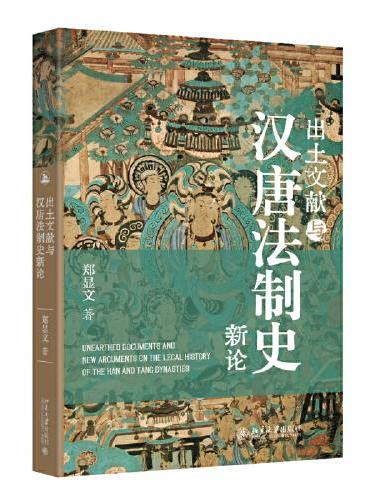
《
出土文献与汉唐法制史新论
》
售價:HK$
85.8

《
最美最美的博物书(全5册)
》
售價:HK$
1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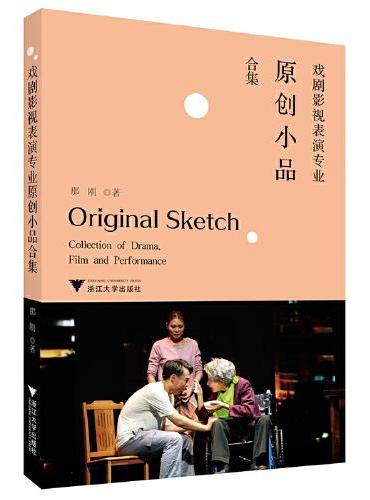
《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原创小品合集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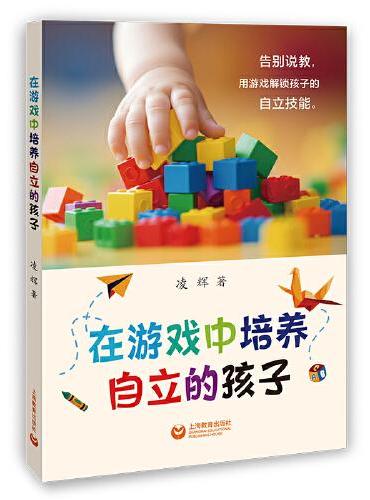
《
在游戏中培养自立的孩子
》
售價:HK$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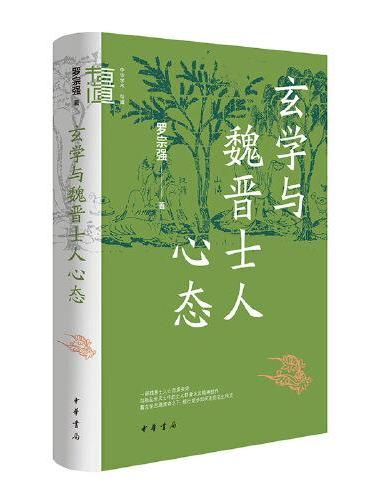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徐贵祥最新作品
荣获2021年度《人民文学》奖
徐贵祥的《将军远行》在其惯有的军旅题材里,调转笔尖,讲述了一个国民党将军和一群士兵寻找179师的远行之旅。既在细节中着眼大处,状写国民党整体的溃败、沉沦,又在幽暗处闪现烛火,描摹个体的忠勇、仁义。一场本是被人设计的死亡远行,最终成了他们投诚解放军的光明之旅,结实,敦厚,温润。
——2021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授奖词
|
| 內容簡介: |
《将军远行》虽然弥漫着荒诞意味,但这不是刻意而为,一次荒诞的战斗,一个荒诞的任务,天然地营造了一个非常态的语境。那支小分队,从踏上寻找之旅开始,他们避开了大路、逃离了阳光、疏远了人间,迷茫、饥饿、阴暗、潮湿始终陪伴着他们,他们的神经一点一点地麻木,肉体一块一块地僵硬,他们既是活着的人,也是正在死去的人,他们既是动物也是植物。他们一息尚存的思维世界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死,在哪里死,穿什么衣服死,死后要不要在墓地上做个记号……他们的呼吸、对话、梦呓、步履,都是尸体的声音和行为逻辑,无不散发出黑色幽默的气味――这是一次死亡的预演,是在死亡之前最后的理性。
——徐贵祥
|
| 關於作者: |
|
徐贵祥,皖西人 ,1959年12月出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 ,曾任解放军出版社总编室主任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等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作品有小说《弹道无痕》《历史的天空》《高地》 《马上天下》《四面八方》 《对阵》等。获第7、9、11届全军文艺奖 ;第4、9、11届五个一工程奖 ;第6届茅盾文学奖 。
|
| 內容試閱:
|
寻找之旅的明与暗
徐贵祥
乍看起来,这个故事有点荒诞。八十年前,发生过多少荒诞的事情啊――经过艰苦卓绝地斗争,抗日战争以胜利而告终,然而老百姓并没有安居乐业,战火重新燃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解放军秋风扫落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部分人跑了,一部分人继续举着青天白日旗帜狼奔豕突,还有一部分且战且退,行进在寻找的路上,等在前方的,是目的地还是墓地,是个未知数。
十几年来,有个名叫仵德厚的人物一直悬浮在脑海中。此人是台儿庄战役中的敢死队长,曾经率领几十名队员突入敌阵,同日军殊死搏斗,九死一生。凭借赫赫战功,此人后来一路攫升,先后担任团长、旅长、师长,并获得过多枚勋章……遗憾地是,抗战胜利了,他和他的很多同僚一样迷失了方向,被拖到了内战战场,最终被解放军俘虏,从爱国英雄沦为阶下囚,坐了十年牢。并且,因为当年记者笔误,报纸上把“仵德厚”写成了“许德厚”,他不仅失去了自由,还丢掉了名字。然后,他回到家乡种地、放羊、在村办工厂搬砖……回想当年,不要说他身边的人,恐怕就连他本人,也把他的敢死队长、少将师长的身份淡忘了,不敢想起,只好忘记,像一个普通劳动者那样生活,倒也心安理得。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个人就像一件破烂不堪的文物,被发掘出来,引起当地政府、媒体以及相关人士的注意。我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固然对他的英勇善战、不朽功勋肃然起敬,而站在作家的立场上,我更关注的是,在八十年前的十字路口,这个人的心里装着什么,关于前途和命运的选择,他是否清楚?答案是,他不清楚,或者说他清楚了却不愿意回头。对比那些顺应潮流的起义者,他是无数迷茫者中间最为典型的悲剧人物。
然而我依然敬重他,为他重新浮出水面、恢复名誉、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而欣慰。毕竟,抗日的战场上有他抛洒的热血。常常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替他思考,为他着急,跟他一起徘徊,一起寻找一条光明的路。
在《将军远行》动笔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我一直眺望,眺望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些人物,我要看到那个空间和那个瞬间里面发生的一切。通过国民党军部警卫连长马直的视角,我最初看到的是,解放战争初期,一支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打散,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副军长李秉章接受了一项莫名其妙的任务――寻找一支杳无音讯的部队。可是,到哪里寻找呢?我和作品中的人物一道陷入迷茫,只好让他们钻进河湾,让他们在假想中的与世隔绝的幽暗的丛林里,让他们在微弱的月光下面,像蚯蚓一样穿行在潮湿的地面上,像幽灵一样游移在明与暗之间。如果说刚刚出发的时候,马直等人还抱有一线成功或生还的希望的话,那么,昼伏夜行十几天,在经历了两次国军散兵的洗劫和侮辱之后,马直等人的心理终于同李副军长接近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又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近在咫尺而遥不可及的“三十里铺”,不仅是目的地,也是墓地,不仅是李副军长的墓地,也可能是他们所有人的墓地。
试想,一个执拗地走向自己的墓地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再试想,一群尚能呼吸的活人,跟着一个半死的人半夜走路,又是怎样的心态?我跟着他们一道前行,多次调整写作方向,比如,让他们离开河湾到解放区投诚,或者,干脆让解放军的尾随部队很快出现,甚至让那个对李副军长有救命之恩的女八路从天而降,从而挡住他们走向死亡的步伐……可是不行,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真实,然而在这部作品里,我不能改变李秉章的方向,我要让他一直走下去,直到他以死明志,直到他“只跟日本鬼子打仗,不跟八路军打仗”的夙愿得以实现。至于通过什么方式实现,李副军长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手中的笔,只能跟着他走。
坦率地说,《将军远行》虽然弥漫着荒诞意味,但这不是刻意而为,一次荒诞的战斗,一个荒诞的任务,天然地营造了一个非常态的语境。那支小分队,从踏上寻找之旅开始,他们避开了大路、逃离了阳光、疏远了人间,迷茫、饥饿、阴暗、潮湿始终陪伴着他们,他们的神经一点一点地麻木,肉体一块一块地僵硬,他们既是活着的人,也是正在死去的人,他们既是动物也是植物。他们一息尚存的思维世界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死,在哪里死,穿什么衣服死,死后要不要在墓地上做个记号……他们的呼吸、对话、梦呓、步履,都是尸体的声音和行为逻辑,无不散发出黑色幽默的气味――这是一次死亡的预演,是在死亡之前最后的理性。
战争是残酷的,而文学是温暖的。作品的结尾是开放式的,我没有让李秉章死去,而是让他失踪,从此他隐姓埋名,从此堙没在茫茫人海。后面关于他的传说,给我们留下了希望,我们希望他活着,尤其希望他像仵德厚那样一直活到九十七岁。这个希望不是空想,在上个世纪抗战结束之后,有很多“敢死队长”流落民间,并且用他们饱经沧桑的目光打量他为之奋斗的土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清贫而安宁的生活中露出会心的微笑。但愿他们在余生中能够看到这部新作《将军远行》,但愿他们对身边的人说,我还活着。
1
一
恒丰战役打到第三阶段,仗就没法打了,南线两个旅被共军穿插分割,五千多人的部队转眼之间不成建制。活着的,把国军的帽子一扔,戴上共军的五角星帽,调转枪口就成“解放战士”了。
还有一些没死的,被共军团团围住,弹未尽粮已绝,大白天饿鬼哀嚎,下雨天孤魂游荡。有个战地记者到阵地上拍照片,专门拍尸体的手指,那些枯枝一样长着霉斑的手指,有的伸向天空,有的戳进泥土,有的插进胸前的肉里,造型五花八门。
副参谋长楚致远向军长廖峰报告,西线九团突围,一个团副带领七十多号人,头天渡过衢河武力进入二师防线,见什么抢什么,打死了二师警卫营副营长,还把医院的两头奶牛煮了。
廖峰脸色铁青,好半天才问,这伙人现在在哪里?
楚致远说,被二师师长韩博涛下令缴械,全都关在师部警卫营的马棚里。
廖峰眉头一皱,关在马棚里,马怎么办?
楚致远怔了一下,反应过来说,没有马了,全都吃到肚子里了……韩师长请示,要不要把这伙人送到军部。
廖峰牙疼似的哼了一声,送到军部?这伙土匪,送到军部干什么,来抢粮食啊。
楚致远说,我也认为不妥,韩师长怕是急疯了……仗打到这个地步,各级长官的脑子都不好用了。
廖峰阴沉沉地看着楚致远,脑子不好用了……你的脑子还好用吗?
楚致远惶恐地说,军座,我……我的脑子也不好用了。
廖峰仰起头来,看看天,看看远处,原地踱了几步,站定,目光在楚致远脸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一字一顿地口述几道命令:一、所有一线部队,死守现有阵地,凡擅自出击者,追究指挥官责任。二、凡突围归来零星部队,由接管部队长官酌情处置,无须向军部转送。九团归队人员,留下团副候审,其他人枪毙。三、请李秉章副军长亲自前去三十里铺地区,带上电台,军部警卫营以一个连的兵力护送,收拢一七九师。
口述完毕,廖峰看着远处说,搞点细粮,给老李带上。
楚致远目送军长,看见初秋夕阳下军长的背影,腰杆依然挺得很直,步子依然从容。楚致远有点伤感,眼窝一热,两行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的脑子还算清醒,军长的三条命令,其他两条都是废话,要一线部队死守,一个个饿得骷髅似的,拿什么死守?军长的意思,不是不让出击,而是不让到共军阵地上抬饭,可那是一道命令能够阻挡的吗?至于归队人员的死活,管他的呢,九团回来的那伙强盗,韩博涛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惟一要做的,就是向李秉章副军长报告军座的指令,寻找一七九师,找得到找不到,那是李副军长的事。
二
警卫营二连连长马直这几天一直琢磨一件事情,跑的决心是不会动摇了,问题是怎么个跑法,跑到哪里去,是向共军投诚还是回家种地,是带枪投诚还是带人投诚……这天半夜,马直把排长张东山和班长朱三召集到一起,挖出埋在地下的一坛小米,倒出一半,关上门熬了一锅稀饭,刚刚盛到碗里,还没有吃到嘴里,营长蔡德罕一脚把门踹开了。蔡德罕看着那锅小米稀饭,眼睛瞪得鸡蛋大,骂了一声,吃独食,屙驴屎。说完,不由分说扑到桌子边,端起一碗稀饭,一边吹气,一边转动着喝,转眼之间就把一碗稀饭喝完了,还舔了舔碗底。
马直站在一边说,营座,这一碗是我的……你要是觉得不够,那就……
蔡德罕说,深更半夜的,你们聚在这里干什么,是不是想跑啊,要真跑,也得跟我打个招呼啊,没准我跟你们一起跑呢,我胳膊腿还行,不会拖累你们。
马直惶惶地说,明人不做暗事,我们确实……
蔡德罕摆摆手,打断马直的话头说,马连长,我知道你对党国是效忠的,所以把这个美差交给你。
马直愣住了,看着蔡德罕。蔡德罕说,军长让李秉章副军长到三十里铺寻找一七九师,要我们派出一个连护卫,你马上到军需处领粮食。
马直怔怔地看着蔡德罕,“嗷”地一下嚷了起来,领粮食?我的天啦。
蔡德罕神秘一笑,马直老弟,老哥我待你不薄,你知道该怎么做。
马直明白了,心中一喜,双脚一碰,立正道,营座,我明白,领到粮食,我一定给你送一点。
蔡德罕说,哦,不说了,不说了,你看着办。
这样就说定了。马直喝完稀饭,让张东山和朱三跟着,到军需处领粮食。所谓的军需处,就是一个帐篷。军需处给他发的粮食,是十块豆饼,就是榨油之后余下的豆渣,这东西过去是用来喂牲口的。
马直对军需官说,我们吃这个也就算了,可是李副军长也吃这个?军需官说,李副军长的给养,由他的勤务兵保管,你们就不要操心了。马直说,那也不能只给这一点点啊,谁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七九师?军需官说,对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七九师,我给你多少算够?
马直说不过军需官,自认倒霉,把豆饼分了两块给蔡德罕派来的兵,这才带着一肚皮牢骚往回赶。
走在路上,朱三说,连小米都吃不上,还回去干啥,不如直接到共军阵地上,今夜就能吃顿饱饭。共军天天都在喊,啥时候过去啥时候吃萝卜炖肉。
马直咽了一下口水说,总得拖几条枪吧,带着豆饼去投诚,太寒酸了。
张东山说,咱们不是要护卫李副军长吗,到时候,咱们把李副军长带上一起投诚,那可是一份大礼,没准人人都能官升一级。
马直说,啊,把李副军长带上……你脑子被炸坏了吧,这个念头你想都不要想,想想都会挨枪子的。
张东山被吓住了,扭头四处看了看,对马直说,我也就是随口一说,你干吗说得那么吓人?
马直说,别胡思乱想了,更不要胡说八道,都回去做准备,每人发一斤豆饼,天亮前赶到军部。
三
警卫营的官兵都知道,李秉章副军长是抗战名将,在当年的沧浪关战役第二阶段,他是东线的敢死团团长,连续几次率部穿插鬼子的防线,身上有十几处伤疤。
关于李副军长的传说很多,沧浪关战役开打的时候,马直和他的兵还没有入伍。离他们最近的一次是太行山黄虎岭战斗,当时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了,但是占德州鬼子的一个联队声称没有接到命令,拒不投降。李副军长带领楚副参谋长在敌人据点外围开设前进指挥所,指挥一七九师和军部炮团以及警卫营对敌进行包抄,战斗打到白热化程度,李副军长亲率一个团从敌后攀岩穿插,同火速赶来的八路军一个团协同作战,将鬼子的援兵包围在不到三公里的桃花峡谷,经过一天一夜战斗,全歼黄虎岭日军一个联队和前来增援的日伪军近八千人。
那个时候,部队的士气多么高啊,可是,鬼子投降了,如今是和共军作战,部队已经不像部队了。
第二天天麻麻亮,马直就起床了,告诉执勤排长张东山,通知大家收拾行李,人走家搬。张东山鼓起眼珠子问,真不打算回来了啊?马直说,回啥,哪里都不是家,走到哪里算哪里。
到外面转了一圈,就回到连部打背包。人走家搬听起来很吓人,下层官兵的家,实际上就是一个背包,背包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就像马直在哪里,警卫二连的连部就在哪里一样。
比起蔡德罕和张东山那些人,马直要讲究得多,只要有条件,他就要洗被子,这是给楚副参谋长当勤务兵的时候养成的习惯。五灵大捷之后,部队在乔城休整,给他发了一条土黄色的新被子,原先的那条也没舍得扔,因为新被子发下来之前,有一个夜晚,一个女人跳到他的被窝里睡了一觉,那床土灰色被子里有那个女人的气味。
问题在于,他不能把两床被子都带走。营长跟他说得明明白白,要轻装。他把旧被子找出来,放到床上展开,情不自禁地扑到上面,使劲地吸了几口气,再把黄色的新被子翻到上面,将被罩剥下来,套在旧被子的外面。新被子固然好,但是颜色浅,用了一年多,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里,马直以他二十二岁的蓬勃雄壮的生命之笔,在被子上描绘了层层叠叠的山水画,因为吃不饱,有些日子没洗了,看起来花里胡哨的。如今,顾不上那么多了,大家都一样,谁也不会笑话谁。当兵的被子,有山水画是正常的,没有山水画,那才会让人笑话。
不到十分钟,马直就把“家”收拾利索了——最近两个月积攒的饷钱,一双布鞋,一支自来水笔,一块从日军尸体上搜来的怀表,一套换洗的军装、衬衫和两条短裤,牙刷牙粉……还有大约两斤小米,也装在袜子里,统统打进背包。当然,还有那个女人的气息。
早晨喝了一碗豆渣汤,马直就把“家”驮在背上,带领他的连队去向李副军长的副官曹强报到。曹强见马直身后只有三十多号人,皱起眉头问马直,怎么就这么点人?
马直立正回答,报告长官,阵亡了一些,跑了一些,能来的都来了。
曹强说,你这个破队伍,靠什么保护李副军长?
马直说,人少好啊,人少不费粮食……
曹强阴森森地看着马直说,楚副参谋长跟我讲,警卫营二连最有战斗力,连长马直脑子好使,没想到就这三十几个叫花子,怎么保护长官啊。
马直这才明白,蔡德罕跟他说的“美差”,原来是他的老长官楚致远亲自点的将,还是老长官好啊,关键时刻信任他马直。这么一想,心里就升起一股豪气,挺起胸脯说,曹副官你不要看不起我们这些叫花子,上半年黄虎岭战役,鬼子偷袭前进指挥所,就是我们二连,跟鬼子展开肉搏,我冲入鬼子堆里把身负重伤的楚副参谋长抢出来,背了七里地……我们二连,就是那次阵亡了三十多个人,到如今还没有补充,我们二连……
曹强打断马直的话头说,别你们二连了,就那几个人瘦毛长的兵,集合。
正说着话,李副军长从帐篷里走出来,看看马直和他身后的兵,看看帐篷外面的两匹瘦马,再看看正在喘气的嘎斯吉普车,对曹强说,车子就不用了,让他们回去。
曹强说,长官,让车子跟着,万一……再说……
李副军长没理曹强,走到两个电台兵面前,打量了一眼说,把帽子摘下来。
电台兵把帽子摘下来之后,马直才发现,原来是两个女兵,一个中尉一个少尉。再仔细打量,那个中尉他认识,副参谋长楚致远的侄女楚晨,就是在乔城跳进他被窝里睡了一觉的那个女人。一个月前马直还在军部机要处门口见过她,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鞋擦得锃亮,腰杆子挺得笔直,他不敢正视她,她却若无其事地喊了他一声,马连长,我看看你的手指。他赶紧逃开了。一年前他在楚副参谋长家里执行勤务,第一次见到楚晨,她就说过,这个军官的手指很干净。这以后,他又有几次见到她,每次擦肩而过之后,他就会躲在隐蔽处,从后面看她,看她笔直的裤线和齐步行进的屁股,感觉那就像一棵亭亭玉立的小树在移动,每一片树叶发出的声音都让他心驰神往。
可是眼前的楚晨,肥大的粗布军装罩在身上,就像一只鹅被罩在鹅笼子里。不仅头发剪短了,脸色也是黄中透灰,难怪近在咫尺,马直居然没有一眼认出她来。
这些胡思乱想从马直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不过两秒钟的工夫,两秒钟后他听见李副军长的声音,谁让你们来的?
楚晨立正回答,报告长官,是楚副参谋长派我们来服务长官的。
李副军长说,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吗?
楚晨说,寻找一七九师。
李副军长点点头说,哦,知道,很好,可是,这个任务,你们参加不合适……曹副官,马上把她们送回去,换两个男的来。
曹强踌躇了一下,正要回答,楚晨大声嚷嚷起来,长官,我们是国民革命军,男女是平等的,长官,你不能歧视妇女……
李副军长头也不回地说,回去,跟廖军长走,好好活着。
楚晨还想争辩,嘴巴张了几下,突然降低了声音,嘀咕道,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曹强对楚晨命令道,你们两个,赶快回去,向楚副参谋长报告,请他派两个男报务员,在姚家疃向我报到。
楚晨看着曹强,又看看李副军长,嘴里还在嘀咕,好好活着,这是什么意思?
李副军长没有理睬楚晨,走到马直身边,摸摸他的后背,掂掂他的背包,然后指着背包旁边的干粮袋问,这是什么?
马直大声回答,报告长官,是豆饼,我们的粮食。
李副军长说,哦,豆饼,很好。
马直正想说什么,李副军长已经转身了,走到一个看起来瘦小的士兵面前,问他,多大了?
小兵立正回答,报告长官,十七了。
李副军长又问,叫什么名字?
小兵回答,姚山竹。大山的山,竹棍的竹。
李副军长点点头说,哦,姚山竹,好名字,咬定青山不放松。
马直说,这是我们连队最小的兵。
李副军长问,怎么来的?
姚山竹说,抓来的,抽丁。
李副军长把手拍在姚山竹的肩膀上,侧脸对曹强说,走吧。
曹强赶紧上前,指着前方的一个村庄说,姚家疃,目前还有我军的一个营,我们从那里进入孙岗,再往前二十里,就是一七九师六天前的防地。
李副军长看着晨光里的村庄,点点头说,好,很好。
曹强向马直一点头,马直挥挥手,临时编组的两个班快速运动,在前面开路。马直带领一个班殿后。
李副军长没有骑马,跟大家一起走,他不说话,别人也不敢说话。马直数了数,队伍一共有四十号人,除了他的连队,还有李副军长的副官曹强,两个卫兵,两个马弁,还有两个电台兵。乍看起来,也是浩浩荡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