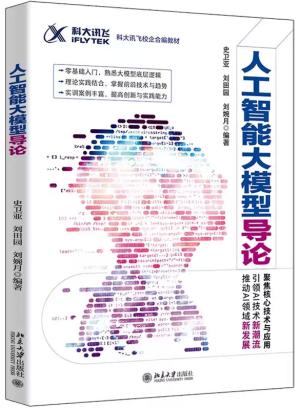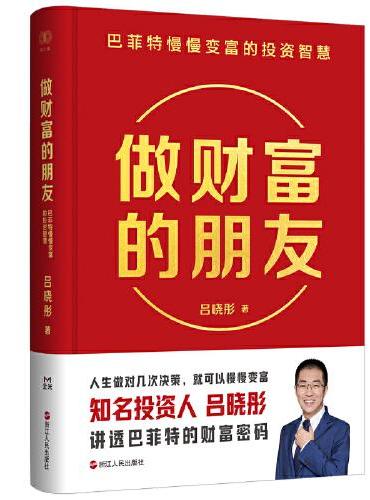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功能训练处方:肌骨损伤与疼痛的全周期管理
》 售價:HK$
140.8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HK$
97.9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HK$
74.8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HK$
75.9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HK$
85.8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HK$
74.8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HK$
75.9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HK$
82.5
編輯推薦:
本书由田晓菲主编,书名仿照宋人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而提名为《九家读杜诗》,但却是由九位当代海外汉学界的学者来进行杜诗的解读。书中尤其试图挖掘杜甫流亡于夔州时的作品,不同于“三吏三别”那样耳熟能详的名篇,夔州时期的“杜诗”则呈现了诗人真实的生活——买菜种菜、修理篱笆、忧虑水患、教育孩子,等等,由此我们也能品读出杜甫的另面,了解他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真实和复杂。
內容簡介:
本书仿照宋人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而名为《九家读杜诗》,由田晓菲主编,收录宇文所安、艾朗诺、倪健、王德威、罗吉伟、陈威、潘格瑞、卢本德等九位学者,从九个角度对杜甫诗作进行细读的文章。呈现出杜诗中地方与帝国、政治与个体、宗教与文学间的微妙张力,并将文本阅读延展到诗歌和视觉艺术、传统和现代等话题上,触及到当代对杜甫接受与再造。
關於作者:
田晓菲,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早期中古中国》杂志主编。著有《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行旅写作》《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秋水堂论金瓶梅》《“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影子与水文:秋水堂自选集》等。英文译著包括《微虫世界:一部太平天国回忆录》《颜之推集》。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参与主编并撰写《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公元前1000-公元900年)》。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获哈佛大学卡波特奖、哈佛大学文理研究学院门德尔松优秀导师奖、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孟旦百年中国艺术人文研究课题奖。
目錄
中文版前言
內容試閱
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