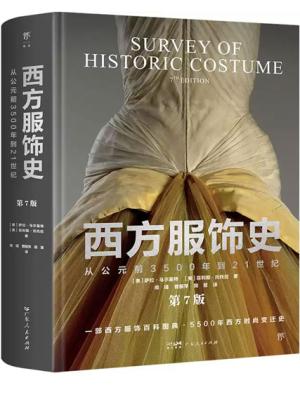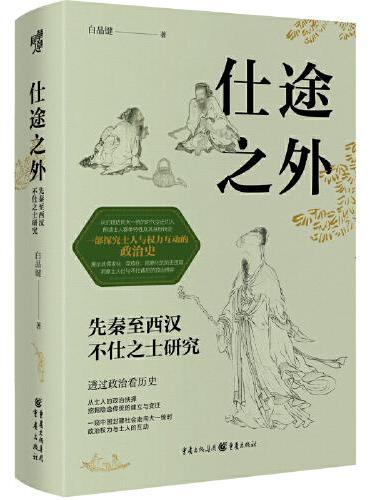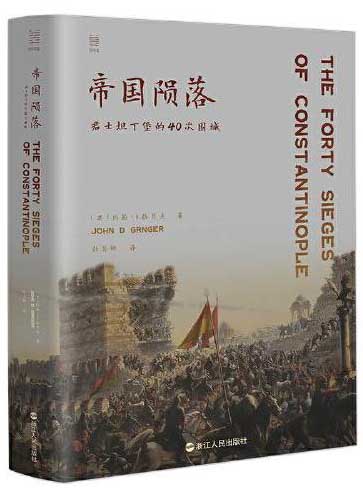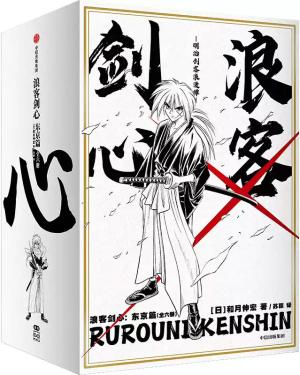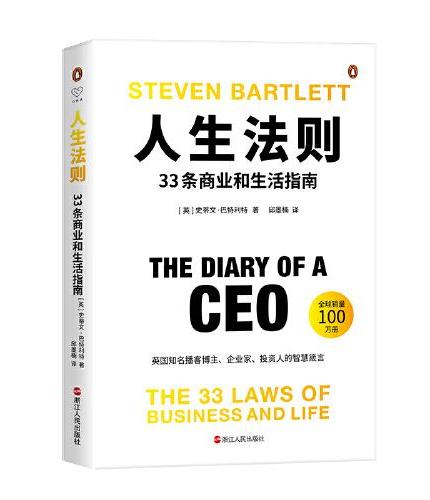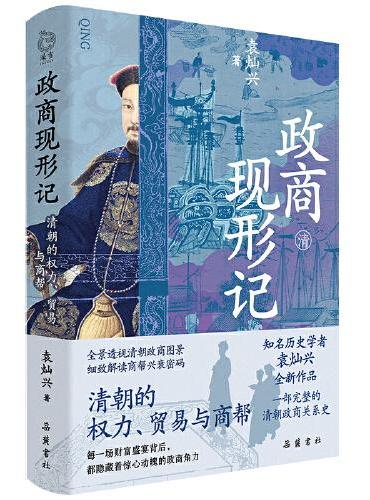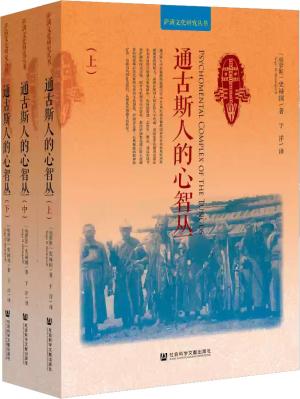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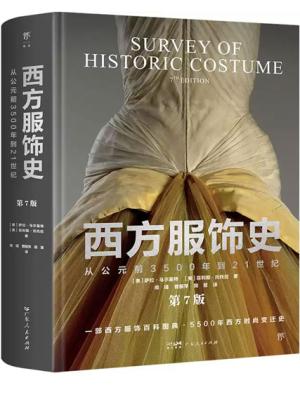
《
西方服饰史:从公元前3500年到21世纪(第7版,一部西方服饰百科图典。5500年时尚变迁史,装帧典雅,收藏珍品)
》
售價:HK$
4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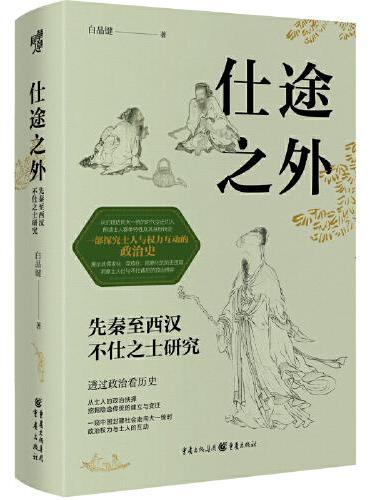
《
仕途之外:先秦至西汉不仕之士研究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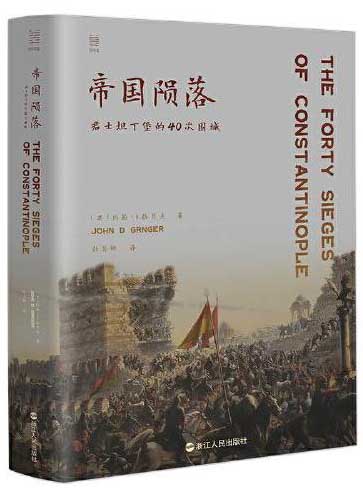
《
经纬度系列丛书·帝国陨落:君士坦丁堡的40次围城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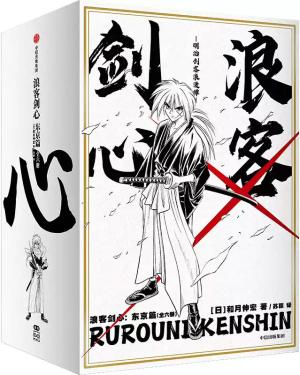
《
浪客剑心:东京篇(全6册)
》
售價:HK$
25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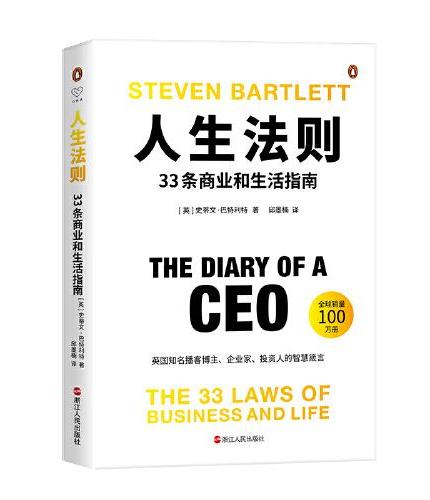
《
人生法则:33条商业和生活指南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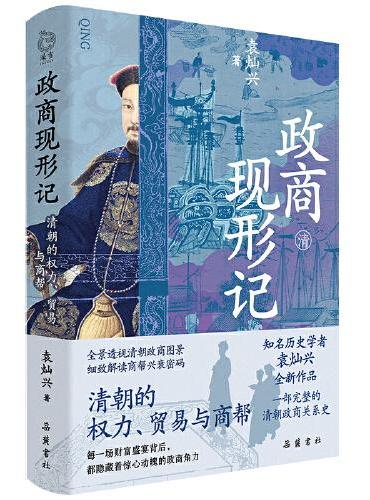
《
政商现形记: 清朝的权力、贸易与商帮
》
售價:HK$
85.8

《
早期干预丹佛模式辅导与培训家长用书
》
售價:HK$
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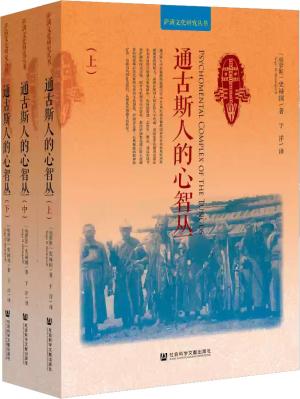
《
萨满文化研究丛书——通古斯人的心智丛(全三册)
》
售價:HK$
351.6
|
| 編輯推薦: |
|
鬼故事和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向来是为学界所忽略的话题,本书作者别出心裁地关注这些小说中的超自然书写,并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超自然书写的背后,竟然有着众多科学依据。本书不仅适合文学领域的专业读者,为理解柯南·道尔、爱伦坡等人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也适合对维多利亚时代发生的社会变化感兴趣的读者。
|
| 內容簡介: |
|
这是对19世纪两种非常流行的小说类型,即鬼故事和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的原创性,以及它们在当代视觉和视觉理论背景下的惊人相似性的研究。斯尔詹·斯马伊奇认为,要理解作家如何呈现鬼魂目击者和侦探,必须考虑这些作家所使用的同时代科学家、哲学家和唯灵论者的观点:这些观点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例如眼见是否为实,我们所“看到”的究竟有多少内容只是推测出来的,是否有其他(直觉的或精神的)观看方式,使我们能够感知身体感官无法接触到的物体和存在。这本书将对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在文化中的理解,以及文学利用各种知识的方式做出重要贡献。
|
| 關於作者: |
斯尔詹·斯马伊奇(Srdjan Smaji?)
生于1974年,杜兰大学维多利亚文学博士,1998年至2010年先后在杜兰大学、新奥尔良大学和弗曼大学教授文学。多次在《英国文学史》《文本实践》和《小说:小说论坛》上发表学术论文。现为独立学者,另著有小说《我们渴望水》(2015)。
李菊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北京大学英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英国18、19世纪文学,英美戏剧等。
|
| 目錄:
|
致谢
缩略语一览表
引言
第一部分 外视觉,内视觉:看见鬼魂与鬼故事
第一章 鬼故事的语境化
第二章 视觉幽灵的兴起
第三章 内在视觉与心灵光学
第四章 “在古老信仰和现代怀疑之间”
第二部分 看见即阅读:视觉、语言和侦探小说
第五章 视觉学习:视觉与维多利亚认识论
第六章 窃视证和被视恐怖症:坡的读者型游荡者
第七章 《月亮宝石》中的污渍、污点和视觉语言
第八章 符号学与百科全书知识:以夏洛克·福尔摩斯为例
第三部分 进入看不见的世界:科学,唯灵论和神秘侦探
第九章 侦探小说的不可思议
第十章 光,以太和看不见的世界
第十一章 内在视觉与超自然侦查:勒法弩的马丁·赫塞柳斯
第十二章 其它维度、其它世界
第十三章 心灵侦探和灵魂医生
尾声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
| 內容試閱:
|
弗格森太太是吸血鬼。
关于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两位可靠的目击者分别在不同场合看到她从自己的男婴脖子上吸血。“一次……保姆离开孩子几分钟。婴儿一声响亮的啼哭,仿佛感到了疼痛,把保姆召唤了回来。保姆跑进房间时,看到她的雇主—弗格森太太趴在婴儿身上,显然在咬他的脖子。”显然?当然不止如此:“脖子上有处小伤口正向外渗出一股鲜血。”婴儿母亲贿赂保姆让她对所看到的情况保持沉默,这种行为除了表明她承认有罪以外很难有别的解释。自那以后保姆密切关注婴儿母亲,婴儿母亲则密切关注保姆,两人都密切关注婴儿。“保姆日夜保护着孩子,而沉默警惕的母亲日夜如同狼伏击羊一样伺机出击。”(“SV”,第537页)或者说就像一个吸血鬼在等待猎物。
由于担心孩子的生命安全,保姆便向弗格森先生坦白了一切。弗格森先生确信他妻子既是爱意满满的配偶也是尽心尽责的母亲,并对保姆的无耻指控感到愤怒,于是轻蔑地告诉保姆“她是在做梦,她的这些猜疑都是疯言疯语,不允许她这样诋毁中伤女主人”(“SV”,第537页)。然而,片刻之后,他的亲眼所见让他不得不相信保姆所讲述的疯狂故事。“他们在说话时突然听到一声痛哭。保姆和主人一起冲进婴儿室。福尔摩斯先生,想象一下他的感受,弗格森先生说道(用第三人称称呼他自己),“当他看到他的妻子在婴儿床边刚从跪姿站起来,看到孩子露出的脖子上和床单上都是血。他把妻子的脸转过去对着光,看到她嘴上全是血,吓得大叫一声。就是她—毫无疑问是她—吸了可怜孩子的血。”(“SV”,第537—538页)眼见为实:弗格森太太是吸血鬼。
但是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保姆和主人看到的一定只是看上去像吸血鬼行为,而真相与所有表象都相反。我们知道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事先就看过了故事的结局,哪怕我们有些人(包括我在内)会带着好奇忍不住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读的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在福尔摩斯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吸血鬼这样的东西。“废话,华生,废话!”福尔摩斯在少有的一次发脾气时这样喊道,“我们该拿这些只能靠用木桩打入心脏才能让他们待在坟墓里的行尸走肉怎么办?真是愚蠢。”华生并不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然而他提出,“吸血鬼不一定非得[是]死人”,而“[一个]活人也可能有这个习惯”。他回想起自己曾经在什么地方读过“老人为了保持年轻去吸食年轻人的血液”的传说。尽管华生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但这个传说为理解社会偏常行为如何被看作反常行为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不寻常的行为如何被不着边际地转变为反常的或超自然的行为,这种转变又是怎样始终取决于权力和权威的判断。某一行为是正常还是反常,取决于这种权力何时何地实行。把这种水平的社会学洞察力归功于华生大概是言过其实了。无论如何,福尔摩斯对任何形式的他者或文化批评理论都不感兴趣。对他而言,老年人吸食年轻人血液的故事带有血腥的哗众取宠和迷信缠身的传闻味道,在这些传闻里,奇怪的事让位于神秘的事,超自然现象就从后门悄悄潜入。他坚持认为,“这样的故事坚实并可信地存在着,而且必将这样保持下去。世界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复杂了,其中没有鬼魂的位置”。(“SV”,第535页)
的确,吸血鬼、鬼魂和这一类故事不能也不应该出现在侦探小说中。如果福尔摩斯真的认为弗格森太太可能是吸血鬼,那么他之前视为“废话”和“愚蠢”的故事就同样有一定的真实性了,且不管这个谜案最终是否有理性的(非超自然的)结局,我们所读到的都不是我们所习惯的侦探小说。实际上,它可能根本就不是侦探小说(只是看上去像而已),而是对侦探小说的恶意模仿。它只保留了这种体裁的表面特征,但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都与侦探小说相去甚远;它扩展了其说服性理论、合理推论和合法演绎的范围,以至于本来会被不假思索地拒绝的结局(吸血鬼、鬼魂和类似的“废话”)都变得十分可用了。如果这一结局适用于道尔后期作品之一的《萨塞克斯吸血鬼案》,那么它是否也适用于之前的故事?或许是因为被钟爱的理性结局总是会过分简化更大的(故意被模糊化的)宇宙之谜的反攻性,挑战了侦探小说对这个世界可信度的理解,因此那些让人头疼的开放式结尾就在侦探小说中被藏了起来,受到了系统性的删减?福尔摩斯对自己怀疑的案件就发出讽刺性的“干笑”,这既“融合了现代和中世纪的特点,也融合了事实和疯狂的想象”(“SV”,第534页),还萦绕着他对这种不合情理的融合后果的焦虑,那个被侦探小说所拒绝的手法就凭此混进了这一体裁。哪怕只是提一下超自然现象,哪怕它立刻被摒弃不用,也足以使这位侦探感觉到错乱,不只是历史时代上的错乱(他被传送到了中世纪?),也是体裁上的错乱:“但我们似乎真的被传送到了格林童话故事里”(“SV”,第535页),他气恼地向华生抱怨。福尔摩斯的抱怨反映了侦探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元文本关怀,即担心这一体裁无法保持纯粹;担心这种让本当保持理性的福尔摩斯如鱼得水的理性体裁处处为超自然现象、神秘学和非理性所污染;担心定义侦探小说特定模式的认知原理和调查步骤与这种体裁所傲慢认定的那些“废话”和“愚蠢行为”一类的东西发生深度牵连。
《萨塞克斯吸血鬼案》预示了这本书如何结束:我想展示的是鬼故事和侦探小说之间的“切换”(用福尔摩斯的话说),或者是它们之间的杂糅。文学体裁没有完全纯粹的,这种特定的混合模式在临近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豁然出现,1924年出版的道尔的吸血鬼/侦探小说,在我将标注的历史时间轴上,就是一个方便的时间坐标。更为重要的是,道尔的故事,凸显了相信眼睛所见事实和怀疑眼睛所见事实之间的矛盾,这里彼此矛盾的认可和对“眼见为实”概念的摒弃证实了凯特?弗林特的说法:“尽管视觉……对于维多利亚人至关重要,但它仍然是个问题重重的类别。”我对此的贡献在于:考察鬼故事和侦探小说是如何与那些关于视觉的当代哲学和科学进行对话,并在对话中建构起来的;发现这两种体裁告诉了我们哪些有关维多利亚时期的视觉理论;以及厘清这些理论又是如何在文学中得以体现并如何促成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形成的。有时我认为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影响有直接线索可寻,例如生理光学和鬼故事之间的联系。在文中的其他地方我并不这样认为,因此我会把哲学—科学和文学文本并置一处,以考察不同形式的话语是如何处理相同问题的,例如维多利亚认识论者和侦探小说作家共同关注的推理与阐释的问题。
第八章:符号学和百科全书知识
如果对于福尔摩斯来说,看见意味着即刻知道,这是因为他确信(道尔也确保会提醒他的读者),在侦查工作中“知道”是在“看到”之前。“偶尔”,福尔摩斯向华生承认,重复了杜宾对于被迫观察的抱怨,“一个更复杂一些的案件出现,然后我必须东奔西跑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事物”。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物总是会看到其他人错过的内容,侦探在存储和检索信息方面的广泛的百科全书知识和技能保证了这一点。“你看,”他对华生吐露道,“我有很多应用于这个问题并奇妙地有助于事情的特殊的知识。”(SS,第16页)福尔摩斯一眼就能够辨别任何已知品牌的雪茄或烟草的灰烬(SS,第28页),因为他已经把“了解事物”作为他的职业(“CI”,第254页)。在这项业务中,训练至关重要。“对于训练有素的眼睛,特里奇努波利方头雪茄(Trichinopoly)的黑色灰烬与金盏花的白色绒毛之间的区别,正如卷心菜和土豆之间的区别一样大”,正如任何人读过福尔摩斯的权威专著《关于各种烟草灰烬的区别》都会知道一样(SF,第110页)。“我已经训练自己去看别人所忽视的东西”(“CI”,第254页),福尔摩斯对他的一位客户说。重要的是不要忽视这一点,即福尔摩斯严格训练的不是视力,而是观察者: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数据存储和检索技术,他就不可能有演绎推理的惊人成就。福尔摩斯反复给华生指出观察和看见的关键区别—“你看见了,但你没有观察,区别非常明显”;“你没有观察到,但你看到了……我既看到也观察到了”(“SB”,第211页)—因此不是看得仔细或粗心的问题,而是知不知道去寻找什么和看向什么。
米歇尔?福柯比任何人更有说服力地描述了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一个19世纪新的想象空间的发现”。福柯告诉我们,19世纪的怪诞、梦幻般的想象力越来越多地被书籍而不是鬼魂占据:
鬼魂出现的领域不再是夜晚—理性沉睡之时,或者欲望来临前的不确定的空白之时,而恰恰相反,它出现在人们觉醒,不知疲倦的保持注意力、热心的博学和持续的警惕之时。从此以后,梦幻般的经历来自印刷符号的黑白表面;来自封闭和伴随着一连串被遗忘的词语打开的多尘的书卷;幻像精心地部署在图书馆的书库中,成排的书,标题排列在书架上,形成一个紧密的封闭空间,既把不可能的世界限制在这里,也释放了它。想象的世界存在于书和灯之间。怪诞不再是心灵的财产,也不是在自然的不和谐中发现的。它从知识的准确性演变而来,其珍宝潜伏于文件之中。
福柯自己是一个档案爱好者,他低估了19世纪奇幻文学的超自然尺度,我认为这与“印刷标志的黑白表面”产生的异象体验不相容。尽管如此,他仍然强调了这一时期的藏书癖冲动和新档案意识的兴起。在杜宾的故事中,光线昏暗的图书馆是逃离感性世界的庇护所;不同的是,福尔摩斯的图书馆是一个空间,在这里新鲜奇怪的事物在遇到外部世界之前变得非常熟悉,通过书面文字的转变,成为一个令人宽慰的先验亲密行为。“当然有细节要填写,”福尔摩斯有一次解释说,“但是我对所有主要事实非常确定,就像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它们一样”。(SS,第50页)对《月亮宝石》中梦魇般的符号学景观,专业和业余的调查人员偶尔会做出正确的推测,而且人们一直处于遇到一个空白的、谦逊的能指的危险之中,这个危险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变成了一个符号学的梦幻之地,一个关于详尽百科全书知识和无限档案资源的幻想,确保任何线索都不会被忽视或误解。道尔使这个梦幻之地与空间有限的心理地形兼容,可能会小心翼翼地突破读者轻信的极限。在《血字的研究》开篇页中,有一段福尔摩斯向华生做出解释的著名话语,声称虽然人们能够学习的东西是无限的,但人们可以记住的却是有限的:
我认为人的大脑本来就像一个空的阁楼,你必须用你所选择的家具来装满它。一个傻瓜收进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木材,所以对他而言可能有用的知识被挤出来,或者最多也是混杂了很多其他东西,所以他就很难拥有有用的知识。现在,技巧娴熟的工作人员对于收进大脑阁楼的东西非常谨慎。他只有一些可以帮助他工作的工具,但是这些工具的种类繁多,而且排列整齐。有人认为这个小房间有弹性的墙壁,并且可以在任何程度上扩大,这是错误的。依靠它,有时每一次增加新知识,你会忘了你以前知道的东西。因此最重要的是,不要用没用的事实排挤掉有用的事实。(SS,第11—12页)
福尔摩斯在其他地方重申了这一点,突出了记忆和档案知识的共生关系,淡化了实证观察的作用:
研究可能会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使所有那些通过感官帮助寻求解决方案的人感到困惑。然而,为了使这项技艺达到最高水平,推理者应该能够利用他所知道的所有事实;这本身就意味着,你会很容易地看到,拥有所有的知识,即使在这些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的时期也是一个有点罕见的成就。(“FO”,第300页)
书房中的工作为动手实地工作铺平了道路(并在某些情况下使得实地工作没有必要)。然而,获得所有知识是不可能的,但是,福尔摩斯提出了一个更可信的情景:
然而,一个人拥有工作中可能对他有用的一切知识并非不可能,我自己已经努力去做了……我现在说的和以前所说的一样,一个人应该在他的大脑阁楼中放置他可能使用的所有家具,其余家具他可以放在图书馆的储藏室里,如果想要的话,他随时能够拿到。(“FO”,第300页)
侦探“大脑阁楼”的存储容量会受到限制,“图书馆的储藏室”却不会—特别是如果这个想象中的图书馆放置的不只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书籍,而且包括可以买到或借用的书籍。福尔摩斯对于哪些书放在家里和哪些书存在脑子里一样细心,通常他只会指向他的书架说,“请把你旁边架子上以字母K开头的美国百科全书递给我”(“FO”,第300页),他吩咐华生,好像是给他的私人图书馆员下命令。书店、档案馆和图书馆无法获取的信息可以从福尔摩斯的记录中找到:“多年来,他采取了一个给所有关于人和事物的段落附加摘要的系统,因此很难说出一个他无法立刻提供信息的主题。”当华生在福尔摩斯的索引中查找艾琳?艾德勒时,他发现,“她的传记夹在希伯来犹太教拉比和一位写过深海鱼类专著的职员指挥官之间”(“SB”,第215页)。福尔摩斯的索引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信息来源,也是一种罗盘或星盘,是传记和参考书目的导航工具。
福尔摩斯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收藏者、贪婪的信息消费者、索引制作者,和关于如烟草灰烬和文身等一些生僻主题的专业知识专著的作者(他不得不写这些专著,并不是因为它们可能成为畅销书,而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图书馆藏书架上的空白)。道尔笔下的侦探也会出现符号学焦虑的症状。在某种程度上,在福尔摩斯详尽的索引的字里行间,他对晦涩的知识领域的权威贡献之后(例如,福尔摩斯有可能想象出灰烬学和文身学),读和写的强烈欲望是一种机制,以应对新信息范围不断退缩的焦虑:无论人们知道多少信息,无论公共或私人档案馆有多少信息,总是会有新的事实被收集,被编入索引并整合到现存的知识体系中。无论是在大脑阁楼还是图书馆的储藏室,存储空间总是有限的。就像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动力一样,德里达写道,“档案始终有效,并且先验地反对自己”因为它把“什么是可归档的”限制为“什么值得归档”,排除某些事情以容纳其他事情:“所有档案室都有堆放东西的空间,都有技术的重复,都具有某一外在性。没有不具有外部空间的档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