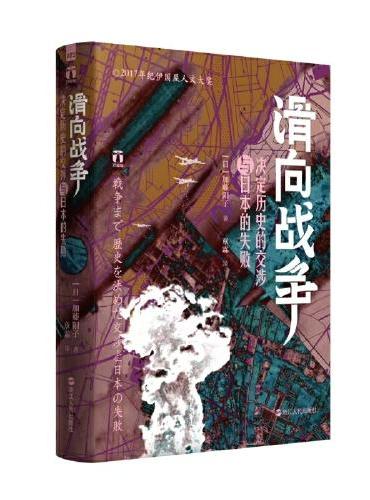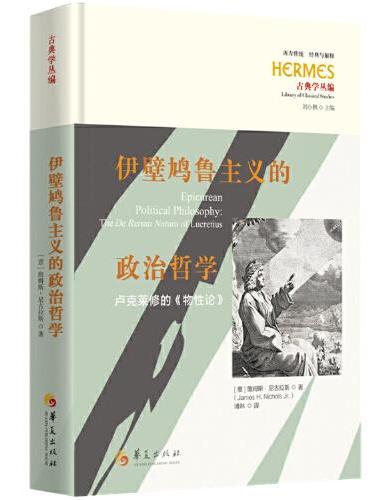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
》 售價:HK$
96.8
《
你可以有情绪,但别往心里去
》 售價:HK$
46.2
《
汴京客
》 售價:HK$
65.8
《
好望角·滑向战争:决定历史的交涉与日本的失败
》 售價:HK$
107.8
《
八千里路云和月(白先勇新作!记述我的父亲母亲并及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 售價:HK$
68.2
《
教师助手:巧用AI高效教学(给教师的66个DeepSeek实战技巧,AI助力备课、教学、练习、考试及测评)
》 售價:HK$
75.9
《
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哲学 : 卢克莱修的《物性论》
》 售價:HK$
68.2
《
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新经济结构
》 售價:HK$
152.9
編輯推薦:
传说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是从伊甸园中流出来的,它们冲刷出的两河流域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在这里,出现了最早的城市文明。
內容簡介:
自19世纪亚述学兴起之后,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长达百余年的研究,让西方人在经历知识和信仰的文化震动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起源,重新认识古希腊、希伯来文明与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
關於作者:
编者、作者:斯蒂芬妮·达利(Stephanie Dalley),英国亚述学者、古代近东学者,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亚述学施利托(Shillito)研究员和萨莫维尔学院荣誉资深研究员。她整理发表了诸多出土于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楔形文字文献,因研究巴比伦空中花园而知名,提出空中花园位于尼尼微,建成于辛那赫里布统治时期。她在多篇学术论文中探讨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影响。
目錄
缩写说明 / 001
內容試閱
引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