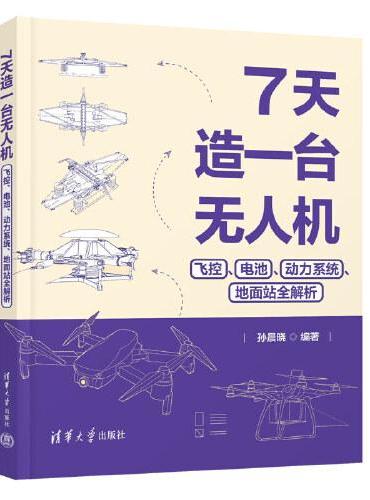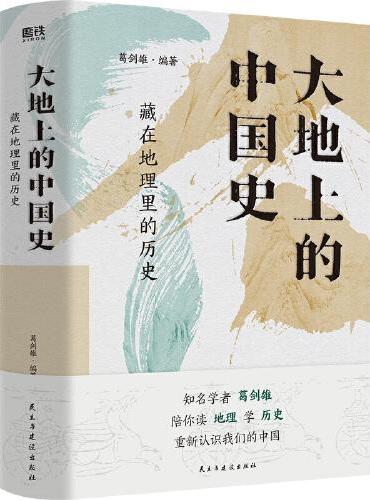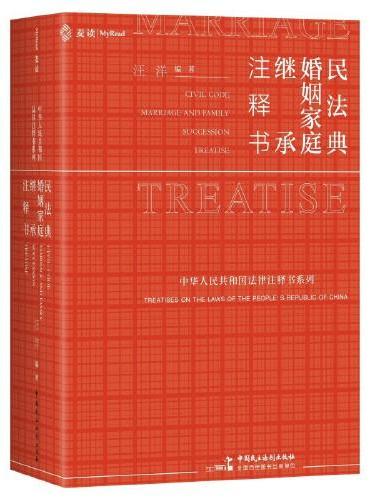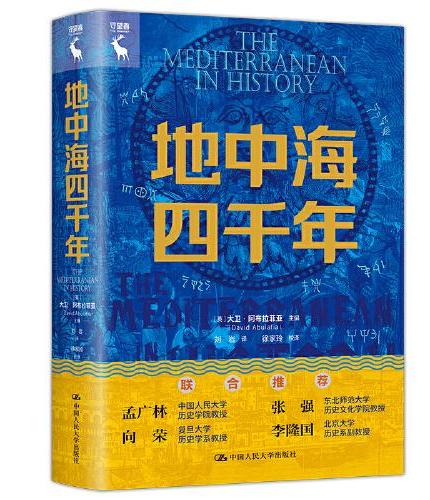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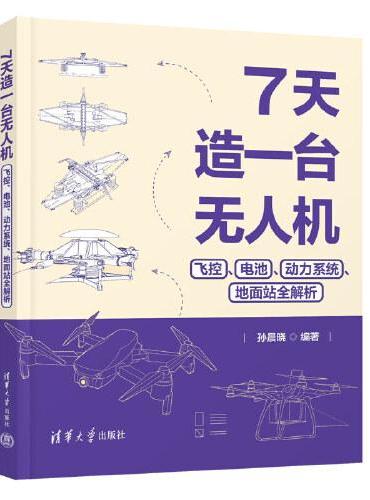
《
7天造一台无人机:飞控、电池、动力系统、地面站全解析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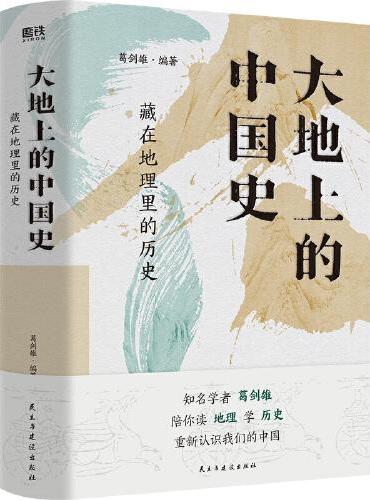
《
大地上的中国史:藏在地理里的历史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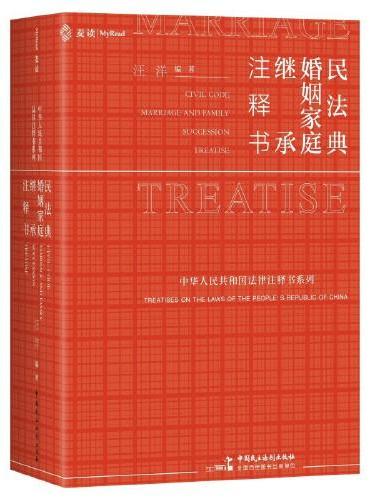
《
《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注释书》(家事法专用小红书,一书尽揽现行有效办案依据:条文释义+相关立法+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地方法院规范+权威案例,麦读法律54)
》
售價:HK$
1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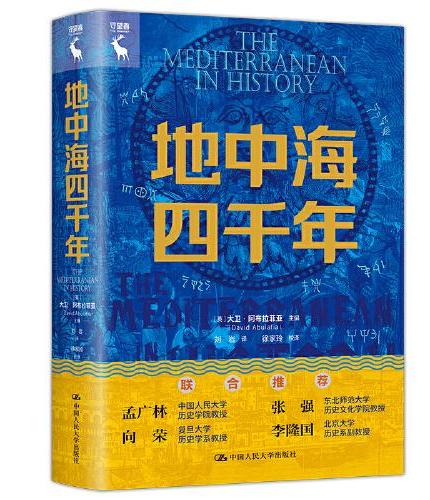
《
地中海四千年
》
售價:HK$
184.8

《
君子至交:丁聪、萧乾、茅盾等与荒芜通信札记
》
售價:HK$
68.2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HK$
41.8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HK$
74.8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HK$
54.8
|
| 編輯推薦: |
实力作家明开夜合人气救赎力作
超甜年龄差 全新番外 独家放送
宁樨遇见温岭远,
当真就应了那句名言——
年少时不能遇到太过惊艳的人。
伪叛逆少女x温柔系中医
你如白塔孤高,亦如玫瑰热烈。
|
| 內容簡介: |
宁樨的叛逆期来的有点晚。
起因是父母的婚姻一拍两散,导火索是奶奶生病,父亲宁治东却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人。
宁樨一个人带着奶奶去看病,然后就遇见了温岭远。
于是,宁樨的叛逆期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延绵而漫长的暗恋……
“你记不记得,我十八岁那年,曾经送过你一束花。”
“卢茨克玫瑰,你说那是世界上唯一象征友谊的玫瑰。”
“我骗你的,卢茨克不产玫瑰。”
“我知道。”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明开夜合
殊无天赋,但愚钝虔诚。
光阴误尽,天长路远,仍有诗酿酒,有心织梦。
已出版《我爱的人》《落雪满南山》《春天的十个瞬间》《白夜恋人》《白杨少年》等十几部长篇小说。
微博@明开夜合盒子
|
| 目錄:
|
玫瑰白塔
明开夜合/著
目录
第一章 霜降
第二章 立冬
第三章 大寒
第四章 清明
第五章 寒露
第六章 惊蛰
第七章 春分
第八章 谷雨
第九章 大暑
第十章 小雪
第十一章 大雪
第十二章 立春
第十三章 小满
番外
|
| 內容試閱:
|
玫瑰白塔
文/明开夜合
宁樨后来回想起,在青杏堂见到温岭远的前一天晚上,她曾经做过一个梦。
梦里有座高耸入云的白塔,在很远的地方。
她这辈子没尽力追逐过什么,除了那座塔。她跑了很久,它仿佛触手可及,可仍然遥在天边。
想起第一次见面,宁樨说,你的名字有种“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气质。
那时候不觉得是谶言。
——题记
第一章 霜降
阿婆的脖子疼了三天,第四天歪着脑袋连行动都变得困难,这才求助宁樨。
宁樨给宁治东打电话,没人接,她在他书房的抽屉里找到一把车钥匙,开车将人载去医院。排了半小时队,前面还有三个号。
阿婆说:“樨樨你去学校吧,要迟到了。”
“没事,我已经请过假了。”
门口虽贴着硕大的标语“请按号入内”,却仍有人携家带口直往里闯。宁樨气得把人一拦:“叫到你的号了吗?”
不知是病人还是病人家属,把装着CT片子的塑料袋一扬,快要怼到宁樨脸上:“医生说了,拿到片子直接进去!”
阿婆是息事宁人的性格,赶紧去拽宁樨:“樨樨,没事没事,我们等等,快排到了。”阿婆一动又牵扯到筋骨,疼得“嘶”了一声。
宁樨赶紧去扶阿婆,看着那人趾高气扬地走进去。
半小时后,才终于轮到阿婆。
医生在阿婆的脖子处揉一揉,捶一捶,按一按,说可能是颈椎引起的,看不出什么,要拍个核磁共振。医生敲键盘写病历,往打印出来的纸张上刷刷写了几行字,让宁樨去放射科预约。
“今天能拍得到吗?”
“要问放射科,估计不能。”
“可是我阿婆很疼。”
“我开点药,先用着,等核磁的结果出来,你拿过来给我看。”
“还要再挂号吗?”
“挂一个吧。”
“可是刚才就有人拿着结果直接进来了。”
医生看她一眼:“那你到时候直接进来,我一三五上午看诊。”
放射科说,三天后的下午来做。
宁樨交了钱,去拿药,还好现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缴费,能省掉再排队的时间。
医生开了止痛药,加上三贴膏药。在医院门口,宁樨当场拆了膏药给阿婆贴上。阿婆头发半白,发丝软软的,穿一件焦糖色的线衣,衣服上有太阳晒过的味道。
宁樨突然想要哭。
“阿婆,你觉得怎么样?”
阿婆说:“有点凉。”
“有效果吗?”
“还好,估计没那么快。”
开车回去的路上,阿婆说:“联系不上你爸?”
“嗯。”
“他可能在忙,做生意都挺忙的,樨樨你也不要怪他。”
宁樨不置可否。
车经过一个叫做“青杏堂”中医馆的地方,宁樨把车慢下来,犹豫片刻,靠边停车,拿出手机,在点评类APP上搜索出“青杏堂”,接着点开了用户点评页。
“半月板损伤,做了四次针灸,效果很明显。”
“听朋友介绍,说温老医生是圣手,专程慕名前来。我的泛发性湿疹在医院治了好久,一直反复。到温老医生这里开了三副药吃,现在状况已经好多了。”
“医馆环境清雅,医生很有耐心。”
……
宁樨又问阿婆:“脖子感觉好点了吗?”
阿婆按着贴膏药的地方,神情有点为难,好像不知道该不该撒谎。
宁樨把车停稳,替阿婆拿包:“我们下去看看。”
三年前,阿婆和阿公还住在老家。阿公去世之后,阿婆搬到南城来生活,却始终不太适应。
飞驰的汽车于她仿佛钢铁猛兽,站在斑马线前,她比第一回单独去上学的小学生还要紧张。直到人行横道对面的红灯变成绿灯,宁樨才挽住了阿婆的手,说:“阿婆,走。”
阿婆放下心来跟着走。她这位孙女,长相冷冷清清的,虽看着不爱搭理人的样子,实际上手掌热乎着呢。
青杏堂的招牌对着马路这一边,进门却要绕去后方。穿过一条两侧种着竹子的石板小巷,便看见一扇大门,门前有一个院子,种了一树不知道什么品种的紫红色小花,院子里有石桌石凳,草丛的石灯笼上长满了青苔。
推开门,入眼的是宽敞的大堂,深棕色的木地板往里一直延伸到很深的地方。大堂的正前方有一面青砖墙,上面悬挂着一块黑漆牌匾,上书银钩铁画的“青杏堂”三个大字。牌匾的前方有一张木质大长桌,堂里两侧各摆放两张太师椅,供人休息。
大堂左侧的一面墙上,悬挂着医馆从医人员的照片和简单履历;右侧有一扇小门,悬着一面竹青色的布帘,后面似乎是药房。
宁樨闻到了中医馆那各种药材混在一起的独特气息——清冽之中混着苦味。
她张望许久,不知道该往哪边走,直到那布帘被掀起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孩走出来:“看诊的吗?”
宁樨点头。
年轻女孩将她们领到左侧走廊的第一间小室里,门口和室内之间被一块木格栅的屏风隔开了,同样是深棕色的木地板,但因临着窗户,比大堂里敞亮。
宁樨和阿婆在太师椅上坐下,等了三分钟,门口传来脚步声,屏风外人影晃动。
紧接着,一个穿白色大褂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身形颀长,眉目清隽,有种冷玉沉金的气质。
宁樨望着他眨一下眼:“我认识你,你是我爸的朋友。”
男人微怔,目光往她脸上看,仿佛很疑惑。
宁樨说:“我爸是宁治东。”
“哦,宁樨。”温岭远微微笑了,“好久不见。”
不怪他不记得,他们只见过一次面,四年前,宁樨十三岁,在一个饭局上。
宁樨都忘了当时自己为什么会被带去,那个饭局沉闷、冗长又无聊。她恰好坐在温岭远旁边,他是她环视过一圈之后,发现的看起来最正常的大人。所谓的正常是指,他不像其他人酒过三巡之后丑态毕露,扯着脖子面红耳赤地划拳劝酒,称兄道弟。他始终神色平静,有些置身事外的意思。
宁樨觉得他可能也无聊,不然不会在她费力地掰着从果盘里拿下的橙子时,主动与她攀谈。
他替她剥橙子,问她叫什么名字。
“宁樨,木樨的樨。”
“秋天出生的?”
宁樨惊讶了一下,因为他没有问“木樨”的“樨”是哪个“樨”,这分明是常识,但她遇到过的好多蠢笨如牛的男生却都不知道。然后在她告知“樨”字怎么写之后,那些无知的男生还会附赠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考试的时候,其他同学都在写第三道题了,你还在写名字吧。
宁樨点头,问他:“那你叫什么?”
“温岭远,山岭的岭,遥远的远。”
宁樨说:“你的名字有一种‘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气质。”
也是因为宁樨这个独特的比喻,时隔四年后,温岭远才能想起来自己确实与她见过。四年时间足以让一个青春期的女孩脱胎换骨,眼前的少女亭亭玉立,依稀只剩一点十三岁的影子。
“这位是你……”
“阿婆。她脖子疼,疼了三天了。医院要拍了核磁共振才能确诊,我担心阿婆疼得受不了。”
温岭远点头:“那你去隔壁房间等一等,我先给阿婆看诊。”
宁樨站起身,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立场讲清楚:“我同学都说,中医都是骗人的。”
温岭远神色未变,看着她:“你选择过来看一看,就说明你还是愿意相信一次的。”
宁樨站起来,站在他面前时,才意识到他有多高。宁樨一米六七,却还是要使劲地仰头去看他。
“那我能相信你?”
“如果没有把握,我不会拿似是而非的话搪塞你,也不会要你付任何诊金。”
宁樨满意这个回答,心里松快了一点。
隔壁房间是茶室,木椅上摆放着杏仁色的抱枕,沿墙壁置放了一个低矮的书架,原本以为是放着与中医相关的书籍,扫了一圈才发现都是纯文艺作品。
宁樨抽出一本白先勇的散文集,在靠近窗户的椅子上坐下。没多久,之前那个年轻的女孩端来了饼干和茶水。
饼干装在藤编的小篮里,垫着雪白的、带花边的滤纸。黑色粗陶的茶壶茶杯,茶汤清澈,尝一口觉得苦,但配合曲奇饼干倒是刚好。
宁樨并不是耐得下性子看书的人,散文集只看了两页就被她放回书架,随后她掏出手机来玩。
微信上有苏雨浓发来的未读消息:“樨樨,你翘课了?”
宁樨:“带我阿婆去看病了。”
明明是上课时间,苏雨浓却很快地回复了她:“怎么是你去,你爸呢?”
宁樨:“不知道。”
苏雨浓:“下午来上课吗?方诚轩刚刚来找过你,说你电话和微信都拉黑他了,问我你去哪里了。”
宁樨:“你跟他说就当我已经死了。”
苏雨浓:“不要这样,他也蛮可怜的。”
苏雨浓把方诚轩和她聊天的截图发了过来,方诚轩连发了一排哭脸表情。
宁樨想起自己还没跟苏雨浓说过周末发生的事。
宁樨:“详情我下午上课来再跟你说。”
退出聊天界面,宁樨又打开微博,最后玩得索然无味,丢下手机发起呆来。
所幸没过多久,温岭远就过来喊她,商量治疗方案。
“脊柱神经受压迫,”温岭远指着放在一旁的骨架模型给她看,“所以伴有持续性的疼痛,后续可能会引发头疼、耳鸣、胸闷等其他症状。”
他看宁樨在发呆,问道:“我解释得清楚吗?”
宁樨点头:“你和医院骨科的医生说得差不多。我以为你会跟我讲一堆什么气虚血虚脾虚的术语。”
“你说的这些术语也并不是骗人的话。”
“但是如果你和我扯这些,我可能就不会相信你了。”
温岭远笑了笑,似乎有些无奈。
“要怎么治疗?”
“针灸、艾灸、配合理疗。”他看宁樨似乎又有疑虑,便说:“可以让阿婆试一次,没有缓解的话,不收你的钱。”
“你这样开医馆,不怕亏本吗?”
“是我爷爷的医馆,亏也是亏他的。”温岭远笑着说。
针灸室里艾草的气味有些熏人,室内坐满了人,有个大爷挨窗坐着,脸上扎满了针,针上缠着线,连着一台小型的仪器,仿佛是通电的。看得宁樨面颊莫名一紧,那位大爷倒是没有一点感觉到疼痛的意思。
温岭远亲自给阿婆安排床位,靠里的一张床,护士刚刚更换过那上面的蓝色无纺布被子。
阿婆有些害怕,问温岭远:“痛不痛啊?”
“扎针的时候会有些微的胀痛。”
宁樨忙说:“可是他们说针灸完全不痛的。”
温岭远看着她:“或者,你先亲自试一试?”当他敛起笑容的时候,同样的五官,却立刻便让人觉得疏离。
或许任何人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质疑专业性,都不会感到高兴。
于是宁樨问了最后一句话:“你亲自下针吗?如果是别人……”她望向门口的其他医生,“我不放心。”
“不是任何人都有做针灸的资质,”温岭远看着她,目光有种让人信任的坚定,“我亲自下针。”
宁樨又被赶回了茶室,那个年轻女孩给她续了曲奇饼和茶水。
她在茶室里等得百无聊赖,这时候宁治东打来的电话,彻底将她的暴躁点燃。
宁治东:“你早上给我打电话了?”
“原来你还活着啊。”
“怎么说话的!”
宁樨吼道:“宁治东,你妈生病了,你一点都不关心,还在外面花天酒地。”
宁治东想撒气,但找不到立场,噎了半晌,才说:“你阿婆怎么了?严重不严重?”
宁樨不想说话。
“樨樨你先照顾阿婆,我后……最迟大后天就回来。我给你打点儿钱,不够尽管跟爸爸开口要。张阿姨呢?她没照顾着吗?”
宁樨把电话挂了,宁治东也没再打过来,半分钟后,手机收到了银行卡里入账十万块的信息。
宁樨捏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觉察到门口有人,她抬头看去,是温岭远。他站在那里,不知道站了多久了。
温岭远走过来,拉开椅子,在她对面坐下:“针已经扎上,同时在熏艾灸盒,大约半小时。”
宁樨木然地点头。
“你饿了吗?要不要帮你点餐。”
“不用……”
温岭远看着她,目光温和:“你爸不在家?”他没有隐瞒自己听到了宁樨打电话这件事。
宁樨摇头。
“家里没有别的大人了吗?”
宁樨低着头笑:“你说是不是好奇怪,平常不需要的时候,烧饭的阿姨,开车的司机,总要来烦我,连花瓶应该放在哪里都要问我的意见,放在哪里不可以?有什么好问的。可是需要的时候,他们一个都找不到,不是请假就是有事。”
明明只是刚认识,按照她的习惯,是要把他划在陌生人的范畴的。可她却选择把抱怨给他听,可能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说,也会愿意听她说的大人。
“饼干好吃吗?”
宁樨愣一下:“还可以。”
“还有其他零食,要不要试试。”
“我不是小孩儿,你不要用这种方法哄我。”
温岭远笑了笑,有些不置可否。他把粗陶茶壶提了过来,拿起那只干净的茶杯,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你不用去忙吗?”
“中午没有那么忙。”
“那我阿婆……”
“实习的医生看着,有事会叫我。”
宁樨端起面前的茶杯,问:“这是什么茶?”她觉得有些苦,但闻起来很香,她习惯了喝七分糖,加很多珍珠和奶盖的奶茶,有些苦的纯茶接受起来也没有什么障碍。
“碧螺春,也可能是龙井,我不知道。”
宁樨投去疑惑的目光。
温岭远意会:“这是爷爷安排的,他喜欢这些传统文化。”
“你不喜欢吗?”
“我不排斥。”
“那你为什么要学中医?”
“因为我不排斥。”
……
有人来唤,温岭远站起身:“你稍坐。”
宁樨把饼干吃完,温岭远才回来。他告诉她阿婆在做理疗了,二十分钟就能结束。可能中午也不是那么“不忙”,温岭远刚想坐下又被叫走。
没多久,那个年轻女孩又来添置零食,不单单是饼干,山楂片、小麻花、花生酥,各式甜点都端了一点,在小篮子上堆成了一座小山。显然是温岭远特意叮嘱过的。
年轻女孩没忍住多看了她两眼,兴许是因为医馆的零食库存第一次消耗得这么快。
宁樨问:“你叫什么名字?”她预感后面很长一段时间自己都要和她打交道。
“池小园。”
宁樨点头。
池小园紧张地看着她,不明白她问自己名字的用意,想投诉她吗?
然而宁樨什么也没再说,把手伸去那座小山,拣几片山楂片。池小园莫名其妙地走了。
山楂解腻开胃,宁樨越吃越饿。等得快没耐心时,温岭远扶着阿婆出来了。
宁樨丢下吃一半的零食赶紧迎上去:“感觉怎么样?”
阿婆笑说:“温医生手法好,脖子好多了。”
宁樨松了一口气,不管能不能治本,阿婆能熬到做核磁共振那天就好。
“后面还要做几次?”
“四次。”
“每天都来吗?”
“最好每天都来。”温岭远身体朝外转,“走吧,我送你们到门口。”
宁樨跟在他后面,又问:“不需要喝药吗?”
“不需要。平常注意保暖,如果家里有按摩仪,日常使用有缓解作用。”
“没有。你有推荐的品牌吗?”
温岭远顿下脚步看她一眼,笑着说:“自己去做功课,不然你要说我打广告了。”
穿过竹径,回到大路旁。
温岭远说:“我帮你们打一辆车。”
“不用,我开车来的。”宁樨话音刚落就知失言,果然温岭远的目光立即落到她脸上。
他站立一瞬,却同宁樨招招手,对阿婆说:“您稍等,我跟宁樨说两句话。”
温岭远没将话说透,只说:“以后最好打车过来。”
宁樨耸耸肩。
温岭远伸出手:“车钥匙给我。”
宁樨掏衣服口袋,带出一堆零零散散的玩意儿,草莓水晶的发箍、用得快只剩下包装袋的小包手帕纸、缠作一团的耳机线……
宁樨从缠绕的耳机线里把车钥匙解救出来,递给温岭远。
温岭远打量着她,她穿一件杧果黄的宽松卫衣、偏运动款的灰色阔腿、帆布鞋,完全一副高中生的打扮。
宁樨一点没有被抓到无证驾驶的心虚,虽然她能领会他的好意。温岭远将她叫到一边说这件事,是不想引起阿婆的恐慌。温岭远果真是个极其温柔周到的人。
宁樨回到阿婆身旁,将她的手一挽,笑着说:“阿婆,温医生说开车送我们回家。”
“真的吗?不耽误温医生工作?”
“他说不耽误。”
“那温医生可真是个大好人。”
温岭远问了目的地,拿手机开导航,然后将手机竖放在下方的储物格里。
宁樨陪着阿婆坐在后座,趴在座椅的缝隙间同温岭远说话:“你为什么后来没再跟我爸吃过饭?”
“我之前在崇城,今年年初才回南城。”
“在崇城做什么?”
“一家中医院工作。”
“现在回来是继承家业?”
宁樨自己都被这个说法逗笑,哪知道温岭远说:“如果是指青杏堂,那算是吧。”
“你们生意蛮好的。”宁樨笑说,“家大业大。”
这时候手机导航的声音被一条微信消息提示音打断,宁樨条件反射地看一眼,手机顶端通知栏里,一个叫钟映的人问:“在做什么?”
宁樨没有偷窥他人隐私的兴趣,身体往回挪,靠在后座椅背上,转而跟阿婆说起话来。
二十分钟后,车停在了宁樨家的车库。
温岭远将车停好,把钥匙交还给宁樨,特意小声地叮嘱她:“以后不准再开了。”
阿婆邀请他进屋去喝杯茶,温岭远笑着说:“下次再来叨扰,我得回医馆了。”
阿婆吩咐宁樨:“樨樨,那你送送温医生。”
温岭远笑着说:“不用了,你们进屋吧,阿婆您注意休息。”
宁樨家住的是别墅,外观气派,内里堂皇,只是不适合居住,尤其是老人。阿婆的卧室在二楼,但她至今住着一楼的客房。
三层的别墅,因为家里人少,就显得格外冷清。
宁樨不会做饭,也不可能让身体不舒服的阿婆做,只好点外卖。
“阿婆,我下午不去学校了吧。”吃外卖的时候,宁樨说。
“怎么能不去上学呢。”
“您一个人在家。”
“小张明天就会过来了。”
“可是您不是不喜欢张阿姨?”
“胡说,我哪有不喜欢她。”
宁樨有时候会想,为什么自己住这么好的房子,拿着用不完的零花钱,却觉得生活的每一秒都有一种无力感。
阿婆从老家搬来之后,这种感觉尤其明显。
阿婆明显不适应这种成天也找不到一个人说话的日子,电脑用不好,网络电视看不懂操作,不敢乱按。小区七弯八拐,每栋建筑都是一模一样,走出去总迷路。她已经六十六岁,谨小慎微地度过了一辈子,临到头了却要重新学习复杂的、没有章法可循的城市生活。
“那您下午要不要去公园逛一逛?河滨公园也有很多老爷爷老奶奶。”
阿婆摇头:“我找不到路回来。”
“我放学去接您。”
阿婆犹豫一下,却还是摇头:“樨樨你别管我了,你上学要紧。”
怎么能不管呢。可是,她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管。
宁樨拿筷子拨着明显煮得过软的米饭,低着头说:“那您想回老家吗?等您脖子治好了,还是回老家去生活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