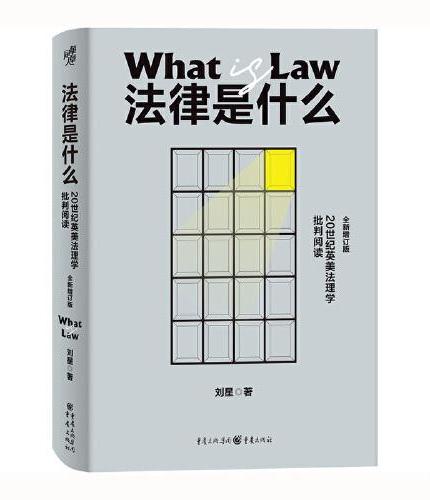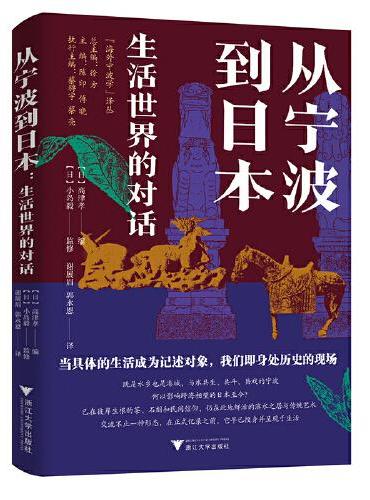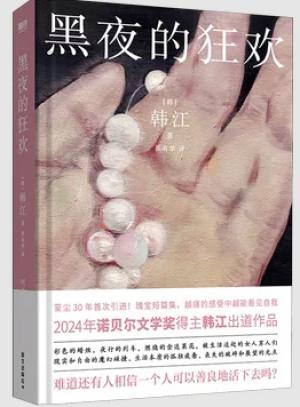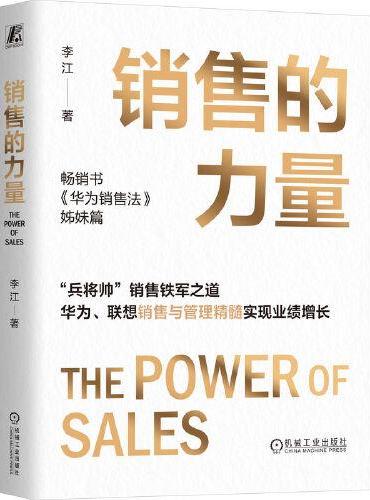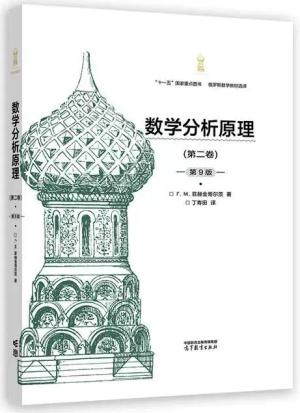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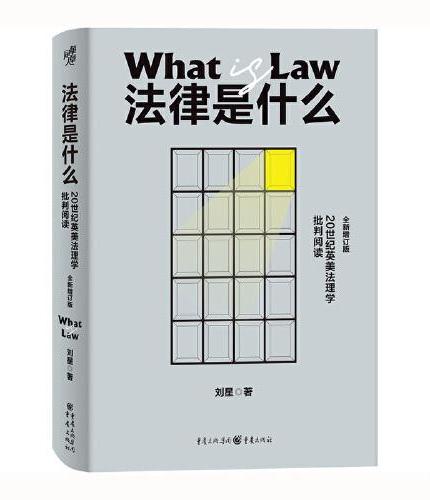
《
法律是什么:20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全新增订版)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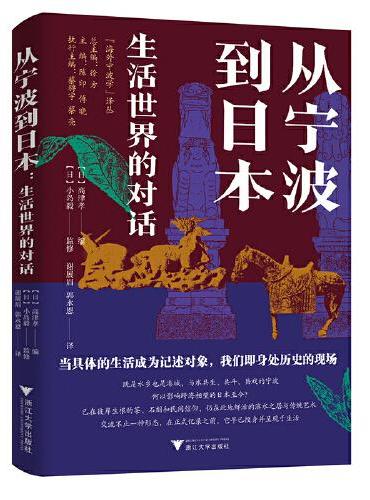
《
从宁波到日本:生活世界的对话
》
售價:HK$
74.8

《
西夏史(历史通识书系)
》
售價:HK$
77.0

《
怪谈:一本详知日本怪谈文学发展脉络史!
》
售價:HK$
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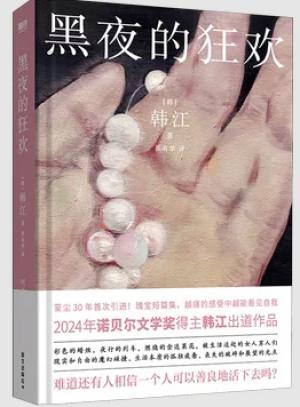
《
韩江黑夜的狂欢: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出道作品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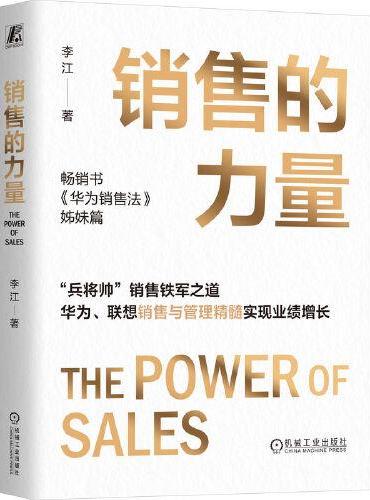
《
销售的力量
》
售價:HK$
97.9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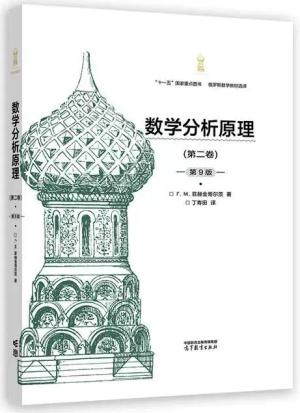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名家推荐:
作者以媒体人的敏锐,学者的怀疑和现代人的感知,认识或重新认识空间和时间上的远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追随作者了解这些远方,必定会发现有些远方其实并不远,甚至就在自己身边。
——葛剑雄(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历史学家)
一位好作家,从前人们往往说会有两套笔墨。乃庆看上去也是,但慢慢读着,感觉他到底还是相融相通的一套。记得从前读过他结集的一本老厚的电视方面的专著,回头看,无论是影视传播学、社会学还是文学,乃庆文章,都一样真诚明晰,一样情深意厚。
——李幸( 媒介批评家、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
《高湾史记》记录的是乃庆兄地理上的故乡,《与我相关的远方》则更像一个走出故乡的游子寻找精神原乡的记录。无论是黄叶村的曹雪芹,汝州的《汝帖》风穴寺“临济喝”,李白梦游的天姥山,虎跑禅寺的弘一,还是《西风烈》里的党项西夏,翠湖畔的陆军讲武堂和西南联大,苏东坡 的最后岁月,清凉山的李煜,抑或欧洲的梵高、卡夫卡等等,无不从眼前景物,延展至历史场景和主人的命运,更有今世共情的叹息和省思。这其实是对历史的另一种重新打量。
—— 朱学东 (自由撰稿人 《中国周刊》《南风窗》原总
|
| 內容簡介: |
|
作为媒体策划人和文化学者,作者以一己之身为“半径”,丈量大地,思接千载,以自己的所思所感与山水风物相对应,以当代人的视角梳理历史,反思经验,观照人文。所以该书不是一部轻快悠游的“游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托物寄兴,而是努力拨开眼前的认知迷雾,穿越眼前的世界,寻找消逝的高贵灵魂,探索历史命运的肯綮和国族兴衰的诡谲,力图发现它们和个人命运之间生生不息的关系,借此感悟人生和生活的真谛。所以也不妨说,这是一部纪行书,也是作者的一部心灵史。
|
| 關於作者: |
阚乃庆,教授、高级编辑,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
出版专业著作《最新欧美电视节目模式》《出入同门》等三部,诗集《耕读集》、纪实文学《高湾史记:一个运河村庄里的中国》,发表专业论文50多篇,另有舞剧、小说、散文等多部作品及数百篇各类文章面世。
创办新闻、教育、人物、文化、生活、娱乐、少儿等多个电视频道和栏目,策划“中国高速公路万里行”“绝对唱响”等多个大型媒体项目,主创《精神的力量》《闪亮的坐标》《邕江》等多部重点媒体节目;《情怀》《吴韵汉风》等20多部电视作品获得国家及省级大奖;其中《为祖国喝彩》获全国电视文艺特别节目最佳作品奖,《国家记忆》获上星频道最具开创性国史节目等十多项大奖,纪录片《黄河流过的村庄》获央视年度优秀节目一等奖、优秀对农电视作品一等奖。
|
| 目錄:
|
001 _ 自序:有限的抵达
随风而逝的灵魂
009 _ 山河血证
030 _ 清凉山月
058 _ 梦别天姥
076 _ 苏东坡最后的四十八天
094 _ 西风烈
107 _ 眺望明孝陵
120 _ 风雨东林
136 _ 寂寥黄叶村
155 _ 虎跑访禅
175 _ 文心武胆话翠湖
191 _ 谒路遥墓
心在云层之上
197 _ 汝州识象
213 _ 大器天池
216 _ 大雪无声
220 _ 水木天涯
风从异方来
233 _ 在阿姆斯特丹顺访一无所成者梵高
243 _ 卡夫卡和他的女人们
尘埃里的花朵
265 _ 2019重返生活
270 _ 2020我曾经的沧海
283 _ 2021面朝大海
明明就在那里
299 _ 天心月圆
311 _ 兄弟,今晚我们谈谈
317 _ 适彼乐土
330 _ 后记:流年似水
|
| 內容試閱:
|
自序
有限的抵达
残荷孑立,孤蝉嘶鸣,蜘蛛盘踞网上虎视眈眈,螳螂高张臂刃耀武扬威,金鱼的鳍尾摇曳在厚黑的缸底,蜗牛以不可见的速度前行,留下鲜亮的涎迹,带刺的月季缠着痩硬的铁篱,如彼此伤害的恋人,紫藤的柔须则是人的欲念,绝望地伸向遥不可及的天空……
暑假结束,当我风尘仆仆地从南太行的大山深处和西太平洋的万顷碧波中归来,位于江南的小院陌生了,茂盛得毫无节制,荒芜得生机勃勃。我明白,这一切,都缘于我不在的这两个月,两个月的“安那其状态”,无剪无锄,无培无育,无增无删,动植物恢复了元气,还原了自然,成就了一片朴茂元真的生命状态。
世界环环相扣,万物静默如谜。
这个世界是连绵的,“我在”“曾在”“将在”,三个时空即构成“我”存在的三个层面。没有了“我”的世界仍然美好如初。我生前如此,身后也会如此,毫无疑问,毫无悬念。
那么,“我”的价值何在?
雅斯贝尔斯认为,“存在”的意义除了人作为一种存在而存在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价值,即人知道自己存在的存在。
在《旧约》里,约伯受到惩罚,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世间的一切最终都归于劫灰,最终归于尘土——至此,劫灰与尘土了无分别。我们身处的世界,有不同的维度,既有时间上的长度,也有空间上的宽度,自然界的演化和人类的历史都在这两个维度上并行不悖地展开。而作为个体的人,只是三维动物,对于四维的时间,只能看到一个片段,感知世界的一个截面。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赫拉克里特面对眼前奔涌不息进入爱琴海的基非索斯河,有感于“万物皆流,无物常驻,宇宙中的一切都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悟出“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著名哲思。而同一时代的孔子在东方的一座并不著名的尼山脚下,面对五川汇流,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千古一叹。其实,汤汤激流也罢,静水流深也罢,在“逝者如斯夫”的语境中,一切都是过眼烟云。瞬时花开,刹那雪灭,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渺微琐屑,都短生促息,都无足称道。
人,也是这个世界的“劫余”。《石头记》把男主的前世定义为女娲补天留下的一块石头,幻形入世,情僧恨海,四大皆空,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来自自然,复归自然,无痕无迹,无悲无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思想设定了舞台,又反观了表演。
“我”是演员,也是看客。演得逼真,看得沉醉。
秋天的后半夜,蛩虫振翅,做最后的秋声。我独卧江南,看法国的纪录片《脸庞·村庄》。年轻的街头艺术家JR带着祖母级的当年新浪潮女神阿涅丝·瓦达尔,开着改装车在法国乡间游弋,把随机遇到的人拍成人像照片,打印成巨幅招贴画,张贴在他们的农舍、仓库上:有开着拖拉机耕种800顷土地的足不出户的农民,已经垂垂老矣的矿井工人,三代传承、乐在其中的乡村敲钟人……最终,JR把印着阿涅丝布满皱纹的眼睛和皮肉松弛的脚趾的巨幅招贴画贴到列车的车厢上,铿锵的车轮噙着铁轨,带着阿涅丝的脚走到她不曾去过的地方,让她的眼睛看看她未曾见过的陌生世界,借此完成了新浪潮向世界的最后告别。——在这里,以不蹈陈俗、即兴创作的法国新浪潮和“以发现代替虚构”的不列颠叙事传统颉颃并进,竟然殊途同归——是创作力的匮乏所致还是向优秀传统不自觉的敬礼,似乎都是,也都不是。
大地的事,其实从来不仅是大地上的事。阿涅丝看到的都是“有我之境”,而一个人的生命半径究竟有多大?究竟会经历多少“有我之境”?究竟要走过多少千山万水,才能走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我在但丁所说的“人生的中途”,带着发肤生出的苔藓味,离开了那个醉生梦死的江边小城,告别了悠游生活,其内心依据,其实是一种企图心,一种不甘沉沦、不愿因袭的妄念。
自觉不自觉地,我们都会在路上,都会遭遇陌生。王船山先生说过“人于所未见未闻者不能生其心”。行走大地,也就和读书阅世一样,成为人生的必修课。世界要让自己的脚去走,万物要靠自己的心丈量。触摸山河,历史无言,沧桑变迁的密码尽在山顶流岚、涧底落红之中。稻粟千重浪,恍惚千军万马走过路过,断壁残垣间,仿佛繁花簇锦开过盛过。大漠孤烟,是西域人家的一脉千年香火,残阳昏鸦,是朝代更迭的一抹血色温柔。
印度裔的奈保尔出生在美洲的海岛,他在《大河湾》中道出了生存的悖论。在写作中,他的眼前不断浮现这个星球的远景,还有上面的芸芸众生——他们迷失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却永不停息地奔波劳碌,可怕的劳碌,无谓的劳碌。几乎就在我完成对家乡的诚意之作《高湾史记》的同时,我开始了另一种写作。这次的目的地不是熟悉的家乡,而是陌生的远方。远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都与我相关。我体会到,所有的远方都是故乡,所有的写作都是对家乡的朝圣之旅。关心书本里的思想,关心人生经历中的思想,关心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思想,然后以一己之笔,一己之力,参与思想。——这,才是最美好的原乡。
古代人推崇通人,所谓通物、通史、通天地,历史即人生,人生即历史。——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在央视策划《国家记忆》时,我提出“触摸有温度的历史”——历史需要人的感知,需要人的体温,需要千千万万的盲人摸象,而只要盲人足够多,就有还原全象的可能。历史本来没有真相,有的只是不断接近事实的过程。
伫立山河,俯察古今,我们和古人享受着同一个世界,体验着同一种生命感受。《传道书》里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爱过、恨过、迷茫过、得意过,痛苦过、欢乐过……所有这些,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除了死亡,我们的先人已经尝试了一切,他们用各个不同的人生,解释了这个世界的秘密。
世界是一个大生命,个体是一个小生命。
每个生命本身就是一部微型历史。
每个人的生命的每一瞬间,都处在历史的交汇点上。那些精微如闪电一般瞬间照亮生活的精微感受,那些在世界和历史重要节点上的个体人生状态,那些隐藏在黄土草丘里的曾经生动怒放的生命,那些消隐在山河之间的大开大合的历史,那些有限世界里的无限,那些曾经鲜活的枯寂,无疑是这个世界的精彩,也是历史馈赠的珍宝。
一个是人性的恒量,一个是世界的变量,这两者之间的参差交互,构成了神秘诡谲的社会关系。
在这样的视野里,曹雪芹以一生的悲苦哭成“石书”不啻命运的无情播弄;“一代词帝”李煜承受了不能承受的社稷之重,其实是一次人生的错位玩笑;艺术达人李叔同成为一代宗师弘一的背后是对极致极乐追求而不得;卡夫卡与三个女人的关系则解释了他隐秘深邃的内心秘密;梵高的一无所成的背后有着他并不深谙的潜在规则;李白乖戾嚣张的人生与其狂悖不羁的诗性,相生相长,如影相随;苏东坡在江南的炎炎夏日里,则补写了他人生的最后缺笔……历来的人们都被他所展现的表象所过分看重或者看轻,人性的弱点浮沉其间,加之大时代的裹挟推搡,历史的吊诡、人生的多态、生活的苦乐就此铸成。
“写作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这是一次避轻就重、耗费心神的精神之旅,是一场注定无望的寻找,一次向不可知的圣殿的朝圣,一次自我疗伤,一次自我了断,在人们熟视无睹甚至不再耐烦的,却又始终陌生的历史真相中爬梳、探索,在人性的幽微迂曲中体会、求问,在未启的事实前悬想、索答,在青 之末揣摩涟漪的形貌,在草蛇灰线中猜度人生的履痕,在熙攘人流中感受现实无法挣脱的苍凉,在言语的外壳中撬开欲盖弥彰的生活,在文本的微弱气息中感受人性末梢的悸动。这其间,拒斥与接纳,执着与超脱,缠绕与间离,开放与闭合,相生相长,如影伴形,所有的努力只是有限的抵达,最终在人生的宿命和充满隐喻的生活中,望峰息心,止于归宿。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然而,大地太大,即使登临大山绝顶,也不足以见其大。一山一水,难以拼凑大地的全景。必须借助思想的力量,只有借助思力,方能济目力之穷。
就这样,写作就不仅仅是一种描摹、一种塑造、一种考证,也是一种对人性的追问、对人生的寻踪,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度对话,是对生命的勘探。借助我的经验、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对世界的有限认知,建设自我,观照天地,钩沉历史,体味人心,在山重水复中看到柳暗花明,在乱花迷眼中找到真正的自我。而从各个不同的生命景象中,展开合理的逻辑,借由实证主义的写作精神和自觉的文体意识,对此展开演绎、归纳、书写、歌哭,我认为这才是一种生命的学问,一种真正有价值的存在。
这是生命的敞开,也是生命的凝聚。这是我的寂寞园地,我的纸上江山,我一个人的夜半歌声,一个人的张灯结彩,一个人的临水照影,一个人的锦衣夜行,一个人的耕云播雨,一个人的犯上作乱。
在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自我勘探,自我开发,一边坚守,一边建设,在不断的拆迁中不断装修自己的内心。
这是我的远方,永远无法抵达的远方。
后记
流年似水
天光熹微,弥漫无间,东边的天幕被晕染上一层滞闷的灰白色,任由虬曲的树枝写上奇怪而放纵的联翩墨篆。
灰絮般的云在天上迟迟疑疑地走着,深藏其中的月亮半掩半露,忽明忽暗。但太阳毕竟还没有出,在黑暗与光明之间,一切的形象既清晰有力,又混沌昏昧,如同这个微妙的世界。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晦”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一切并不妨碍早行人的脚步,昏昏沉沉中,从Y州到N京的汽车载我上了路。
昼与夜,明与暗,从概念上说,如刀刃和刀背一样明晰,但是现实的情形恰恰相反,像山连着山,风吹着风,水流着水,云推着云,绵延无际,和融一处。正如此刻的我,站在年度的时间分界线上。都说时间是虚拟的概念,也是人为的刻度,但此刻总是有着不同于寻常日子的感觉。正好可以借此停一停匆忙的脚步,听听内心世界的声音。
透过模糊的车窗,田野萧瑟一片,村舍、树木、电杆,慢慢现出千篇一律的轮廓,远远近近的,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快速后逝,如同一个人物带出一个人物,一个情节推动着另一个情节。
那么,即将过去的岁月,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分花拂柳的情愫、创榛辟莽的艰辛,还是罡风劲扫的凌乱,浮萍之末的微茫?抑或不可挽回的无奈,似水流年的苍凉乃至溃败?
我印象中的新年,总是飘雪。最难忘的2019年也是从山东半岛的那场大雪开始的。我和巨宗、峻兄赶到烟台和晓明相见,兄弟聚会,分外亲热。几天的短暂相聚带来的温暖,足以融化心地的冰凌,焐热整个的寒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我们兄弟四人最后的聚会。
春节过后,在民工还没出发的日子,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一通忙乱,事务结束,南太行开始下雪,雪落无声,自天而降,走在寂静的街巷,铺天盖地的大雪,掩住所有的坎坷,遮了一切的不平。在城市的灯光映照下,雪夜显得生动无边。大雪天,所有的高铁和航班都取消了,只有铁路职工通勤乘坐的绿皮火车还在通行。张利兄帮我拖着箱子,在冰地上和我相扶相将,歪歪扭扭地赶到车站,随后招着手,汇入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我揣着朋友的暖意,学着边上的行人跺着脚候车。来了来了,一阵长长的笛声,绿皮车终于伴着一阵冷风进站,呼哧呼哧的,像一只庞大的节肢动物。吊着冰冷的扶手,我踏上了车。随即掉进了一个沸腾闹猛的人肉火锅里,一帮红男绿女还沉浸在过年热闹中,大家挤坐其间,嗑着各色植物的果实,嚼着各种动物的头颈爪喙,跟近处的邻座或远方的手机联系人窃窃私语高声说笑。铁轮噙轨,满载着人间的大热闹、大快乐,在中原的烈风中,在我的热泪中铿锵前行。窗外的山岭头顶雪冠,一律迤逦后退,终至不见。
邕江,在我的过去一年的经历中,无疑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左右江汇拢后,流经了一段平阔的江面,成就了邕江和枕河而建的南宁。我和郑浩兄一见如故,共同的情怀和志趣让我们对这条南方的大江倾注了心血。在这座热诚大度的南国绿城,追溯前世今生,踏访人间烟火,感受现代文明。特别是活色生香的南方美食,各种食材,各种混搭,颠覆了对寻常美食的舌尖体验,多姿多彩,无所不及,这才是生活的本真滋味,也是对苦难人生的最好回馈。
耿耿难忘的一场生离死别。短短三个月,病魔夺去了我的晓明兄弟的生命。我明白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真相,让我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命运的无常与人生的无奈,也深切地体会到失去血肉兄弟的至痛。我的兄弟是完成了人世间交付的所有责任和使命后,毫无亏欠地离开的。那个晚上,从住处的窗口向外远望,海潮退去,白日明净的沙滩此刻黑乎乎的一片,显出丑陋不堪的一面。我们兄弟,从十几岁朝夕相处在一起,风风雨雨几十年,早就把彼此焊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此时生生撕裂,情何以堪?勒内·夏尔在《沉睡的苏醒》里说,“留给我们的遗产没有任何遗言”。我们探望、吊唁、祭扫,办追思会,借助各种外在的、内心的仪式和话语,好不容易走出了心里的浓重阴影。可是在大连,一场风雨中的海边一瞥还是击中了我。那是一场积蓄已久的秋天的豪雨,一早,冀兄带我到星海湾,这是我熟悉已久的地方。风雨大作,惊涛击石,浪沫飞溅,往复不已。我伫立在漫天风雨中,眺望远方的海天。我不止一次从这片海域乘船,我知道,那边就是烟台,现在成了我的兄弟的埋骨处。我眼中的海天混茫一色,界线难分。吴为山的青铜塑像高矗在海边,老子和孔子在海天间相对论道:天地无涯,而人生有涯,该如何自处处世?两位中国文化的圣者各持一端,殊途同归。而这个千古不绝的天问,需要每个人做出回答,但是却没有答案。
天渐渐亮了。此刻我体会到了雨果说的一句话,暗夜之后的白昼如同一场胜利。江南的山形由远至近,渐渐显形,像名家笔下的水墨山水,渐远渐淡,终至不见。
车过长江,大江澎湃,浩荡东去。
我想起了拉萨河。
雪山冰川的涓涓水滴从念青唐古拉山一路走来,在拉萨打了一个结,浩荡而去,汇入雅鲁藏布江,这段黄金水道被称作拉萨河。从拉萨到日喀则,伴着深嵌峡谷中的雅江驱车而行,灰褐色的大山如艨艟巨舰,不断从车窗外驶过。眼睛单调得如史前蛮荒。但是水畔居然有绿色,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不会想到竟然有柳树。是的,柳树!柳树竟然在这片地球上离天最近的地方生长,虽然不复是绿意的葱茏和纷披的样貌,而是虬曲而干硬,但是挺立如仪,显得倔强而有力。
在拉萨见到久违的兄弟,分外亲切。一批批援藏人,像一棵棵杨树在高原的阳光下生长。相信是布达拉宫的绝世美丽,大昭寺的神圣悠久和八廓街的人间烟火,特别是拉萨河的丰沛激情,给了这帮来自天南地北的仁人志士以别样的滋养。晚上去拉萨河边的露天剧场看实景剧《文成公主》,恢宏的场面,泼彩似的灯光,如云的畜群,无不让人惊叹。当剧中演到文成公主进藏的大戏时,雪花从天而降,飘飘洒洒,风雪助演,分外动人,把这场历史大戏演绎得荡气回肠,活色生香。我开始相信亚里士多德说的那句话——艺术往往比历史更真实,因为它表现了人性。文成公主也罢,布达拉宫也罢,抑或眼前的这部大戏,都是由拉萨内外的人的汇流而成,是他们在雪域高原一次次生命的绽放,成就了这一切。如同在西藏随处可见的转山人,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一个个等身长头,成就了大功德,也成全了自我。
还有一道水,鸭绿江。
这是一方特殊的水道。水道并不宽阔,水流也不湍急,船行中流,对岸就是那个让人爱恨交加的邻国,那叶在国际汪洋中逆流而上的独木舟。可远远看去,这里的一切都很平和安详。山色青黛,河水清澈,屋舍俨然,庄稼和树木安静地成长,人们在田亩间行走,山道上时见穿着单调的男女骑着自行车,驮着物件来来往往,根据身形的弯曲可以想象山形的起伏。走在高句丽的故地,坐山临水的丸都山城,由整块凝灰角砾凿成的好大王碑,用上万块巨石垒成的长寿王陵,记录着这个强悍的王朝曾经的辉煌,一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东亚民族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里,消失在一堆堆荒石蔓草间。王陵之上,安静如盘古,我登临其上,眺望着不可见的远方,在此我心下暗记,要珍惜眼前,珍惜美好,珍惜拥有的一切。而青岛沙滩上的趾感、上海桐阴下的屐声、苏州深巷里的斜雨,以及河下古镇的热汗、绍兴旧城的酽烈、春秋淹城的陈迹,和八都岕的灿叶、三茅峰下的烟火一样,都铭刻着岁月的赠予和人世间的谐和。我知足,我感恩,一切都是好的安排。我明白,只要心怀感念,哪怕是踽踽独往,都是一次壮观的锦衣夜行,一次深铭五内的心灵之约,一次与自我的久别重逢。
前不久,母亲八十大寿,我带着老人家回到久违的运河村庄。家乡的亲人们燃炙高香,香烟缭绕,飘散在收获后的田野上,不可复见。在里下河的暖阳下,父亲怀拢手杖打着瞌睡,母亲兴高采烈地与围着她的乡亲攀谈。我在想,父母的一生总体是完满的,他们心想事成,自己多年在乡间积下的功德,经过岁月的渲染,也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儿子撇开年底的事务,特地从上海过来,他和侄子一起买了最新型号的IPAD,两个小子说是送给奶奶追剧,老人自是欢喜不迭。堂兄门前的小沟用水泥驳了岸,儿子小时候在这里待过几年,但他可能并不知道,小沟通灌河,灌河通运河,运河通长江,自然也连接着黄浦江。这些水道不可同日而语,看似也不相干,但对于我们家族来说,却都有着神秘的命运关联。年前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儿子买了房。一次去外地讲学,经停上海,我在房子里暂住。晚上,小区偶尔传来黄浦江上一二声汽笛,看着灯光下无边无际的水泥森林。我想,儿子,你在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安了家,拥有了我在这个年龄无法拥有的一切,以后的人生就靠你自己了。
从城市职场归来的子侄们与乡间显然是隔膜的,看着孩子们在乡间无所事事地甩泥块。我知道他们打不远打不准,原因是“随挥”不够,就是手臂和要掷出的东西要保持尽可能长时间的接触,并赋予它带有方向感的力量,这才能扔得准而远,这是所有投掷的要义,也是做事的要诀。稻盛和夫说,仅有一次的人生,稀里糊涂地过就未免太可惜了。面对迟早到来的死亡,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做“随挥”?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空间,要与哪些物事交集往来?佛在《金刚经》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人生世间,无非就是要处理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不与那些不想不愿不甘的人事物相纠缠,需要无畏、智慧和欢喜。
邕江、渤海、拉萨河、鸭绿江,还有我身边的大运河、太湖、扬子江,黄浦江,一道道水来一道道痕,纵横交错的水道,在不期然间构成我逝去的生活场景。
会议开始了。主题是要为这个稳固如磐的社会再筑根基。高头讲章,人头森森。我开会的地址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励志社,那是近一个世纪前民国一个风光而显赫的所在。碑文仍在,桌榻依旧,重髹的藻井鲜明妍丽,但那时的衣香鬓影、高朋嘉宾已不复见。 “革命革心,立人立己”,曾经的革命者也是怀揣救世情怀,抱定澡雪精神,“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择志,决志,励志,行志,慎心,坚心,省心,信心,但时移世易,一切竟也随雨打风吹去。“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历史的吊诡一如人的命运,难以测度,不可捉摸,让人感慨。
墙外就是热闹的中山东路,车流滚滚,日夜不休。高而且大的梧桐像一排严整的军阵,它们已经站立了一个世纪,见证了这个江城的血雨腥风。阳光如金,把这个天下驰名的军阵镀上了一层辉煌的金色。今年恰逢罕见的暖冬,晚上饭饱后散步,在等红灯时,我看到一掌阔大的叶子,缀在老朽的枝上。它大概是在犹豫:是掉呢,还是不掉?
“不要沉湎于过去,不要为未发生的事情担心。”莱昂纳多·科恩《颂歌》里这样说。在塞外鼓荡已久的寒潮终于到来,高铁的钢铁巨舱载我回到江南。风雨模糊了车窗,局促了我的视线,没有地平线,或许就难以找到方向感。这场年底的例行差旅将告结束,我像宽慰好友一样宽慰自己:人生下半场即将开始,要接纳自己,与不满足不满意和解。脸上不必有戚容,心底定要有阳光。
回到斗室,暮色四合。灯光所及,叶落满园。院篱外的紫藤开始卷曲蔓条,收缩起生长的欲望。我想,中山东路上的那片叶子该掉下来了吧?
2019年岁末于江南
序一
一部行旅之书,万千思接天下
人生在世,其价值可能并不在于读了多少书,行了多少路,想了多少事,写了多少字,重要的在于读了行了想了写了,更在于认真读了行了想了写了吧。
乃庆嘱序,盛情难却。为别人的书写序,一般而言要比作者年长一些,高明一些,于我而言,感觉只因为年长。
与乃庆相识,在江苏电视台。当时我的兴趣所在,是媒介批评。电视,在中国可能要算是传媒的一个异数——比我出生得晚,而在某种意义上,死得比我还早;其盛时轰轰烈烈,寂时冷冷清清。于是不少明白人,在电视看上去还挺景气的时候出来了。乃庆本来就是在学界和业界来回转换的,本意去大学做个教授,结果人家觉得人才难得,让他做了学校的宣传部长。折中一下也好,可以一边做教授一边做部长。
我对乃庆的这一转型有兴趣,专程去拜访过他——2016年在太湖边上一个叫九龙湾的地儿。如今已不记得谈了些什么,无非是交换一些对人生志业的看法吧。其后,就陆续读到他写的本书里的一些文章。
记得第一次读的是关于苏东坡的那篇,洋洋洒洒,有几万字,感觉学到了很多。从前对苏轼的了解,都来自正史,轶事里印象深的只有“东坡肉”,因为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时候,吃过“作家宴”,其中有这么一道菜,还有“水淹七军”“火烧连城”,好像又叫“三国宴”。就在乃庆这篇长文里,知道了更多的轶事,而且更有趣。从此把东坡看成了跟自己一样的有着各种常人弱点的人。乃庆写人,往往通过行旅,当代如此写作的,余秋雨无疑是个开路者。不过余秋雨的路很正,告诉我们的都是大道理。其写过苏东坡,但记不清写什么了。卡夫卡应该没写过,但乃庆写的就是我感兴趣的,比如只是写了几个与他相关的女人,从而一改从前我对卡夫卡的阴暗印象。印象中乃庆文章没有太多道理,只有将我们拉近所写对象的引力。
本书诸篇,均有此等引力,或曰功力。
乃庆这部《与我相关的远方》,题材无疑在其专业与政务之外。本书之前,他出版过一部《高湾史记》,令我印象深刻。如果说那些与行旅有关的读书感悟,我写不到像他那样扎实,但还算是敢写的(我微信公众号名即“老李读行”),只是一读到“高湾”,就感觉自己力有不逮。这是一部社会学与人类学加历史学范畴的长篇著作,在浸润于乡土风情的个人认知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写就。于是不免“羡慕嫉妒恨”,因为其站得住脚能够永垂。而其有此功力,再出版这部充满哲思的历史人文散文集,无疑也是值得一读的。
一位好作家,从前人们往往说会有两套笔墨。乃庆看上去也是,但慢慢读着,感觉他到底还是相融相通的一套。记得从前读过他结集的一本老厚的电视方面的专著,回头看,无论是影视传播学、社会学还是文学,乃庆的文章,都一样真诚明晰,一样情深意厚。
我与乃庆最大的区别在轻与重:浅尝辄止是我,简单清浅如我;认真厚重是他,豪放婉约如他。他还有很多技能是我无力为之的,如书法与古体诗。文人做到像他那样,也就到头了吧,包括还要处理诸多事务,多么像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
本来不配写序的,想不如做一个导读,可是又怕导歪了,便想还是读者自己慢慢玩味去吧。总体而言,倒是可以说,乃庆这部《与我相关的远方》,圆心在他生活工作过的扬州南京无锡,半径则画到了整个中国及欧洲—— 一部行旅之书,万千思接天下。从其所着力摹写的人物看,先后出场的有曹雪芹、朱元璋、李白、李叔同、李元昊、苏东坡、李煜、梵高、卡夫卡、路遥、顾宪成……从抵达的目的地看,先后有北京香山、长白山天池、中原汝州、浙东天姥山、杭州虎跑寺、西夏王陵、昆明翠湖、江苏常州、南京清凉山、欧洲阿姆斯特丹、陕西延安、山西太行山、无锡张泾……
时常想,世上书这么多了,还差自己的一部吗?想下来的结果是,个人活在世上,需要与人连接,个人对他人会有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长成的,他人,既是历史的,又在当下。所以,我们应该读读真诚的有趣的厚重的书写。
《与我相关的远方》,即为如此这般的一部美文集。
李幸(媒介批评家、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
2022年4月于广州
序二
一切景语皆情语
跟乃庆兄一样,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也到过不少地方,访友问古。但过去都不过留下“到此一游”和“到此一醉”而已。读完书稿《与我相关的远方》,我突然间在书中的文字中找到了一种久违的知己感,当然,还有自惭。
2014年6月,在杭州街头漫步的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以后每到一个地方,就记录下眼睛里闪过的那些能够记住且有共情的景色、文物和人事吧,这才对得起自许的码字者和记录者的名头。我后来还一本正经地在自己的电脑里和个人博客上冠之以“行录中国”,一个如此高大上的名目。
但是,自那以后,我走过更多地方,自许“行录中国”的文字却没有留下多少,如今甚至想法也差不多烟消云散了。不仅诺言空许,也辜负了许多提供帮助期待看到我的文字记录的朋友。
正是怀着这种复杂的情感,让我集中精力,在两天内克服手机和电脑阅读的障碍(我习惯读纸书),读完了《与我相关的远方》。乃庆兄书中所写到的一些地方,诸如黄叶村、明孝陵、虎跑寺、清凉山、东林书院,更不用说苏东坡老死的常州,我都到过,书中记录的那些人那些事,许多我也知道,但我却陷溺于醉酒,困于自己的疏懒,竟然没有写过一篇。
也是借他人的文字,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吧。我在乃庆兄的文字里,读到了许多类似的感悟,那些书中所写的我未曾抵达的地方,也会列入我未来云游的目的地。至于书的最后部分,乃庆兄对故友的几篇完全个人化的追忆怀想,读来同样打动我,不仅让我有知己之感,甚至想立即和乃庆兄把盏叙谈。
我和乃庆兄是一面之交。某年我应展江老师之邀到扬州,因我曾在媒体业服务,展江老师找了扬州几位媒体业的同行一起餐聚聊天,乃庆兄正好回扬州,因此结缘。我和乃庆兄不仅曾是同行,我们俩也都写自己的故乡,他出版的关于故乡的记忆《高湾史记》,确实类似史记的写法,写出了宝应县氾水镇高湾村的生生不息、烟火万卷,不像我写江南故乡,只是杂乱无章地随记。《高湾史记》记录的是乃庆兄地理上的故乡,《与我相关的远方》则更像一个走出故乡的游子寻找精神原乡的记录。无论是黄叶村的曹雪芹,汝州的风穴寺“临济喝”,李白梦游的天姥山,虎跑禅寺的弘一,还是《西风烈》里的党项西夏,翠湖畔的陆军讲武堂和西南联大,苏东坡的最后岁月,清凉山的李煜,抑或欧洲的梵高、卡夫卡等,无不从眼前景物延展至历史场景和主人的命运,更有今世共情的叹息和省思。
这其实是重新打量历史。在现实与历史、残景与人文之间腾挪辗转,是需要很高的知识门槛的,必得对历史掌故和人文典籍熟悉,尤其还需有激发的共情。我偷懒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是对历史资料的把握远远不够,也很难专注去查证阅读。但这正是乃庆兄所努力的。就在今年的清明节,乃庆兄所写的《清明留言》一文中。他提到三十多年前在锡山旅游,路边看到一方老旧模糊的明代字碑,是纪念五百年前一位叫崔溥的朝鲜文官的,他即找来崔溥所撰的《漂海录》来研读。没有这种对历史资料的钻研,很难如此开阖收放自如为文。
梁衡先生在总结文章如何才能写好时,提出了“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我个人认为,形事典理之外,其实情最重要。观堂先生《人间词话删稿》中有言:“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虽是论诗词,但论散文之道,同样妥帖。
“每个人的生命的每一瞬间,都处在历史的交会点上。那些精微如闪电一般瞬间照亮生活的精微感受,那些在世界和历史重要节点上的个体人生状态,那些隐藏在黄土草丘里的曾经生动怒放的生命,那些消隐在山河之间的大开大合的历史,那些有限世界里的无限,那些曾经鲜活的枯寂,无疑是这个世界的精彩,也是历史馈赠的珍宝。”
这是乃庆兄自序中的话。我转录于此是想说,除了对历史资料熟悉之外,更要有面对眼前的历史遗存生发的真实共情,残景古人才能入文,文章也才能圆融而不生硬,无论关山万里还是历史深处的远方,才会与我相关相近相亲,才会有刘勰所言的那种“神与物游” “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关于人文景观与历史人物的书写,古代诗文中亦多见。当代中国以散文随笔之法写作者甚多,我之陋见,滥觞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但是,即使是同样的题材,也并不是说别人写了我就不能写。虽然李白游黄鹤楼时写“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故事是千古美谈,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因为阅历见识不同,即使面对相同的人文景观,也会有不同感受,这种私人感悟才是最真切珍贵的。
“尔未看花时,此花与尔同归于寂。尔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时明白起来。”王阳明说得对。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本来就应该是读书人尤其是曾经记录者的自觉。
“关心书本里的思想,关心人生经历中的思想,关心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思想,然后以一己之笔,一己之力,参与思想。——这,才是最美好的原乡。”
诚哉斯言。
朱学东(自由撰稿人 《中国周刊》《南风窗》原总编辑)
2022年4月于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