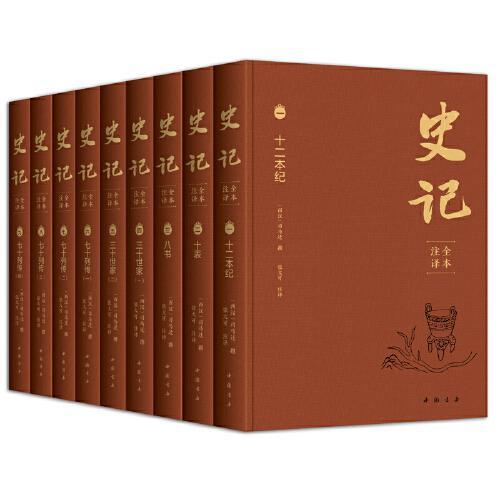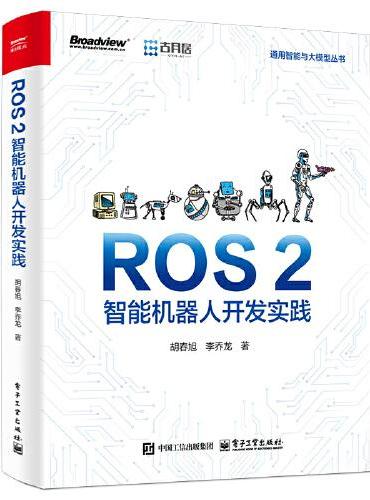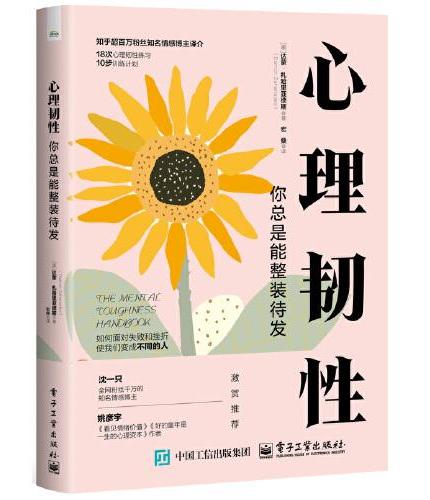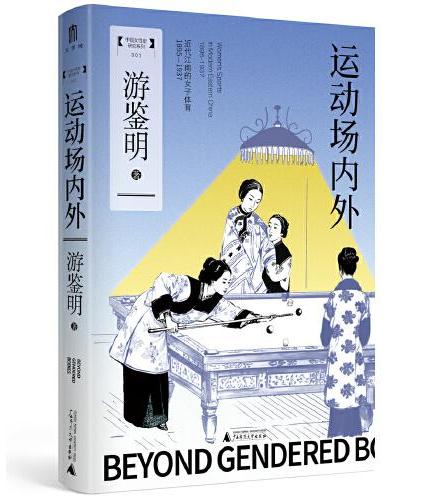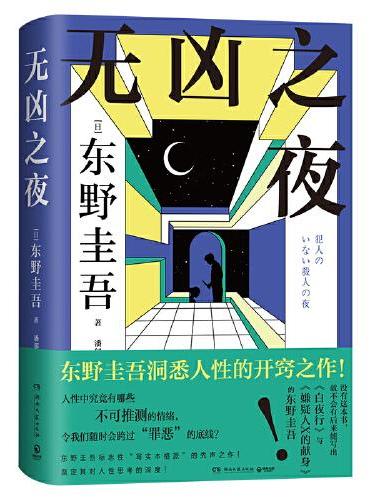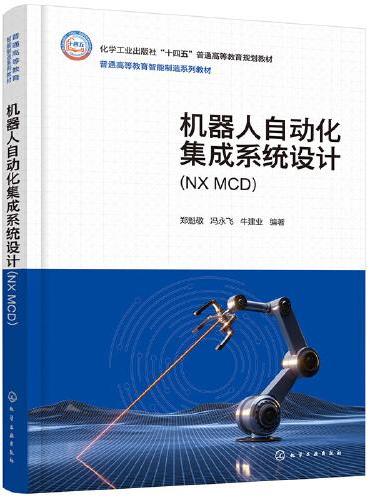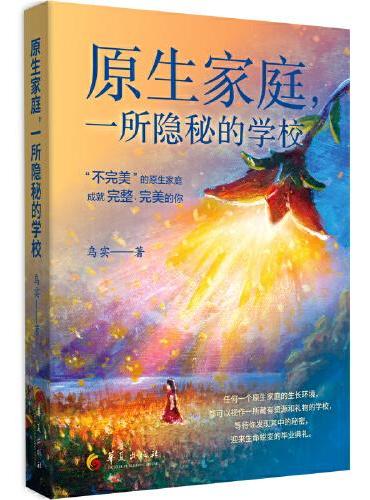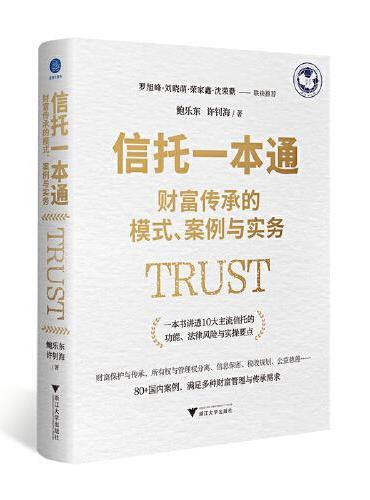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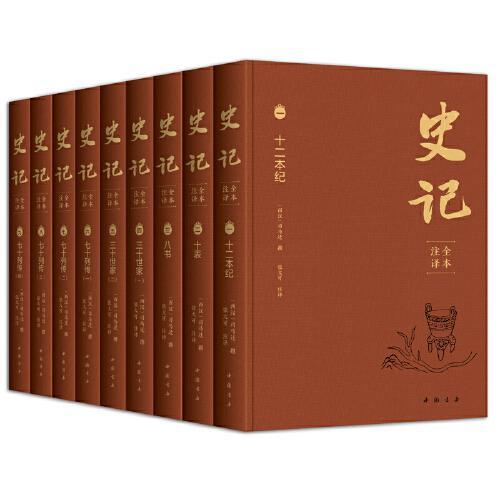
《
史记全本注译(布面精装,全套9册) 附赠“朕来也”文创扑克牌1副!
》
售價:HK$
7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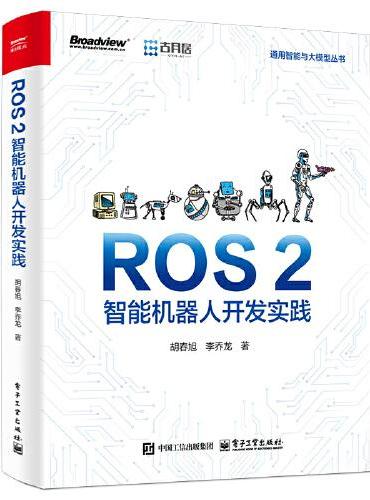
《
ROS 2智能机器人开发实践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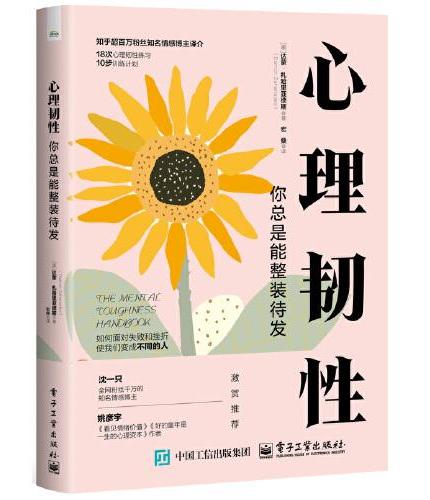
《
心理韧性:你总是能整装待发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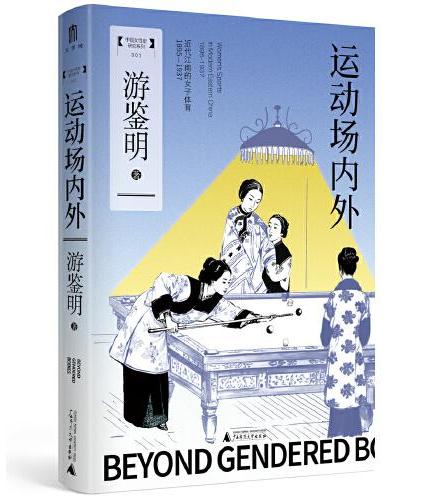
《
大学问·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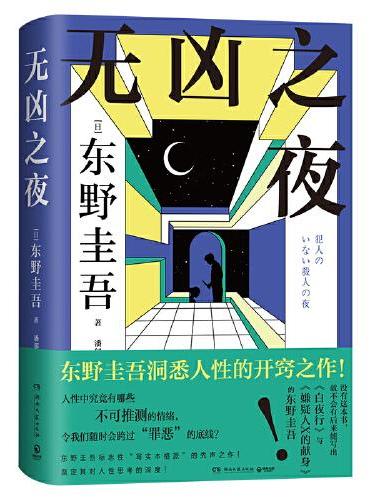
《
无凶之夜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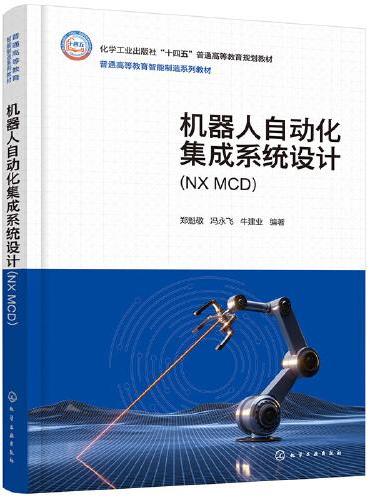
《
机器人自动化集成系统设计(NX MCD)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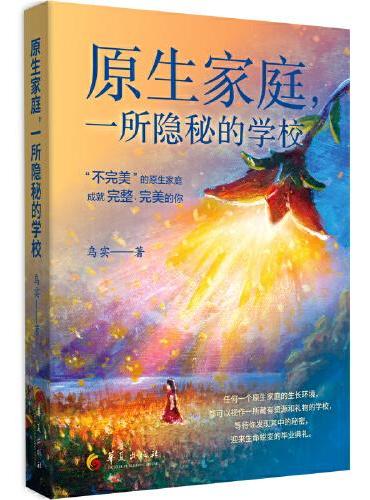
《
原生家庭,一所隐秘的学校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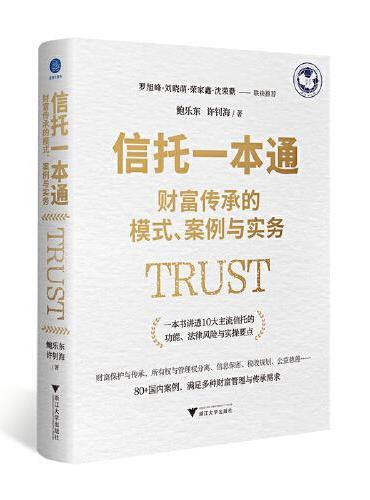
《
信托一本通:财富传承的模式、案例与实务(丰富案例+专业解读,讲透10大信托业务功能、法律风险与实操)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塞林格继《麦田里的守望者》与《九故事》之后,续写纯真与温柔之歌。
本书由《弗兰妮》与《祖伊》两篇互相关照的中篇组成。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自我存在的矛盾感,及对精神救赎的探讨推向更深层次。小说依靠精妙的对话推进,充满隐喻,百转千回,酣畅淋漓。美貌的妹妹弗兰妮如同“女版霍尔顿”,迷惘至极,濒临窒息;哥哥祖伊用洋溢着灵感和幽默感的语言,奋力将妹妹从自闭的壳中解救出来。
这也是一个关于爱,关于爱的表达的故事。
|
| 內容簡介: |
“——我们总是,总是,总是忘不了我们那点叫人作呕的、微不足道的自我。”
弗兰妮,是塞林格笔下大名鼎鼎的“格拉斯家族”的小妹。祖伊,是她上头的哥哥。他们的大哥西摩,《九故事》的“香蕉鱼”一篇中写过他,在度蜜月时突然开枪自杀,留下了一堆谜团,还有一本神秘的绿色小书。
多年后,弗兰妮正就读于知名大学,面对男友的夸夸其谈,她出于“古老而顽固的心理模式”,努力扮演温顺的小鸟。她随声附和,但内心烦躁难耐。她对世间的庸俗浅陋感到厌倦,也为自己的清醒而痛苦。她想从大哥西摩留下的那本绿色小书中寻找平静,却变得更加无法融入现实社会。当弗兰妮躺在家中,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力气,祖伊用一番辛辣而机智的话,解救了她……
|
| 關於作者: |
J. D. 塞林格(1919—2010)
青年人的精神守望者,传奇的文学隐士。
20岁前,热衷写作和表演,编辑校报,在校剧团反串女角。三进大学,三度退学。
20岁后,开始发表短篇,参加诺曼底登陆、许特根森林血战,反间谍,审讯纳粹,解放集中营,获总统嘉奖令和五颗战星。
30岁前后,退伍后战争创伤应激障碍严重,以写作和修禅疗伤。陆续发表《九故事》中的短篇。其中一篇由好莱坞改编入围奥斯卡奖,但塞林格观影后大为光火,之后拒绝任何影视改编。
32岁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用首印稿费买下偏远山乡一处不通水电的老宅。
33岁,搬出纽约公园大道的公寓,隐居乡村,开荒种地,结婚生子。
35到40岁之间创作《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之后未再正式公开发行作品,声称只为自己而写。
91岁逝世。全球读者自发纪念,网络朗诵塞林格作品。
|
| 內容試閱:
|
“哦,见到你真好!”车子启动后弗兰妮说,“我想你。”话音刚落她就意识到这话根本不是真心的。她再次感到内疚,于是拉起赖恩的手,紧紧地,温柔地,跟他的手指交叉在一起。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两人来到市中心一家名为“稀客来”的饭店,选了一张相对安静的桌子坐了下来。这家饭店颇受本地学生中专心学习的一拨人的青睐——耶鲁或者哈佛的学生们通常会漫不经心地把他们的女朋友带到这里,而不是“默里”或者“克鲁尼”饭店。据说这一带的饭店中只有“稀客来”的牛排不是“那么厚”——拇指和食指之间约一英寸的厚度。“稀客来”是吃蜗牛的地方。在“稀客来”,大学生和女朋友通常会各点一份色拉,或者很多时候两人谁都不点色拉,因为色拉酱里有大蒜。弗兰妮和赖恩都在喝马提尼酒。酒大约是十到十五分钟之前上的,赖恩尝了一口,然后往椅背上一靠,很快把房间扫视了一圈,明显有些沾沾自喜,因为他正在一个品位无可挑剔的地方和一位相貌无可挑剔的女孩约会——这个女孩不仅容貌极其出众,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好看得一点儿都不落俗套,不是那种羊绒毛衣和法兰绒短裙的千篇一律的好看。赖恩瞬间的心理暴露没有逃过弗兰妮的眼睛,她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沾沾自喜。但是出于某种古老而顽固的心理模式,弗兰妮选择为自己的这种洞察力感到内疚,作为惩罚,她强迫自己格外投入地倾听赖恩接下来的长篇大论。
如果一个人独霸话语权超过一刻钟,并且相信自己已经进入一个只要开口就不会出错的状态,那么他说话的样子就会和现在的赖恩一模一样。“我的意思是,说白了,”他说,“他缺少的东西其实就是睾丸气。你明白吗?”赖恩向他的倾听者弗兰妮靠过去,极其夸张地耷拉着肩膀,两个前臂分别放在他的马提尼酒杯的两侧。
“缺少什么?”弗兰妮说。她说话前不由自主地清了清嗓子,因为她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说话了。
赖恩犹豫了一下。“阳刚之气。”他说。
“你刚才说的我听到了。”
“不管怎么样吧,可以说,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母题——我本想尽力委婉地说明的,”赖恩说,紧抓自己刚才的话题不放,“我是说,上帝啊。我是真的以为这篇文章会像他妈的扔出去的铅球一样,可是文章拿到手,我一看,一个他妈的斗大的‘A’,我发誓我差点晕过去。”
弗兰妮又清了清喉咙。显然她判自己做一个纯粹听众的徒刑已经服满了。“为什么?”她问道。
赖恩看上去似乎略微有点儿被打断的意思。“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觉得这篇文章的下场会像一只铅球?”
“我刚跟你说了。我刚刚说完。这个布鲁曼是个大大的福楼拜迷。至少我这么觉得。”
“哦。”弗兰妮答道。她微笑了一下,啜了一口她的马提尼。“这酒真棒,”她说,眼睛看着玻璃杯,“它不是二十比一的浓度,太好了。我不喜欢一杯都是杜松子酒。”
赖恩点点头。“反正我想那篇鬼文章就在我房间里。如果我们这个周末有机会,我就读给你听一下。”
“棒极了。我很想听。”
赖恩又点了点头。“我是说我也没说什么惊世骇俗之类的东西。”他换了个坐姿,“但是——我不知道——我想我对于作者为什么近乎神经质地执着于字眼推敲的强调还是有点道理的。我是说从我们今天所知的一切角度来看。不光是精神分析那一套废话,但是当然也有一定联系。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可不是弗洛伊德的门徒,但是有些东西你不能光给它们贴个弗洛伊德的标签就算完了。我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完全是正确的,我指出所有那些真正厉害的家伙——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没一个是咬文嚼字的。他们就是在写。知道我的意思吗?”赖恩多少带些期待地看着弗兰妮。他觉得弗兰妮一直都是格外认真地在听他说话。
“你的橄榄,你还吃不吃了?”
赖恩很快地扫了一眼自己的马提尼酒杯,然后又看看弗兰妮。“不吃了,”他冷冷地说,“你要吃吗?”
“如果你不吃的话——”弗兰妮说道。她从赖恩的表情知道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她突然不想吃橄榄了,而且奇怪自己干吗会提出要这颗橄榄。然而赖恩把他的马提尼递过来的时候,她只能接受橄榄,然后假装津津有味地吃下去。桌上放着赖恩的一包烟,弗兰妮抽出一支来,赖恩帮她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支。
谈话被橄榄打断之后,有一段短暂的沉默。赖恩再次开口了,但只是因为他不是那种能憋住一句俏皮话的人。“这个布鲁曼觉得我应该找个地方发表这篇文章,”他突然说,“可是,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好像突然累坏了一样——或者说像是被榨干了一样,既然整个世界都在贪婪地攫取他的智慧果实——他开始用手掌心揉自己一边的脸颊,下意识地不太文雅地从一只眼睛里抹去一粒眼屎。“我是说,关于福楼拜这些家伙的评论文章,实在太他妈多了。”他若有所思地停下来,看起来有一丝忧郁。“事实上,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真正有见地的——”
“你说话的样子就像一个代课的。是真的。”
“你说什么?”赖恩故作镇静地问。
“你说话完全就像一个代课的。我很抱歉,但这是事实。你真是这样的。”
“是吗?那么请问一个代课的是怎么说话的?”
弗兰妮意识到赖恩火了,而且也知道他火到了什么程度,但此时她的心里,自责和恶毒的成分各占一半,她感到自己想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代课的是怎么说话的,但在我们那地方,教授不在的时候,或者精神出问题或者去看牙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代课的过来。通常是个研究生之类的。总之,如果是堂——比方说,俄罗斯文学课吧,他就会走进来,衬衣纽扣个个扣紧,还打条领带,然后就会把屠格涅夫骂上半个小时。接着,等到他说完了,也就是等他把屠格涅夫糟蹋尽了,他就开始讲司汤达或者他在硕士论文里写的其他什么作家。我上的那个大学的英文系大约有十个这样的代课的,他们跑来跑去,净糟蹋东西。他们聪明到什么程度,他们几乎不开口——请原谅我的自相矛盾。我是说你要是跟他们起了什么争执,他们做的就是露出那副笑眯眯的表情——”
“你今天吃错药了吧——你知道吗?你他妈到底怎么了?”
弗兰妮飞快地弹了弹烟灰,然后把桌上的烟灰缸朝自己这边挪了一寸。“对不起。我糟透了,”她说道,“一个礼拜以来我都感觉充满了破坏力。太糟糕了。我真可怕。”
“你那封信可他妈没这么有破坏力。”
弗兰妮郑重地点点头。她的眼睛看着落在桌布上的一小方温暖的阳光,有一张扑克牌的大小。“我写的时候不得不强迫自己。”她说。
赖恩正想开口接话,一个收拾空酒杯的侍应生突然出现在桌旁。“再来一杯吗?”赖恩问弗兰妮。
没有回答。弗兰妮正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一小方太阳光,仿佛她正考虑着要不要躺进去。
“弗兰妮,”赖恩耐心地叫了一声,是叫给侍应生听的,“再来一杯马提尼,要不要?”
弗兰妮抬起头来。“对不起。”她看着侍应生手中的空酒杯,“不要。要。我不知道。”
赖恩干笑了一声,眼睛看着侍应生。“要还是不要?”他问。
“要,劳驾了。”弗兰妮似乎警觉到了什么。
侍应生这才离开。赖恩目送他出去后回头看着弗兰妮。她正在侍应生新换的烟灰缸里弹烟灰,嘴巴没有完全合上。赖恩看了她一会儿,心里越来越烦躁。很有可能他是讨厌而且害怕在自己认真交往的女朋友身上看到任何疏远的痕迹。不管怎样,他肯定担心这个吃错药的弗兰妮也许整个周末都会这样闹别扭。他突然向前靠过去,把手臂放在桌上,一副要把这件事摆平的样子,上帝可以做证。但是弗兰妮比他先开口。“我今天不行,”她说,“我今天真是没救了。”她发现自己看着赖恩,好像他是个陌生人,或者是地铁车厢里一幅宣传某油毡牌子的张贴广告。她再次隐隐地感到不忠和内疚,这一整天似乎注定要这样了,她条件反射地伸手握住赖恩的手。但她几乎即刻又抽回了手,从烟灰缸里捡起她的烟。“我马上就会好的,”她说,“我保证。”她对赖恩微微一笑——可以说是真诚地一笑——这一刻如果赖恩也能回报以一笑的话,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许至少不会糟糕得那么彻底,但是赖恩正忙着摆出他的招牌式疏远姿态,他选择了保持严肃。弗兰妮吸了一口烟。“要不是现在说这个太迟了,”她说道,“要不是我傻瓜似的决定拿个优秀学生奖,我想我早就不读英语专业了。”她弹了弹烟灰。“我受够了这些老学究和自以为是的毁人精,我简直要喊救命。”她看着赖恩。“对不起。我不说了。我向你保证……我要是真有种,今年就根本不会去大学报到。我不知道。我是说这真是场不可思议的闹剧。”
“妙,真是妙啊。”
弗兰妮觉得自己被赖恩讽刺也是活该。“对不起。”她说。
“别再说对不起了——行吗?我想你大概从没意识到你实在太以偏概全了。如果所有英文系的人都是这样的毁人精的话,那么整个就会完全不同——”
弗兰妮打断了他,但几乎听不见她说了什么。她的眼睛越过赖恩炭黑色的法兰绒大衣的肩头,望向饭店大厅的某处。
“怎么了?”赖恩问道。
“我是说我知道了。你是对的。我就是不对劲就是了。别管我。”
但是一旦赖恩跟谁起了争执就非得占上风,否则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是说,妈的,”他说道,“生活中各行各业里都有没用的人。我是说这是基本道理。我们先别谈该死的代课的了。”他看着弗兰妮。“你在听我说话吗,还是又怎么了?”
“是的。”
“你们学校的英文系有两个全美国棒的家伙。一个曼留斯。一个艾斯波斯特。天哪,我真希望这两人能在我们这儿。至少他们算是诗人,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们不是诗人,”弗兰妮说,“这是糟糕的部分原因。我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诗人。他们不过是写诗的人,然后可以到处发表出版诗集罢了,但他们不是诗人。”
她停下来,意识到了什么,把烟灭了。她的脸色好像越来越差,有好几分钟了。突然,甚至她的口红都显得淡了几分,就像刚用餐巾纸抹了一下。“我们别说了。”她说,几乎有些坐立不安,她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捻碎了。“我实在不行了。我会把整个周末毁了的。也许我凳子下面有个暗门,那我就可以消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