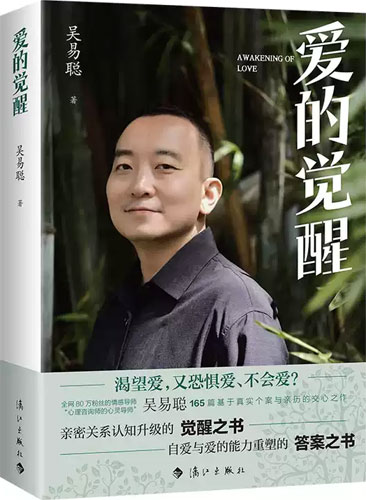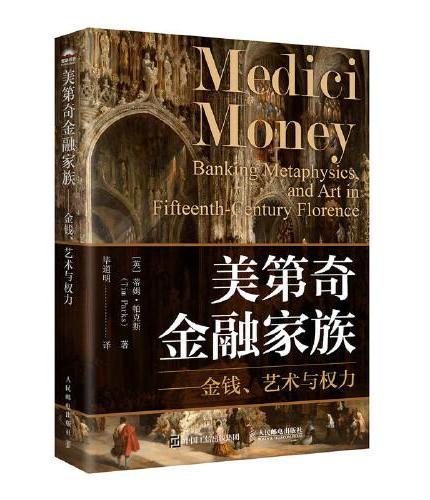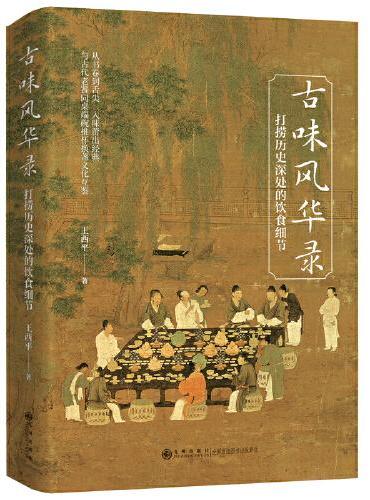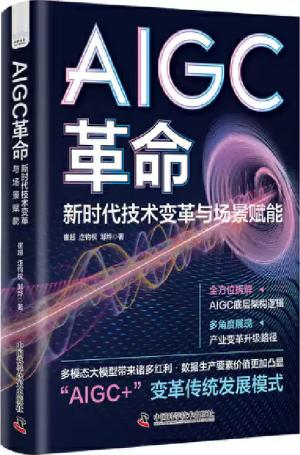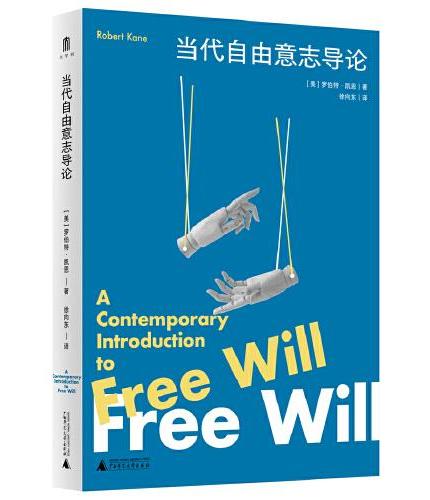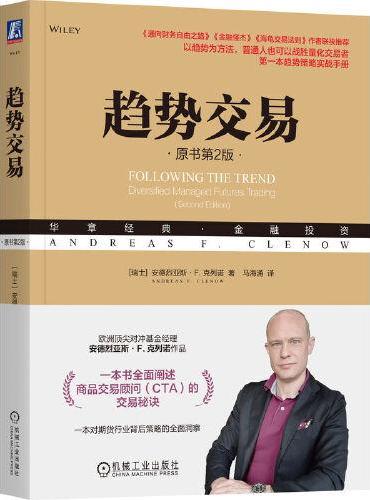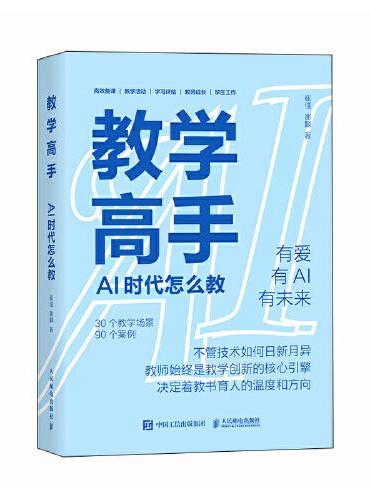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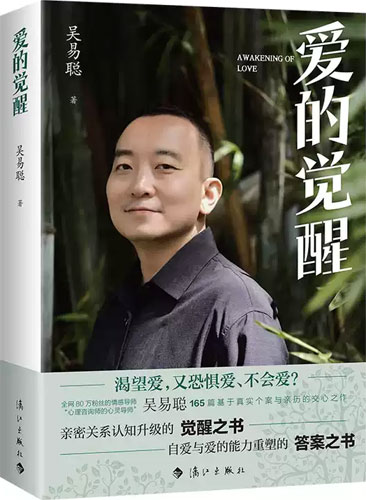
《
爱的觉醒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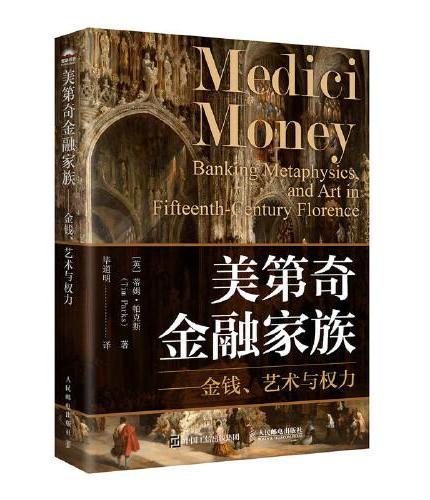
《
美第奇金融家族——金钱、艺术与权力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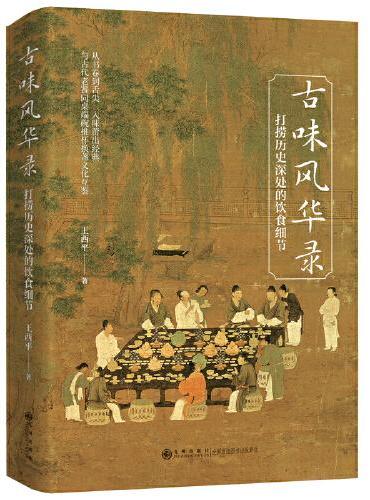
《
古味风华录:打捞历史深处的饮食细节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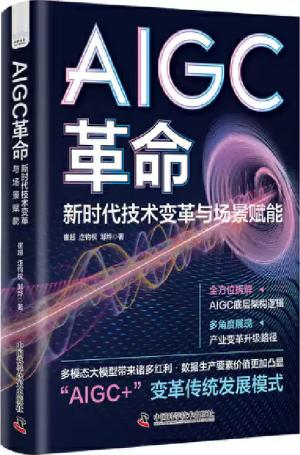
《
AIGC革命 :新时代技术变革与场景赋能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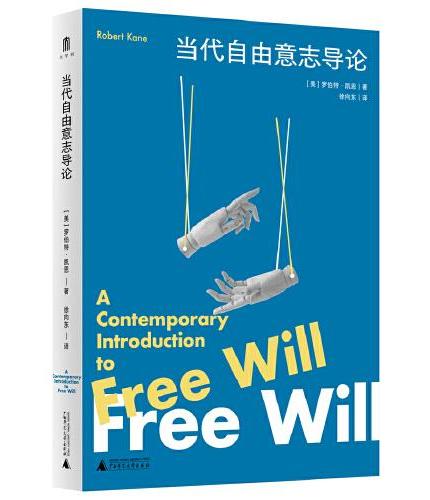
《
大学问·当代自由意志导论(写给大众的通俗导读,一书读懂自由意志争论。知名学者徐向东精心翻译。)
》
售價:HK$
74.8

《
(格式塔治疗丛书)进出垃圾桶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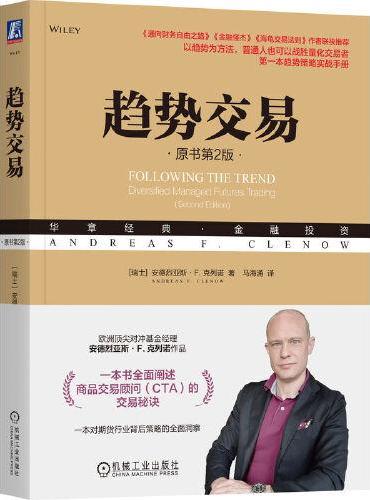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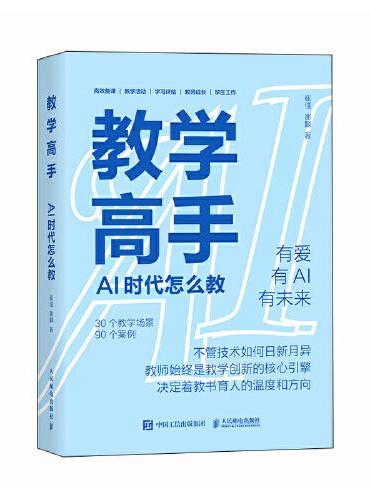
《
教学高手:AI 时代怎么教
》
售價:HK$
65.8
|
| 編輯推薦: |
每本值得珍重的书,都需要,独特的打开方式。
以特有的小心,读那些伟大的书,让我们有可能,成为更好的人。
|
| 內容簡介: |
|
黄德海是优异的评论家,更是卓越的阅读者,涉猎广、用心专,所见所指皆为人心与世事之根本。本书在版的基础上予以增补:解读《左传》《随笔集》这样的经典之作,摹想玻尔、海森伯、薇依这样的伟大心灵,分享金庸、金克木、张五常等对作者本人影响甚深的作家与作品——于此基础上,增加了对《三体》《青鸟故事集》《沈从文的前半生》这样写于当代,具备经典视角作品的参详。同时,还收录了作者日常阅读中记述的十数则格言及其理解。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作者让我们更了解自己,以便有可能,成为更好的人。
|
| 關於作者: |
黄德海
1977年生,山东平度人,现居上海。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曾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著有《世间文章》《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等。
|
| 目錄:
|
书到今生读已迟(代序) ………………… 1
跳动的火焰
自愿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 ………… 3
你越过了遥远的距离把手伸给我 ………… 9
一个好的墓志铭,用不着这么准确 ……… 16
六鹢退飞过宋都 …………………………… 23
善念进入崎岖起伏世界的真实模样 ……… 30
抓住内心世界隐秘的起伏 ……………… 37
一直移动着的时间 ………………………… 44
从没真正离开 / 存在的鬼神世界 ………… 51
如果我们把梦看成一个作品 ……………… 59
爱命运
涉及一切人的问题 ……………………… 67
月明帘下转身难 ………………………… 85
安宁与抚慰 ……………………………… 105
在世俗的门槛上 ………………………… 112
利玛窦的礼单,或万历二十九年 ……… 126
《三体》:大荒山寓言 …………………… 136
备忘抄 …………………………………… 150
目前无异路
金庸小说里的成长 ……………………… 165
斯蒂芬张的学习时代 …………………… 178
海中仙果结子迟 ………………………… 190
有这样一个老头 ………………………… 201
从艰难的日常里活出独特的生命形状 … 211
开阔健朗与细心耐烦 …………………… 218
用使人醉心的方式度过一生 …………… 225
附 录
内心的指引 ……………………………… 233
为谁写作?(代后记) ………………… 263
增订版补记 ……………………………… 269
|
| 內容試閱:
|
为谁写作?(代后记)
据汉娜·阿伦特说,瓦尔特·本雅明的理想,是“写一部通篇都是引语、精心组合无须附带本文的著作”。这样一本著作,“将残篇断语从原有的上下文中撕裂开来,以崭新的方式重新安置,从而引语可以互相阐释,在自由无碍的状况中证明它们存在的理由”。不用说写一本著作,即使要在很短的篇幅内谈论“为谁写作”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要求也太高了。退而求其次,试把眼见所及的言辞,缀合成篇。
1751年,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出版。在这篇为法国第戎科学院有奖征文撰写的文章里,他谈到了为谁写作的问题:“每个艺术家都想得到赞赏。同代人的赞誉,乃是艺术家的酬报中珍贵的部分。如果不幸在他生活的民族和时代里,闻名一时的学者竟让一群轻浮的年轻人左右他的文风,杰出的诗剧被人遗忘,美好的音乐遭人鄙弃;在这种情况下,他怎样去博得人们的称赞呢?他只好把他的天才降低到他那个时代的水平;他宁肯作一些在他活着的时候招人喜欢的平庸篇什,也不愿写在他死后很久才享盛名的杰作。”
在这段文字之后,卢梭直呼伏尔泰的本名,责问他:“为了故作风雅,你牺牲了多少强壮有力的美?为了炫耀你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所能表现的风流才华,你少写了多少伟大的作品?”那么,表现强壮有力的美,写出伟大的作品,却不是为了博得同时代人的赞誉,究竟是为了谁呢?
对卢梭本人来说,这大概不是什么问题。他在序言里已经坚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绝不为当代追随风尚的读者写作:“我既不打算取悦那些才俊,也不想讨好各位名流。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些屈从于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社会风向的人……既然想超越所生活的时代,就不能为这样的读者而写作。”卢梭的这一意志,有尼采遥相呼应。在《敌基督》前言里,尼采写道:“本书属于极少数人。这些人中也许已经没有谁还活着……我怎么可以让自己混同于今天已经长出耳朵的人?惟有明天之后才属于我。有些人死后才出生。”
为未来而写作,不光两个相隔不远的哲人,也几乎是古今有大志的写作者的志向。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谓,“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正是这个意思。被称为“精神大师”的室利阿罗频,也把自己划入了这个范围:“我们不属于过去的黄昏,却属于将来的午昼。”他们用自己的文字,呼唤着那些人群中“有耳能听”的人,或者,如庄子《齐物论》云:“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想来不致误会吧,“英雄与一代凡人皆为知己”,为未来的写作,并不是作者故意脱离时代,与时代格格不入,他们只是不愿降低自己的水准,屈从于某些风气而已。
对卢梭这一吁求朴素的回应,该算是他的同时代人本杰明·富兰克林。1771年,富兰克林给儿子写信,追溯家史,尤其是回忆他个人的一生。这封信,就是后来著名的《富兰克林自传》的部分。作品开头,富兰克林交待了写这些信的原因:“我出身贫寒,幼年生长在穷苦卑贱的家庭中,后来居然生活优裕,在世界上稍有声誉,迄今为止我的一生一帆风顺,遇事顺利,我的立身之道,得蒙上帝的祝福,获得巨大的成就,我的子孙或许愿意知道这些处世之道,其中一部分或许与他们的情况适合,因此他们可以效仿。”
富兰克林这种写下自己一生,以供后人效仿的写作,很有古典“大人”之风。在古希腊,人应效仿的典范是神,如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法义》中所言:“一切事情中重要的事情,就是获得关于神们的正确思想。有了这种思想,你就可以过一种好的生活,否则,你得过一种坏的生活。”照希罗多德的说法,“赫西俄德与荷马……把诸神的家世交给希腊人,把诸神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交给所有人,还说出了诸神的外貌”。这些作品,摹写诸神的世系和特性,面向一国民众的当下和未来,确立一国的特殊生活方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特殊生活方式的养成,有赖于高于人的存在——诸神。在富兰克林的自传里,这个高于人的存在,被称为上帝。这类写作,把属神的高贵带到人间。就像卡夫卡在一次谈话中说的,写作“倾向于祈祷”,“艺术就像祈祷一样,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爱的东西,从而变成一只馈赠的手”。那么,有没有一种写作,写到神不是为了世间的生活,而是只为这高于人的存在而写?
在谈论俄尔甫斯教祷歌时,韦斯特(West)描述了一种颂神的氛围:“某一个私人文化团体的成员夜聚屋内,借着烛火,在八种焚香的气息萦绕中向他们想到的神祷告,唱这些祷歌。”这种向神书写的文字,也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按《诗大序》的说法,《诗经》里的“颂”,就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屈原的《九歌》,也明明确确是愉神之作。王逸《楚辞补注》:“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在这个写作的序列里,因为对象是高于人的存在,人要把好的自己和自己好的所有展现给神看,写出自己的勇敢、节制和虔诚,写出世上的美好和庄严。
萨特和加缪在很多问题上意见分歧,但在为谁写作的问题上,看起来却相当一致。对萨特来说,“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自己,那不符合实际……没有一种艺术不为别人或是没有别人参加创造的”。加缪也认为,“一个作家很大程度上是为被阅读而写作的(至于那些说他们不是的那些作家,让我们钦佩但不要相信他们吧)”。以上为了不同对象的写作,仿佛也验证了他们的结论。那么,有没有一种写作,不是,或首先不是为别人而写的呢?就像维特根斯坦相信的那样:“就改善你自己好了,那是你为改善世界能做的一切。”
1903年,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写信,“尊敬的先生,除此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劝告:走向内心,探索你生活发源的深处,在它的发源处你将会得到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必须’创造。它怎么说,你怎么接受,不必加以说明”。这样一种首先指向内心的写作,不止属于诗。在《以学术为业》中,马克斯·韦伯坚决地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在眼前这份草稿的这一段里所做的这个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同学术无缘了……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这种先要经过自我确认的写作,差不多可以称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这些写作者来说,“关心你自己”、“认识你自己”、“照顾你自己”是的目标,他们在内里认识自己、澄清自己,并通过写作把这个认识和澄清提纯,甚而由此走向幸福之路,把自己的一生谱写为独一无二的乐章。
不管是为当代人写作,为未来者写作,甚至为一个民族,为至高的存在,抑或只是朝向自我的写作,凡写下的文字,都不能期望它真的会“像跳动的火焰点燃了火把,立即自足地延续下去”。如同柏拉图在《斐德若》中所说,文字本身是不可靠的,何况还伴随着误解:“没有任何理性的人敢于把他那些殚精竭虑获得的认识托付给这些不可靠的语言工具,更不敢让那些认识遭到书写下来的文字所遭受的命运。”因而,不管是为谁的写作,或者为了传达什么珍贵的东西,即使写作者本身极其严肃,终,对它是否或如何传达给听者的期待,差不多只能是但丁《神曲》里所说的:“放弃一切希望。”或者,对待为谁写作这件事,应该如基尔克果《恐惧与战栗》作为草稿的题词那样,给自己一个坚决的答复:
“写作吧。”
“为谁写作?”
“为那已死去的,为那你曾经爱过的。”
“他们会读我的书吗?”
“不会!”
书到今生读已迟
一
处身于现在的时代,不幸到永远也无法回到文化的未开化状态,因此,一个企图在精神领域有所领悟的人,就必然被迫跟书生活在一起。照列奥·施特劳斯的严苛说法——生命太短暂了,“我们只能选择和那些伟大的书活在一起”,“在此,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好从这些伟大的心灵中选取一位作为我们的榜样,他因其共通感(common sense)而成为我们和这些伟大的心灵之间的那个中介”。
可是你没有恰好生于书香世家,也没在很早就遇上一位教你如何阅读的老师,当然就不会走运到一开始就遇上那些伟大的书。对书抱有无端爱意的你,开始阅读的,只能是你将来弃之如敝屐的那些——小时候,是战天斗地的连环画,地摊上有头无尾的儿童读物,动物的凶残和善良;稍大一点,大人藏在抽屉里的书被悄悄翻出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神鬼出没的无稽传说,形形色色的罪案传奇,以男女情事为核心的拙劣编造……运气好一点,你会碰上巴金的《雾雨电》,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甚至封面上印着“迅鲁”的《呐喊》。
那时候,你把从各种渠道弄来武侠、言情、校园小说包上封皮,偷偷摸摸地在教室里经历别人的喜怒哀乐。很快,你吃了平生次冤枉。有个跟你一样喜欢读书的家伙,把一本看卷了边的书像往常一样丢在你的床上,封面上是个妖娆的女人。你还没来得及翻看,书就被没收了,对你期许甚深的老师不待你辩解,就对你一顿拳打脚踢,并从此不再理你。
没错,这不过是你事后的回忆,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是传奇、武侠,更不会知道,有些故事旨在引逗你想象异性日常之外的样子——只有对书的盲目热爱(Eros)引导着你。
你从一个藏书颇富的人家搞到一批历史小说,《杨家将》、《薛刚反唐》、《罗通扫北》、《三请樊梨花》、《朱元璋演义》……那一年在瓜棚里,你还不知道有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女孩正满怀恐惧地盯着这个世界,只顾沉浸在那些早已老旧的故事里,忘记了周遭的燠热,忘记了太阳正慢慢落下西山,直到一本本厚厚的书来到后一页,直到再上学时,你不知为什么再也看不清黑板。
戴上眼镜的你到县城去上学了,那些小小的博学者开始出现,她/他们嘴里,全是些陌生的故事和人名,全是你没读过,也从未听说过的清词丽句。恍若走入飞地,飞地上的一切,你都那么陌生。好吧,那就开始领略这个美丽新世界。你每天早晨五点准时起床,背一个小时的诗词,然后去跑步,胸怀里全是“少年心事当拏云”的豪情。
夜晚,你去读那些陌生的名字写下的陌生故事。你当然记得,那天有人丢给你一本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说可以完全代替你脑子那些满是手汗污垢的租来的小说。你严严实实地蒙在被子里,借着手电的光照,一口气读完。此后两个小时的短暂睡眠,你在半梦半醒间跟达尔达尼央不停地说着话,仿佛在为他筹划,也好像是在劝说自己,用的是庄重的大腔圣调。睡梦中的对话让你疲惫不堪,幸亏同宿人的起床声,唤醒了精疲力尽的你。
你不会忘记,那个次吻你的女孩带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个名字拗口的人写的书又厚又重,情节紧张到让你溽暑里满身冷汗,你才不管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结局如何,只急着要知道那个纯洁的女孩索尼娅终是怎样的归宿。天蒙蒙亮的时候,书读完了,你一直擎着书的左手开始抽筋。用冷水洗把脸,你振奋地写好一封信,骑行了六十里路,把信悄悄塞进她的邮箱。
那时候你肯定不会知道,出于热爱的读书时光已经结束,而那个女孩,也将在不久之后决绝地离你而去。
二
有个幸运的孩子叫约翰·穆勒,你要长大了才知道羡慕。就是他,在父亲督促下,几乎在少年时期就完成了自己所有的读书储备。他三岁开始学习希腊文,没有进过学校,却在十七岁之前阅读了绝大多数希腊罗马古典,系统学习了几何与代数、经院派逻辑学、政治经济学、化学和植物学,终,他以等身的著作,证实了完备而系统的阅读的必要性。
按父母的理想计划塑造孩子的愿望,是极其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并极易导致精神问题。果然,二十岁的时候,约翰·穆勒遭遇严重的精神危机。以毒攻毒,他竟用对华兹华斯的阅读,安然度过此次危机。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还没有奢侈到要考虑精神危机,甚至都没来得及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就要按照小穆勒的方式,给自己制定一个完备的学习计划。
你找来了各个学校开列的文史哲书目,比较,甄别,剔除,然后手抄了一份自己的定本,从头到尾读起来,读罢一本,划掉一本。你根本不明白当时哪来的好胃口,不管什么类型的书,只要是这份书目上,《诗集传》也好,《判断力批判》也罢,或者是《蔷薇园》,《薄伽梵歌》,你都能兴致勃勃地读过去。有时候从图书馆出来,夜已经很深了,路两旁是婆娑的树,抬起头,能看到天上密密的星。那样的晚上,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股力量,让你觉得身心振拔,走路的时候,脚上都仿佛带着弹性。
以后你会经常想起那些日子,想起你初读索福克勒斯时感受到命运的肃杀,想起你竟然无知到连读《天官书》都用白文本,想起你对读莱辛和罗丹时的惊喜,想起你读完《高老头》时内心的悲愤,想起你读《元白诗笺证稿》时的砉然之感,想起你发现《批判哲学的批判》逻辑矛盾时的欣喜,想起你在摇曳的烛光里读完了黑格尔的《美学》,蜡烛也堪堪烧完,“噗”的一声,你沉浸在怡人的黑暗和静谧里。
即便有这样的美好时光,你还是骗不了自己。虽然书单上剩下的书越来越少,可书中的世界依然纷繁复杂,你也并没多少让自己身心安顿的所得。因为缺乏共通感,你没有找到自己的榜样,并未出现的那个人,当然也不会成为你和伟大的心灵之间的中介。你变得焦虑,转而根据正在读的书的脚注,来寻找下面该读的书,努力找到每本书更高的精神来处。
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一定是得了“大书贪求症”,每天都规定自己读起码多少页“伟大的书”。你当时的想法是,等有一天把这些“大书”读过一遍,那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一定会显露出她澄澈的面目,跟你平常看到的那个绝不相同。事与愿违,你不光没有读懂那些大书,身心还仿佛被抽走了一些什么,连阅读平常书籍的乐趣都失掉了。那时,你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觉得你肯定不是被选定的读书人,竟有段时间废书不观。那些美丽的夜晚不再有了,脚步也渐渐失去了弹性。
你闷坐在宿舍里,蔫蔫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头。走廊上语声渐渺,你看见自己在一间灯火通明的屋子里读书,情境好像是冬天,你身上裹着毯子。其时你大约是被书迷住了,因为你不断用已经发红的手掌拍打着桌子。一个不知是什么的东西,黑魆魆地向读书的你袭来,拿走了你的什么东西。读书的你丝毫没有觉察,继续不时地拍下桌子。你大声地提醒读书的你注意,但声音仿佛被什么扼住了,压根发不出来。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读书的你,被那个黑魆魆的东西不停地从身上一次次拿走什么。读书的你仍然没有注意,还在兴高采烈地拍着桌子。你看见读书的你一点点枯槁下去,只剩下一副支离的骨架。这时,那个黑魆魆的东西又来了,直奔那副骨架。你实在急坏了,用尽全身的力气提醒那个读书的你,快跑!快跑!读书的你依然一动不动,黑魆魆的东西碰上骨架,骨架慢慢倒下。你走上前,要扶起那副骨架,骨架慢慢转过了头,突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你袭来。你觉得身上有个地方咯噔一下,什么东西确定无疑地流失了。你从梦中醒来,好大一会儿不能动弹。
当从另一个真实的梦魇中醒来的时候,你沮丧得无以复加,觉得在真实世界和精神领域,你都失去了依傍,那个伟大的心灵置身的世界,跟你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
三
你要到很久以后才看到这个故事。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记载,有一次色诺芬被苏格拉底拦住去路,问他在哪里可以买到各种食物,色诺芬逐一道来。话锋一转,苏格拉底紧接着问:“人在哪里可以变得美好?”色诺芬哑然无对。“来跟我学习吧。”苏格拉底吩咐道。
在此之前,你只知道,叶芝拥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相信“一扇看不见的大门终会打开”。可你并不相信,因为你为自己制作的书单差不多读完的时候,那扇紧闭的大门并没有敞开,有一种什么东西,始终障碍在你和书之间。你也慢慢明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障碍。一位你敬重的前辈学人,就很长一段时间困在各路经典里,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厌烦情绪。有一件事情始终让他一筹莫展,“如果心仪古典作品的话,该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处境与这些作品建立起活生生的联系?”那些伟大的书一直都在,却从未进入活生生的日常世界。
差不多到这时,你才意识到,仅靠年少情热去读那些沉默的书,任凭你横冲直撞,它们紧闭的大门并不会因为迁就而轻易敞开,自己还会因为碰壁太多而失去基本的阅读热情。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你仿佛看到那扇此前紧闭的大门,慢慢地闪开了一道缝隙,有澄澈的光流泻出来。从这条小小的缝隙里,你略微窥见了某种被称为“宫室之美,百官之富”的东西,心下快活自省,口不能言。
你不禁想起了自己当初读《笑傲江湖·传剑》时的情形——一代宗师风清扬出场,令狐冲进入习武的高峰体验。在风清扬指导下,令狐冲一时“隐隐想到了一层剑术的至理,不由得脸现狂喜之色”,一时“陡然之间,眼前出现了一个生平从所未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天地”。你心中涌起了什么障碍被冲破的感觉,顿觉世界如同被清洗过一遍,街道山川,历历分明。
写作此节时,金庸仿佛神灵凭附,在恩怨纠葛的世情之外另辟出一片天地,清冽的气息在书中流荡。当然,次读这本书的时候,你还不会想到,有一天,你或许也会碰上令狐冲那样的好运气。想到这里,你不禁展颜微笑,内心的某个地方,缓缓放松下来。
你不再咬紧牙关,要把无论怎样艰深的书都啃下来。你试着寻找阅读中的“为己”之道,尝试去理解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学着辨识自己的性情,并根据自己的性情所向选择读物。那些离你或远或近的“大书”,不再只是“他人的故事”;那些伟大心灵的神态和举止,有时就在你面前清晰起来——他们甚至会不时参与你对日常事务的判断。
“书到今生读已迟”,即便你有再好的运气,也永远不会知道,苏格拉底是如何阅读那些古代圣哲著作的;更不会知道,色诺芬是不是从学之后,明白了“人在哪里可以变得美好”。但你现在确信,有些人就如苏格拉底一样,在引导人过一种亲近幸福的生活。你现在也相信,那个关于苏格拉底的阅读传言是真实的,他说:“古老的贤人们通过把他们自身写进书中而留下的财富,我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展开它并穿行其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