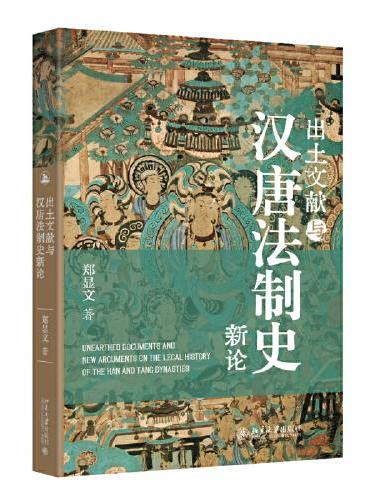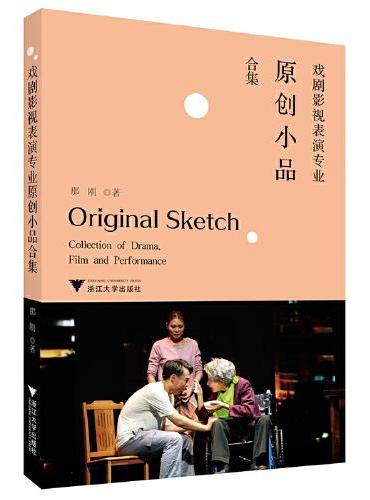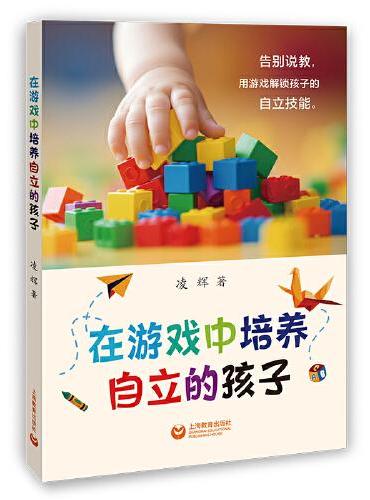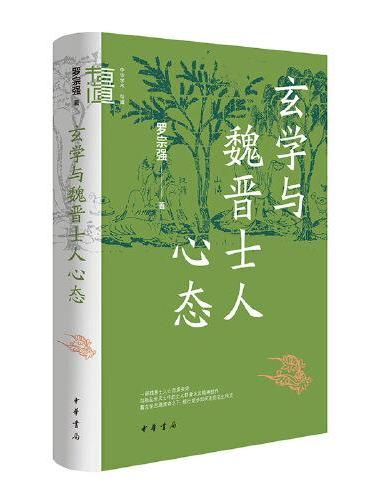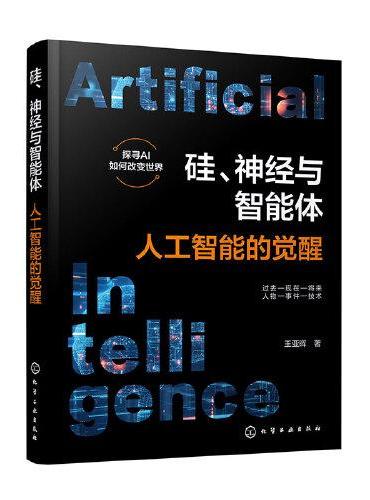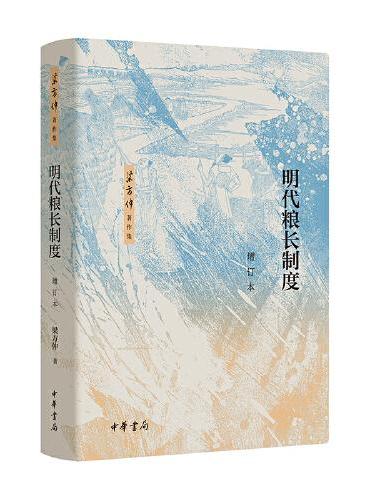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方尖碑(全2册)
》
售價:HK$
1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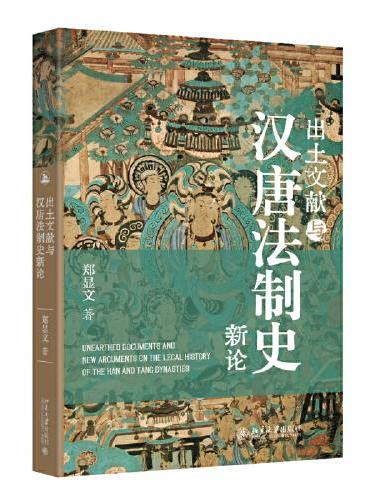
《
出土文献与汉唐法制史新论
》
售價:HK$
85.8

《
最美最美的博物书(全5册)
》
售價:HK$
1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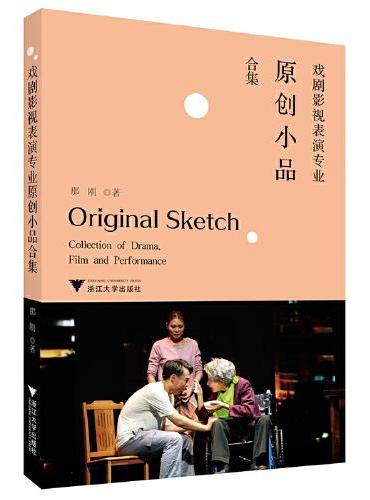
《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原创小品合集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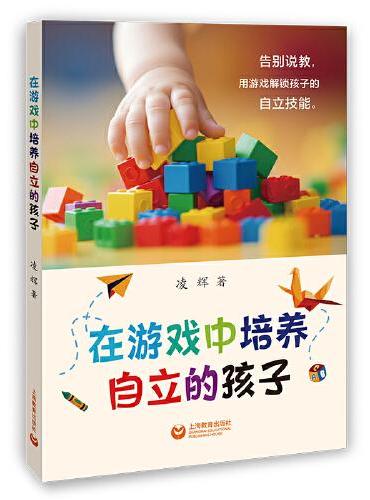
《
在游戏中培养自立的孩子
》
售價:HK$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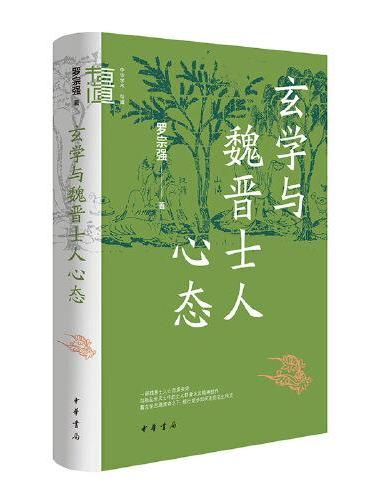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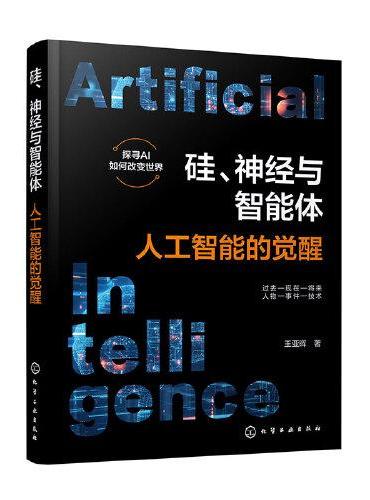
《
硅、神经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觉醒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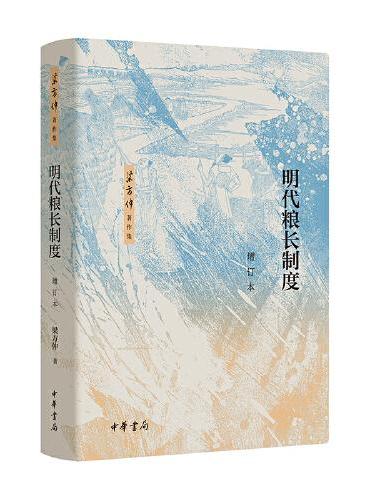
《
明代粮长制度(增订本)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HK$
68.2
|
| 編輯推薦: |
|
该书收录了蒙先生有关易学的所经典论文,不仅多方面展现了蒙先生在易学研究与自身“情感哲学”思想构建过程中的观点变化与发展,同时还回顾了蒙先生对《周易》的精彩解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 內容簡介: |
|
蒙培元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其主要哲学思想被称为“情感儒学”(他自己称之为“情感哲学”),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本书根据蒙先生在易学研究上的三个发展阶段,将其易学著述分为上编、中编、下编结集而成。本书收录了蒙先生有关易学的所有经典论文,不仅多方面展现了蒙先生在易学研究与自身“情感哲学”思想构建过程中的观点变化与发展,同时还回顾了蒙先生对《周易》的精彩解读。
|
| 關於作者: |
蒙培元,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历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访问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黄玉顺,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博士生导师。师从冯友兰先生嫡传蒙培元先生,是当代中国“儒学复兴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建构了“生活儒学”及“中国正义论”体系。
|
| 目錄:
|
目录
上编
“言意之辩”及其意义 3
“形而上”与“形而下” 15
《周易》“道器”范畴的理学诠释 22
《周易》“太极”“阴阳”范畴的理学诠释 42
《周易》“神化”“动静”范畴的理学诠释 61
《周易》“一两”范畴的理学诠释 80
《周易》“形上”“形下”范畴的理学诠释 94
《周易》的天人哲学 103
《易传》中的道德本体论 116
中编
《易经》的整体主体思维 125
略谈《易经》的思维方式 137
浅谈范仲淹的易学思想 143
《周易》形而上者观念的主体思维 149
《周易》天道性命观念的主体思维 157
《周易》与“天人合一”说的发生及发展 165
《周易》“言意之辩”的玄学诠释 183
下编
天·地·人
——谈《易传》的生态哲学 197
《易传》:儒学经典的初步诠释 211
《周易》哲学告诉我们的人生道路
——《周易人生智慧丛书》序 214
《易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 216
张载易学与中国哲学生态观 229
孔子与《周易》 250
《周易折中》整理本推荐意见 259
伏羲与《周易》文化 262
孔子是怎样解释《周易》的 274
伏羲何以是“人文始祖” 284
《周易》哲学的生命意义 287
伏羲与《周易》
——兼评安志宏的《周易》研究 294
附录
作为情感哲学的中国哲学 蒙培元 303
情感儒学:当代哲学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 黄玉顺 322
|
| 內容試閱:
|
上编 “言意之辩”及其意义
一
魏晋时期,曾经就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场热烈的讨论,这就是有名的“言意之辩”。这一问题和玄学家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即哲学本体论问题,特别是认识论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讨论的中心是,思想能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语言能不能表达思想,语言在认识中起什么作用?一句话,语言和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一是“言不尽意论”,一是“言尽意论”。它们虽然代表不同的哲学思想,但是从不同侧面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促进人类认识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讨论,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历史的根源。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玄学取代两汉经学,是学术史上的一次变革。它一扫两汉以来的章句、象数之学,代之以抽象本体之学。它讨论世界的本体是什么等问题,同时涉及认识的方法和手段等问题。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谈玄说远、崇尚无为的风气。封建士大夫阶级提倡清谈,常常讲一些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以表示清高、风雅。此外,当时还广泛开展了评论人才的活动,名士们以臧否人物、考察得失相唱和。特别是理论上开展的关于“名教”和“自然”的争论,更加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所有这些,都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认识自然和人的本质的过程中,在对待名教和自然的问题上,言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样,言意关系问题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这个问题,并不是魏晋时期才开始提出来的。魏晋玄学也有它的思想来源,玄学家总要从先秦著作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思想资料。其中,《周易》《老子》《庄子》当时被称为“三玄”,就是他们的主要依据,他们以解释这些著作的方式来阐明他们的思想。“言意之辩”即直接来源于《易传》。《〈周易〉·系辞传》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这是比较早的关于言意问题的论述,其中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可是在“言意之辩”中,这句话被用来向两个方面发展了。这场争论涉及的范围很广,它还同《论语》中的一句话有关。《论语》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时的学者们对这句话也发生了争论。孔子既然讨论过“性与天道”一类本体的问题,并且著成了文章,那么,从孔子的著作中能不能了解到关于“性与天道”的思想呢?回答是不同的。但是,言意之辩决不限于对先秦著作的解释。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就变成关于本质或本体的思想以及一般思想能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问题。
二
“言不尽意论”者以嵇康为代表,同时还有荀粲、殷浩、殷融、刘慎、何襄等人,但具体观点和论述有所不同。
荀粲是玄学中较早的一位人物。据说,他独好言道,谈尚玄远,尤好言意之辩。“粲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魏书·荀彧传》。他认为,关于“性与天道”一类思想,不能从圣人的著作中得知。因此,“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魏书·荀彧传》。。这无疑是对儒家经典的一次攻击,但它是通过讨论言意关系问题表现出来的。对《易传》中的那段话,荀粲也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同绝而不出矣。”《魏书·荀彧传》。这里所谓象,即《周易》中表现卦义的物象,如乾有刚健之义,便以龙象来表示,龙即代表刚健;坤有柔顺之义,便以马来表示,马即代表柔顺。辞是说明卦象卦义的言辞,如象辞、爻辞之类。荀粲认为,言所尽的只是具体的意义,并不是“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所谓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就是物象和语言之外的意义,也就是关于“性与天道”一类的思想。他认为在一般言、象之外,存在着“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它是“理之微者”,微妙难明,“蕴而不出”,非物象所能表示,非语言所能表达,它是超乎言、象之上的,语言对它是无能为力的。在这里,荀粲把语言同思想(意)区别开来,看到了语言本身的意义,还不等于思想,它有合理之处。事实上,语言(包括语义)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并不等于思想本身。但是,他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说什么语言不能表达思想,这就有问题了。所谓“理之微者”,且不说它的来源和内容是什么,它毕竟是某种抽象思维的产物(任何思维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按照荀粲的观点,它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语言的作用。实际上,语言所表达的,不仅是反映具体事物的思想,而且是反映一般规律的思想;不仅是反映事物现象的思想,而且是反映事物本质的思想。就是说,语言不仅表达形象思维,而且表达抽象思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产物,具有抽象的特征。《周易》中的八卦是一种符号,它代表某种意义;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意义,又使用了不同的物象;为了说明物象所代表的意义,不得不使用语言。这本身就说明语言具有抽象的意义。列宁说:“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6页。因此,它才能成为进行思维、表达思想的工具。当然,抽象和一般也是随着认识的提高不断发展的。黑格尔说过,古代哲学家给予我们的“乃是一个贫乏的规定,每个人都知道一般,但却不知道作为本质的一般”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7页。。魏晋玄学确实接触到本质的一般和本质的抽象问题,但他们所谓本体,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如果认为,关于本质的抽象根本无法用语言去表达,这就违背了事实,它实际上把思想神秘化了。
有个叫张韩的,为了证明“言不尽意论”的正确,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说:“余以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全晋文·不用舌论》。舌头是说话用的,人无舌当然不能说话,但是可以通心,交流思想。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无舌不能说话,即不能用语言表达思想;有舌虽能说话,同样不能用语言表达思想。因此,只有不说话,才能“通心”。他利用生理器官的某些特殊现象,证明有离开语言的思想,这是很有意思的。现在,不是也有人用类似的例子证明没有语言的思想是存在的吗?
“言不尽意论”的代表是嵇康。他著有《言不尽意论》一文,但今已不存,无从得知其全部思想,只有从他的《声无哀乐论》一文还可以看到某些基本观点。首先,他用音乐作例子,说明心声之间,即思想感情同客观声音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说:“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待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嵇康集·声无哀乐论》。就是说,音乐是由金石管弦等物质发出来的声音,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哀乐之情则出于人心,是主观的东西。二者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假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嵇康集·声无哀乐论》。既然心声二者没有任何联系,因此,要了解人的情感不必从表情上观察,考察人的思想不必从声音上辨别。嵇康对自然声音和主观感情进行了区分,反对从声音表情上了解人的本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完全否定。但是,音乐毕竟是社会的人经过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是借助于客观物质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对人会发生影响,产生共鸣。不仅如此,“言为心声”,“诗言志,歌咏言”。语言、诗歌都是表达内心感情的。嵇康否定了它们之间有任何联系,把音乐简单地看作自然之物,丝毫不能表达思想感情,这就错了。音乐也有自己的特殊语言,历史上所谓“知音”的佳话,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嵇康本人就是一位高超的琴师。
嵇康从心声二物的观点出发,进一步作出了言不尽意的结论。他说:“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嵇康集·声无哀乐论》。“知之之道”就是意,它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其客观内容;而语言仅仅是一种标识,并没有确定的含义。各地风俗语言不同,但可以有共同的思想认识,因此,“言非自然一定之物”。嵇康已经看到不同地域和民族的语言差别问题,他也并没有完全否定语言的作用。他承认,语言作为一种“标识”,可以代表事物,但仅仅起一种符号的作用而已。既然是“标识”,也就不能完全表达思想。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语言作为社会的产物,是历史上形成的,它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这说明它和思想是有区别的。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范围之内,语言又是“约定而俗成”的,是大家公认并共同使用的。异俗之言,并不影响共同语的使用;不同语言,也还可以翻译。因此,语言不能说仅仅是“标识”,它一旦形成,便有确定的社会含义,和思想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如果仅仅根据异俗之言不能强通,就认为“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仅仅是一种“标识”,因而得出“心不待言,言不证心”的结论,那就未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但“言不尽意论”在当时,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起了积极作用。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情在词外曰隐。”他也承认有言外之旨、词外之情。嵇康曰:“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陶潜有“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诗句,就是这种方法的表现。有些作品中的“诗情画意”确实是非常令人寻味的。《世说新语·巧艺篇》说:“顾长康幽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种“传神写照”的方法已成为我国艺术史上的美谈。此外,它还影响到学习方面。陶潜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所谓不求甚解,当然不是不求理解,意在领会精神。这也是大家喜欢引用的。这些例子说明,“言不尽意论”虽有错误,但其中包含了积极的成分,不能一概否定。不然,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积极作用呢?
三
在言意关系问题上,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提出了“得意忘言论”。它和“言不尽意论”有区别又有共同之处。
王弼的“得意忘言论”,也是以讨论《周易》中的言、象、意的关系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但由于他是以老庄解“易”,他的思想就更加带有玄学的特点。我们知道,老子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说法,《庄子》则明确提出“得意忘言”的思想。《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即由此发展而来。
首先,王弼提出了语言如何产生的问题。他认为言是由意即思想产生的。他说:“言生于象”,“象生于意”。《周易略例·明象》。又说:“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周易·乾卦·文言》注。又说:“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照他的说法,物象是根据义而生出来的,语言则是根据物象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先有思想,后产生语言。语言只是一种间接的工具,语言和思想之间还有“象”。这显然是受到《周易》的影响,不过也说明,他认为先有抽象思维,后有形象思维,而语言是从具体的形象思维中产生的。
“意”又是什么呢?意又叫作义,它是圣人“上观天文,俯察地理”而得到的对于世界本质的认识。义是就客观内容说的,意是就主观认识说的,它并不是圣人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义又叫作理,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王弼说:“举夫归致以明至理,故使触类而思者,莫不欣其思之所应,以为得其义焉。”《老子旨略》。“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周易·乾卦》注。他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他并不否定“触类旁通”等逻辑推理。他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世界是可知的,并不是不可知论者。当然,王弼的认识论决不仅仅是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他的根本目的,是要认识理之“宗极”即本体。他解“一以贯之”说:“贯犹统也。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论语释疑》。又说:“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论语释疑》。“理极”就是“一”,也就是本体“无”,它是万物的“宗主”。因此,如果得到它,就可以统治万物。“得物之致,故虽不行而虑可知也;识物之宗,故虽不见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老子》四十七章注。即不必经过实践和感性经验就可以推知万物,可以分别一切是非。但是怎样得到本体呢?他说要“得意忘言”!
王弼是不是完全否定语言的作用呢?并不是。他明确承认,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是说,他肯定了语言的作用。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周易略例·明象》。因为象是由意产生出来表现意的,言是由象产生出来表达象的,言的作用也就是表达意。因此,要尽意必须通过言,离开语言就无法尽意。从这一点看,他承认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同“言不尽意论”特别是荀粲等人的观点是有区别的。
他接着说:“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他虽然承认语言可以尽意,但又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种间接的工具和手段,和思想(意)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因此,“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周易略例·明象》。。王弼的思想,“贵在得意”,“义苟在健,何必马乎(在《周易》中马有时又代表刚健)?类苟在顺,何必牛乎?义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周易略例·明象》。既然言、象和意有区别,故不能执守言、象而不放。这也有合理的一面,它对于反对汉以来寻章摘句,解释名物的窃句、象数之学,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他又认为,言、象既是达意的工具,目的在于得意,所以得到了意,就可以把象忘掉,得到了象,就可以把言忘掉。这种“过河拆桥”的方法,是王弼思想的一个特点。在王弼看来,语言和思想的联系是间接的,也是暂时的;语言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思想一经得到,语言也就完成了它的任务,成为多余的东西,可以扔掉。这时,所谓“意”也就真正得到了,但同时也就真正变成了没有语言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是否存在,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从这里,他又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固执言、象即不能得意,要得意,就必须忘言忘象。只有忘言才能得象,只有忘象才能得意。这就是说,没有语言的思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样,他就把语言和思想对立起来,终于又否定了语言的作用,这就和“言不尽意论”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和他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有直接联系。在王弼哲学中,本体是一个超言绝象的存在,它不仅不可作感性认识的对象,而且不可作理性认识的对象。“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为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为体,故但志慕而已。”《论语释疑》。本体道无所不通,但又不可用名称去形容;无所不由,但不可用语言去说明。既然不用语言,也就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认识。王弼认为,有言则有分,“有分则失其极矣”,有言则“居成”,居成则“失其母”。《老子》三十九章注。因为语言既有肯定,同时又有否定;既有所指,同时又有非所指。而本体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由的,对于这样的本体,只有无言。这和庄子哲学确有相通之处。这实际上是宣扬一种直觉主义。他所谓圣人“从事于道”,“与道同体”“行不言之教”等说法,也就是宣扬这种无言的哲学,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
在王弼看来,语言是纯粹主观的东西,“意”才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语言只能表达现象的认识,不能表达本质的认识。他虽然肯定了逻辑思维的作用,却对它作了严格的限制。一般说来,人的思维,包括逻辑思维,都是离不开语言的,对《周易》的认识也应如此。人们认识世界,一般地都要使用语言作为工具,逻辑思维更是如此。词以及由词组成的句子,是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思维的直接表现。这样的逻辑思维,当然是离不开语言的。王弼确实看到本质和现象的区别、思维和语言的区别,但是由于他把本质看作一种超言绝象的精神本体,这样就把思维和语言二者割裂了、对立起来了(语言和思维并不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因而得出了得意必须忘言的结论。
四
和“言不尽意论”相对立的是“言尽意论”,它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语言同思想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是欧阳建。
其实,和“言不尽意论”同时,就有言尽意思想的提出。荀粲兄荀俣云:“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魏志·荀彧传》。他不同意荀粲的观点。他认为圣人之所以“立象”“系辞”,就是为了“尽意”,其微妙之旨就表现在言、象之中,通过象表现出来,因此,它是可以了解的。就是说,言是能够尽意的。
但系统地阐述这个观点的是欧阳建。他在当时可谓异军突起,旗帜鲜明地和“言不尽意论”展开了辩论。他的“言尽意论”,已经摆脱了解释《周易》的形式,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
他首先肯定,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理)是不以人们对它们的名称和语言为转移的。“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全晋文·言尽意论》。但这只是谈语言和客观对象的关系问题,还没有直接谈到言意关系。他接着说:“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全晋文·言尽意论》。这才谈到言意关系问题。按照欧阳建的说法,意就是对客观事物及其理的认识,它是一种理性认识。有了这种认识,必须靠语言才能表达。“言不扬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足。鉴识至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全晋文·言尽意论》。这就是说,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名词(概念)是认识事物的。没有语言就无法交流思想,没有名词就无法认识和分辨事物。仅就这一点来看,它和王弼的说法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这一点王弼也是承认的。他又说:“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随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全晋文·言尽意论》。这一段话,就把欧阳建和王弼区别开来了。这里有几层意思:(一)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本身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名称和语言,但是要认识事物,就必须使用名称,要表达思想,就必须使用语言。因此,名称、语言对于认识事物、交流思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既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二)他用形影关系比喻言意关系,这个比喻生动地说明,语言和思维之间具有必然联系,二者不可分离。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5页。欧阳建已经认识到这个道理。(三)他还认识到,语言是随着思想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的思想和认识不是停止不前的,人类的语言也不是僵死不变的。认识不断前进,语言也在不断丰富;新的认识领域被打开了,新的词汇也就随之产生了,语言的含义也就相应地扩大了。这个“言因理而变”的思想,已经被人类认识史和语言发展史所证实。正因为言意如“形存影附”,不可分离,欧阳建的结论是,言能尽意。他是完全肯定了语言的作用。
五
从这场辩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初步认识。
,这场辩论和哲学认识论问题有密切联系,但又不等于认识论问题,它还涉及心理学、语言学的问题。因此,要作具体分析。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从思维和语言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说明了二者的关系,充分肯定了语言的作用,批判了“言不尽意论”的错误,这是他的贡献。但是他又说,言意“不得为二”,这就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别,忽视了语言在表达思想方面并不是没有局限性这个事实。言意是不是像形影关系一样不可分离,这是可以研究的。据现代心理学实验证明,大脑皮层是思维的物质基础,在大脑中还有语言中枢。语言中枢中的某些部分被破坏后,语言将受到严重影响,但思维并不受影响。这个事实说明,思维和语言从生理机能来说,还是有区别的。至于有没有离开语言的思维,语言是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这是另一个问题,这是要进一步探讨的。在这一方面,“言不尽意论”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既然语言和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别,语言并不等于思想,那么,差别究竟何在?事实上,因某些特殊原因而不能说话的人(包括儿童)确实是有思想的。人们在运用语言时,常常感到词不达意,或有未尽之意,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嵇康等人否定语言的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但他们确实看到某些现象和问题。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科学的论证,但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解决人类思想之谜,至今还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问题同哲学基本问题虽有联系,但毕竟是不同性质的另一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上区分唯物唯心的基本问题,也是区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重要问题,但语言同思维的关系问题就不能这样说。思维和它的物质外壳即语言的关系问题,并不等于哲学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物质(大脑)的产物,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至于如何反映、用什么方式反映,这是另一个问题。也不能从这里推出,它就是二元论或不可知论,因为思想能不能用语言去表达,这并不否定思想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事实上,嵇康也承认客观世界是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人是可以认识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得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结论。
第二,这场辩论涉及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影响到当时,而且影响到以后,对宋明理学也有影响。二程所谓“玩其辞,得其意”,“下学上达意在言表”就是讲言意关系。宋朝的鲁饶说:“若读书而能求其意,则由辞以通理而可上达。若但溺心于章句训诂之间,不能玩其辞之所以然,则是徒事于语言文辞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宋元学案》卷八十三。鲁饶是一个理学家,他认为言是下学,是“下面一层事”;意是上达,是“上面一层事”,二者明显有区别,但可寻言以观意,下学而上达。这和理学家所讨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本体论问题有直接联系。明朝的薛瑄说:“凡圣贤之书所载者皆道理之名也,至于天地万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实也。”故“学者当会于言意之表”《明儒学案》卷七。。他也认为言意虽非一事,但言可尽意。但罗洪先则认为,“言固不尽意也”。他说:“可闻者言也,所从出此言者,人不得而闻也。岂惟人不得闻,己亦不得而闻之,非至静为之主乎?……惟所从出者存于其中,受命如响,如是而言如是而默,言默殊而吾未尝有二主也。”《明儒学案》卷十八。罗洪先是王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宣扬一种唯心主义“主静”说,认为本体就在心里,无论言与不言,都有一个主使者即心之体在起支配作用,他把语言看作是本体的一种外部表现,“不言”也是本体的表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