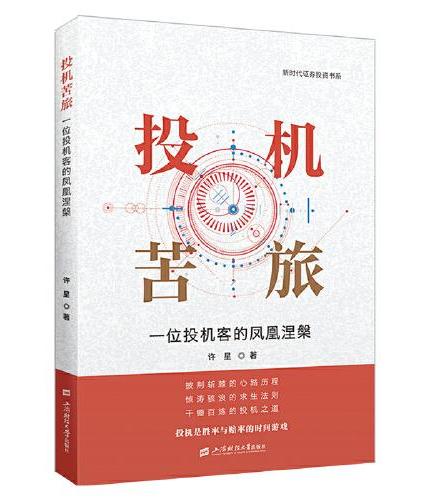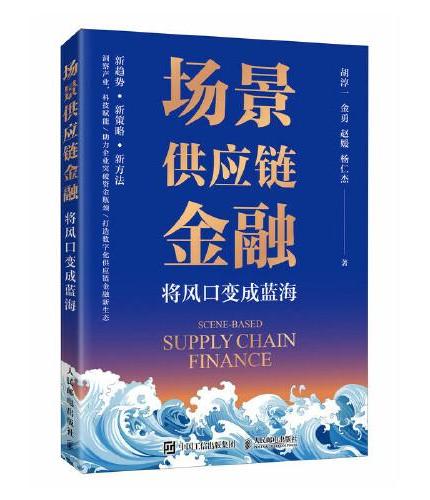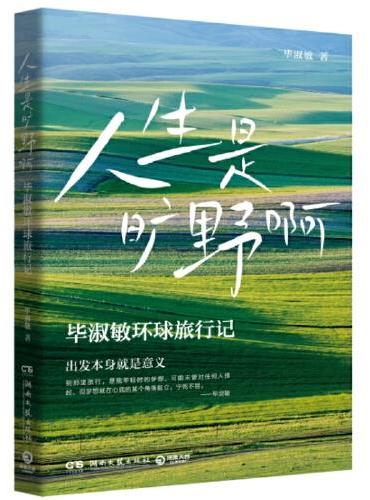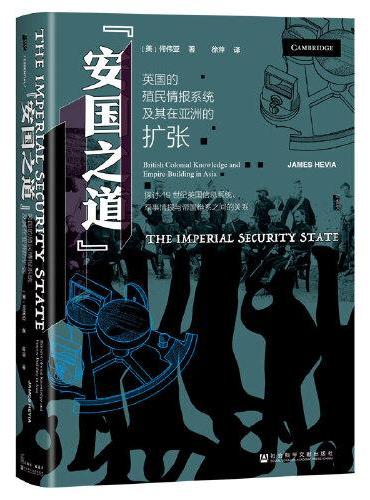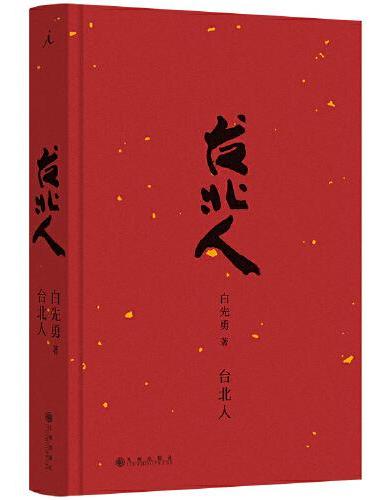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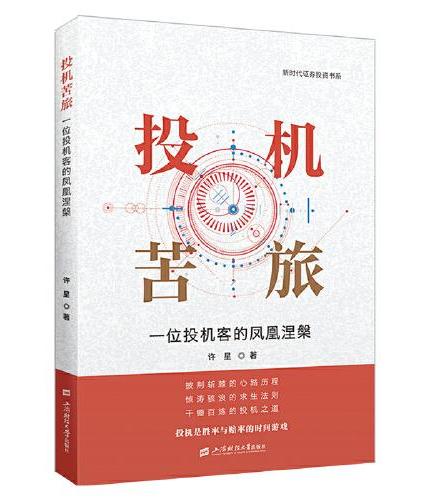
《
投机苦旅:一位投机客的凤凰涅槃
》
售價:HK$
88.5

《
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
》
售價:HK$
69.4

《
日子慢慢向前,事事慢慢如愿
》
售價:HK$
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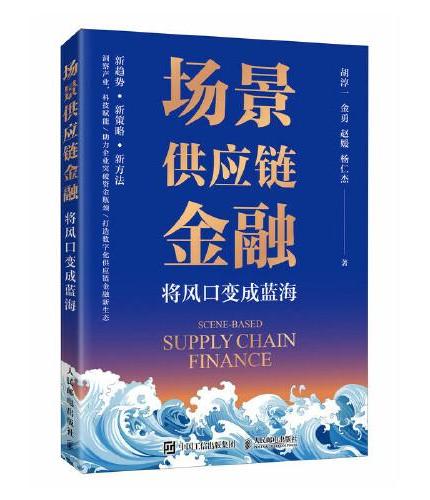
《
场景供应链金融:将风口变成蓝海
》
售價:HK$
111.8

《
汗青堂丛书146·布鲁克王朝:一个英国家族在东南亚的百年统治
》
售價:HK$
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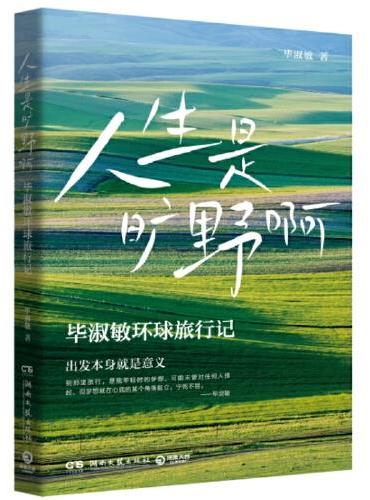
《
人生是旷野啊
》
售價:HK$
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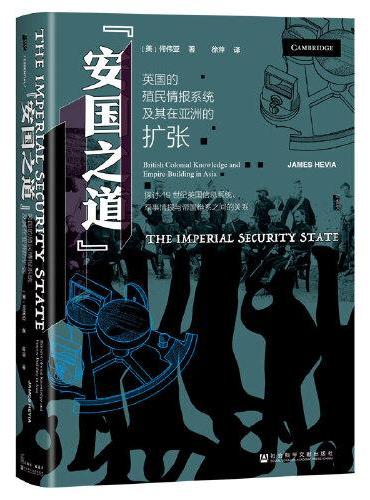
《
甲骨文丛书· “安国之道”:英国的殖民情报系统及其在亚洲的扩张
》
售價:HK$
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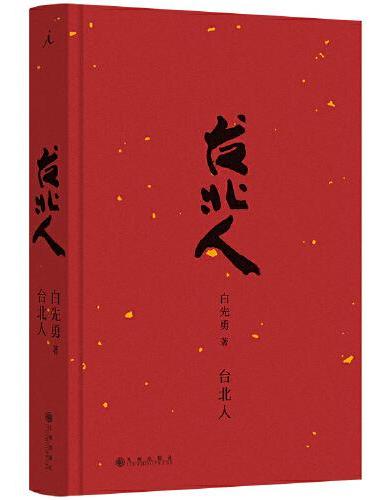
《
台北人(2024版)
》
售價:HK$
87.4
|
| 內容簡介: |
|
《驳圣伯夫》既非论文亦非小说。一块小玛德莱娜蛋糕,牵引出丝丝缕缕、连绵不绝的无意识回忆,然后笔锋一转,作者强烈抨击权威批评家圣伯夫批评方法的机械和错误,及因此造成的对当年法国文坛所有文学天才的轻视与误读。书中既有抒情的叙述,又有理性的思辨,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映照。
|
| 關於作者: |
|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性敏感,富有幻想,自幼患哮喘病,终生为病魔所困。经常出入文艺沙龙,与文学艺术界的名流广泛接触。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和他所倡导的“诗化哲学”。
|
| 目錄:
|
目次
译本序
作者前言
睡眠
房间
白天
伯爵夫人
《费加罗报》上的文章
阳台上的阳光
跟妈妈谈话
圣伯夫方法
热拉尔·德·奈瓦尔
圣伯夫与波德莱尔
圣伯夫与巴尔扎克
德·盖芒特先生心目中的巴尔扎克
该死的族群
人物姓氏
返回盖芒特
圣伯夫与福楼拜
结论
附录
普鲁斯特生平及创作年表
|
| 內容試閱:
|
译本序
圣伯夫是法国文学史上位专业文学批评家,也曾出版过三部诗集和一部长篇小说,但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一八二八年出版的专著《十六世纪法国诗歌和法国戏剧概貌》被誉为探索浪漫主义渊源的力作,从而使他立足文坛。自一八三○年,他在《东西两半球杂志》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声名鹊起,经久不衰。他先后出版《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史》(1840—1859),《当代人物肖像》(1846—1871),《妇女肖像》(1848),《月曜日丛谈》(十五卷,1851—1862),《论维吉尔》(1857),《帝政时期的夏多布里昂及其文学团体》(1861),《文学家肖像》(1862—1864),《新月曜日丛谈》(十三卷,1863—1870)等,可谓著作等身,浩如烟海。从三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末,近四十年间,圣伯夫称霸文艺评论界,甚至叱咤风云于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他培植了继承其业绩的一批学界强人,诸如勒南、泰纳、布尔热等。虽然曾受到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以象征主义为主体的“世纪末”思潮的冲击,但其影响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减弱。可以说,圣伯夫文学批评的影响长达百年之久。
对这样一位文学批评权威,个发难的,就是本书作者普鲁斯特。早在一九○五年,普鲁斯特就指出:“圣伯夫对同时代所有伟大的作家概不承认”,后来进一步指出,圣伯夫对同时代天才作家的批评全盘皆错。
首先应当说明,普鲁斯特并非全盘否定圣伯夫的功绩,始终承认圣伯夫关于十九世纪以前经典作家的论著,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甚至能够勉强接受著名文艺评论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保罗·布尔热对圣伯夫的颂扬——
“圣伯夫才识高明,体事入微,连细微的差别都提到笔端。他大量采用趣闻逸事,以便拓展视听。他关注个体的人和特殊的人,经过仔细探究之后,运用美学规律的某个典范高瞻远瞩,而后根据这个大写的典范作出结论,也迫使我们得出结论。”
普鲁斯特认为这是布尔热给圣伯夫方法下的定义,揄扬可信,定义简要;但竭力反对推广圣伯夫方法,因为此方法不利文学评论,更不利文学创作。普氏提出怀疑进而否定圣伯夫方法,是从现实出发的,有根有据的:为什么这位杰出的批评家,对同时代所有的文学天才会一概熟视无睹?嫉妒吗?彼时许多同情天才未被承认的人是这么想的,但不足为据。圣伯夫处在文坛至高无上的地位,何必嫉妒其时默默无闻或深受贬压的斯当达尔、奈瓦尔、波德莱尔、福楼拜呢?那么有可能嫉妒名人名家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缪塞吗?也说不通,因为他早已放弃文学创作,专事文学评论,同行不同类,何必相轻?如果用在他阻止某些学者入选法兰西学院,或许说得通,他确实利用在学院举足轻重的地位,反对过一些人入选。再说,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缪塞等巴结他都来不及呢,比如乔治·桑想去拜见,或引见缪塞,都得使出浑身解数,甚至女性魅力;巴尔扎克对他百般殷勤,好话说尽;连雨果都始而把他奉为座上客,继而把他视为知己挚友,终而因他染指其爱妻而反目,但拿他无可奈何。
普鲁斯特不从圣伯夫与大作家们的私人关系去批判圣伯夫的文学评论,相反,他非常厌恶甚至气愤圣伯夫在文学评论中常常拉扯作家的品行、为人、私生活以及跟他个人的关系。比如对斯当达尔《巴马修道院》的评论,圣伯夫说不同意巴尔扎克对此书的赞扬,远没有巴氏的热情,说它与前人的历史题材小说相比,雕虫小技而已,但笔锋一转,称赞斯当达尔男女私情上“正直可靠”(其实非常糟糕,据说此公实际死于梅毒),说他虽缺乏小说家的素质,但为人谦虚,是有儒雅风度的谦谦君子。再如,圣伯夫对待波德莱尔的态度更“令人发指”,他口口声声称波德莱尔是他的私交挚友,说波氏“谦虚”“平和”“有教养”“识大体”,等等,但对这位十九世纪伟大的诗人(普鲁斯特语)的创作闪烁其词,不置可否。波德莱尔的一些诗歌受到司法追究时,他“见死不救”,只做了个小小的姿态,以示同情。令普鲁斯特不解和难受的,是波德莱尔自始至终对圣伯夫顶礼膜拜,低声下气,摇尾乞怜。波氏的朋友们实在气愤难平,说了一些坏话,波氏马上出面制止,并写文章公开声明这与他无关。此类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总之,圣伯夫对同时代天才作家这种一打一拉的恶劣手法,深深激怒一向文质彬彬从不说粗话的普鲁斯特:“读圣伯夫,多少次我们恨不得痛骂几声:老畜生或老恶棍。”
普鲁斯特骂过之后,冷静下来,承认圣伯夫说得对:正确判断久已得到公认并列为经典的作家是容易的,难就难在把同时代的作家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而这恰恰是批评家固有的职责,唯能履此职责,批评家才名副其实。可惜圣伯夫本人从来没有身体力行。普鲁斯特认为,问题出在圣伯夫的批评方法不对: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的艺术奥秘,圣伯夫不从他们的作品去寻找,一味热衷于收集他们的近亲好友熟人乃至对手敌人所作的议论、所写的书信、所讲的故事,有点像咱们的“查三代”“调查社会关系”。圣伯夫过于重视作家的出身、地位、境遇、交往,他对夏多布里昂的阿谀奉承便是明显的例子。确实,作家或艺术家的政治立场,为人处世,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很容易引起争议。历史上一直存在抑或因人废文,抑或因文废人,抑或因文立人的现象。普鲁斯特早在本世纪初就批判圣伯夫对人和文不分的批评方法,这里的文当然指文艺创作。他主张把论人和评文分开,文学批评必须从文本出发。常言道:“圣人中没有艺术家,艺术家中也没有圣人。”不要因为大仲马和小仲马父子为同一个烟花女争风吃醋而否定《基督山伯爵》和《茶花女》的小说价值。也不要因为维克多·雨果放荡得连女用人都不放过而谴责《悲惨世界》中纯洁的爱是虚假的。更不要因为波德莱尔恶习多多而批评他的诗歌伤风败俗,进而否定其艺术性。谁要是读了《忏悔录》而谴责卢梭道德败坏,那就是普鲁斯特所指“不善于读书”的那类人。
普鲁斯特认为,圣伯夫没有看出横在作家和上流社会人物之间的鸿沟,没有懂得作家的自我只在其著作中显现,而在上流社会人物面前只表现为像他们一样的一个上流社会人物。诗人和作家“外部为人”的趣闻逸事无助于理解他们的作品,弄清楚诗人和作家所有的外部问题恰恰排除了他们真正的自我。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是用“内心深处的声音所唤醒的灵感”写就的。普氏说: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不是我们在习惯中在社会中在怪癖中所表现的那个我。
从上述论点,我们逐步看出,普鲁斯特批判圣伯夫的目的是想建立并阐述自己的文艺观,也是他写本书的目的。他说:本书借圣伯夫之名加以发挥的将大大多于论及他本人,指出圣伯夫作为作家和批评家所犯的错误,也许能对批评家应是何人、艺术应是何物说出个所以然来。难怪许多不熟悉普鲁斯特的法国读者,包括文学系大学生,不明白本书前后部分好多章节尽谈作者身边琐事,看上去同赫然醒目的论战性标题《驳圣伯夫》风马牛不相及。相信中译本读者也会有同感,不要紧,谨请读者诸君硬着头皮读下去,读完就会明白的。因为推倒圣伯夫方法谈何容易,而纯学术理论批判又不是小说家的任务,普鲁斯特只想通过小说,确切讲,散文性小说,阐述自己的文艺观。关键的命题是:文贵乎真。圣伯夫方法的要害也是求真实。问题是求什么样的真实,怎样的真实才算真正的艺术真实。圣伯夫一贯主张小说应在写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用他的话来说,进行“天才的艺术加工”。举个典型的例子,圣伯夫竭力鼓励龚古尔兄弟去罗马实地勘察,体验生活,深入调查他们那位移居罗马的姑妈的身世。回来后,他们以姑妈为女主人公的原型,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写出了小说《热尔韦泽夫人》。圣伯夫对这部不成功的小说评论道,小说的创作方法是对的,但缺少艺术性。仿佛艺术性和方法是两回事。对此普鲁斯特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也是他酝酿已久的创作思想,日后更开现代小说的先河,同时为后来的文本主义和结构主义批评奠定了块基石。
普鲁斯特认为调查得来的素材只能作为参照,作家必须依据切身的感受才能表现本人的思想,唯其如此,作品才是真实的。为了阐述这个思想,普鲁斯特在本书中用了近乎一半的章节(虽然是后人根据他的设想选编的),讲述他对周围日常事物的感受,从睡眠、房间、光线、天气、太阳、雨水、花园、街道、教堂、钟楼到贵族社会的人物、姓氏、门第、外貌特征、言谈举止、生活习俗等,写的全是感觉:听觉、视觉、触觉、嗅觉、性觉、悟觉,等等。而感觉与印象不可分离,于是他用了大量篇幅谈印象(不是一般的印象,而是想象的印象,即普鲁斯特所谓的“无意识的回忆”)。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比如由听觉引起的联想:一天,作者听见侍者不小心把银匙碰响了瓷盘,清脆的声响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一次火车经过夜间运行,于清晨停在山区乡间小站,铁路工人用锤敲打火车轮子,在清脆的敲打声中,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前来兜售牛奶咖啡。姑娘红润的脸颊宛如天边的朝霞,他“一见钟情”,感到美丽的姑娘与众不同,具有个性。
村姑特殊的美使他悟出,人们头脑中固有的美女形象是枯燥乏味的,对美女的欲求是根据人们的认识想象出来的,抽象的,没有诗意。而送热牛奶咖啡的姑娘使人产生一种想象的快乐,非现实的快乐,作者顿时感到清空醇雅。这种想象印象的真实性弥足珍贵。艺术声称近似生活,若取消这种真实性,就取消了珍贵的东西。艺术家、诗人、作家应当做的,是追究生活的底蕴,全力以赴打破习惯的坚冰、推理的坚冰,因为习惯和推理一旦形成,立即凝固在现实上,使人永远看不清现实。而两个印象之间的巧合则使人发现现实,从而产生想象的快乐,即诗人真正的快乐。种种印象,哪怕产生一分钟的现实感,也是难能可贵的一分钟,令人欢欣鼓舞。从这个印象和所有与之相似的印象中脱颖而出某种共同的东西,优于我们生活的现实,甚至优于智力激情爱恋的现实。由此产生的愉悦,空明如翼,轻柔若风,是心灵上难得的一瞬即永恒的愉悦。它那具有灵性的光芒使人们幽闭的心灵顿时明媚透亮。这就是艺术魅力,任何其他魅力都不可代替。
由此,普鲁斯特得出一个结论:“艺术上没有(至少从科学意义上讲)启蒙者,也没有先驱。一切取决于个体,每个个体为自己的艺术从头开始艺术或文学尝试,前人的作品不像科学那样构成既得真理,可供后人利用。今天的天才作家必须一切从零开始。他不比荷马先进多少。”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是那种迎合读者口味的作者,必然会使一部分读者失望,因为这部分读者总希望读到想得到的东西,或想找到某些理论或现实问题的答案。所以,谨请这样的读者换种眼光去读普鲁斯特的书,把它当作一个未知世界,那么您会发现他对已知的世界有了新的发现,作了新的解释。
本序写到这里已经够长了,似乎可以结束了,但还有重大的问题要交代,不得不延长篇幅,尚希读者诸君鉴谅。
......
我不知道为什么硬要回忆那个早晨,其时我已经病了,整夜没睡,清早上床,白天大睡。曾几何时,我晚上十点就寝,尽管小醒几次,却一觉睡到翌日清晨,真希望这样的时日重现,但今天似乎觉得那是另一个人的生活了。经常灯刚灭,我便入睡,快得来不及思量:我睡了。半小时后,我想到应该睡着了,这个想法反倒把我弄醒,以为手上还拿着报纸,心想把它扔下,自言自语“该熄灯睡觉了”,但十分惊异,我周围只见一片昏暗,这片昏暗使眼睛颇感舒适,可脑子也许就不那么舒适了,对我的脑子来说,这片昏暗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思议,有如真正叫人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
我重新点上灯,看了看时间:还不到子夜。只听得火车的汽笛声忽远忽近,描绘着荒原的广漠:荒道上有个旅客匆匆赶往临近的车站,月光溶溶,他刚离开朋友们,此时正把跟朋友们一起享受的快乐铭刻于记忆,还刻上回家的快乐。我把面颊贴在枕头美丽的面颊上,枕头的面颊如同我们童年的面颊,始终饱满和鲜嫩,就这样,两张面颊紧紧贴在一起了。我又点上灯看了看表,还是不到子夜。此时在一家陌生旅馆过夜的病人疾病大发,痛醒之后,庆幸瞥见门下有一线亮光儿。好运气,天亮了,过一会儿侍者就会起床,只要按铃,就有人来救护。他忍着痛苦,耐心等待。恰好他依稀听见脚步声……但就在那时门下的亮光熄灭了。时已子夜,原来人家熄灭了煤气灯,而他还以为是晨光,这样,他不得不孤独无助地苦熬一夜了。
我熄了灯,又睡着了。有时,就像夏娃从亚当的一根肋骨脱胎而出,有个女人从我姿势不当的大腿中间钻了出来,我即将领略女性的快感,满以为是她奉献给我的。我的身体感到她的体温,正准备贴紧时,我惊醒了。世上剩下的女子与我刚离开的女子相比远远不可同日而语,我面颊还留存她亲吻的余温,我的躯体酸痛,好似还在承受她的躯体重压。渐渐对她的记忆消散了,我忘却梦中的姑娘,忘得很快,恰似露水夫妻一场。有时,我梦见儿时散步,感觉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但到十岁时就永远消失了,那些感觉尽管微不足道,可我们渴望重新认识,好比某公一旦知道再也见不到夏天时,甚至怀念苍蝇在房间里嗡嗡作响,因为蝇声意味着户外烈日当空;甚至怀念蚊子咝咝,因为蚊子咝噪意味着芳香的夜晚诱人。我梦见我们的老神甫揪我的卷发,吓得三魂冲天,如鼠见猫。克洛诺斯被推翻克洛诺斯,古希腊神话中提坦六神幼者。他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做了神王,并奉母亲地神之命,阉了父亲,为提坦们留下空间。他娶妹妹瑞亚为妻,有过五个孩子,但一一被他吞食,因为他听信预言:他也将被自己的孩子推翻。当瑞亚为他生下六子宙斯时,用襁褓裹了一块石头给他吞下。宙斯长大,果然把他推翻,并迫使他吐出所有的兄弟,然后把他打入地狱底层。,普罗米修斯的发明,耶稣的降生,把压在人类头上的天空闹得不亦乐乎,但都不如我卷发被剪去时的盛况,那才叫惊心动魄呢。说实话,后来又有过其他的痛苦和惧怕,但世界的轴心已转移。那个旧法则的世界,我睡着时很容易重返,醒来时却总逃不脱可怜的神甫,尽管神甫已去世那么多年,可我仍觉得他在我头后揪卷发,揪得我生疼。在重新入睡前,我提醒自己说,神甫已仙逝,我已满头短发,但我依旧小心翼翼把自己紧贴枕头、盖被、手绢和庇护的被窝墙壁,以备再次进入那个千奇百怪的世界,那里神甫还活着,我还是满头卷发。
感觉也只在梦中重现,显示着消逝岁月的特征,不管多么缺乏诗意,总负载着那个年纪的诗篇,好比复活节的钟声那般饱满噌吰,蝴蝶花尽管绽蕾怒放,可春寒料峭,吃饭时不得不生火取暖,使我们的假期大煞风景。这样的感觉在我的梦中有时也重现,但我不敢说重现时诗意盎然,与我现时的生活完全脱离,洁白得像只在水中扎根的浮生花朵。拉罗什富科说过,我们唯有初恋才是不由自主的。其实,少年手淫取乐也是如此,我们在没有女人时聊以自乐,想象着若有女人贴身陪伴。十二岁那年,我次把自己关进孔布雷我们家的顶层贮藏室,那里悬挂着一串串菖蒲种子,我去寻找的快乐是未曾感受过而又别出心裁的,是别种快乐不可代替的。
贮藏室其实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房间严密上锁,但窗户总敞着,窗外一棵茁壮的丁香沿着外墙往上长,穿过窗台的破口,伸出她芬芳的脑袋。我高踞在古堡顶楼,身只影单,这种凌空的表象使人心动,引人入胜,再加层层结实的门闩锁扣,我的独处更有安全感了。我当时在自己身上探测寻求我从未经历的一种愉悦,这种探求叫我兴奋,也叫我惊心动魄,其程度不亚于要在自己身上给骨髓和大脑动手术。时时刻刻我都以为即将死去。但我不在乎!愉悦使我的思想亢奋膨胀,觉得比我从窗口遥望的宇宙更广袤更强劲,仿佛进入了无限和永恒,而通常面对无限和永恒我则凄然惘然,心想我只不过是稍纵即逝的沧海一粟。此刻我仿佛腾云驾雾,超越森林上空的如絮云朵,不被森林完全吞没,尚留出小小的边缘。我举目远眺美丽的山峰,宛如一个个乳房矗立在河流两岸,其映象似是而非地收入眼底。一切取决于我,我比这一切更充实,我不可能死亡。我喘了口气,准备坐到椅子上而又不受太阳干扰,但椅子让阳光晒得热烘烘的:“滚开,小太阳,让我干好事儿。”于是我拉上窗帘,但丁香花枝挡住了,没完全拉上。后,一股乳白色的液体高高抛射,断断续续喷出,恰似圣克卢喷泉一阵阵往外喷;我们从于贝尔·罗贝尔留下的人物画也可认出这种抛射,因为断而不止的抛射很有特性,其耐久的弧度像喷泉,显得十分优雅,只不过崇敬老画家的人群抛出的花瓣到了大师的画中变成一片片玫瑰色,朱红色或黑色了。
其时我感到一股柔情裹挟全身,原来丁香的馨香扑面而来,刚才亢奋时没觉察到,但花香中夹着辛辣味儿和树液味儿,好像我折断花枝时闻到的气味。我在丁香叶上只留下一条银色液迹,条纹自然,宛如蛛丝或蜗牛行迹。然而,丁香花枝上的蛛丝痕迹在我看来有如罪孽之树的禁果,又如某些民族奉献给他们神明的那些未成器官的形式,从这银白色蛛丝痕迹的外表下几乎可以无限引伸出去,永远看不到终点,而我不得不从自己体内抽出来,才得以反顾我的自然生命,此后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扮演魔鬼。
.......
|
|